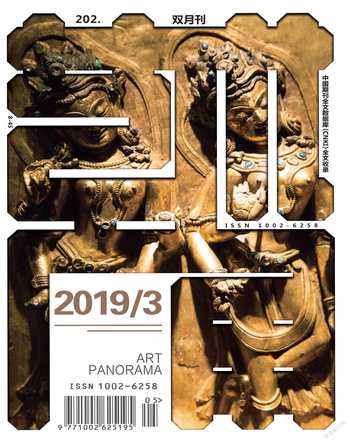澡堂與瀑布的交響曲
王穎
從畢贛迄今為止的兩部作品《路邊野餐》(以下簡稱《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下簡稱《地球》)中可以看出,這是一位“向內創作”的作者,他的作品是長時間對自我的檢查和審視的結果,這種精神內部的活動幾乎不受任何外在情況的影響,并決定其作品的功能和特征。
一
對于他而言,創作最大的功能是自我精神的療愈——小時候父母經常吵架,后來離婚,他和父親生活,主要是奶奶照顧他——經過斷斷續續信息的拼湊,筆者所了解的畢贛就是這樣長大的。“母親拋棄了我”是他的心結。他說小時候一直以為月亮跟著自己走,在關心自己。他非常在乎這個事,以至于不敢拿這個問題去找老師求證,害怕真實會破壞他幻覺里的溫暖。月亮之于他,有一點像火柴之于賣火柴的小姑娘。
他用兩部電影紓解了這個心結。《路邊野餐》講一個中年人的故事,但電影中各個年齡階段、不同性別的角色身份互相重疊,共同指向“失去”“找回”“救贖”。時針在電影的最后時刻終于倒轉,前景雖然是昏睡毫不知情的陳升,但這“唯心主義”的一刻安慰的是電影中所有為失去感到痛苦的人。畢贛在這部片子里如同水庫泄洪,打開水閘,放走了濕漉漉的孤單和傷痛。
第二部電影的故事更為完整,畢贛把敘事視點集中在羅纮武這個角色身上,用他代替自己來宣泄情感。又因為資本的加入,他把這個簡單的故事套上一個類似王家衛式香港警匪片的殼子:羅纮武帶著被母親拋棄的傷痕長大,遇到長得和母親很像的女人就會愛上她。女人是那種黑色電影中典型的“蛇蝎女人”,利用他殺人,又對他不忠,拋棄他。多年以后他依靠一點信息尋找她,卻在關鍵時刻沉入夢中,失去了最后見到她的機會。但是,在夢中他見到真正的“她”(年輕、純真),也終于回到“創傷性場景”——被母親拋棄的一刻。
“母親拋棄了我”這個心結被解開,得益于它經過一遍遍越來越夸張的講述,從客觀事實變成了審美對象。畢贛電影中所有的男女關系都是母子關系的翻版和重演,《地球》中,羅纮武在夢里所遇到的姑娘干脆叫“凱珍”,據說那是畢贛母親的名字。電影里的重頭戲就是“男人被女人拋棄”:作為審美對象存在的話,“被拋棄”甚至是有快感的。一定要一遍遍地被拋棄,自我才能一遍遍地被確認、被肯定、被看見。在第二部電影里,他攝影機前的女人除了“拋棄”男人,又加了不忠(和多個男人有染)和狠毒(類似潘金蓮殺夫)。“母親”這個角色霸占了“羅纮武”的人生幾乎所有的欲望。
在許知遠的訪談節目《十三邀》里,畢贛認為:“作品首先要先解決自己,一定是自我的訴求為先。”他覺得這兩部電影已經“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自己,“有甜蜜,有痛苦,全部都在里面。”把郁結抒發之后的他現在很平靜:“爽得很,連詩都不想寫了。”
畢贛是自己最好的心理醫生。如果他不拍電影,這個郁結不解開,就留在那里,當然也不至于影響生活,但表達乃至表達的過程讓人生得以結束一個必經的迷茫糾結的階段,進入了更為成熟的平臺。甚至連這個心結是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真正解決了,也不再重要。事實上通過把它審美化,它本身已經不再是真實的了,而成了“電影中的”“角色的”“別人的”東西,畢贛從里面抽身而退。
“拍別人的事”會讓人像旁觀者那樣冷靜又清醒。他會思考:“那個東西真的是痛苦的嗎?拋棄你的人欺騙你的人,真的是可惡的嗎?”在思考中就會慢慢放棄對這個事情的執念,給它一個結束。畢贛是一個很有儀式感的人,因為他在兩部電影里都要求對時間之流中必然要發生的痛苦的別離補上一個正式的告別。在《野餐》里,陳升給妻子唱了《小茉莉》,然后把李泰祥的《告別》的磁帶留給了她;在《地球》里,羅纮武回到了母親離開他的瞬間,問了她一個最想要問的問題,然后幫助她離開。分離不可改變,但如果有了“告別”的正式儀式,就可以放下執念,畫上句號。完成儀式之后的男人都有一個長時間的行走,用以消化這種痛苦,然后完成這個痛苦,結束這個痛苦。
畢贛接受許知遠的電視采訪時說:“我小時候在澡堂旁邊的房子住,那個房子因為很潮濕,所以電路經常出現問題。每天晚上醒來,我父母在吵架,然后那個電燈都會閃,在我的電影里面總是有那個閃爍的電燈。那是個很沒有安全感的意象。把它拍到電影里就很有安全感,因為那是電影里的東西。”——把所有的不安、焦慮和缺失在電影里表現出來,然后“全關在那兒”:“現在我已經全關好了,踏實了。”電影中的角色承載著他的痛苦,成為藝術的永恒,他自己則借以回到短暫的世間享受同樣短暫的平靜。
但是,解決了和母親的關系問題,一切就得到解決了嗎?在畢贛的電影里,值得羨慕的父親都是他人的。《野餐》里花和尚和陳升都是眷戀孩子的男人,然而在電影中正在做著父親的“老歪”是個不懂照顧孩子的廢柴。《地球》里,羅纮武的朋友白貓的爸爸“老鷹”是個有本事的厲害人物,他的手槍(權力、力量、主宰)就來自于白貓爸爸,然而他自己的爸爸,一開場就死了。
畢贛以后會不會開口講“父親的缺席”?
二
就像他自己所說:“還不到三十歲,心里的東西也沒有多少”,這兩部電影表達的東西不算豐富,也不算晦澀難懂。兩部電影結尾都與時間有關。第一部是時針倒轉,第二部是煙花點燃——鏡頭從點燃的煙花開始,跟隨他們去“愛的房子”接吻,然后拋下他們,回到點燃的煙花。煙花仍舊保持在之前的狀態,接著,它忽然如夢初醒地返回到時間的序列之中,迅速燃燒,光明隨之消失。那么,在旋轉起來的房子里接吻的時刻,真的在時間之流中存在過嗎?畢贛所表達的是兩個與時間有關的母題:瞬間與永恒,虛無與真實。所謂時間就是這樣:過去的事情不可重來,珍貴的時刻瞬間即逝,遁入虛無。而畢贛在電影里試圖對抗時光,讓時針倒轉,重新回到過去,將短暫難忘的一刻封存珍藏。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對抗令人熱淚盈眶。
作為一個業余詩人,畢贛擅長使用意象,他的電影因為充滿意象而變得幽深、紛亂、迷離。他喜愛監獄和洞穴,顯然是將自我指向“記憶的囚徒”;他喜愛水,因此他的電影隨處可見瀑布、湖泊、泳池,以及從屋頂滲入的水滴,他的整個電影都是濕漉漉的;他喜愛圓形物體,壞了的鐘表、畫在手腕上的手表、壞了的風扇、掛在墻上的蒸鍋篦子,同時出現在屋子、陽臺、舞場的舞廳鐳射燈、屋頂上遠遠近近的球狀儲水罐。在《十三邀》里,《野餐》的取景地、畢贛外婆家的門外,就有一個球狀儲水罐,據說那是畢贛對太空想象的緣起。《地球最后的夜晚》雖然和《路邊野餐》一樣,名字來自于一本可能畢贛自己都沒有讀過的外國小說,但也許最初的靈感從這里開始。畢贛又善于用互文將這些意象聯系在一起、將他的兩部作品聯系在一起,使密密麻麻的意象之間互相映照、彼此加強。還有他對于長鏡頭的迷戀,固執地在一個長鏡之內封存時間和空間,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表現出“夢”的質感……這都“非常大師”。當然他還遠遠不是大師。他有點像塔可夫斯基的清新版本、通俗版本,只不過這個年輕人對作者電影的追求如此熱烈天真,讓人心動。
三
許知遠在采訪畢贛的這期《十三邀》一開始就說:“來凱里的感覺很像那次我去汾陽。我特別羨慕他和賈樟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私人經驗特別自信。”
因為這種“自信”,貴州凱里繼山西汾陽之后,成為中國電影里邊緣城市的又一個標本。但是畢贛影像里的凱里并不是中國大時代中邊緣城市的一個縮影,也不是這個邊緣城市精髓和氣質的提煉,而只是畢贛一個人的凱里,是他所看到的、生活著的凱里。他的電影里也有賈樟柯電影中常見的臺球桌、馬戲團、舞廳卡拉OK,但這些場景在賈樟柯電影中是社會和時代的記錄,在他的電影里則更像是心理影像。和賈樟柯相比,畢贛在電影中所講述的私人經驗是更徹底的私人心理經驗和情感經驗,而不是私人經驗里面比較社會化的那一部分。他的角色承擔的只是他個體的精神欲求,而賈樟柯則會把人物放在一個大的變化的時代之中,通過他與時代的關系,來展現整整一類人的精神空間。
畢贛和賈樟柯的這種區別,是兩種審美趣味的區別,也是兩種文化形態的區別。畢贛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許知遠在《十三邀》中一直在暗示他“作為藝術家,作為知識分子”有義務做啟蒙,拿侯孝賢和賈樟柯作為比較,認為藝術家要關心時代,起碼要關心“全人類”,只表達“私人經驗”是一種“沉溺”。許知遠是典型的傳統精英文化的立場。但畢贛正好相反,他認為要尊重別人的生活、別人的勞動,討厭好為人師的姿態,解決自己的問題就好了。“大師會觀照人類,我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年輕人,我觀照不了人類,我觀照自己就很吃力了。”對此,許知遠的回復是:“也許等你長大一點了,你就會知道,不去關心那些更廣闊的東西,就沒法關心真正的自己。關心更普遍的人類,就是關心自己。”
在中國,一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很難得到尊重。對個人主義者最大的善意是說他“還沒有長大”,“等你長大一點你就發現……”這種潛意識中的居高臨下代表的是整個社會的審美價值取向:對于個體情感的表現和挖掘永遠不夠深刻和宏大,任何時候,對時代的表現和關注才是一部稱得上是“好”的作品的起點、標配。
然而,個體經驗的表達真的沒有宏大的時代敘事更有價值嗎?事實上,真正幽深而細微的個體經驗并不容易表達。它需要徹底的坦誠、細膩的感知、天才的方法。真正的個體經驗是完全個體的,也是普遍人類的。完美的個體經驗的表達非常罕見,值得珍視。很難想象中國會出現費里尼的《阿珂瑪德》和阿方索卡隆的《羅馬》那樣的作品,在任性而平靜的私人視角中,時代因為人幽深而廣漠的情感而存在。
四
事實上,畢贛的電影使一個母親焦慮,因為它存在的基石即是母親對孩子的傷害。這傷害是無意的,也是難以避免的。母親這個角色本身就帶有原罪。
《路邊野餐》里,畢贛的媽媽客串了一場戲,飾演一個來給自己的寶寶看病的媽媽。畢贛不太想拍自己媽媽的臉,一直用其他人的身體遮住她,或者只給一個側影。他的媽媽看起來是一個踏踏實實的勞動婦女,對于自己在畢贛電影的誕生中所起到的驅動力,可能沒有足夠的認識,這是好事。
畢贛小時候的房子在澡堂旁邊,但是在電影里,他任性地把澡堂變成了瀑布。瀑布邊的房子是一個有趣的意象,據說拍完電影后它就被遺棄了,很快被植物占領,真正成為山野的一部分。從澡堂到瀑布,很像是現實和藝術之間的關系。現實的鈍感、紛雜和日常,轉變成藝術中優美、鮮明的意象,還帶有一絲含混而夸張的黑色幽默。
現實生活中的痛苦當然是真正的痛苦、值得尊重的痛苦。但是在藝術中它變得如此巨大,大到淹沒和掌控人的一生,那是審美附帶的幻覺。發生的,就是應該發生的。不妨把痛苦和表現痛苦,都看成一個封鎖在長鏡頭中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