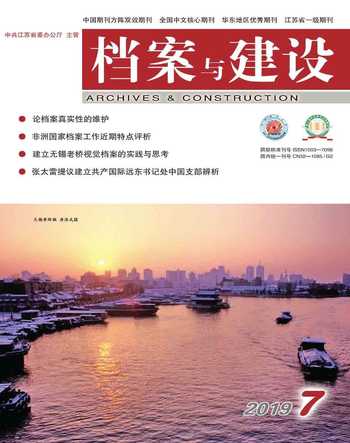張?zhí)滋嶙h建立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辨析
王龍騰 蔡文杰
摘要: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的設(shè)立,承襲的是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設(shè)置地區(qū)科的制度設(shè)計(jì),中國(guó)支部從不缺少掌握中文的語言人才,目前僅有張?zhí)妆蝗蚊鼮檫h(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書記的檔案資料。以往研究認(rèn)為的張?zhí)滋嶙h建立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的觀點(diǎn)是很難成立的。
關(guān)鍵詞:張?zhí)祝还伯a(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阿勃拉姆松
張?zhí)资侵袊?guó)共產(chǎn)黨早期的重要領(lǐng)導(dǎo)人之一,忠誠(chéng)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家,中國(guó)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tuán)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和青年運(yùn)動(dòng)卓越領(lǐng)導(dǎo)人,廣州起義的主要領(lǐng)導(dǎo)人,他把短暫的一生獻(xiàn)給中國(guó)革命事業(yè),建立了不朽功績(jī)。[1]但是,由于原始的檔案資料缺乏,關(guān)于張?zhí)椎脑缙诟锩鼩v史研究中存在一些訛誤之處,其中就包括不少研究者認(rèn)為張?zhí)自?921年初到達(dá)位于伊爾庫(kù)茨克的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后,提議建立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又譯作“中國(guó)部”“中國(guó)處”“中國(guó)科”等,為行文統(tǒng)一,除直接引文外,皆稱“中國(guó)支部”),所依據(jù)的資料也都是《張?zhí)钻P(guān)于建立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的報(bào)告》(以下簡(jiǎn)稱《報(bào)告》)。已有研究者指出,《報(bào)告》實(shí)際上是遠(yuǎn)東書記處負(fù)責(zé)人鮑里斯·舒米亞茨基1928年發(fā)表在《革命的東方》上的回憶張?zhí)椎奈恼隆吨袊?guó)共青團(tuán)和共產(chǎn)黨歷史的片段——悼念中國(guó)共青團(tuán)和共產(chǎn)黨的組織者之一張?zhí)淄尽返囊徊糠帧<热弧秷?bào)告》來自舒米亞茨基的回憶,同時(shí)它又是孤證,那么基于它而得出的觀點(diǎn)的準(zhǔn)確性和可信度,就有待于其他資料或邏輯的檢驗(yàn)。不過有人仍然認(rèn)為:“1921年春,張?zhí)鬃鳛橹泄沧钤缗赏伯a(chǎn)國(guó)際的使者赴伊爾庫(kù)茨克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工作,在該處負(fù)責(zé)人、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全權(quán)代表舒米亞茨基的領(lǐng)導(dǎo)下組建中國(guó)支部”[2]。本文依據(jù)遠(yuǎn)東書記處的歷史由來和張?zhí)兹温氂谶h(yuǎn)東書記處的相關(guān)檔案史料,對(duì)張?zhí)滋嶙h建立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的觀點(diǎn)作一簡(jiǎn)要辨析。
一、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
1919年3月召開的共產(chǎn)國(guó)際一大,宣告“一個(gè)新的時(shí)代,即資本主義解體的時(shí)代,資本主義內(nèi)部崩潰的時(shí)代,無產(chǎn)階級(jí)共產(chǎn)主義革命的時(shí)代已經(jīng)開始了”[3]。甫一成立的共產(chǎn)國(guó)際集中注意力于歐洲資本主義國(guó)家的共產(chǎn)主義革命,無奈效果不彰,預(yù)想中的世界革命高潮沒有來臨。但是西方不亮東方亮,亞洲國(guó)家風(fēng)起云涌的民族革命運(yùn)動(dòng)和其領(lǐng)導(dǎo)力量的缺乏引起了共產(chǎn)國(guó)際的注意。隨后,在1920年7、8月間召開的共產(chǎn)國(guó)際二大上,通過的《關(guān)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和《關(guān)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bǔ)充提綱》,指出“共產(chǎn)國(guó)際應(yīng)當(dāng)與政治上經(jīng)濟(jì)上受壓迫國(guó)家中的決心推翻帝國(guó)主義的革命力量建立聯(lián)系”[4],以支持和領(lǐng)導(dǎo)亞洲國(guó)家的民族革命運(yùn)動(dòng),共產(chǎn)國(guó)際將鼓動(dòng)革命的重心轉(zhuǎn)向亞洲。為貫徹共產(chǎn)國(guó)際二大的精神,遠(yuǎn)東地區(qū)聯(lián)系和推動(dòng)亞洲革命的各方組織應(yīng)運(yùn)而生,包括俄共(布)西伯利亞局、俄共(布)遠(yuǎn)東局及其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委員會(huì)等,這種分散性和無組織性使它們無法協(xié)調(diào)行動(dòng),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fèi)和彼此間的摩擦。
鑒于上述的混亂狀況,為了“從組織上落實(shí)遠(yuǎn)東工作并對(duì)其實(shí)行集中管理”[5],1920年7月,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又譯作“東方民族處”)在伊爾庫(kù)茨克成立,其組成人員有:西伯利亞局主管東方工作的全權(quán)代表岡察洛夫、主席布爾特曼、主席助理加蓬、9月底到任的主席團(tuán)書記和情報(bào)科長(zhǎng)勃隆施泰恩,布爾特曼和勃隆施泰恩主持日常工作。它在成立初期即設(shè)立中國(guó)支部和朝鮮支部,而蒙古支部和日本支部的設(shè)立稍遲,其中日本支部設(shè)立時(shí)間最晚,因?yàn)椤案緵]有合適的懂日語的工作人員,……此日本處的組建和在日本有計(jì)劃開展工作的安排,一直到太郎同志到伊爾庫(kù)茨克之后才算開始”[6]。相較之下,中國(guó)支部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中國(guó)處由一名俄國(guó)共產(chǎn)黨員阿勃拉姆松(東方學(xué)院的學(xué)生,操一口流利的漢語)主持”[7]。與日本學(xué)者石川禎浩所強(qiáng)調(diào)的需關(guān)注中共黨員在與共產(chǎn)國(guó)際交往過程中個(gè)人外語交際能力的影響[8]相似,蘇俄方面設(shè)立有關(guān)中國(guó)等外國(guó)事務(wù)的機(jī)構(gòu),同樣受限于是否有相關(guān)語言能力的人才,以致于東方民族部專門致信其所在地的伊爾庫(kù)茨克省委,要求:“1.任何知曉布里亞特語、蒙古語、朝鮮語和漢語的共產(chǎn)黨員干部的派遣,均需經(jīng)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許可;2.不征用任何布里亞特、中國(guó)、朝鮮的共產(chǎn)黨員負(fù)責(zé)干部”[9],以此掌握蘇俄本地和東方國(guó)家兩方面具有相關(guān)語言能力的人才。
東方民族部試圖集中和統(tǒng)一遠(yuǎn)東革命工作的目的并沒有達(dá)到,各方的掣肘和摩擦依然存在。其一,俄共(布)遠(yuǎn)東局對(duì)東方民族部事務(wù)進(jìn)行干預(yù),譬如攔截和扣留東方民族部的往來文件,阻撓東方民族部的信使和代表順利通行等,東方民族部因此申明“遠(yuǎn)東局的管轄范圍應(yīng)只限于領(lǐng)導(dǎo)俄國(guó)遠(yuǎn)東地區(qū)的黨組織”[10]。其二,外交人民委員部與東方民族部工作不協(xié)調(diào),譬如越過東方民族部向朝鮮、蒙古的革命組織撥發(fā)經(jīng)費(fèi)。其三,東方民族部的上級(jí)主管部門——俄共(布)西伯利亞局并不重視東方民族部的工作,“完全埋頭于西伯利亞區(qū)域內(nèi)的行政事務(wù)和黨務(wù),實(shí)際上沒有可能充分注意、沒有力量領(lǐng)導(dǎo)國(guó)外工作”[11]。對(duì)于這些問題,東方民族部的解決建議是同共產(chǎn)國(guó)際建立直接關(guān)系,將其改組歸屬到共產(chǎn)國(guó)際系統(tǒng),以“嚴(yán)格統(tǒng)一工作,由一個(gè)機(jī)構(gòu)行使全面的領(lǐng)導(dǎo)”[12]。一個(gè)新的機(jī)構(gòu)呼之欲出。
二、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
在東方民族部的建議和努力下,1921年1月5日和7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huì)和共產(chǎn)國(guó)際執(zhí)行委員會(huì)先后通過決議,決定在東方民族部的基礎(chǔ)上,成立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其組成人員有:共產(chǎn)國(guó)際駐遠(yuǎn)東全權(quán)代表舒米亞茨基,副代表加蓬(后來是明斯克爾),責(zé)任書記維經(jīng)斯基和鮑德里茨基,共產(chǎn)國(guó)際青年工作全權(quán)代表達(dá)林等。舒米亞茨基要求賦予他共產(chǎn)國(guó)際、青年共產(chǎn)國(guó)際、紅色工會(huì)國(guó)際、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全權(quán),這使得遠(yuǎn)東書記處成為具有廣泛代表性且強(qiáng)有力的組織,從而全面領(lǐng)導(dǎo)起遠(yuǎn)東的革命工作。遠(yuǎn)東書記處所擔(dān)負(fù)的任務(wù)是:第一,向共產(chǎn)國(guó)際匯報(bào)遠(yuǎn)東各國(guó)工人運(yùn)動(dòng)和革命運(yùn)動(dòng)的狀況及性質(zhì),向這些國(guó)家的工人和革命組織介紹共產(chǎn)國(guó)際的方針任務(wù);第二,幫助這些國(guó)家的工人和勞動(dòng)群眾尋找建立階級(jí)組織的最佳形式和進(jìn)行革命斗爭(zhēng)的有效方法[13]。
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承襲東方民族部設(shè)置地區(qū)科的制度設(shè)計(jì),并接受東方民族部此前提出的制度安排:“書記處編制為十一人,其中四人由東方國(guó)家日本、中國(guó)、蒙古和朝鮮的革命組織和共產(chǎn)黨組織選出。其余七人由共產(chǎn)國(guó)際執(zhí)行委員會(huì)指定任命,包括主席團(tuán)三人(主席、副主席和書記)以及日本處,中國(guó)處,朝鮮處和蒙古處的四名主任。”[14]這在事實(shí)上確定了遠(yuǎn)東書記處的集體領(lǐng)導(dǎo)原則,即由一位俄羅斯人和一位“當(dāng)?shù)亍睍涁?fù)責(zé)地區(qū)科工作,由他們組成領(lǐng)導(dǎo)委員會(huì)[15]。基于此項(xiàng)原則,1921年2月16日,遠(yuǎn)東書記處任命中國(guó)支部、朝鮮支部等機(jī)構(gòu)的工作人員:“阿勃拉姆松——任中國(guó)部俄方書記,符拉索夫斯基——任中國(guó)部俄方副書記,拉利多維奇——任朝鮮部俄方副書記,李森戈(音)——任朝鮮部俄方書記”[16]。可以看出,日本支部暫時(shí)還未設(shè)立,而中國(guó)支部中方書記和朝鮮支部朝方書記均空缺。日本支部暫未設(shè)立的原因,和東方民族部初建時(shí)日本支部設(shè)立時(shí)間較晚的原因一樣,即缺少相關(guān)語言能力的人才——1920年11月,當(dāng)時(shí)的東方民族部派太郎進(jìn)行聯(lián)系日本的工作,規(guī)定出差期限不超過四個(gè)月,因此,太郎此時(shí)應(yīng)該還沒有回到蘇俄[17]。
至于中國(guó)支部中方書記和朝鮮支部朝方書記均空缺的原因,則需要從歷史上尋找答案。早在1920年10月27日,東方民族部就召開會(huì)議討論并提出擬議中的遠(yuǎn)東書記處下設(shè)地區(qū)科的人選“:朝鮮代表為李森(音)Лисенг和樸鎮(zhèn)惇,中國(guó)代表為阿勃拉姆松和劉紹周,蒙古代表為鮑里索夫和博德,日本代表暫定太郎一人”[18]。11月24日,東方民族部決定派勃隆施泰恩和阿勃拉姆松赴莫斯科,當(dāng)面向共產(chǎn)國(guó)際和俄共(布)中央提議將東方民族部改組為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又提出其下設(shè)地區(qū)科的建議人選:“4)日本處長(zhǎng)——太郎同志。5)中國(guó)處處長(zhǎng)——阿勃拉姆松同志。6)朝鮮處長(zhǎng)——樸鎮(zhèn)惇。”[19]前后對(duì)比可以發(fā)現(xiàn),原為中國(guó)支部人選的俄國(guó)共產(chǎn)華員局成員劉紹周被淘汰,這是因?yàn)樵跂|方民族部負(fù)責(zé)人勃隆施泰恩和中國(guó)支部負(fù)責(zé)人阿勃拉姆松看來,劉紹周“政治素養(yǎng)差,就其素質(zhì)和信仰看,遠(yuǎn)非接近社會(huì)主義運(yùn)動(dòng)的人”[20],甚至他所在的俄國(guó)共產(chǎn)華員局也被指“表現(xiàn)不好,政治上不堅(jiān)定,其成員政治水平不高,根本沒有能力在華人中間開展革命工作”[21]。因此,1921年初遠(yuǎn)東書記處成立時(shí),中國(guó)支部中方書記暫時(shí)空缺。同樣的情況也發(fā)生在朝鮮支部,本為朝鮮支部人選的樸鎮(zhèn)惇也沒有出現(xiàn)在遠(yuǎn)東書記處朝鮮支部的名單里,這是因?yàn)闁|方民族部曾嚴(yán)厲批評(píng)“樸鎮(zhèn)惇、樸愛不停地進(jìn)行反對(duì)我部和朝鮮共產(chǎn)主義中央委員會(huì)的活動(dòng),向擬前來的朝鮮代表們聳人聽聞地介紹蘇俄情況,嚇唬他們,勸他們不要到伊爾庫(kù)茨克來”[22],顯然,這對(duì)于從東方民族部改組而來的遠(yuǎn)東書記處也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不難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中方書記的職位虛位以待。
三、張?zhí)讚?dān)任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書記
1921年初,張?zhí)鬃鳛橹袊?guó)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代表,赴伊爾庫(kù)茨克參加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的工作,他此前在北洋大學(xué)學(xué)習(xí),曾為天津的英文報(bào)紙《華北明星報(bào)》(North China Star)和俄共(布)黨員柏烈偉做英語翻譯,英語能力十分出眾。張?zhí)椎竭_(dá)伊爾庫(kù)茨克的具體時(shí)間不得而知,石川禎浩推測(cè)為1921年1月至2月間[23],達(dá)林回憶為1921年3月[24]。無論為何時(shí)間,至少在1921年2月16日,遠(yuǎn)東書記處任命中國(guó)支部工作人員時(shí),張?zhí)咨形吹竭_(dá)伊爾庫(kù)茨克,或已到達(dá)伊爾庫(kù)茨克但還未進(jìn)入遠(yuǎn)東書記處的視野。
張?zhí)兹ヒ翣枎?kù)茨克工作,首先是由于組建中的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迫切需要一個(gè)由中國(guó)的“革命組織和共產(chǎn)黨組織選出”[25],并且同時(shí)掌握中文和外語(俄語或英語)的中國(guó)支部中方書記。因此,1921年3月22日,遠(yuǎn)東書記處召開會(huì)議,決定任命張?zhí)诪檫h(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的書記,“到中國(guó)共產(chǎn)主義組織的代表大會(huì)派出新的書記時(shí)為止”[26]。次日,遠(yuǎn)東書記處負(fù)責(zé)人舒米亞茨基簽發(fā)第41號(hào)命令:“張?zhí)淄揪幦霑浱幑ぷ鳎瑫喝沃袊?guó)支部書記”[27],張?zhí)鬃源碎_始擔(dān)任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中方書記一職。但是,目前尚未見到遠(yuǎn)東書記處根據(jù)張?zhí)椎奶嶙h建立中國(guó)支部的決議或命令。
一方面,從東方民族部到遠(yuǎn)東書記處,與日本支部時(shí)常因缺乏相關(guān)語言能力的人才而設(shè)立滯后不同,中國(guó)支部始終在熟練掌握中文的阿勃拉姆松的領(lǐng)導(dǎo)之下,中國(guó)支部不存在需要張?zhí)椎絹砗蟛拍芙⒌恼Z言障礙。恰恰相反,已建立的中國(guó)支部的中方書記一職正需要人員填補(bǔ)空缺,張?zhí)椎牡絹砜芍^恰逢其時(shí)。另一方面,由東方民族部改組而來的遠(yuǎn)東書記處,承襲東方民族部原來設(shè)置地區(qū)科的制度設(shè)計(jì),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等地區(qū)科的設(shè)立和東方民族部一脈相承,而且中國(guó)支部的俄方書記阿勃拉姆松等已到任。至于需要等待張?zhí)椎竭_(dá)后,根據(jù)他的提議建立中國(guó)支部,這在邏輯上也是講不通的。
縱觀歷史,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的設(shè)立承襲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設(shè)置地區(qū)科的制度設(shè)計(jì),中國(guó)支部從不缺少掌握中文的語言人才,目前僅有張?zhí)妆蝗蚊鼮檫h(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書記的檔案資料,這三個(gè)方面說明以往研究認(rèn)為的張?zhí)滋嶙h建立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的觀點(diǎn)是很難成立的,而張?zhí)讚?dān)任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書記則是毫無疑義的。
*本文系天津市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規(guī)劃重點(diǎn)委托項(xiàng)目“張?zhí)讓?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組織建設(shè)歷史貢獻(xiàn)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TJKSZDWT1837)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xiàn)
[1]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xiàn)研究院:《革命先驅(qū)千秋忠烈——紀(jì)念張?zhí)淄菊Q辰120周年》,《人民日?qǐng)?bào)》2018年6月19日,第6版。
[2]葉孟魁、趙曉春:《〈張?zhí)钻P(guān)于建立共產(chǎn)國(guó)際遠(yuǎn)東書記處中國(guó)支部的報(bào)告〉作者考辨》,《黨的文獻(xiàn)》2011年第2期,第118頁(yè)。
[3]戴隆斌主編:《共產(chǎn)國(guó)際第一次代表大會(huì)文獻(xiàn)》,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頁(yè)。
[4]戴隆斌主編:《共產(chǎn)國(guó)際第二次代表大會(huì)文獻(xiàn)》,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643頁(yè)。
[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chǎn)國(guó)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guó)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頁(yè)。
[6][7][9][10][11][12][14][16][17][18][19][20][21][22][25][27]中共一大會(huì)址紀(jì)念館編:《中共首次亮相國(guó)際政治舞臺(tái)(檔案資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2、83、44、70、87、71、72、94、74-75、62、73、86、87、86、72、103頁(yè)。
[8][日]石川禎浩:《中國(guó)近代歷史的表與里》,袁廣泉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77頁(yè)。
[13]李穎:《共產(chǎn)國(guó)際負(fù)責(zé)中國(guó)問題的組織機(jī)構(gòu)的歷史演變(1920-1935)》,《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09頁(yè)。
[15]索特尼科娃、李穎:《1920-1931年間負(fù)責(zé)中國(guó)問題的共產(chǎn)國(guó)際組織機(jī)構(gòu)的回顧》,《湖北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4年第6期,第66頁(yè)。
[23][26][日]石川禎浩:《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成立史》,袁廣泉譯,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1頁(yè)。
[24][蘇]C·A·達(dá)林:《中國(guó)回憶錄(1921—1927)》,侯均初等譯,李玉貞校,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