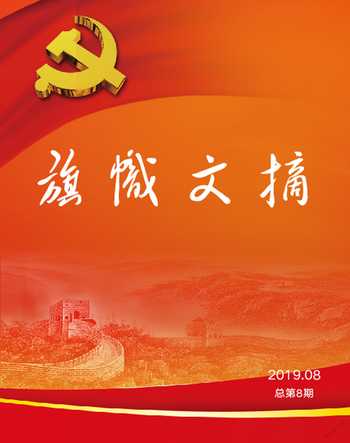中國(guó)古代數(shù)學(xué)家和他們的學(xué)問(wèn)
仙湖客
明清之際,西方的數(shù)學(xué)體系傳入中國(guó),中國(guó)的學(xué)者們?cè)谡痼@之余,也不斷反思,梳理中國(guó)古代數(shù)學(xué)發(fā)展的脈絡(luò),探究中國(guó)古代數(shù)學(xué)與當(dāng)時(shí)的西方數(shù)學(xué)問(wèn)的異同。經(jīng)過(guò)一番研究比較,人們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的西方數(shù)學(xué)知識(shí)固然先進(jìn)而自成體系,但其實(shí)也是中國(guó)“古已有之”的,不足為奇。康熙時(shí)代,“西學(xué)中源”說(shuō)被不少學(xué)者認(rèn)同,他們想當(dāng)然地認(rèn)為:商高、陳子等人的“勾股術(shù)”,劉徼的“重差術(shù)”,就是西方幾何學(xué)的源頭,李冶、朱世杰的“天元術(shù)”“四元術(shù)”,就是西方代數(shù)學(xué)的源頭,楊輝、朱世杰等人的“垛積術(shù)”,就是西方微積分的源頭,等等。我們的古人在數(shù)學(xué)方面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讓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光榮的名字:商高、陳子、劉徼、祖沖之、祖暅、沈括、秦九韶、楊輝、李冶、朱世杰……
——周公(《周髀算經(jīng)》)
三千多年前的某一天,周朝的著名政治家周公在周王的花園里,碰到了數(shù)學(xué)家商高。
周公問(wèn)商高:你們這幫數(shù)學(xué)家不是故弄玄虛的吧?什么天有多高地有多大,日月星辰一天走幾度,怎么你們都知道啊?(“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數(shù)安從出?”)
商高從容回答:數(shù)學(xué)家的學(xué)問(wèn),妙就妙在并非什么都要用尺子來(lái)量,只須通過(guò)數(shù)學(xué)計(jì)算,一樣可以得到正確的數(shù)字。比如這個(gè)直角三角形——他用一根牛的大腿骨和一段繩子作道具,比比劃劃,向周公解說(shuō):牛的大腿骨立在地上,高四尺,從牛骨的底端沿地面伸開(kāi)一段繩子,使這段繩子正好長(zhǎng)三尺,再將余下的繩子折向牛骨的頂端,請(qǐng)問(wèn),最后這一段斜向牛骨頂端的繩子,應(yīng)該長(zhǎng)幾尺?不須用尺子量,它的長(zhǎng)度一定是五尺。可見(jiàn),數(shù)學(xué)家能算出太陽(yáng)的高度來(lái),不是什么稀奇事。
商高總結(jié)說(shuō):在一個(gè)直角三角形中,如果兩條直角邊的長(zhǎng)度分別是三和四,那么斜邊的長(zhǎng)度一定是五,“勾三股四弦五”。這一個(gè)著名的論斷被記載在著名的《周髀算經(jīng)》一書(shū)里,這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勾股定理”的一個(gè)特例。
勾股定理作為一個(gè)大自然的秘密,注定要被世界上各個(gè)地方的人們分別發(fā)現(xiàn),或早或晚,因?yàn)檫@個(gè)定理就隱藏在人們的身邊,在每一個(gè)直角三角形里,除非你永遠(yuǎn)不蓋房子,不造馬車,不修陵墓,不建金字塔,否則,這個(gè)秘密就會(huì)不可避免地被人們發(fā)現(xiàn)。
在中國(guó),勾股定理的發(fā)現(xiàn)被歸在這個(gè)名叫商高的數(shù)學(xué)家兼天文學(xué)家的名下,所以后來(lái)又有人稱它為“商高定理”。當(dāng)然,如果僅僅有“勾三股四弦五”這一句話,那還不算真正全面闡述了勾股定理的內(nèi)容,“勾三股四弦五”只是勾股定理的一個(gè)特例。
若干年以后,周公的后人陳子也成了一個(gè)數(shù)學(xué)家,他曾詳細(xì)講述了運(yùn)用勾股定理測(cè)量太陽(yáng)高度的全套方案,為此,陳子說(shuō)了一句更為重要的話,同樣被記載在《周髀算經(jīng)》這部書(shū)里,他說(shuō):“求斜至日者,以日下為句,以日高為股,句股各自乘,并以開(kāi)方除之,得斜至日。”
在商高和陳子的時(shí)代,人們以為腳下的大地是一個(gè)大得沒(méi)邊的平面,只要知道了從觀察點(diǎn)到太陽(yáng)正下方的距離,知道了太陽(yáng)離地面的垂直高度,當(dāng)然就可以求出太陽(yáng)到觀察者的直線距離了,從觀察點(diǎn)到太陽(yáng)的正下方是勾(“以日下為句”),太陽(yáng)到地面的垂直距離是股(“以日高為股”),剩下觀察點(diǎn)到太陽(yáng)的距離,就是弦(“斜至日”),如此如此,求“斜至日”的辦法是“勾股各自乘,并開(kāi)方除之”:勾和股先自己乘自己一遍,加起來(lái)的和再開(kāi)平方,就得到了弦長(zhǎng)。雖然和我們今天對(duì)勾股定理的表述在習(xí)慣上有所不同,但這也是對(duì)勾股定理的完整表達(dá)。
據(jù)《周髀算經(jīng)》記載,陳子和他的科研小組測(cè)得日下六萬(wàn)里,日高八萬(wàn)里,根據(jù)勾股定理,求得斜至日整十萬(wàn)里。他進(jìn)而還算出了太陽(yáng)的直徑,為了達(dá)到這個(gè)目的,他用一只長(zhǎng)八尺,直徑一寸的空心竹筒來(lái)觀察太陽(yáng),讓太陽(yáng)恰好裝滿竹筒的圓孔,這時(shí)候太陽(yáng)的直徑與它到觀察者之間的距離,其比例正好是竹筒直徑和長(zhǎng)度的比例,即一比八十。
可惜,這些結(jié)論都是錯(cuò)的!
——陳子(《周髀算經(jīng)》)
看起來(lái),陳子是當(dāng)時(shí)的數(shù)學(xué)權(quán)威,《周髀算經(jīng)》這本書(shū),除了最前面一節(jié)提到商高以外,余下的部分說(shuō)的都是陳子的事情。
一天,一位名叫榮方的人跑來(lái)請(qǐng)教陳子:聽(tīng)說(shuō)根據(jù)先生的學(xué)問(wèn),可以算出太陽(yáng)有多高多大,一天之中太陽(yáng)行多少里,天有多高地有多遠(yuǎn),總之想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是這樣嗎?
陳子回答:然。
等了一陣不見(jiàn)下文,榮方只好再問(wèn):“方雖不省,愿夫子幸而說(shuō)之。”陳子回答:其實(shí)也沒(méi)什么難的,不過(guò)是運(yùn)用一些算術(shù)的方法就足夠了,你回去好好思考一下吧。就這樣把榮方打發(fā)回去了。
榮方回去想了好幾天,還是想不出有什么好辦法可以算出太陽(yáng)的高度來(lái),只好又去請(qǐng)教陳子:“方思之不能得,敢請(qǐng)問(wèn)之。”
陳子曰:“思之未熟。此亦‘望遠(yuǎn)起高之術(shù)’,而子不能得,則子之于數(shù),未能通類,是智有所不及,而神有所窮。”一點(diǎn)也不客氣地批評(píng)了榮方。
注意陳子所說(shuō)的“望遠(yuǎn)起高之術(shù)”,這是當(dāng)時(shí)人們?cè)谏a(chǎn)實(shí)踐中,特別是大型的建設(shè)活動(dòng)中,已經(jīng)熟練掌握的一套測(cè)算距離和高度的方法,陳子認(rèn)為同樣可以用來(lái)測(cè)算太陽(yáng)的高度。
倒霉的榮方思考了好幾天,還是想不出問(wèn)題的答案,不得不第三次去請(qǐng)教,陳子這才原原本本,把這一套方法向榮方講了一遍。
陳子講得信心十足,卻根本沒(méi)有意識(shí)到,他想當(dāng)然的許多東西,其實(shí)都是錯(cuò)的。他不知道他腳下的大地,看似無(wú)邊無(wú)際,平坦無(wú)垠,實(shí)際不過(guò)是小小一丸球,體積僅為太陽(yáng)的130萬(wàn)分之一,以地球之微來(lái)測(cè)太陽(yáng)之巨,無(wú)異于“以蠡測(cè)海”。
除了太陽(yáng)的高度,陳子還講了許多問(wèn)題,天有多高地有多大,太陽(yáng)一天行幾度,在他那兒都有答案,所以人們認(rèn)為《周髀算經(jīng)》又是一部天文學(xué)著作,記載了不少當(dāng)時(shí)人們已經(jīng)掌握的天文學(xué)知識(shí)。書(shū)的最后部分,陳子指出: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有十二月十九分月之七,一月有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有零有整,不失精確,而且基本上都是對(duì)的。
所以,三千多年前的陳子,他的學(xué)問(wèn)也不是那么簡(jiǎn)單的,雖然他不是全對(duì)。
——?jiǎng)⒒眨ā毒耪滤阈g(shù)注》序)
到了三國(guó)魏晉時(shí)代,中國(guó)又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大數(shù)學(xué)家,他的名字叫劉徽。
根據(jù)劉微的著作,人們推斷他生活的時(shí)代是“三國(guó)魏晉”,他的出身,他的生平事跡則沒(méi)有人知道,但他的家庭條件比較好應(yīng)該是可以肯定的,因?yàn)閺男。陀袡C(jī)會(huì)在老師或長(zhǎng)輩的指導(dǎo)下研究數(shù)學(xué)這門學(xué)問(wèn),如他自己所稱的那樣:“幼習(xí)九章,長(zhǎng)再詳覽。觀陰陽(yáng)之割裂,總算術(shù)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學(xué)習(xí)數(shù)學(xué)不是一年兩年了,很有心得。
劉徽一生的數(shù)學(xué)成就斐然,其中最為人們熟知的一項(xiàng),是他詳細(xì)記錄了用“割圓術(shù)”算出圓周率“密率”的方法,這在當(dāng)時(shí)絕對(duì)是領(lǐng)先世界的數(shù)學(xué)成就。
劉徽也研究自商高、陳子那時(shí)就遺留下來(lái)的數(shù)學(xué)難題:“太陽(yáng)到底有多高猜想”。劉徽汲取了前人的經(jīng)驗(yàn),提出更加完美的方案,假如我們腳下的大地真的是一個(gè)大得沒(méi)邊的平面,那么,用劉徽的這套辦法,就會(huì)真的計(jì)算出太陽(yáng)的高度來(lái),如假包換。他的方案是:
立兩表于洛陽(yáng)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景。以景差為法,表高乘表間為實(shí),實(shí)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間為實(shí),實(shí)如法而一,即為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為句、股,為之求弦,即日去人也。
讓我們簡(jiǎn)單翻譯一下,大體上說(shuō),他的方案是這樣:
在洛陽(yáng)城外的開(kāi)闊地帶,一南一北,各立一根八尺高的標(biāo)桿,在同一天的正午時(shí)刻測(cè)量太陽(yáng)給這兩根標(biāo)桿的投影,以影子長(zhǎng)短的差作分母,以標(biāo)桿的長(zhǎng)乘以標(biāo)桿之間的距離做分子,兩者相除,所得再加上標(biāo)桿的長(zhǎng),就得到了太陽(yáng)到地表的垂直高度。再以南邊一桿的影長(zhǎng)乘上兩桿之間的距離作為分子,除以前述影長(zhǎng)的差,所得就是南邊一桿到太陽(yáng)正下方的距離。以這兩個(gè)數(shù)字作為直角三角形兩條直角邊的邊長(zhǎng),用勾股定理求直角三角形的弦長(zhǎng),所得就是太陽(yáng)距觀測(cè)者的實(shí)際距離。
當(dāng)我們按照劉徽的思路,將他的這一套方案具體到一張幾何圖中的時(shí)候,我們就會(huì)驚訝地發(fā)現(xiàn),他的方案看似莫名其妙,毫無(wú)邏輯可言,實(shí)則運(yùn)用了相似三角形相應(yīng)邊的長(zhǎng)成比例的原理,巧妙地用一個(gè)中介的三角形,將另外兩個(gè)看似不相干的三角形聯(lián)系在了一起。這一切,和我們今天在中學(xué)幾何課本中學(xué)到的方法一模一樣。而劉微其人生活的時(shí)代,距今已近兩千年了。
——?jiǎng)⒒眨ā毒耪滤阈g(shù)注》序)
和陳子一樣,劉徽測(cè)算太陽(yáng)高度的方案因?yàn)榍疤岬腻e(cuò)誤,結(jié)果當(dāng)然也是錯(cuò)誤的,不過(guò),這套方案本身并不是為了測(cè)量太陽(yáng)的高度而專門設(shè)計(jì)的,方案的原始目的只是測(cè)算地面上的高山大河,測(cè)算山有多高,河有多寬,路有多遠(yuǎn),只要忽略地球的表面是個(gè)球面這一問(wèn)題,劉徽的方案堪稱完美。
曾經(jīng),在長(zhǎng)沙馬王堆的漢墓里出土過(guò)一幅帛畫(huà)的地圖,人們將它和實(shí)際的地形相比較,發(fā)現(xiàn)地圖驚人準(zhǔn)確,考古工作者還利用這張將近兩千年前的地圖作向?qū)В职l(fā)現(xiàn)了周圍一帶其他的地下遺跡。這看起來(lái)似乎很難讓人相信,但有了劉徽所記載的這一套測(cè)天量地的方法,這也就不算是什么奇跡了。
劉微總結(jié)的這一套測(cè)天量地的數(shù)學(xué)方法叫做“重差”。“重差”也是劉徽的一部數(shù)學(xué)著作的書(shū)名,這部著作研究的第一個(gè)例題是測(cè)算一個(gè)海島有多高多遠(yuǎn)的問(wèn)題,因此它還有一個(gè)名字叫做“海島算經(jīng)”。這部著作篇幅不長(zhǎng),似乎沒(méi)有出過(guò)單行本,長(zhǎng)期以來(lái)附在《九章算術(shù)》的后面,流行于世,所以歷代的《九章算術(shù)》都有十卷。
劉徽對(duì)“重差術(shù)”進(jìn)行了比較全面的總結(jié),無(wú)論是測(cè)量一座山有多高,一條河有多寬,一道溝有多深,都可以用到重差術(shù),其原理就是利用兩根或兩根以上的標(biāo)桿,將被測(cè)量的對(duì)象納入到一組相關(guān)的三角形中間來(lái),又通過(guò)三角形之間的關(guān)系,算出所要求得的對(duì)象。顯然,古代的“重差術(shù)”,現(xiàn)在叫做“測(cè)量”或者“測(cè)繪”,也就是陳子提到的“望遠(yuǎn)起高之術(shù)”。
重差術(shù)經(jīng)過(guò)了實(shí)踐的檢驗(yàn),劉徽曾自信地說(shuō),利用這種方法“雖天穹之象猶日可度,又況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哉!”
——《九章算術(shù)》
和直角三角形一樣,圓這個(gè)幾何圖形里面,也隱藏著一個(gè)大自然的秘密,那就是圓周率。
我們的古人實(shí)在是太有才華,不管是中國(guó)的外國(guó)的數(shù)學(xué)家們,居然如此巧妙地,分別找到了計(jì)算圓面積的方法,讓人想不佩服都不行。
我們?cè)囋诩埳袭?huà)一個(gè)圓,將這個(gè)圓沿直徑分成兩個(gè)半圓,然后分別將兩個(gè)半圓像切西瓜一樣割成八塊,讓它們像切好的八塊西瓜一樣,一個(gè)挨一個(gè)放在桌子上,或者,想象它們是一把只有八個(gè)齒的梳子,現(xiàn)在我們有兩把這樣的梳子,再將這兩只梳子齒對(duì)齒地插在一起,于是就湊成了一個(gè)近似的長(zhǎng)方形,它的短邊正好是這個(gè)圓的半徑,它的長(zhǎng)邊不是一條直線,而是由六段弧線構(gòu)成的。讓我們?cè)僮鬟M(jìn)一步假設(shè),假設(shè):我們當(dāng)初不是將半圓分成八份,而是分成了六十份,甚至三百六十份,那么,這條長(zhǎng)邊就會(huì)變成一段近似的直線,這條近似的直線非常接近半個(gè)圓周的長(zhǎng)度。
兩千多年前人們計(jì)算圓面積的方法就是這樣“化圓為方”,將圓周長(zhǎng)的一半與圓的半徑相乘,正如《九章算術(shù)》方田章中所指出的一樣:
“圓田……術(shù)曰:半周半徑相乘得積步。”
圓面積的計(jì)算方法太簡(jiǎn)單了,簡(jiǎn)單到就像一層窗戶紙,一捅就破。但是,幾千年以前的數(shù)學(xué)家們,不知道花了多大的工夫,經(jīng)歷了多少不眠不休的思考,才終于捅破了這層窗戶紙。“假令圓徑二尺,圓中容六觚之一面,與圓徑之半,其數(shù)均等。”劉徽則在他的《九章算術(shù)注》里詳細(xì)寫(xiě)到了如何計(jì)算“圓周率”,也就是圓的周長(zhǎng)和直徑之間的比率。
在長(zhǎng)期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中,人們發(fā)現(xiàn)圓的周長(zhǎng)和直徑之間有一個(gè)固定的比率,它的數(shù)值大約是3,只不過(guò)還要多那么一點(diǎn)。《九章算術(shù)》方田章的第三十一題是這樣的:今有圓田,周三十步,徑十步。問(wèn)為田幾何?
我們一看這個(gè)圓就有點(diǎn)問(wèn)題,世上并不存在一個(gè)直徑為十,周長(zhǎng)為三十的圓,“徑一周三”是中國(guó)古代圓周率的“約率”,在《九章算術(shù)》整本書(shū)里,圓周率采用的都是這個(gè)約率,顯然,這個(gè)約率相當(dāng)粗糙,給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實(shí)踐造成了不少煩惱。數(shù)學(xué)家們清楚,圓周率一定不是3,而是比3稍微大一點(diǎn)的一個(gè)數(shù)字。追逐圓周率這個(gè)大自然秘密的競(jìng)賽,就這樣開(kāi)始了。
計(jì)算圓周率的突破性進(jìn)展,是由劉徽來(lái)完成的。劉徽在為《九章算術(shù)》作注的時(shí)候,詳細(xì)記載了用“割圓術(shù)”計(jì)算圓周率的方法,他正確計(jì)算出了圓內(nèi)接正192邊形和3072邊形的邊長(zhǎng),從而得到了圓周率3.14和3.1416的數(shù)值,成為當(dāng)時(shí)領(lǐng)先世界的數(shù)學(xué)成就,這是我們都熟悉的史實(shí)。
“割圓術(shù)”的辦法,就是不斷增加圓內(nèi)接正多邊形的邊數(shù),讓這個(gè)多邊形的邊長(zhǎng)不斷地逼近圓周的方法。劉徽在《九章算術(shù)注》中寫(xiě)道:“假令圓徑二尺,圓中容六觚之一面,與圓徑之半,其數(shù)均等。合徑率一而外周率三也。”畫(huà)一個(gè)直徑二尺的圓,在圓中作一個(gè)內(nèi)接正六邊形,正六邊形的周長(zhǎng)和圓的直徑比例為三比一。正六邊形的邊長(zhǎng)恰好與圓的半徑相等,利用這一條件,依勾股定理,可以求得這個(gè)等邊三角形的高。一切從這里開(kāi)始,按同樣步驟重復(fù)下去,圓內(nèi)接正多邊形的邊長(zhǎng)會(huì)不斷接近圓的周長(zhǎng),求得的圓周率也就會(huì)越來(lái)越精確。
劉徽想到了,而且做對(duì)了。通過(guò)這種方法來(lái)計(jì)算圓周率,要經(jīng)過(guò)怎樣龐大的計(jì)算,可想而知,其中還要反復(fù)用到繁難的開(kāi)方計(jì)算,可是古代的數(shù)學(xué)家們毫不畏懼,勇敢迎接挑戰(zhàn),一點(diǎn)一點(diǎn),再接再厲,試圖揭開(kāi)這個(gè)隱藏很深的秘密。
——秦九韶(《數(shù)書(shū)九章》序)
生活年代較劉徽晚一點(diǎn)的祖沖之,也是一位著名的數(shù)學(xué)家,他同樣利用了“割圓術(shù)”的辦法,窮追圓周率這個(gè)大自然中無(wú)盡的秘密,通過(guò)艱苦的努力,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jī),刷新了記錄,名垂后世。
和劉徽的情況稍有不同,祖沖之在當(dāng)時(shí)(南朝宋、齊)的政府里面任有職務(wù),所以在官方的史書(shū)中,留下了一篇簡(jiǎn)短的傳記。據(jù)說(shuō)他很有巧思,曾經(jīng)設(shè)計(jì)制造過(guò)一些自動(dòng)化的機(jī)械,可以與諸葛亮的“木牛流馬”相媲美。
祖沖之的兒子祖暅也是一位數(shù)學(xué)家,父子兩人合著了一本名叫《綴術(shù)》的數(shù)學(xué)著作,書(shū)中就記載了他們將圓周率計(jì)算到3.1415926與3.1415927之間的成果,這在當(dāng)時(shí)也是相當(dāng)突出的成績(jī)。可惜,后來(lái)《綴術(shù)》一書(shū)失傳了,只有從其他著作的引文中,后人才能看到這本書(shū)的片斷。
祖暅癡迷數(shù)學(xué)的程度有甚于他的父親,當(dāng)他思考數(shù)學(xué)問(wèn)題的時(shí)候,哪怕天上打著驚雷,他也可以充耳不聞。一天,祖暅一邊走路,一邊思考數(shù)學(xué)問(wèn)題,不小心撞到了別人的身上,一時(shí)傳為笑談,事情被寫(xiě)進(jìn)了他們父子兩人的傳記之中。
到了十三世紀(jì)的宋元時(shí)期,中國(guó)古代的數(shù)學(xué)發(fā)展又迎來(lái)了一個(gè)黃金時(shí)代,達(dá)到了一個(gè)新的高峰,可惜這是中國(guó)古代數(shù)學(xué)史上的最后一個(gè)高峰,此后,中國(guó)古代數(shù)學(xué)再也沒(méi)有突破性的進(jìn)展,而西方的數(shù)學(xué)研究則取得了飛躍的進(jìn)步。
在這個(gè)最后的黃金時(shí)代,中國(guó)出現(xiàn)了四位最重要的數(shù)學(xué)家,被后人稱為“宋元四大家”,他們是南宋的秦九韶、楊輝,金元時(shí)期的李冶,元朝的朱世杰。
秦九韶早年“訪習(xí)于太史,又嘗從隱君子受數(shù)學(xué)”,學(xué)成以后,寫(xiě)成了著名的《數(shù)書(shū)九章》一書(shū)。在該書(shū)的序言中,秦九韶寫(xiě)道:“數(shù)理精微,不易窺識(shí),窮年致志,感于夢(mèng)寐,幸而得知,謹(jǐn)不敢隱。”日思夜想,夢(mèng)寐求之,一旦有所收獲,趕緊記錄下來(lái),留給后世。科學(xué),就在這樣點(diǎn)點(diǎn)滴滴的努力中,得到了進(jìn)步。
楊輝是南宋另一位著名的數(shù)學(xué)家,他在數(shù)學(xué)方面的著作很多,除了對(duì)學(xué)科中的某些領(lǐng)域有所開(kāi)拓以外,他還將《九章算術(shù)》中的題目重新做了排列分類,指導(dǎo)人們學(xué)習(xí)研究,對(duì)古代數(shù)學(xué)的教育和普及做出了貢獻(xiàn)。
朱世杰是元朝享有盛譽(yù)的職業(yè)數(shù)學(xué)家,后人稱他“以數(shù)學(xué)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踵門而學(xué)者云集”,學(xué)術(shù)地位非同一般。朱世杰的數(shù)學(xué)代表作有《算學(xué)啟蒙》和《四元玉鑒》兩種。《算學(xué)啟蒙》是一部通俗數(shù)學(xué)名著,曾流傳朝鮮、日本等國(guó),古代朝鮮曾以《算學(xué)啟蒙》開(kāi)科取士,深刻影響了這些國(guó)家的數(shù)學(xué)教育和發(fā)展歷史。《四元玉鑒》則是中國(guó)宋元時(shí)期數(shù)學(xué)高峰的又一個(gè)標(biāo)志,其中最杰出的數(shù)學(xué)成就有“四元術(shù)”、“垛積術(shù)”與“招差術(shù)”等。
而四人中最為出色的,應(yīng)當(dāng)是李冶。
——《四元玉鑒》序
“宋元四大家”中的李冶,是真定欒城縣(今河北省石家莊市欒城區(qū))人,金朝進(jìn)士。當(dāng)蒙古帝國(guó)的軍隊(duì)攻入中原、圍困金朝的南京汴梁之際,李冶就在圍城之中。城破之后,李冶輾轉(zhuǎn)北上,來(lái)到河北一個(gè)名叫“封龍山谷”的地方,隱居下來(lái),一呆就是二十年。在這里,李冶開(kāi)辦了一所名叫“封龍書(shū)院”的學(xué)校,教授他畢生精研的數(shù)學(xué)。李冶著有《測(cè)圓海鏡》和《益古演段》兩部數(shù)學(xué)著作,其中《測(cè)圓海鏡》的成書(shū)標(biāo)志著“天元術(shù)”的成熟,《益古演段》則是“天元術(shù)”的普及讀物。
李冶在他的著作中,研究了把實(shí)際問(wèn)題化成高次方程的數(shù)學(xué)模型,他稱方程中的未知數(shù)為“天元”,稱他的求解方法為“天元術(shù)”。有研究者指出:李冶的《測(cè)圓海鏡》標(biāo)志著“天元術(shù)”的成熟,此后,元朝郭守敬編撰《授時(shí)歷》,使用“天元術(shù)”求周天弧度,又用“天元術(shù)”來(lái)解決水利工程中的計(jì)算問(wèn)題,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天元術(shù)”很快發(fā)展為“二元術(shù)”、“三元術(shù)”,以至朱世杰的“四元術(shù)”,成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數(shù)學(xué)發(fā)展史上的一次高潮。
1265年,應(yīng)元世祖忽必烈的反復(fù)邀請(qǐng),七十三歲的李冶離開(kāi)封龍山谷,來(lái)到北京城里,在元朝剛剛建立的翰林院里任職。可以想象,一個(gè)隱居了二十年的老數(shù)學(xué)家,到了翰林院這樣的機(jī)關(guān)里,還能有什么大的作為?這份工作顯然不適合李冶其人,所以他“就職期月,復(fù)以老病辭去”,堅(jiān)決地托病辭職了。
李冶離開(kāi)北京回山,從此不再離開(kāi)封龍山谷半步,他繼續(xù)埋頭研究、教授數(shù)學(xué),直至87歲去世。史家評(píng)論李冶:“講學(xué)著書(shū),秘演算術(shù),獨(dú)能以道德文章,確然自守,至老不衰。”他還有兩句詩(shī)流傳至今,很好道出了他在封龍書(shū)院的身心狀態(tài):“隱身免留千載笑,成書(shū)還待十年閑!”
公元1279年年初,南宋王朝最后的武裝力量在廣東崖山海域覆亡,其后某一天,八十七歲的老數(shù)學(xué)家在遺囑中寫(xiě)道:“吾平生著述,死后盡可燔去,獨(dú)《測(cè)圓海鏡》,雖九九小數(shù),吾常精思致力焉,后世必有知者,庶可布廣垂永乎?”
前不見(jiàn)古人,后不見(jiàn)來(lái)者,中國(guó)古代數(shù)學(xué)家們的一生是何等寂寞啊!李冶老人不知道,他當(dāng)年研究的“九九小數(shù)”,今天已經(jīng)成了人類最重要的學(xué)問(wèn)之一,豈止“布廣垂永”,而且日新月異,人才輩出。后人也到底沒(méi)有忘記這些古代數(shù)學(xué)的先驅(qū)者們,1992年,在李冶的故鄉(xiāng)河北欒城,人們建起了一所“李冶陳列館”,以此紀(jì)念李冶誕生800周年。李冶這位中國(guó)古代數(shù)學(xué)家,已被公認(rèn)為中國(guó)乃至世界的文化名人。
李冶先生泉下有知,可以含笑而無(wú)憾了。
(:看歷史 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