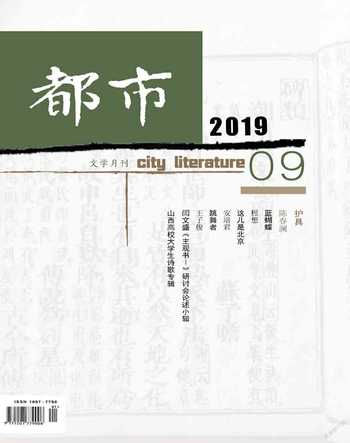散文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
魯順民
我跟文盛的交往年頭特別長,他首批的散文很多都發表在我們刊物上。今天的主題是“散文的可能性”,實際上應該改為“閆文盛散文———散文的不可能性”,他的散文,無論是作為編輯剛開始看,還是后來出書后作為讀者看,總給人一種提心吊膽的感覺。提心吊膽什么呢?他離你慣常的閱讀,或者距離慣常的散文樣式很遠,他筆下的事物、人物、情緒,幾乎都不可能構成慣常散文的元素,即便你讀完,仍然心有余悸———剛才讀的是不是散文,是不是文章?這種懷疑一直存在。哪怕是今天洋洋灑灑八十萬字也好,十多萬字也好的《主觀書》出籠。
這種閱讀經驗距離你的閱讀期待實際上也很遠,說白了,看閆文盛的散文,總有一種“別扭”的感覺。好好寫著人,突然這個人消失了,滿篇說的是他跟這個人交往時候自己的心態和自己的情緒、情感,是真的在寫人嗎?好好寫著一件事,突然這件事情神龍見首不見尾,無始無終,然后作家的情緒占了上風;好好寫一種情緒,以為是有什么感悟,其實也不是,他在那里追問。追問又質問,追問并不是尋求某種故事意義上的真相或者結果,而是尋求哲學意義上的答案或者質詢。我們似乎可以這樣來理解閆文盛的散文。
首先,他的散文具有高度的私人化傾向,與其說,他通過散文表達,是想與這個世界進行對話,給眼前事物以全新的命名,倒不如說,他一直在跟自己對話,獨白,自我剖白。這個大家都能夠體會到,正因為如此,他的散文顯得比較散漫,因為在寫下一篇的時候,可能就沒有打算讓哪一個人看。
其次,縱觀閆文盛寫作,他一直在破壞,在冒犯,在違章。在前六七年,哪一期缺稿子,就想起文盛撲閃撲閃美麗的大眼睛,就讓他趕緊拿來稿子,很密集地發過一兩年。剛開始是小說,后來就寫散文了。但他的小說是“別扭”的,是異于標準小說的,然后又是散文,仍然是別扭的,異于常規散文的。但他做得很好,為什么呢?他最早是寫詩的,寫詩的人特別可怕,屁大點的事,他能寫得那么復雜,無論是山也好,水也好,哪怕是一瞬間的心情也好,可以攪動得空間很大,寫詩已經很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詩人放下寫詩的筆去寫文章。那幾年他寫小說寫得風生水起,眼看要達到我期待的目標,他突然不寫,然后大量寫散文,寫他的《主觀書》。詩人寫散文,寫小說者不乏其例,這樣的人混跡于小說家散文家行列,是下決心拿人飯碗。
《主觀書》剛開始,我也曾經說過,我說你不要這樣來寫,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可是《主觀書》一旦集結成集之后,拿到手里,雖然好多發表過,但還是吃了一驚,就像造句一樣,一旦排比,就出現一種氣勢,呈現出一種面目。讀他的《主觀書》,我想起了本雅明,想起了佩索阿,更想起了卡夫卡,他老是跟我談論起這些外國作家。他在談論這些外國作家的時候,我剛開始很擔心,我說你不懂外語,最好不要說這些話,而且我勸他學點外語,讀點原著。但是更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他突然考上研究生了。
可能大家不知道,文盛是一個學習能力特別強的人,在初中的時候學習就很好,初中一畢業,當年就考上了中專,是山西省水利學校,他是學水工的。一個搞理工科的人很不服氣,就搞了文學,而且還是寫作的研究生,就像跨過好幾個朝代,突然邁入現代一樣,常常讓你吃驚。他的這種人生狀態也幾乎是一種不可能。不可能,是因為不可復制。
還有,六七年中間,我頻繁到各地去,在各個省見不同群體的文學朋友,他們老跟我講文盛的散文,我剛開始沒有覺得怎么樣,后來說的人越來越多,有女性,當然更多的是男性,有實力派作家,也有新銳文學新秀,我已經覺得文盛的散文寫得好,沒想到他這樣好,影響如此之大。大家可以看看《主觀書》后面那些評論家給他的評論,那些評論都很客觀,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評論。
但作為編輯,常常約文盛的稿子,首先還是喜歡他的表達,就是他的語言。精到,老到,結實,準確,很少有人談起過他的語言。翻閱《主觀書》,不管你對文章怎么看,你不得不佩服他對敘述、結構的把控能力,這種把控能力實際上是作為一個作家具備的基本功。可惜的是,許多作家并不具備這個基本功,甚至鄙棄這種基本功訓練。我常常把有無此種訓練與能力,視作一個作家有無創造力的一種氣質。文盛是有這個氣質的。
細想一想,一個寫作者,民間叫寫家。寫家的本事,就是靠敘述來創造現實世界不可能性之外的一種可能世界,從而贏得“作家”的稱號。文盛顯然做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