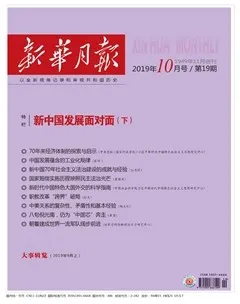用數據模型解讀人類科技創新
陳自富

最近十幾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高速發展,不僅在生物學上,而且在知識這種似乎人類有絕對優勢的領域,人類自身的創造物反過來也在一個新的層面上挑戰著對自身的認知。面對這些挑戰,人們逐漸從更廣泛的角度考察人類本性,例如從社會學來看,從事勞動是人的一個重要特征,而這種勞動必然與其他物種之間存在某些差別,并為此推動著人類社會的發展。
人類勞動的一個獨特性是具備創新能力,即不僅能夠制造各種工具,而且能發現和發明知識,并具備綜合性運用知識和工具,在社會協作下大規模改變自然的能力,從而產生一個與自然界并行的技術人造物世界,這種具有能動實踐性特征的創新能力,在各種新技術層出不窮的當代,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人類的本質特征。因此,人類的全部科技創新活動不僅形成了我們區別于其他生物或人造物的基礎,而且也是推動人類社會擺脫自然界生物進化規律限制,不斷發展和進步的核心動力。
人類迄今為止的科技創新活動,發生在廣袤復雜的外部自然環境中,也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多次重大的社會變遷,因此要在這樣一個巨大的時空范圍內來描述和解釋人類的科技創新,并通俗易懂地為讀者闡述其中的各種規律和發現,無疑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任務,《人類科技創新簡史:欲望的力量》通過宏觀大時間尺度描述的方法,嘗試完成這個任務。
與編年史方法不同,如此長時間跨度的科技創新史描述需要一個獨特的視角,作者從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歷程出發,將科技創新區分為“生存大革命”“交流大革命”“效率大革命”這三個跨度漫長的科技活躍時代,同時提出從交流大革命到效率大革命之間存在一個跨度長達一千六百多年的轉折時代,而在以傳統工業革命為核心的效率大革命之后,從上世紀初到今天,則是尚未結束的第二個轉折時代。
這種大時間尺度的科技創新歷史描述,是作者在理論上進行的與前人不同的探索。例如傳統上我們習慣用標志性的生產工具來描述處于不同生產力階段的社會,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等就是如此,或者將技術與社會因素結合起來描述,例如摩爾根的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前者的分類對科技創新而言過于簡略,后者則更多從精神或社會文化層面出發,難以明晰地描述科技創新長河中的主要脈絡。
而《人類科技創新簡史》一書,采用了一個基于計量方法的長時間尺度重大科技成就數據庫,該數據庫對公元前10000年到今天的人類科技創新成就進行了詳細統計,并基于相關科技史專家的研究成果對這些成就進行了若干重要度排序,同時也橫向比較了世界上不同地區從孤立、隔絕到逐步融合過程中的科技傳播及影響,從而能夠定量地從不同維度來描述不同技術革命時代的基本特征,而作者獨創的生存、交流和效率的維度,則是從理論上引入了心理學思想資源對科技創新歷史分期的一種大膽嘗試,不僅符合對人類生存和社會進步歷史的常識認知,也在科技創新成就的數據上得到了有力支撐。
從歷史中發現人類社會的規律,為未來決策提供指引,是一種常見的基本想象。傳統上對于科技史的研究,很多是從科技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出發,來解釋科技創新活動的種種規律,這種從社會學維度來研究科技史的所謂“外史”方法,其有利之處是可以在一個受限制的時空范圍內揭示科技創新活動的某些規律,但其弊端是往往忽視了科學和技術發展歷史中的內在思想變化歷程,有時容易導致片面的外部環境決定論,例如地理或社會制度決定論等。
與之并行的還有科技創新活動本身內容的歷史研究,這種研究試圖找到科技活動的內在發展規律,即所謂“內史”方法,該方法的優點在于從單獨的專門學科或技術活動出發,擺脫外部社會環境影響,揭示科技活動的內部規律,其前提是假設科技有其自身獨立的發展邏輯,外部社會因素只能暫時施加影響,因此人們的決策應遵循科技的內部規律。但這種進路的缺點也很明顯,首先是外部環境對科技活動的影響有時確實很重大,例如戰爭、瘟疫或自然災害會導致科技創新活動的傳承中斷,其次則是對于科技活動本身內容的研究,當代的科技史研究者往往容易從當前的科技發展水平出發,將歷史上的科技成就看成是朝向當代科技的直線累積式進步歷程,這種后見之明忽視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科技創新活動差異,用近代科學的尺子去衡量歷史上從巫術到宗教的各種解釋,不能反映人類科技創新長河中的真實情況。
因此,將外史和內史的方法結合起來,從社會、學科思想、文化、宗教等各個維度來綜合地描述科技創新歷史,似乎是一個必然的選擇,但佳作卻不多見。而《人類科技創新簡史》一書引入了心理學和管理學中的思想資源,在傳統科技史工作者的常規進路之外,構造了一個宏大模型,來解釋人類漫長的科技創新活動及成就。
作者從心理學中的動機理論出發,以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于上世紀40年代提出的人類需求層次模型為基礎,結合其在創新管理中關于需求與科技創新動力學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個獨特的“需求層級科技分類體系”,即將人類歷史上的科技活動和成就,從低到高分為生存/溫飽、安全/健康、交流/娛樂、機動/靈活、效率/利用、探索/超越這六個層次,每個層次與馬斯洛需求模型的相關層次對應,從而以此解釋人類不斷探索自然、改造世界的科技創新活動的動機,這種動機不僅來自于人類的生物需求,更多地來自社會文化需求,以及人類超越自我生物和社會局限的需求。
從本質上來看,這種以滿足內外部需求的動機論,大體上可以認為是一種科技史的外史研究,即除了從人類的生物學維度考慮之外,更多的是考慮人類作為一個社會整體,面臨各種社會性需求,在文化、宗教和自然環境的約束下所從事的科技創新活動,因此仍然是一種社會性維度。但此處的不同在于其與心理學中動機理論的思想資源結合,并將這種心理學解釋納入一個完整的需求如何驅動科技創新的動力模型,從而試圖在傳統的外史方法之外尋找科技創新活動中的新規律。這種大膽嘗試在科技史研究與企業創新管理研究之間搭建了一個新的橋梁,雖然還不完美,但卻啟示人們應注意創新活動中經濟、管理與科技內容本身發展之間的聯系。
《人類科技創新簡史》有一個重要特點,使之區別于一般的科普類通俗讀物。在上文中需求層級科技分類體系所展現的邏輯自洽性之外,作者與其團隊合作者還花費了6年多時間建立了人類科技史的“重大科技成就數據庫”,收錄了3000多項首創科技成就條目,時間跨度上從公元前一萬年到當今,空間范圍上覆蓋了中國、印巴、中東、歐洲、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作者利用這個數據庫的詳細史料,并結合歷史上的世界人口、國內生產總值等統計數據,試圖從中找到經濟發展、科技成就、科技傳播、社會制度、自然環境等宏觀要素之間的聯系與規律,為需求層級科技分類體系的邏輯自洽性在歷史事實上提供經驗證據。表現了作者力圖實現一種類似自然科學那樣條理清晰、數據完整的邏輯說服力,這種將理論模型與歷史計量方法相結合的嘗試在科技史領域并不多見,尤其是在本書所論及的宏大領域。作者不僅想回答人類為什么進行科技創新和如何進行科技創新的問題,而且還討論了中國為什么沒有誕生近代西方科學技術,以及什么樣的社會制度、文化和商業氛圍更有利于科技創新。
雖然很難在本書論及的這些重大問題中從正反兩面給出完整的答案,但將重大科技成就數據庫用于科技創新史的研究,似乎比傳統的案例研究方法具有更加客觀和明晰的說服力。例如該數據庫顯示,迄今為止中國的重大科技成就累積量約占世界總量比例的6.2%,中東地區約8%,歐洲地區約52%,而開發較晚的北美地區則占26%,由此至少從科技成就領域來看,“歐洲中心論”在客觀數據上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從時間維度來看,結合世界人均GDP增長率數據,1800年前基本為0,之后在英國等少數科技先進國家出現持續增長,全球性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始于“二戰”后的20世紀50年代,與此對應的是每10億人口的年均重大科技創新數量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早期達到最高峰,這個數據對比說明了人類的重大科技創新顯著超前于社會和經濟發展,因此適合作為預測未來發展的領先指標。
作者建立的重大科技成就數據庫,雖然主要來自相關科技史專家的二手材料,但其創新之處是引入了全新的理論模型,同時又不限于數據庫本身,而是試圖在經濟、政治、宗教、文化等宏觀背景下,將模型與數據結合起來,使數據對相關理論的支撐更加堅實,這種宏大的寫作思路在全書材料的組織中井然有序,觀點鮮明,從而展現了一種與以往科技通史或專題史著作不同的說服力。
人們研究科技創新歷史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預測未來,并制定相關的行動策略,作者在書中預測了人工智能和能源轉型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并對未來的科技創新是否還能延續上一波的高峰提出了謹慎質疑,認為“二戰”后建立的全球化體系雖然不完美,但迄今仍未出現替代者,因此中國能否從近代的跟隨者角色成長為新的科技創新活動的弄潮兒,仍然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作者的觀點是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的科技創新高潮,類似生物界的寒武紀爆發,可能最終會歸于沉寂,而數據庫也顯示近百年來人類重大科技創新的活躍度在放緩,這些論斷給讀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
作者關于未來科技發展的上述討論,與解讀歷史相比無疑需要更多的理論模型和數據支撐,歷史經驗能否外推,本身似乎是一個概率事件,但本書展現的方法論努力,雖然只是創新管理與科技史研究的交叉結果,對于歷史計量方法的不同見解,以及理論與數據之間是否相互支持,學術共同體是否完全接納其中的觀點,都是本書之外可以探討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將探討人類為何創新、如何創新、未來技術如何發展的宏大主題,通過一本并非大部頭的通俗著作展現給普通讀者,并試圖給出獨立思考后的答案,本身就需要極大的勇氣和努力。
(摘自8月7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