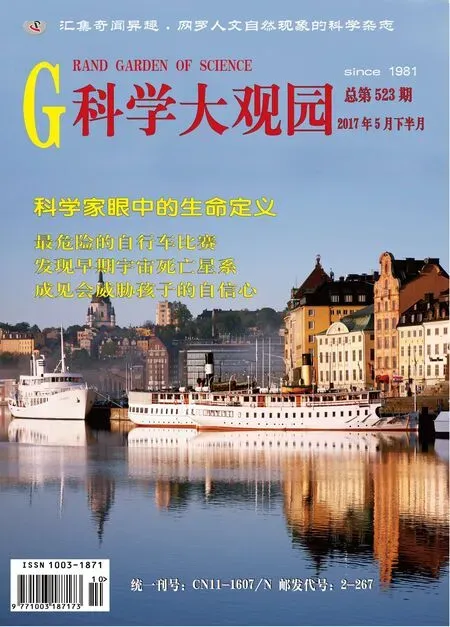調試天眼的人白天摳精度 晚上試觀測
自2016年成功落成以來,“天眼”FAST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又一個驚喜。
說到成就“天眼”的人,除了南仁東等科學家,不得不提的,還有如今日夜堅守在“天眼”身旁的調試組。
從“月宮一號”屢創世界紀錄,到“海眼”系統攻克世界級難題;從世界在研最大水陸兩棲飛機完成首飛,到全球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中國天眼”落成啟用,這些重要科研成果,離不開我國科學家的篳路藍縷、披荊斬棘。青年科技人才是我國科研隊伍中最富活力和最具創造潛力的群體。他們意氣風發、竭智盡力,他們以夢為馬、不負韶華。今年的5月30日,是“全國科技工作者日”,在這屬于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節日里,讓我們向科技致敬、為創新喝彩。
在這個100平方米左右的總控制室里,沒有會變出奇異圖形或復雜代碼同時還閃著各種不同顏色光的大屏幕,沒有緊張的口令,沒有急促的腳步聲,也沒有擊掌和歡呼聲……只有一排電腦安靜地端坐在桌子上,和一個同樣安靜地端坐在電腦前的年輕小伙子。
“你的同事還沒來嗎?”筆者試探著問。“他們輸入完觀測數據已經走了。我一會兒寫完總結也走了。” 小伙子叫李志恒,操作筆記本電腦,身穿白T恤衫和牛仔褲,是FAST調試組的一名工程師。
9點55分到了。從遙遠的太空傳來的電磁波無聲無息地落在群山環抱的大窩凼里,然后轉換為信號靜謐地流淌進計算機集群,計算機沉默地跑著數據,憑借調試人員設計的程序努力辨別脈沖星信號。
原來,那些驚天動地的新發現誕生得這么安靜。與脈沖星有關的中國故事,就從這個萬籟俱寂的地方開始。
古今中外,總有一些人想弄明白這幾件事:我們從哪兒來?宇宙有多大?最小的粒子有多小?在貴州的深山里,就有這么一群人。
寫完工作總結的李志恒打開一款名為Stellarium的天象模擬軟件,展示出一片效果逼真的太空。“我們的工作有點像淘金。” 他指著銀河系的繁星說。
目前全球經認證的脈沖星共有2600多顆,它們可以成為人們研究“最小粒子”的實驗室,幫忙探索宇宙到底有沒有邊界等。這種能對人類認知宇宙產生巨大幫助的天體就像金子一樣稀有和珍貴。
只是,在2016年FAST落成啟用之前,中國在這項為人類天文事業“淘金”的工作中還沒有成為主力。為此,FAST的總工程師南仁東生前說:“別人都有大射電望遠鏡,我們沒有,我挺想試一試。”
20世紀90年代初,在國家天文臺工作的南仁東最初將中國的大射電望遠鏡夢寄托在了平方公里陣列望遠鏡SKA身上。那是一項大型國際科研合作項目,其技術路線是將上千個反射面天線和100萬個低頻天線組成一個超過100萬平方米的接收區域,收集來自宇宙的電磁波信號。
當時在國際射電天文圈里有兩張活躍的中國面孔,一個是南仁東,另一個是他的師弟,后來成為FAST工程副經理的彭勃。他倆輪流飛往國外參加研討,執著地想將SKA的建設引入中國,別人笑稱彭勃是“SKA獨立大隊”、南仁東是“SKA獨立支撐”。
但有一天這兩個互為支柱的人吵起來了。這條路越往前走南仁東越覺得走不通,他開始反對在中國建SKA。“把SKA弄過來,弄死你我,都弄不成!” 他跟彭勃說,南仁東的學術風格以“謹慎保守”著稱。
“先弄過來!弄死你我,還有后來人!” 彭勃和南仁東正好相反,他外號叫“彭大將軍”,出了名的敢想敢說敢干。
而后經過多次爭論和多方論證,南仁東和彭勃的同門師兄,天文學家吳盛殷計算出,在中國建設一個約500米口徑的射電望遠鏡最合適,既能超越已有設備,又現實可行。大家便統一想法,將SKA的夢想,嫁接到現如今的FAST身上。
于是一群對探索終極問題有熱忱的人開始創業。為了解決望遠鏡的支撐問題,他們需要找到一個天然的“大坑”,讓望遠鏡像一口鍋一樣“坐”在里面;為了解決電磁波信號接收機,即饋源艙的移動問題,他們需要設計一個可靠又省錢的機械結構;為了讓望遠鏡能夠在最大范圍內靈活追蹤天上的目標,他們需要望遠鏡反射面能動——正是這些挑戰,逼出了FAST的三大技術創新。
夢想裹挾著創新的風險一步一步把時間的坐標推到現在。他們成功了,FAST成為世界上最靈敏的射電望遠鏡。不過FAST工程團隊名單上前三位中,南仁東和吳盛殷已去世,當年算得上是年輕人的彭勃也戴上了老花鏡。
彭勃記得他早年作為留學生代表接受德國電視節目采訪時說:“中國也要在望遠鏡靈敏度發展曲線坐標圖里點個點!” 朋友聽了這話私下跟他說:“你敢在德國吹牛。要點個點,就必須做第一,當世界老大。”
“當老大就當老大!” 他回答說。從FAST的想法成形,到今天成為全球最靈敏的宇宙“淘金”設備,過去了20年,盡管時間長了些,但彭勃并沒有吹牛。
“那個造望遠鏡的過程就像懷孕。” 準備收工的李志恒告訴筆者,他回頭看了一眼總控室的監測屏幕,接著說:“我們現在調試的過程,相當于要把這個孩子養育成才。”
時間來到2018年,更年輕的人們繼續探尋終極問題的答案。
FAST調試組正式成立于2017年4月,成員數10人,80后岳友嶺是調試組的負責人之一。調試組成員大多是FAST團隊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也是現在的中堅力量。
當年FAST令人驕傲的三項自主創新延伸至今,便意味著調試工作在國際上“無先例可循”。這些平均年齡30多歲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正小心翼翼地為射電天文觀測開辟一種新的、中國的解決方案。
“簡單來說,FAST相當于人類感官的延伸。”總控室里的計算機集群嗡嗡作響,晚上11點多,李志恒繼續搜腸刮肚地打比方。
我們的感官無法識別和處理宇宙中的天體傳來的電磁波信號,FAST的運行系統就充當了媒介的角色,它將信號收集、處理,再翻譯成人類能理解的形式。
但中間這個轉換的過程非常復雜。拿觀測脈沖星來說,天體呈周期性發射的微弱的電磁波射向地球,有一部分落在FAST的反射面上,反射面將這種電信號匯聚到饋源艙接收機處,接收機將電信號轉換成光信號,通過光纜將光信號傳回總控室,再把光信號轉換回電信號,進而轉換成數字信號,計算機集群就根據事先設定好的程序將這些數字信號儲存、計算,最終結合科學家的分析,識別出能夠代表脈沖星的一串特殊的信息。
由于FAST的技術路線新穎,以上每兩個逗號之間,都有難以計數的問題等著調試人員去解決。所以他們現在的日常工作是白天“摳精度”,晚上試觀測。
讓這個龐大的裝置達到毫米級精度殊為不易。“摳精度”的過程,可謂險、難、繁、重。大家經常卡在某個問題上,“一卡就是一兩個月”。
岳友嶺認為,FAST調試進度很難量化,盡管試觀測效果已經超越了現有的其他射電望遠鏡,但要達到“好用”,還要解決數不清的問題。
“我們不怕折磨,我們能找出問題出在哪兒,就是需要想辦法解決。”調試中遇到的“麻煩”在岳友嶺眼里,都可以用“有趣”來形容。
岳友嶺是個愛動手的天文專業博士后,38歲就頭發花白,但仍有一雙18歲的眼睛,里面寫著理想和激情。他不覺得自己苦,“立下汗馬功勞的是那些年輕人”。
在調試工作中,岳友嶺的角色是站在望遠鏡硬件調試和搜索脈沖星算法的銜接處,負責確保信號準確無誤地從望遠鏡流入到算法中。
現在岳友嶺隔三岔五從北京跑一次貴州,打扮得像個風塵仆仆的背包客。他就屬于那種樂于追求人類終極問題的人。
他可以捺著性子從FAST講到脈沖星講到引力波再講到黑洞,繞一圈再講回FAST,連續講兩個小時,只是一談到自己就支吾不清。你要問他為什么這么喜歡留在FAST孜孜不倦地解決各種“麻煩”,他只能拍著大腿幸福地重復三遍:“我覺得這個事情特別有意思……就是特別有趣!就是……就是……就是你小時候學過的那些事,現在終于可以自己親手做了!”
南仁東和彭勃把自己的人生傾注在FAST上20年,岳友嶺他們也已經干了快10年,在這些“牛人”面前,李志恒覺得自己就像“小螞蟻”一樣微不足道。但他在這項舉世矚目的大工程里,也找到了自己的價值感。
“我們做的其實都是很小、很基本的事情。” FAST團隊里像李志恒一樣做基礎工作的人很多,他覺得,“大家就像螞蟻搬家一樣,舉起塊石頭都不知道是誰出的力,但少了誰也不行。”
宇宙之浩瀚難以想象。可觀測的宇宙中含有1000億個像銀河系這樣的星系,而人類所在的銀河系中含有1000億個像太陽一樣的恒星。可想而知,這些天體發出的電磁波穿越遙遠的時空傳到地球上時已十分微弱。射電天文事業從上世紀60年代發展至今,接收到的電磁波都加在一起轉換成熱量,也燒不熱一杯咖啡。
李志恒覺得,盡管人類的感官沒辦法直接感知宇宙中如此微弱的信號,“卻能憑著自己的一小坨腦花”,想出各種辦法去探知宇宙里發生的事情,“有時候想想,我們也挺偉大的!”
◎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