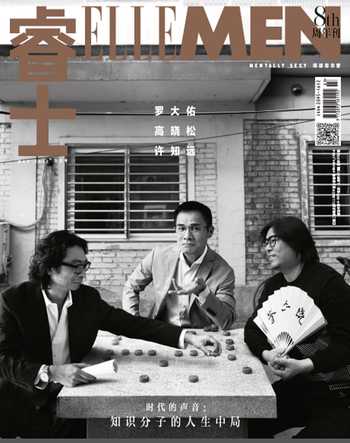尹昉:另一條跑道上的人
錫兵絲






“你的問題是什么?”采訪的過程中,尹昉反問了三次。他語速很慢,有時候話斷了就陷入長久的沉默,你忍不住要切入時,他又接著講了下去。那些空白的時間間隙里似乎包含了許多辯證的思考過程,倒不是出于周全或是防備,只是一種最大意義上的真誠:他在思考,那種思考從你那兒挑了個頭便成了他自己的事兒。他在和自己對話,最初的問題是什么,沒那么重要。
去年10月到現在,尹昉幾乎都扎在北京懷柔,那是電視劇《新世界》的拍攝地。“(2018年)上半年干的事比較多,比較雜,不是那么能夠沉下來,下半年好一點。”他長久地沉在那個小警察徐天的世界里,幾乎不被任何事情打擾。在徐天身上發生的都是極致的故事,但那個骨子里有勁兒的人選擇用對抗給生活以還擊,“他是個愣頭青,挺不服的。”因為那份“不服”,尹昉瘦了15斤。
在進入演員的職業道路之前,尹昉曾經是一名舞者。途中幾次轉換人生軌道,又最終回到了舞者的身份。有什么難以割舍的成分嗎?他不愿意去想。想做的時候便去做了,不想做的時候就不去做。2017年,已經放棄了跳舞的他去看了一場皮娜·鮑什在華的演出,在那場演出中,他看到了舞蹈的另一種呈現方式,“之前跳芭蕾舞有一個標準和高度在那,但那場表演讓你看到標準和高度的消失,只剩下觸動你的東西。”他覺得皮娜·鮑什只是給了他一個環境,讓他和自己的過往進行了一場交流。他開始期待自己跳舞的方式,便又以舞者的身份回到舞臺。
“我不太逼自己,也不太用堅持這個詞”,如今駛入演戲這條新的軌道,也只是一種“選擇”的可能性。“這里面沒有放棄”,他說,“可能我現階段把時間和精力放在某一件事情上,下一個階段放在另一件事情上。”
從《藍色骨頭》、《紅海行動》到《路過未來》,這些作品能讓你感受到作為演員的尹昉在選擇上的某種“正確性”,以及他在其中的“存在感”。“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有我去做的意義——我會讓這件事情不一樣,或者它讓我不一樣。”對于演戲,他的野心存在于此。這算是目的嗎?不是,他不想標新立異,只是想在那個過程中更多地探索、認識演戲,更加真誠地找到那種“不同”和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把演戲這件事做好——目的停留在這里就足夠了。“要是去追求大家公認的一種成功、一種卓越,我覺得我不行,我沒有想贏的動力。我得按自己的方式來。”于是,他尋找到一種“另辟蹊徑”的成功模式:從那種廣泛的競爭中逃離出來,從那種統一標準的圈子中逃離出來,在向前奔跑的過程中盡量地去面對自己,尋找更符合自己意愿的方向。

尹昉前一陣看了《四個春天》,看到老頭老太太坐在一張桌子上相互發微信,笑到收不住。他覺得老兩口在女兒墳前跳舞的那種平凡特別打動他,但又總覺得那些東西都不屬于他。“我從小就覺得自己不會是一個特別平凡的人”,他不知道是一種什么樣的力量牽引著他,也看不到什么野心的驅動力,就是有一種簡單的直覺——終極的那個目標已經在那了。是什么呢?他不知道,總之那個未知已經成為了他的目的地。對于今后即將發生的一切,他都沒有任何的恐懼,“我的強大在于,我好像可以接受所有的發生”。至于理想的生活,他沒設想過。“如果是計劃好了再走,感覺挺無趣的,好好體會每一分每一秒就行了”。
A:高雅不是一個標準,許多劇場作品或舞蹈作品也可以很日常,落差不在于高雅與通俗,而是角度的一個轉變,只是說用不同的方式去轉變和吸收。
A:我的血液不是那樣的,我是一個慢性的人。沒有辦法讓自己永遠燃燒,永遠向前奔跑。
A:害怕自己畏懼,這也挺矛盾的哈?害怕自己不夠勇敢,而失去了一些更不一樣的可能性。有時候走著走著會被某種安全感所捆綁,回過頭去看,就覺得其實可以再突破一些。
A:在日常狀態下,你的生活隨時隨地在被干預。旅行的時候作為旁觀者,那種狀態會特別透明和敏感。它會讓你覺得生活的瑣碎和無常都是可以看得很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