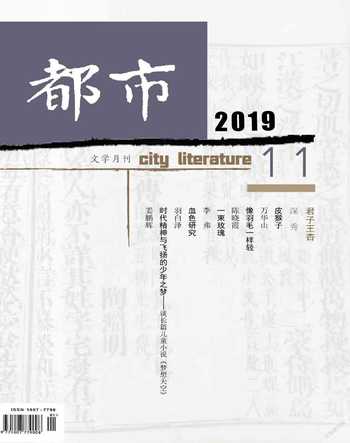夏日微風
劉暉
我拿了成績報告單和作為珠算比賽獎品的兩支“中華牌”鉛筆回到家里,開始過暑假。那時我十歲多一點,長得比同齡孩子高,瘦,不愛說話,經常咳嗽。我的頭發又多又黑,編兩條過肩的麻花辮,辮梢上扎著紅綢結。辮子是我自己扎的,有點毛糙。
我家住在校園的西北角。家里沒人。父親因為恃才傲物被領導發配到鄉下,母親還沒有下班。我打開煤球爐的爐門,拿一根筷子插進鍋里淘好的米中,按照母親預先畫好的記號放上水,開始煮飯。鍋里的水煮開了,白米的清香淡淡地逸出來。我把鍋蓋打開一點,斜放在鍋上,讓水氣蒸發掉一些。然后,我關上爐門,蓋好鍋蓋,把鍋斜放在火上燜飯,隔五分鐘將鍋換一個方向。
米飯的香味暖暖地撲向我的臉。飯煮好了,母親還沒有回來。母親是五年級的班主任,還要負責學校里的文藝宣傳隊,忙得顧不到家。我心里和胃里都空空的,但我已經習慣了等待和饑餓。我把心里和胃里的不舒服當成常態,帶著孩子特有的溫柔和順,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看爸爸給我買的連環畫《小獸醫》和《銀花朵朵開》。這兩本書我不知看過多少遍了,都能將文字背出來。
母親回來了。由于炎熱和疲勞,她臉色泛黃,神情煩躁。豇豆在鍋里燜的時候,她拿起我的成績報告單看。語文100,數學99,體育55。她臉色陰沉得可怕。我知道那個紅筆寫的體育成績讓她很不滿意。她在師范學校時酷愛文體活動,不能接受一個安靜得有點古怪的女兒。她開始按照我們班主任寫在成績報告單上的評語來教育我,至少她自己認為是在教育我。她的聲音平板、嚴厲、生硬,與在課堂上訓學生別無二致,列數我的種種缺點:不合群,不參加文體活動,有驕傲自滿傾向等等。
我低著頭。我又羞愧又煩悶,卻無法躲開羞愧和煩悶,正像我無法躲開母親。如果這算是教育,那么我要說受教育真是世界上最讓孩子們感到痛苦的事。我說不出希望母親怎樣對我,但我意識到我需要的不是這種已在教室里受夠了的冷若冰霜的指責。我想提醒這個正在不停地教訓我的陳老師:“我是您的女兒小慧,您忘了嗎?”
但我什么也沒說。我是一個木訥的孩子,而且從此以后更加木訥。
暑假生活中唯一可盼望的,是父親會送我到鄉下爺爺奶奶家去住一兩個星期。一小時汽車,再走五里路,看到一方清清的池塘時,就到爺爺家了。青磚黑瓦的房子,有著鄉村人家統一的格局:進門是客堂,夯實的泥地陰涼舒適,放著香案和八仙桌,角落里放著一小堆西瓜和幾籮筐新麥。右邊是廚房,放著大灶、水缸、食櫥、柴堆等,左邊是臥房,放著雕刻繁瑣的紅漆花板床,房頂上有一塊玻璃明瓦。姑媽一家住在爺爺家北面,相距不到一里路。姑媽有兩個孩子,老大是女兒,嫁到鎮里去了,兒子胡明在村里的拋光廠上班。
爺爺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他笑著打量我,不停地叫著:“慧慧,慧慧。”他臉上彎彎的笑紋讓我看也看不夠。我笑笑,跑到房子東側的水塘邊去玩。我抓住河邊柳樹的枝條,走到水深沒膝的地方。水波溫柔得讓我暈眩。
爺爺在清涼的早晨帶我翻過草香彌漫的小坡到瓜田里去。濃綠的色彩在仲夏的田野里鋪展。路上碰見人,爺爺就對那人夸我成績好,又懂事。我馬上紅了臉,叫聲伯伯或爺爺,就不再說話。“你孫女真文靜啊。”人們都這樣說。我卻覺得心虛,因為我不相信我是文靜的。我幾乎時時處于不安之中,總是在等待和盼望,卻不知到底等待和盼望什么。
爺爺在田里干活。我坐在用毛竹和稻草搭成的瓜棚里,玩爺爺的草帽。草帽很舊了,散發著植物和人混合而成的香氣,很特別,很好聞。帽沿周圍用藍土布滾了邊,是我奶奶的手工。
黃昏,奶奶穿著洗舊了的斜襟藍布大褂走在田埂上喚鴨子回家:“伊———呱呱呱呱,伊———呱呱呱呱。”聲音在暮色中像河水一樣波動。
在灑了水的院子里吃完晚飯后,爺爺奶奶繼續坐在小竹椅上閑話家常。我關上吱吱作響的木板門,脫掉花布圓領衫和短褲,跨進大圓木盆里洗澡。吸飽了溫水的毛巾碰到肩膀時,我哆嗦了一下,全身肌肉都緊張起來。我撩了水輕輕拍拍前胸。“拍拍胸,不傷風。”母親撩起水拍在我的胸前背后,一邊說著這奇妙的韻文口訣。那是我很小的時候發生的事。現在,母親碰都不碰我了。
我忽然哭起來。我想變小,讓媽媽抱在懷里。“拍拍背,早點睡。”媽媽小聲說。這聲音是從我自己的身體里面發出來的,在現實生活中我不會再聽到這樣的聲音了。
我才十歲多一點,可我的皮膚饑渴已久。我極其笨拙地撫摸自己的身體。我的皮膚因羞怯而充滿張力,排斥著我的手。然后,我摸到了左耳的傷疤。我一生的記憶就是由這道傷疤開啟的,那時我兩歲半———
電壓不足的白熾燈光線昏黃,看上去沒有溫度。電燈正下方的八仙桌旁,母親抱著我看書,不時同父親說一兩句話。奶奶在一邊做針線。我喜歡這種氣氛,不想離開它,害怕失去它。可是母親讓我去睡覺。我扭動身體表示反抗。母親大聲喝斥我,然后把我猛地一推。在我還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么的時候,只聽見奶奶大叫:“不好了呀,耳朵破掉了呀!”我不認為這聲驚叫同我有什么關系。可是大人們都圍了過來,手忙腳亂地抱著我往外跑。
我被臉朝下摁在醫院的床上。我感到了針從我耳廓的軟骨中一次次穿過的銳痛。我的哭叫聲比我的身體要大上無數倍。大人們緊緊地按住我,不停地說:“還有一針了!還有一針了!”可是我耳朵的感覺知道他們是在騙我。疼痛和被騙,讓我哭得很絕望。我的世界像一把破傘,還沒有撐開就已經崩塌了。
父親把我從醫院抱回家后,我哭不動了,安靜下來。父親輕輕地把我放在床上,蹲在床邊看著我。我知道他眼里的神色叫做沉痛。我覺得我應該安慰他,便說:“爸爸,我朝這邊睡,耳朵就不痛了。”這句話將父親的眼淚引出來了。我看到父親流淚,自己又想哭了。
這時,母親在哪里?她為什么不來看看我?
母親弄傷我,母親不來看我,一定是因為我做了壞事,做了極大的壞事。一個對母親做了壞事的孩子是不可饒恕的,我自己都不應該饒恕自己。
在遠離母親的鄉村,我仍然是一個古怪的女孩,時時感到緊張不安。
鄰村的愛蘭姑娘經常來找我的表哥胡明。胡明大概有二十歲,和我父系家族中所有的人一樣身材高大挺拔,穿著白的確良襯衫,看上去英俊和善。他說:“慧慧,今天到我們家吃飯吧?”他笑嘻嘻的,潔白整齊的牙齒閃閃發光。胡明青春煥發的樣子讓我覺得不安,以至于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只能扭過頭去不理他。其實我很喜歡這位表哥,有時甚至想他要是我的親哥哥就好了。我扭過頭不看他,但我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通過空氣感知到他的一舉一動。
胡明跟愛蘭說笑。這兩個近在眼前的人,兩個好看的年輕人,他們就像大門前的守衛一樣,守著一個我無法進入的世界。孤獨像蕁麻的刺,在我毫無防備的時候讓我刺癢難忍。
他們在房間里坐著說話,我就在客廳里看墻上貼的破舊的《紅燈記》劇照。畫面上濃烈的色彩極不真實,更加映襯出鄉村生活中蘊含的無邊無際的靜默和我無法理解的憂傷。
姑媽坐在門口看小雞在場院里走來走去,不住地嘆氣。我偶爾聽到一句半句:
“我們胡家窮是窮點,可是我家胡明有模有樣,哪里比別人差了?”
我在心里同意姑媽的話。我喜歡看胡明和愛蘭在一起,胡明干干凈凈的樣子同眉清目秀的愛蘭很諧調。他們像是美麗而陌生的花卉,讓人懷疑他們是否真正屬于這個村莊,是否某一天會突然消失。
有時,愛蘭挎著竹籃,帶我去田邊割豬草。羽狀葉片的豬草長得極茂盛,肥厚多汁,發出膩滯的刺激人的氣味。我的手臂纖細無力,好長時間才割下一小把豬草,愛蘭的籃子很快就裝滿了。她坐在田埂上休息,順手采來一種被稱為“麻果”的果實,中間用狗尾巴草一穿,旁邊每個小齒上都插上藍色勿忘我花,就成了一只花籃。她還會采兩根長長的狗尾巴草,在茸毛部分打個結,各自的細莖往對方的結子里一穿,可以拉來拉去。愛蘭說,這是胡琴。
傍晚,一群十來歲的孩子在河里游泳。村里的男孩們全都又黑又瘦,靈活得像泥鰍。雙喜大概十五歲,他和弟弟如意都穿著肥大的短褲。有幾個小點的男孩不穿褲子。我不敢朝他們看,但又無法忽視他們的存在。他們的戲鬧聲伴著水聲沒完沒了地在我耳邊響著,但我認定自己走不進他們的世界。
我想起四五歲時我在這里過夏天,每天看到戲水的孩子光著身子跑來跑去,看到他們身上突出的與我不同的東西。我想我也有的,只是我年紀小,它還沒有長大。幾個月之后,冬天的晚上,我發現自己兩腿間還是沒有長出東西來,終于忍不住問父親母親:“我的小雞雞怎么還沒有長大啊?”笑聲從他們口中爆發出來,刺耳極了。我羞愧難當,就此過早地結束了我的天真歲月。我接受自己是女孩這一現實的一開始就是被嘲弄的,自認欠缺的,低人一等的。
我不跟愛蘭說話是因為我覺得她太美,就像我不跟胡明說話是因為他太英俊。我很少說話是因為我在世上太弱小太孤單。我的心理模式在十歲甚至更早的時候就確定了,那就是我越向往什么就越是避之惟恐不及。
兩個星期后我回到縣城家里,看見門前空地上馬齒莧長得更密集更肥厚,那強大的生命力把人類的空間和氣勢逼得后退。
母親把箱子拿到空地上曬。平時密閉的箱蓋此時開得大大的,讓人感到偷窺的緊張和愉悅。我圍著箱子轉來轉去,想細看里面的東西。我知道母親上師范時用的那只箱子里有很多獎狀、獎章和照片。
母親坐在門口走廊上拆毛衣,右腳擱在左膝上,以此為支撐將毛線一圈圈繞起來。她有些發胖,姿態懶懶的,卻又隨時會暴躁發怒。我在她的視線內不敢隨意行動。
母親大概是對轉來轉去的我感到不耐煩了,說:“小慧,四(1)班教室現在成了夏令營的圖書室,你去看書吧。”
我喜歡看書是因為沒有其他東西可喜歡。我去四(1)班找書看。參加夏令營的同學拿著閱覽卡,給坐在門口的方老師看過之后才可以進去。我沒有卡片,站在走廊上不敢上前,直到方老師看到我。
方老師說:“韓小慧,你是不是來看書的?”
我點點頭,覺得手沒地方放,肩膀上不知壓著什么東西,挺不起來。我小聲說:“我媽媽叫我來的。我沒有卡。”
方老師笑起來。我本能地瞇起眼睛。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明亮的笑容,連胡明哥哥的笑也沒有這么亮。他說:“快進來吧,教師子女還要什么卡呀!”
我從方老師面前經過時,和坐在小板凳上的他差不多高。我頓時覺得自己穿著短裙的腿長得令人尷尬。方老師仍然處于一種覺得挺有趣的心情中,對我笑著,拍拍我的大腿,說:“你真是老實得可愛。”
從來沒有人拍過我的大腿。這是一種全新的、特別的感覺。我并沒有覺得不適,也不害怕,而是莫名其妙地輕快起來。
我把方老師給我的特別的感覺藏在心里,終于不堪重負。在悶熱的白紗布蚊帳里,我半夜驚醒,發現自己在流鼻血。
幽暗的夜色中,血是黑的,又腥又甜,粘得無法擺脫。恐懼使我純凈得一無所思,像祭物靜靜地躺在祭壇上,即將被神悅納。我帶著受傷野獸般的謹慎,到水缸邊舀一杯水,到院子里清洗鼻子。然后,我采幾片菊花腦葉子,揉碎了塞在鼻孔里。
菊花腦葉可以止鼻血,這是方老師在體育課上教我們的。我一時想不起方老師的樣子,只覺得他突然變得無邊無際,充溢了我的內心,覆蓋了我的整個生活。
隔壁母親房間里靜悄悄的。她怕熱,所以夏天睡覺時總是把房門敞著。我溜回床上時看見母親床上的蚊帳被風掀起一角。我驚訝地發現床上沒有人,繼而發現床前也沒有鞋。母親不在床上,她去了哪里?我全身發麻,懷疑自己是在做夢。
第二天早上,母親招呼我吃早飯。泡飯加蘿卜干是世界上最讓我厭惡的食物。母親幾乎不看我,但她的面色比平常柔和一些。我想問她昨晚到哪里去了,但我不敢問。如果她問我為什么在半夜起來,我怎樣回答呢?說我想方老師了嗎?
不管怎樣,母親臉上那一點柔和的神情使我稍稍輕快起來。我大口吞咽著無味的泡飯。
胡明哥哥帶著愛蘭來縣城玩的時候,父親還在鄉下。母親對他們很冷淡。胡明給我看他在照相館里剛拍的照片:三七開的頭發梳得一絲不亂,神情儼然,是個很俏的并且知道自己很俏的青年。他拿著照片左看右看,我卻不敢多看他顧影自憐的樣子。
七八天之后,姑媽托人捎信來,說胡明死了。
父親到鄉下處理喪事。我也想去,可是父親不讓我去。“你一個小姑娘,不知道害怕嗎?死人也是好看的?”他訓斥我。我真的不覺得死人有什么好怕的,況且他不是別人,是我的胡明哥哥。他那么干凈,愛俏,臉白白的,笑嘻嘻的,我不知道他為什么突然會死,他死的時候是什么樣子。
三天后父親回來了。他把身上的六十塊錢留給了姑媽,這讓母親勃然大怒。疲倦和憂傷使父親特別溫和,他不說話,慢條斯理地吃飯。母親罵了一陣,覺得無趣,一摔門出去了。
我慢慢移到父親身邊,小聲問:“爸爸,死是什么?”
父親看著我的目光充滿愛憐,又嚴肅鄭重,像面對一個大人。他說:“死就是一個人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再也不回來了。”父親伸手攏我的鬢發時,我很想倚到他身上,但我端立不動。
“可是爸爸,我沒有忘記胡明哥哥,也不會忘記他,那么對我來說,胡明哥哥不就是沒有離去嗎?這樣也算死了嗎?”
父親說:“小慧,你不要多想。你是個聰明的孩子,但有時想得太多了,所以你不快樂。”
我固執地問:“胡明哥哥為什么會死?”
父親站起來,不耐煩地說:“我叫你別問了。”
晚上,我聽見父親母親在房間里的低語,知道胡明哥哥是自殺身亡,因為愛蘭家里不同意他們的婚事。
胡明和愛蘭,他們是那么美的兩朵花,美得讓人不安,似乎從一開始就不屬于這個世界。愛戀與憂傷,美麗與死亡,它們在我腦中不住地糾纏,也把我和世界焊接在一起。
父親又到鄉下上班去了。學校里的夏令營還沒有結束。
母親晚飯后出去,直到我睡覺的時候還沒有回來。不知什么時候,我被母親叫醒:“小慧,小慧,你睡著了嗎?”
我睜開眼睛,看到母親的頭從蚊帳外面伸進來,好像懸掛在那里一樣,讓我感到陌生和害怕。我說還沒睡著。她說:“你愿意和我一起睡大床嗎?”
我鼻子一酸。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盼著能和母親睡在一起,后來看看沒指望,也就忘了去盼。今天母親一提這事,我便明白我從來沒有放棄過這一盼望。
“小慧,你不愿意的話就算了。”
我急忙說:“我愿意的,媽媽。”
母親的蚊帳里充滿白蘭花和清涼油的味道。黑暗中母親的眼睛亮閃閃的。我從沒見過她像今天這樣美,也從沒像此時一樣覺得她陌生。我不明白我為什么如愿以償躺在她身邊時會有這種陌生和不適的感覺。我的身體和我的心都保留著她給我洗澡時的印象:她撩起熱水拍到我的胸口,說:拍拍胸,不傷風。在哄我睡覺時,她會拍著我的后背說:拍拍背,早點睡。
我閉上眼睛,想躲進耳朵破損之前的嬰兒時期的記憶中。那時的記憶如此稀薄,縹緲如霧。母親突然說:“小慧,你覺得媽媽好嗎?”
我無法回答。我知道我的沉默和遲疑會讓她失望,可我就是無法回答。
“媽媽近來脾氣不好,是有原因的。你才十歲,不會明白一個女人最需要的東西是什么。你爸爸被貶到鄉下,你又這么小,我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這是很苦的。”
我真心真意地說:“媽媽,你讓方老師跟你說話吧。”
媽媽一怔,隨即說:“小慧,方老師很喜歡你,是吧?”
“是。”
“那么,你不要在別人面前提方老師,好嗎?”
“好的。”
我不懂母親的意思,但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她。
方老師到我家來,請我母親和他一起給夏令營的孩子們排練舞蹈。他說我也可以到夏令營里去玩。
方老師給同學們測彈跳力。每個同學拿一支粉筆,站在地上伸直手臂,在黑板上畫一個點,然后原地跳起時再畫一個點,方老師量出兩點間的距離,讓我把他量出的厘米數記下來。
我為自己能幫老師做事而覺得驕傲。有時記錯了,他就站在我身后,抓住我握筆的手改正過來。他幾乎是從后面抱住我。這時,我想象是父親抱著我,但是胡明笑嘻嘻的臉卻又突然飄浮在我眼前。幸好,這樣怪異的時刻只是一瞬間。
清新明麗的上午,母親和方老師一起給孩子們排練舞蹈。音樂教室里,八個男孩和八個女孩在練習跳舞。母親彈琴,方老師教動作。我熟悉那支歌曲,是《萬紫千紅》。方老師穿著紅色的背心式球衣,手臂舉起時看得見腋窩里濃密的汗毛。
休息時,方老師倚在風琴旁邊,母親隨手彈著《康定情歌》。方老師和著樂聲唱起來。他的聲音高亢明亮,好像整個八月的陽光一時間都灑落到教室里了。
中午的校園很亮很靜,蟬聲不絕于耳。家家的大人小孩都在午睡,我卻沒有午睡的習慣。一般情況下我自己洗洗臉,洗洗胳膊,在肘彎里涂上海鷗牌痱子粉,躺在床上望著蚊帳頂,望著窗外綠葉婆娑的刺槐樹,頭腦越來越活躍,自己給自己編一些離奇的、遠遠超出我十歲半生活經驗的故事。午睡時間就是我自言自語的時間,我像那些槐蠶一樣通過纖細的絲把自己吊在半空,隨風搖擺。
不知多少次了,這個片段又突然出現在我的意識中———
村子里的男孩子們從我身邊呼嘯而過。他們赤裸著上身,又黑又瘦,舉止靈活。他們盯著我,很默契地手拉著手橫在路上,擋住我。我往左邊走,他們橫著跳到左邊;我往右邊走,他們又跳到右邊。我恐懼而迷惑,站在路中央。我無法突破這些男孩子織成的網,無助地哭起來。
在正午的明亮中,在積了灰的白紗布蚊帳頂部,這個情節清晰地顯現,但我一直不知道是確有其事還是出于我的幻想。每一次,我的心都會往下沉。我本來就不是活潑的孩子,這樣的情節就更讓我縮回內心。這一情節預示了我對男性世界的態度:崇拜,恐懼,無法進入,無力突破。
我的狂亂活躍的午睡時間是我一個人的秘密,母親是不知道的。這一天的中午,我在恍惚中聽見母親走出家門。我悄悄起身,遠遠跟著她。我看見她走進了音樂教室。
我想琴聲就要響起來了。在這炎熱安靜的中午,琴聲的出現將會是某種儀式的高潮。我站在廁所旁邊的冬青樹下等。沒有琴聲,一直沒有。
我繞到音樂教室后面,趴在窗臺上往里面看。母親坐在風琴前翻一冊《戰地新歌》,彎曲的脖子又白又美。我看到靠墻的長凳上躺著一個人,那個人是方老師。
“小方,你也該成家了。聽說下學期會分來幾個師范生,你自己留意一點,總會有姑娘適合你的。”
方老師不說話。母親的側影凝然不動。
“小方,我不能這樣偷偷摸摸的。老韓他不得志,心里窩火,不理睬我也是暫時的。我雖然苦悶,卻不能對不起他。”
方老師說:“我原來以為你很特別,敢愛敢恨,敢想敢做,現在發現你和別人一樣,和這個小縣城里所有的庸人一樣。你不了解我,而且,你也不了解你自己。”
“你要我怎樣了解你?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有好感,那個女人恰好也需要他,僅此而已。”
方老師坐起來,盯著我母親,眉宇間英氣逼人。他說:“雅芬,我喜歡你不僅僅因為你是一個女人。我喜歡你身上的味道,這讓我想起我媽媽。她死的時候我剛兩歲,我還沒被她抱夠……”
母親扭頭望著方老師。慢慢地,她站起來,走到方老師面前,把他的頭抱在胸前。方老師的雙臂緊緊摟住我母親的腰。母親的手輕輕地、無意識地、有節奏地拍他的后背,像拍一個嬰兒。
我立刻覺得天昏地暗,我在這個中午失去了兩個我愛的人:我的母親和方老師。他們互相擁抱,而我只能偷偷地看著。我失魂落魄地走回家,一路上喃喃叫著:爸爸呀,爸爸呀。
整個校園仍然沉浸在午睡時分的安靜和荒涼之中。這個世界昏過去了。這個世界代替我昏過去了。我寧愿昏過去的是我。為什么我沒有昏過去?為什么我在手術臺上縫耳朵受痛受騙時沒有昏過去?我想把自己丟到太陽底下曝曬,曬成一根干樹枝。我不想要這個孤單的我,因為孤單讓我又敏感又脆弱,沒有人保護我,沒有人遮擋我。我的孤單比裸體更令人羞恥。
開學了。
父親的才華終于得到一位要人的賞識,于是他被調回縣城。
家人團聚,父親的心情好起來。母親的臉色也柔和了,顯得更加漂亮。她在家里喜歡哼唱蘇聯歌曲,走路時腳步富有彈性。對我這樣一個不聲不響、從早到晚心事重重的女兒,她打量著,困惑著,然后扭頭走開,不再理會。我用沉默呼喚母親到我身邊。母親聽不見我的呼喚。那么,我的呼喚是誰聽去了呢?如果世上沒有聽見,就不會有呼喚。
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我把種種復雜難解的感受藏在心靈的角落里,專心學習。后來我上大學,工作,結婚,有了一個成天對著我笑的女兒雪兒。
休產假時我住在母親家里。父親母親都退休了,對著外孫女笑得合不攏嘴。我看見母親有一顆牙掉了。那個黑洞很刺眼,令人傷感。
母親給雪兒洗澡時,撩起溫水輕輕拍在她的胸口。雪兒咯咯地笑起來。母親說:“寶寶乖呀!拍拍胸,不傷風……”
我的眼淚流了下來。我曾經以稚嫩的心靈承受著生活中的種種困惑,現在終于明白我是幸福的。除了認真地、謙恭地接受生活給我的種種安排,我不需要做更多的事。
我的女兒在我母親的撫弄之下笑聲不斷。母親,這個孩子是我身上開出來的花,我通過她那花瓣一樣晶瑩嬌嫩的皮膚感覺到你的愛撫,我生下她來就是為了重新認識和再次感受你對我的愛。我和你,我們彼此相愛,從來,一直,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