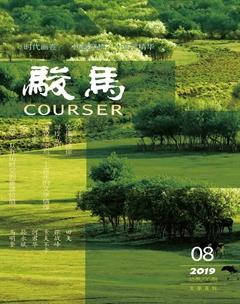簽字
一進門王大爺就對躺在床上的老伴嚷嚷:“二狗子回來了,二狗子回咱這當經理來了。”病懨懨的老伴嗔怪地白了他一眼,不滿地說:“都快60歲人了,還大呼小叫的,和年輕時一樣沒有穩當勁,二狗子,哪個二狗子?”王大爺心里有點埋怨老伴反應慢,“二狗子,就是咱東院的那個趙懷恩呀,小名叫二狗子,他從市里調咱這當公司經理來了。他來了就好了,咱也有靠山了,這回咱兒子就有調回來的希望了。二狗子是吃我媽咱家老太太奶長大的,說起來也算是一奶同胞了”,王大爺絮絮叨叨說著。一聽兒子能調回來,寶貝孫子也就有人照顧了,王大媽高興地直抹眼淚。
說起來兩家是有淵源的,以前兩家住東西院,王大爺和趙懷恩都是同一年出生,只是王大爺比趙經理早出生幾個月,也就當哥了。那時趙經理的母親奶水不足,把個孩子餓得哇哇哭叫,恰好王大爺母親奶水足,就兩個一起奶,一個孩子吃奶沒有問題,兩個孩子都吃,就有困難了。有時兩個孩子把她咂痛得直皺眉頭,只好就讓他先吃,說大的讓小的,把趙經理的母親感動得眼淚漣漣,非讓孩子認王大爺的母親干媽不可,并且為了感激王大爺母親奶育之恩,還給孩子取名趙懷恩,意思是懷念恩情,記住這段恩情,又為好養活,另給孩子起個小名叫二狗子。所以說王大爺和趙經理是一奶同胞是有道理的。
兩人同歲,一起讀完小學、初中,后來王大爺接了父親的班進了工廠,二狗子讀了大學分到市里上班,兩人生活軌道完全不同。直到十多年前,王大爺的母親去世,二狗子才回來一次,兩人也沒說多少話,只感覺生活情況不同,共同語言也不多,以后兩家聯系就越來越少了。
和大多數工人生活經歷類似,王大爺辦了內退兒子接了班,只是公司的廠子越發的不景氣,工資低不說,有時幾個月開不出工資來。廠子又因活源不足,一部分工人被安排到外地承包工程,王大爺的兒子也在其中去了外地。
生活就這樣不咸不淡地過著,天有不測風云,一場大病,王大爺的老伴的命雖然保住了,卻致終生癱瘓,需要人照顧。沒幾年,兒媳婦又因車禍撇下唯一的孩子去世了,這幾件事把王大爺快壓垮了。
老伴生活離不開人,孫子上學需要照顧飲食起居,把個王大爺忙得團團轉。這還好說,不料想這孩子迷上電子游戲,經常不上課,偷跑到網吧打游戲,成績直線下滑。班主任找王大爺談了好幾次,警告說,如果再這樣下去,就讓轉學另找學校。王大爺急壞了,找到孫子,一狠心一個耳光扇過去,那孩子眼睛里噙著淚轉身跑了,王大爺心軟了,喃喃地說:“沒媽的孩子可憐呀。”王大爺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束手無策,只想著把兒子工作調回來,好好管一下孩子,要不孩子一輩子就廢了。
第二天,王大爺匆匆吃完早飯就來到公司總部大樓,還沒進大門,就被保安攔住了,保安問他找誰,有約嗎?必須得先登記,王大爺急了:“我找二狗我兄弟,你們的趙經理,用約嗎?還得登記。”兩人正吵著,辦公室主任正好經過,問清了情況,讓王大爺進了大樓。王大爺在經理辦公室外徘徊了半天,才鼓起勇氣推開了經理辦公室的門。一進門,王大爺就喊“二狗”,一想不對,忙改口趙經理。趙經理愣了一下,從老板桌后轉過來,握了一下手讓王大爺坐。王大爺半個屁股坐在沙發上,把家里的特殊情況和來意說了,趙經理沉默了半晌說,“公司困難,家家都有難唱的經,你去公司勞資部找張主任吧。”說完,在王大爺的申請書上龍飛鳳舞簽上了“同意”和自己的大名,王大爺興沖沖離開了公司大樓,自己好久沒這么高興了。
王大爺沒回家,直接去了公司勞資部,張主任一聽和趙經理這么近的關系,連忙讓到沙發上,接過王大爺申請書一看,臉色微微一變,熱情也打折了,對王大爺說,“調動的事,還得研究研究”,讓他回家聽信。王大爺心想,調動也不差這一天兩天了,二狗子簽字了,他們不敢不辦,就高興地答應著回去了。
一個月過去了,也沒等到信,王大爺坐不住了,又找了兩次張主任,張主任還是讓等等,再后來,張主任避而不見了。一趟趟跑也沒辦成,王大爺火上大了,有個內部人士悄悄告訴他,申請書上趙經理是橫著簽“同意”的,橫著簽意思是“可以擱著不辦”,要是豎著簽就辦成了,豎著簽是“一辦到底”呀。
王大爺一聽恍然大悟,這領導簽字太有奧妙了,大有玄機啊。
【作者簡介】劉慶光,呼倫貝爾人。在《駿馬》《鄂溫克文學》《呼倫貝爾日報》等報刊發表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