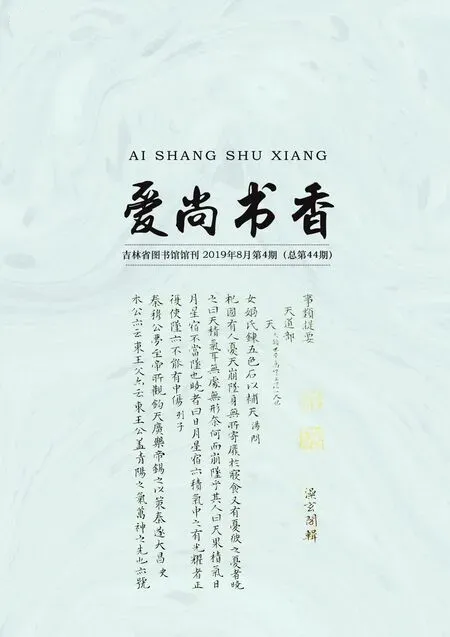文壇藝苑舊行跡(五則)
聶鑫森
“二髯”敦煌過中秋
民國時的名流中,被譽為美髯公的有兩位:于右任、張大千。他們長髯飄飄,風神俊秀,聲名遠播。
于右任既為當時的政要,又是詩人、書法家,而張大千更是書畫界的大腕。同時,他們對敦煌文化的保護、宣傳和弘揚,功不可沒。乙未年盛夏,我與株洲友人同訪敦煌莫高窟,所見所聞,深感人類文化瑰寶的存留和傳承,是一個極為艱辛和卓越的過程,令人肅然起敬 。
“二髯”曾在1941年10月5日,農歷為中秋節,相會于敦煌莫高窟,把酒臨風,吟詩賞月,并商談敦煌石窟的保護,成為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張大千在《敦煌石窟記》中寫道:“我于三十四年(1941年)二月前往敦煌,于去年(1943年)冬十二月始返成都,去敦煌勾留了兩年又七個月,作長時期之研究,并收敦煌現存之北魏及隋唐壁畫,率門人子侄及番僧數輩,擇優臨摹,依其尺度色彩不加絲毫己意逐一臨撫,得畫一百二十余幅……”隨行人員中,既有他的夫人楊宛君、次子張心智,還有門人(學生)及畫界友人的學生。所謂“番僧數輩”,是指張大千結識的幾位藏族喇嘛畫師。
那時的敦煌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氣候嚴峻,生活條件艱苦。張大千自籌資金、自置設備、自理生活,對敦煌文化進行一些搶救性的保護工作,殊為不易。在為莫高窟編號記錄時,“先生見下層小洞多為流沙埋沒,為完整考察起見,先生遂出資請人掏沙,或自己挖個小洞鉆進去考察、記錄”。(張永翹《張大千全傳》)
張大千說他臨摹壁畫百余幅,是不準確的,他的兒子張心智在所寫《張大千敦煌行》中稱:“臨摹將近三百幅壁畫(最大幅達幾十平方米),全都是在絲綢和布匹上畫的,所著的顏色,多是石青、石綠、朱砂等礦物質顏料。”
1941年中秋節,“先生老友、民國政府監察院長于右任在甘寧青監察使高一涵等甘肅省軍政官員的陪同下,在視察河西時,專程來到敦煌莫高窟與先生相聚。先生十分欣喜,一直陪同參觀莫高窟并為詳細講解”。(《張大千全傳》)下午亦然。當時的張大千四十三歲,于右任六十三歲。
當晚,張大千請于右任、高一涵等人,到他上寺寓所晚餐,親自下廚掌勺。然后,飲酒賞月,相談甚歡。“席間大家談到莫高窟的價值和保護問題。”(姜德治《敦煌史話》)于右任激情滿懷,作詩記其事:“敦煌文物散全球,畫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殘龕同贊賞,莫高窟下作中秋。”他在詩后加注:“莫高窟所在地為唐時莫高鄉,因以得名。是日在窟前張大千寓作中秋,同到者高一涵、馬云章、衛聚賢、曹漢章、孫宗慰、張庚由、張石軒、張公亮、任子宜、李祥麟、王會文、南景星、張心智等。”
張大千還向于右任稟報他對石窟的考察過程,介紹許多珍貴文物被外國文化強盜斯坦因、伯希和等偷盜、破壞,令國人痛心。于右任沉吟良久,又作詩:“斯氏伯氏去多時,東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學已名天下,中國學人知不知?”
“同時,先生又將自己前不久在敦煌拾到的唐時張君義斷手及告身拿出給眾人傳觀,見者莫不感慨。于右任又有詩記之。”
我翻閱家藏的《張大千詩詞集》兩大本,這一晚他確實沒作詩。他只想通過于右任向政府及社會各界進言和大力宣傳,對莫高窟及榆林窟等古跡進行有成效的保護和研究。同時,張大千還提出建立敦煌藝術學院的設想,于右任頗感興趣。
高一涵雖是個高官,亦有文人情懷,他作了長詩《敦煌石室歌》:“我來又后四十年,煙熏壁壞損妍鮮……張子(張大千)畫佛本天授,神妙直追吳道玄。請君放出大手筆,盡收神采入毫顛……”
夜深人靜,皓月當空。“席后,先生與右任等當晚為隨行者互相作畫寫字至深夜。”(《張大千全傳》)這就是先賢的雅集和書畫筆會。
張大千這一夜雖未作詩,但在敦煌期間卻留詩多首見于他的詩詞集。如《題莫高窟仿古圖》:“燕塔榆林一葦航,更傳星火到敦煌。平生低首閻丞相(唐代大畫家閻立本),刮眼莊嚴此道場。”
八年抗戰中的齊白石
丹青巨擘齊白石,生于1863年。他于五十五歲時避亂北京,兩年后在此定居,直到1957年辭世。1937年7月7日,日寇發動“盧溝橋事變”,齊白石當時七十有五。從北京淪陷至抗戰勝利的八年中,他雖年老力衰,仍在多災多難的煎熬下,保持一腔愛國熱情和崇高的民族氣節,決不媚敵、事敵,至今尤為人稱道。
這八年中,齊白石的家庭屢遭不幸。1937年春,他的一個女孩齊良尾病死。1940年2月,他的結發妻子陳春君在故鄉湘潭逝世;同年12月,他的兒子齊良年因病而亡。1943年12月,繼室胡寶珠病故。因敵特騷擾,物價飛漲,這個人口眾多的家庭,生計艱難,但齊白石頑強地活著,如松柏歲寒而不凋。
《白石老人自述》一書中,寫到“七?七事變”的情景:“后半夜,日本軍閥在北平廣安門外盧溝橋地方,發動了大規模的戰事”;“第二天……果然聽到西邊嘭嘭嘭的好幾回巨大的聲音,乃是日軍轟炸了西苑。接著南苑又炸了,情勢十分緊張”;“到了七月二十八日,即陰歷六月二十一日,北平天津相繼都淪陷了。”他說:“那時所受的刺激,簡直是無法形容。我下定決心,從此閉門家居,不與外界接觸。藝術學院和京華美術專科學校的教課,都辭去不干了。”
齊白石維持家計的主要經濟來源,是靠畫畫、賣畫、刻印所得。因他的名聲很大,便常有日偽官長和手下的人前來買畫、索畫和表示親近,他便貼出告白云:“齊白石老人心病復作,停止會客。……便又補寫:‘若關作畫刻印,可由南紙店接辦。’”(《齊白石年譜長編》)1940年春節后,“為躲避騷擾,又在大門加貼‘畫不賣與官家,竅恐不祥’告白,云:‘中外官長要買白石之畫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知,恕不接見。’”(同上)
在《白石老人自述》中,他說:“我還聲明:‘絕止減畫價,絕止吃飯館,絕止照相。’……我是想用這種方法,拒絕他們來麻煩的。還有給敵人當翻譯的,常來訛詐,有的要畫,有的要錢,有的欺騙,有的硬索,我在墻上,貼了告白:‘與外人翻譯者,恕不酬謝,求諸君莫介紹,吾亦苦難報答也。’”
1941年5月的一天,忽有幾個日本憲兵來到齊家。看門人尹春如攔阻不住,他們直闖進來。齊白石從容鎮靜,“我坐在正中間的藤椅子上,一聲不響,看他們究竟要干些什么,他們問我話,我裝得好像一點兒都聽不見,他們近我身,我只裝沒有看見,他們嘰里吐嚕,說了一些我聽不懂的話,也就沒精打采地走了”。
1943年,齊白石八十三歲。“因不堪官兵騷擾,這年起閉門作畫,拒售,并在大門張貼‘停止賣畫’告白。從此無論是南紙店經手,或是朋友介紹,一概謝絕不畫。”(《齊白石年譜長編》)
北京淪陷后,北平藝術學院改為藝術專科學校,由日本人任顧問,并配有日本教員,一切權利歸日方。曾邀請齊白石主持該校,被他拒絕。1944年夏,學校給齊白石配送燒煤,6月7日,他在答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信中說:“頃接藝術專科學校通知條,言配給門頭溝煤事,白石非貴校教職員,貴校之通知誤矣。先生可查明作罷論為是。”
齊白石既是書畫、金石家,也是詩人。在這漫長、黑暗的歲月里,目睹日寇橫行,金甌殘破,國恨家仇時刻縈系于懷,便借詩文畫印予以傾吐。
他為學生李苦禪所畫鸕鶿圖題跋:“此食魚鳥也,不食五谷鸕鶿之類。有時河涸江干,或有餓死者,漁人以肉飼其餓,餓者不食。故舊有諺云:鸕鶿不食鸕鶿肉。”以此諷刺做日寇幫兇的漢奸走狗。
他畫群鼠圖,題詩為:“群鼠群鼠,何多如許!何鬧如許!既嚙我果,又剝我黍。燭炧燈殘天欲曙,年冬已換五更鼓。”畫蟹題款曰:“處處草泥鄉,行到何方好;去年見君多,今年見君少。”鼠和蟹都是指代日本侵略者,他堅信天將曉、敵必敗。
他在為友人所畫的山水卷上,題了一首七絕:“對君斯冊感當年,撞破金甌國可憐,燈下再三揮淚看,中華無此整山川。”
經過中國人民浴血八年抗戰,1945年,“到了八月十四日,傳來莫大的喜訊,抗戰勝利,日軍無條件投降。我聽了,胸中一口悶氣,長長地松了出來,心里頭頓時覺得舒暢多了。”10月10日,友人來齊家看望八十五歲的白石老人。“留他們在家小酌,我做了一首七言律詩,結聯云:‘莫道長年亦多難,太平看到眼中來。’”(《白石老人自述》)
這年的12月28日,徐悲鴻與沈尹默共同發表《齊白石畫展啟事》,稱:“白石先生以嵌崎磊落之才,從事繪事,今年八十五歲矣。丹青歲壽,同其永年。北平陷敵八載,未嘗作一畫、治一印,力拒敵偽教授之聘,高風亮節,誠足為儒林生光。”這是對齊白石抗戰八年期間,為人為藝的最高評價!
特殊年代的賞花會
2002年,葉至善、俞潤民、陳煦所編《暮年上娛:葉圣陶、俞平伯通信集》,由花山文藝出版社付梓面世。該書收錄俞平伯與葉圣陶二老于1974年到1985年之間的來往書信,涉及內容十分寬泛:國運家事、典籍字畫、詩詞唱和、學問切磋,其文人風骨、情懷、意趣歷歷如在眼前,為研究二老的重要資料。特別是1974年至1976年,正處在“文革”的晚期,二老的生存境遇十分艱難,但他們依舊營造出一種傳統文化的古典氛圍,護衛心中的一塊凈土,活得從容且率真,令人感佩。
以賞花邀飲雅集為例。他們(還有其他老友)多次以賞花名義相召而聚,親自然,敘友情,唱和詩詞。“事情的起源是因為葉圣陶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樹。‘文革’后期開始,每年海棠花盛開的時候葉圣陶總會邀請俞平伯、王伯祥、顧頡剛、章元善共同賞花,這一聚會被他們戲稱為‘五老賞花會’。”(鮑良兵《“暗淡歲月”中的文化傳統——以〈暮年上娛——葉圣陶、俞平伯通信集〉為中心》)
1975年4月4日,葉圣陶致俞平伯信中寫道:“奉遐來敝寓小敘,或在十二日或在十九日,看海棠如何而定。定即以電話奉告。且將約元善兄共敘。”而俞之回信稱:“……前歲四月十九日,五老會于敝廬;去歲四月十九日,賢喬梓臨況。今年十九,有興再為一敘乎?”從書信上查對,五老賞花于這年的4月19日舉辦,俞平伯在信中稱為:“逃學飲酒,良可笑也。”
俞平伯生于1900年,辭世于1990年,系詩人、作家、紅學家。在1974年至1976年,他的年紀為七十四至七十六歲。他與葉圣陶的訂交,始于1918年,青年時代共同創辦《詩》月刊,組織“樸社”;合編文學刊物《我們的七月》《我們的六月》;合出新詩合集《雪朝》、散文集《劍鞘》……可謂情深義重。到1966年5月16日“文革”風暴驟起,俞平伯被抄家、批判,1969年下放干校勞動鍛煉,1971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照下,提前從干校回到北京。葉圣陶則在1966年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長之職,此后一直在家中閑居。
“1967年,我剛到北京時,聽文研所沙予說,俞先生被趕出老君堂原宅,搬入跨院北房內,頗有戀舊之情,有詩云,‘先人書室我移家,憔悴新來改鬢華。屋角斜暉應是舊,隔墻猶見馬櫻花。’”(林東海《大家風范——記俞平伯先生》)被迫遷家的磨難中,俞平伯仍能感受到馬櫻花的詩意氤氳。
養花、賞花,自古以來就是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花為他們的生活增添盎然情趣,也是一種精神的高雅寄托。新中國成立后,這種文人的情懷與趣味,往往被視為另類,遭人白眼,但這種文人傳統卻依舊頑強地傳承著。
章詒和在《往事并不如煙》一書中,專設一篇《最后的貴族——康同璧母女印象》。康同璧(1883—1969年),為康有為的二女兒,新中國成立后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康老住在東四十條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里”,院子里一株“御賜太平花”,是當年光緒皇帝賞賜給康有為的。“所以,每年花開時節,我(指康同璧)都要叫儀鳳(同璧之女)制備茶點,在這里賞花。來聚會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因章詒和之父母章伯鈞夫婦,偶訪而逢此盛會,“羅儀鳳把張之洞、張勛、林則徐的后人,以及愛新覺羅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紹給我的父母。園中一片舊日風景。顯然,這是一個有著固定成員與特殊意義的聚會。在康同璧安排的寬裕悠然的環境里,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成為對歷史的重溫與懷念。主客談話的內容是詩……”
何謂太平花?它為虎耳草科。落葉灌木。葉對生,長橢圓形,邊緣有稀疏小齒,基出三大脈,兩面常無毛。夏季開花,總狀花序,萼光滑,花瓣四枚,白色。產于我國北部和中部,栽培供欣賞。(《辭海》)
太平花并非什么稀罕珍奇的花,但它是光緒皇帝賜給康有為的,并植之于家院。作為康之后人,康同璧自然對此花有一種特殊情感,此花既是一段往昔歲月的記憶坐標,又是對父親的一種懷念,所以開花時,會邀約一些與其父有關系的名人后裔前來賞花宴飲。章詒和說:“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對前朝舊友的涵容熱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義’為先——老人恪守這個信條自屬于舊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時,社會流行的是‘階級、階級斗爭’學說,貫徹的是‘政治掛帥’的思想路線。”
粉碎“四人幫”,所謂“文革”壽終正寢。在當今,不僅是文人騷客,一般平民百姓對于養花、賞花亦興致勃勃。正如宋人楊萬里《南國賞花》所稱:“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花好多。”
田漢與聶耳
每當我們唱起莊嚴、雄壯的《國歌》,崇高的愛國熱情就會油然而生。它的詞曲作者田漢、聶耳,雖早已離我們而去,但他們弘揚民族精神、壯我國魂的赤子衷腸,至今令人感懷不已。
由著名音樂家賀綠汀口述、李華鈺整理的《我同聶耳最后相處的日子》一文,稱:“1933年秋至1935年春,我在上海音專繼續從黃自教授學作曲。當時正值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后,日寇鐵蹄橫行上海,國難家仇,激勵著我參加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動,青年作曲家聶耳和戲劇家田漢,亦在此為救亡運動效力。我曾看過聶耳參加演出并作曲的《揚子江暴風雨》,深感他那些富于時代精神和戰斗氣息的歌曲,給苦難的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的鼓舞和教育。”
田漢(1898-1968年),湖南長沙人,為戲劇活動家、戲劇家、詩人,“1930年前后參加民權保障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并任執行委員)和左翼戲劇家聯盟,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辭海》)
聶耳(1912-1935年),云南玉溪人,為現代作曲家,于1930年至上海,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左翼音樂、戲劇、電影等工作,從事創作及藝術評論活動”。(《辭海》)田漢年長聶耳十四歲,他們既是肝膽相照的戰友、同志,又是才情并茂的文朋詩友。
《國歌》原名《義勇軍進行曲》,田漢所作歌詞的雛形,“是田漢1934年5月創作的《揚子江暴風雨》主題歌《前進歌》:‘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把強盜們都趕盡!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向著自由的路前進!’同年冬,田漢又為上海地下黨創辦的電通公司寫了一個電影劇本《風云兒女》,他在一張香煙盒包裝紙的背面寫下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作為這部影片的主題曲……后來,夏衍完成了分鏡頭劇片,交給聶耳譜曲”。(陳漱渝《田漢的命運》)
著名作家、報人曾敏之,為田漢好友。他說田漢一生寫過六十三部話劇、十二部電影劇本、二十七部戲劇劇本、新詩舊體詩兩千多首、七百多篇文章,此外還有翻譯作品、書信等,總計一千萬字左右。“在三十年代與聶耳、冼星海、張曙合作創作了許多歌曲,其中如《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廣泛流傳,成為鼓舞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號角,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浩歌聲里請長纓——記田漢》)
參與《風云兒女》音樂創作的,有賀綠汀、聶耳。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則由聶耳作曲,賀綠汀說此曲:“以慷慨雄壯的旋律,堅定勇敢的進行節奏,鼓舞人民團結抗戰,它唱出了時代的聲音、人們的吼聲。不久,聶耳懷著提高音樂文化素養、提高音樂創作的心情,經日本去蘇聯學習和考察。他走后,我只好去找阿甫夏洛穆夫配樂隊伴奏,這樣,這首歌曲通過影片和唱片,沖破了黑暗社會的阻力,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號角。”(《我同聶耳最后相處的日子》)
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水逝世。當時的田漢,作為左翼運動的領導人,因叛徒出賣被捕后受盡磨難,剛剛出獄不久。聞此噩耗,極為悲痛地寫下《哀聶耳》一詩:“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幾吞聲。高歌正待驚天地,小別何期隔死生。鄉國只今淪巨浸,邊疆次第壞長城。英魂應化狂濤返,重為吾民訴不平。”
聶耳二十三歲辭世,為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嘆息。而田漢這樣一位對革命做出過重要貢獻、才華橫溢的文化巨擘,卻在“文革”中被“四人幫”迫害致死!
數年前,我曾訪云南昆明,到西山拜謁聶耳之墓。墓碑為郭沫若題字,碑文鐫刻田漢、聶耳合作詞曲《義勇軍進行曲》的影塵前事,讀之使人銘記先賢的豐功偉績。他們與《國歌》同在,將傳之千秋萬代!
高長虹這個人
由蕭乾主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的《新筆記大觀》中,收入姚青苗的《我與高長虹同住一孔窯洞》一文。文中說:“我初會高長虹是在1941年秋天,當時我在閻錫山的妹夫梁綖武主持的二戰區黨政委員會掛了一個名,住在資料室。……高到來時,身著一套蹩腳的西裝,手提一只皮包,沒帶行李,風塵仆仆。”總務處安排高長虹與姚青苗同住一孔窯洞,每夜面對一盞暗淡的油燈,兩人作長談。高長虹“對春秋史興趣濃厚,時作讜論。還記得他幾次談到由歐洲回國途經香港時見到茅盾的情形,他把應茅盾之請所寫的幾篇論文的剪樣拿出來給我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那篇記述他與許廣平交往經過的記錄。”
在魯迅的日記、書信、文章中,關于高長虹也有多處記載。高長虹與魯迅的關系,在新文學史上,頗讓人注目。
“這個僅有小學畢業證書的山西盂縣舊書香之家子弟,1924年二十二歲時只身闖入北京,實行他的文學‘狂飆運動’,以所辦的《狂飆周刊》獲得魯迅的青睞,遂結為盟友,共建‘莽原社’。”(張放《孤獨的“狂飆”高長虹》)當時的魯迅很欣賞高長虹的才華,稱“他很能做文章”(《兩地書?一七》),曾全力提攜他,還熬夜為他編校書稿。魯迅一般不參與“語絲諸子”等文人們飲宴,卻愿意同高長虹等文學青年聚餐,如魯迅1925年4月11日的日記,寫到他們“共飲,大醉”。
高長虹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又受尼采作品影響,自信到狂傲的地步。當他漸成氣候,就表現出難與魯迅和平共處的姿儀,或在編輯事務上與魯迅意見相左,或主觀臆想產生誤會。還有一個隱潛的原因,是高長虹暗戀許廣平而不得。“魯迅結識許廣平時,長虹與許廣平也有過‘八九次’通信聯系討論文學,然而誰也不知道他正對許患著單相思,當魯許明朗化后,長虹即多少轉入一種陰暗的報復心理。”(見張放文)陳漱渝在《高長虹的家世及其與魯迅交往的始末》一文中,對此亦有詳細的記敘。高長虹在詩《給——》及一些隨筆中,對魯迅進行含沙射影或露骨地攻擊,如:“月兒我交給他了,我交給夜去消受。”(《給——》)“我對于魯迅先生曾獻過最大的讓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走出出版界》)
對于高長虹的胡攪蠻纏,魯迅不能保持沉默了,于是進行有力地反擊。對于高長虹所稱的“月兒”“交給”“夜”的關系,寫出《新時代的放債法》一文,給予辛辣的譏諷與尖刻的駁斥,令高長虹在圈內圈外無地自容,不得不敗北而隱匿。以后,他漂泊海外,窮困潦倒;到抗戰時方回國,在1941年后去了延安。
高長虹對魯迅的不恭和誤解,其錯在自身,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在更高層面上說,他于抗戰時回國,并去革命圣地延安,表明他對時局具有明晰的評斷。姚青苗在文中稱:“高長虹的皮包里還裝著一篇他寫的《為什么我們的抗戰還未勝利》的草稿,直言不諱地揭露和指斥國民黨當權派的腐敗墮落與后方社會的混亂、黑暗。”此文還被油印了七八十份,散發給一些“進步同志傳閱”,同時引起了敵人的注意。“但此文并非出自共產黨人之手,而是無政府主義者高長虹的手筆,他們也無可奈何,只好視而不見。”
1941年底,高長虹由向導領路,徒步去了延安。經有關方面考察,“給了他一個陜甘寧邊區文協副主任的職務,還在魯藝兼課。他在延安住了大約五年。1946年隨軍奔赴東北解放區。1949年病逝撫順,剛屆知天命之年。”(姚青苗文)姚說的病逝沒有說明是患什么病,張放文中則說高長虹的思想、性情,與革命隊伍的格調、氛圍難以“完全合拍”,“故此生活郁郁寡歡,神智漸出問題,據說四十年代末病故于東北解放區一所精神病院。”
在張麗婕所編的《民國范兒》一書中,有《高長虹》一文,稱高長虹生于1898年,卒于1954年。“《太原日報》有文章說,找到了當年在沈陽東北大旅舍招待科負責照料和管理高長虹的當職員工崔遠清、閻振琦、李慶祥三位老同志,他們共同回憶……1954年春季的一天早上,二樓服務員向招待所報告,高長虹房間沒開門,人們都以為他在睡覺。到了上午九點許,閻振琦見門還未開,趕忙跳到二樓外雨搭上,登高往內眺望,才大吃一驚地發現老人趴在床邊地板上。閻設法打開房門,才得知老人已經死亡。……經檢查確認高長虹夜里系突發性腦出血死亡。”此文還說:“高長虹生活很儉樸,享受著供給制縣團級干部待遇,吃中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