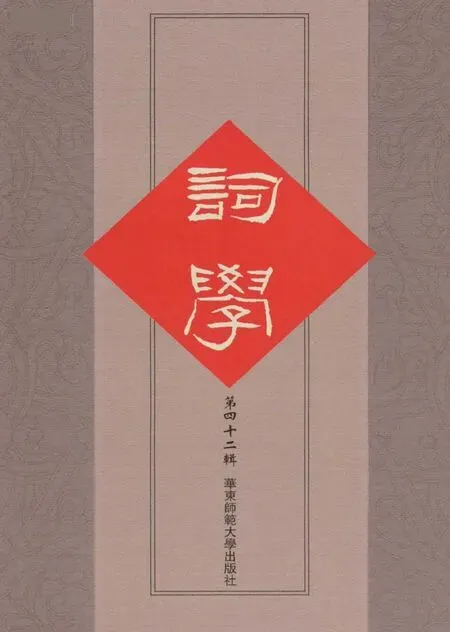《花間集》二言句的功用、體式及指向
劉 學
內容提要 數量過百的二言詞句,在《花間集》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豐富功用,包括押韻、延聲、引起、過渡、意象與情緒書寫等,形成了單頭二言、雙頭二言、隨韻二言等功用體式,並進一步指向了兩宋時期換頭二言功用體式的主流。二言詞句作爲詞調音樂的一個顯性表徵,其功能呈現、發展與部分消亡,也從一個角度指示了詞體演進的路向。從該角度去窺探《花間集》在詞體演進中的意義,也應具有合理性。
關鍵詞 花間集 二言句 功用 體式 隨韻
二言句在詞體研究中未受重視,主流句式如三言、五言、七言等都有專論,〔一〕而二言句式的專門研究尚未見到。王力《漢語詩律學》認爲二言句在詞中頗不多見,〔二〕故所論甚簡;馮勝利的漢語韻律句法學幾乎未涉及韻文中的二言句。〔三〕詞學領域、詩學領域以及音樂學領域可供藉鑒的研究也不太多。
其實,唐宋詞共有二言句約二千五百句,〔四〕雖然規模數量遠不及主流的句式,並非微乎其微。二言句作爲詞體最古老的句式之一,其功用隨著唐宋詞體的演進而發生演化,在詞體構成與體式演變方面的意義不容忽視。因此,本文從二言句的角度對詞體演進的里程碑《花間集》及其體式方面的意義展開考察與探討。
一 二言詞句的源流
二言詞句的源起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然而與《花間集》相關的背景值得關注:一是比《花間集》更早的《雲謡集》尚未出現二言句;二是二言句在《花間集》同時期的詩歌中已經式微,卻在詞體中獲得了生命力。結合相關背景,以下試從源與流兩方面對二言詞句進行探討。
(一)二言詞句的源起
一詩歌來源
二言句的源頭可追溯至最早的詩歌體式二言詩,由於遠古時單純的思維,簡單的語法結構,歌唱中常有泛聲語助詞,再加上人的先天二節拍節奏感,詩歌都是二言形式。〔五〕皇帝時的《彈歌》、《呂氏春秋·音初》所載娀氏《燕歌》、《周易》中的一些早期歌謡,均爲二言詩。劉勰將二言詩的發端斷於《彈歌》。〔六〕此後,二言句疊加成爲四言句。隨著語彙、語法趨於豐富與複雜,曲調趨於多變,詩歌中的一言句、三言句也産生了。〔七〕隨著四言詩的興起,二言詩便逐漸消亡了,因此二言詩並不能對二言詞句的形成産生直接的影響,而二言詩形成的語言基礎和韻律特點,以及得以保留的二言詩句則與二言詞句的關繫更近。
二言詩消亡之後,二言句散見於樂府詩、唐代古體詩、聲詩等詩體中,不僅數量少,達意的功用也比較弱,如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的二言句就很少,且多「嗚呼」、「嗟嗟」等虛詞。〔八〕儘管如此,這些詩體應是詞體二言句的近源,至少對於詞體二言句有所啟發。
從形式上看,樂府詩和雜言古體詩的二言句與《花間集》的二言句頗爲相似,多居詩首、詩中,間有疊用。如這首唐元和初童謡:
打麥,麥打。三三三,舞了也。〔九〕
其與早期的轉應詞有著形似,其中二言句疊韻、頂針、轉應等用法,也見於早期的轉應詞,如唐代戴叔倫的《轉應詞》。同一時期形式相似的音樂文學樣式,雖難以判定其體式形成之先後,彼此之間的影響與生發是一定存在的。
樂府詩和雜言古體詩爲二言詞句提供了主要的形式與用法參照,而以近體詩爲主體的聲詩則在適應演唱的痕跡上提供了參考,例如和聲辭和疊句均被任中敏先生當作判定詩作可歌的依據,〔一〇〕即聲詩演唱痕跡的留存。《花間集》所收皇甫松的《採蓮子》和孫光憲的《竹枝》均保留了此種痕跡——和聲辭「舉棹」、「年少」、「竹枝」、「女兒」。這些和聲辭爲詞外之辭,有規律地間於詞中或隨於詞後,在同一調中有固定位置,以聲爲主,自有其聲,諧韻且兼備聲義,與唐聲詩的和聲辭沒有區別。〔一一〕雖然這些附加之辭不屬於詞正文,也未計入本文的二言句,但詞調與聲詩的諸多相似與相通之處由此可見。唐聲詩的疊句是演唱中的詞句疊唱,常被傳寫者刪去。〔一二〕如《渭城曲》之「三疊」,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文獻的記載纔能略窺其貌。與之相參,可以討論文人詞筆下的二言疊句是否爲疊唱的文字形態。
儘管外在的形似無法掩蓋根本的差異,詞中二言句在與聲樂結合及適應演唱方面應受到樂府、聲詩等音樂文學的影響。詞體二言句式的産生是以前代二言詩句爲積累、配合音樂的要求、又與同時期其他音樂文學樣式相互生發的結果。
二語言基礎
音步就是由音節組成的語言節奏單位,二言句包含兩個音節,構成了漢語的一個音步,即雙音節音步,這是二言詞句形成的語言基礎。根據馮勝利的漢語韻律學研究,漢語雙音步大約發源於春秋戰國時期,在東漢時期由於四聲俱備而確立了音步的雙音節結構,〔一三〕然而此時二言詩已經消亡。隨著各具特色的詩歌句式不斷發展,二言句式在詩歌中日益式微,其何以在詞體中獲得生命力?
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二言句實現了最基本的韻律詞,而且雙音節詞是真正的「標準音步」,相對單音節詞、三音節詞而言,具有穩定性與優先實現權。四言以上的句子則是音步的疊加。〔一四〕由於二言句作爲標準音步具有承擔韻律功能的優秀能力,可以很好地通過韻律去呼應與表現音樂,因此被樂曲形式豐富多樣的詞體所吸納。而長短句的詞體形式又爲二言句在適應音樂的同時、聯合其他句式以彌補表意能力的不足提供了條件。《花間集》二言句的字聲組合有四種情況: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其數量依次爲:六十四、九、十七、十二句。〔一五〕「平仄」爲其主要字聲形式,或許與唐宋樂一重一輕的搏拊拍有關繫。〔一六〕因此,二言句在詞體中的大量出現,正是二言句基於其韻律特點,密切配合詞調音樂的産物。
三詞人的有意創造
田玉琪《談詞的句中韻》一文認爲二言獨韻的形成與詞的音樂節拍密切相關,以其爲演唱中之「大頓」。〔一七〕這是對於本文上一部分的支持。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爲二言短韻除了樂曲的豐富與變化所致,還應考慮文人的自覺創造。
由於二言句押韻的功能非常突出,因此詞人添加小韻而形成二言句的情況也較多,通過同調詞的句式比較可以察之。例如溫庭筠的《訴衷情》起始有兩個二言句「鶯語。花舞。春晝午。」〔一八〕而在《花間集》其他詞人筆下,該調起句均爲七言句,如韋莊詞爲「碧沼紅芳煙雨靜」,〔一九〕顧夐詞爲「永夜拋人何處去」,〔二〇〕溫詞當添加了兩個句中韻而形成了二言、二言、三言數個短句。同一詞人對於同一詞調的句式也有所選擇,如孫光憲《上行杯》數首,相同位置或用三言句「帆影滅」,或用二言句「沾泣」,〔二一〕可見同樣配合樂曲,填詞所要考慮的押韻與文字也會影響到句式的使用。二言句式在《花間集》、《尊前集》的文人詞中獲得很大的發展,當有這方面的因素。
(二)唐宋詞二言句的流變
檢視《全唐五代詞》〔二二〕和《全宋詞》(含補輯)〔二三〕,總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六首詞作含有二言句,根據總體特徵與新變,二言句在唐宋詞的流變大致可分爲四個時期:
其一是《花間集》收録之前的時期。〔二四〕此時二言句處於發軔階段,風格樸拙,類型簡單。該階段僅有十六首含有二言句的詞,其中五首敦煌詞,〔二五〕其餘則是中晚唐知名詩人韋應物、白居易、杜牧等五人的作品。該階段的二言詞句明顯帶有與樂府、聲詩相似的特徵,《調笑》轉應詞和《宴桃源》(如夢令)的疊句説明其可歌性。總體而言,該時期的二言句數量少,體式未穩,全部位於詞首或詞中,但在同一詞調中的具體位置與用法常常發生變化。這也充分説明,詞中二言句並非直接繼承自詩體,而是受到詩中二言句的影響、經由詞體自身生發和展開的結果。
其二是以《花間集》爲代表的唐末五代時期,二言句作者有十二人,相關詞作共計七十一首,不僅囊括了上一個階段二言句的所有使用類型,而且發展出新的功用,奠定了後世二言詞句繼續新變的基礎。具體而言,承前一個時期,詞調中二言句平均數量較多,疊韻較多,鞏固了二言句押隨韻的形式,還出現了唯一一首以二言句換頭的詞——歐陽炯的《更漏子》。
該時期的二言句在數量上並不能與兩宋詞比肩,但在二言句演進過程中卻是關鍵的一環。在這個環節中,《花間集》所録之詞構成了作品主體,其所收詞人則構成了作者主體,僅劉瞻、李存勖和馮延巳不屬該集。當然,花間詞人的二言句創作也溢出了《花間集》的範圍,少數作品見於《尊前集》及其他文獻,因此探討二言句體式的演進也要參考花間詞人的這些「溢出」之作。
其三是北宋時期,共有二言句詞四百一十九首,詞人共計七十四人。該時期最大的特點是二言句換頭功用的發展與普及,用於換頭的二言句將近半數。同時,二言句進一步鞏固了《花間集》以來的用法,《調笑》、《如夢令》等最早的含二言句的詞調仍然被填寫,其中蘇轍的《調嘯詞》(調笑令)還發展出五個二言句的罕見體式。蘇軾是二言句的偏好者,共留下了四十三首含二言句的詞。還有晁補之、黃庭堅、秦觀、賀鑄等詞人大力創制二言句,同蘇軾一起鞏固了二言句的押韻、疊韻、隨韻等用法。
其四是南宋時期,含二言句詞創作數量大增,多達一千一百八十首,二言句近一千六百句。二言句換頭的體式繼續推進,用法也更加精微,而北宋令體樂曲的失傳導致令體詞調有所萎縮,除了少數南宋詞人的新創,含二言句的令體詞調幾乎只有《南鄉子》、《如夢令》、《定風波》等幾個仍然活躍,這説明二言句有其應運而生的音樂條件。當然,慢體詞調格律化使得二言句在文字格式中得以保存,獲得了繼續流傳的可能。
在上述流變中,《花間集》正處於由二言詞句功能原型生成向體式普及與深入發展的關鍵點上。
二 《花間集》二言句的類型與功用
那麼,二言句在《花間集》中究竟有哪些類型,具有怎樣的功用呢?本部分將展開具體考察。
(一)類型列示
據楊景龍《花間集校注》,《花間集》共有一百零二個二言句,分佈於五十一首詞作,〔二六〕約占全集詞的十分之一,集中於《河傳》、《荷葉杯》、《風流子》、《訴衷情》、《上行杯》等幾個詞調。這些二言句全部位於詞首與詞的中間位置,沒有在詞尾的。其作者九人,爲《花間集》所收詞人的半數。以下將列表展示具體情形:

《花間集》中的二言句及其功用體式〔二七〕

續表

續表
(二)功用分析
《花間集》中不同類型的二言句,發揮的功用也有差異,歸納起來,主要有韻律、結構和書寫三方面的功用。
一押韻、延聲
在韻律方面,二言句的主要功用是押韻與延長聲音,其中以押韻功能最直接、顯著。《花間集》全部一百零二個二言句,僅二句未押韻。〔二八〕其押韻比例不僅高於五、六、七言長句,也高於同爲短句的三言句。很大程度上,二言句就是爲押韻而生成,從而增大了韻腳的密度,調節了詞調的節奏。
二言句押韻方式豐富多樣,普通方式是與前後句同韻部,強化了全詞的主體韻部,形成聲韻的重復,增強韻律感,上表中未標功用體式的十一首詞都屬於此類。但二言句最具特色的押韻方式卻是押隨韻,即僅與前句同韻部,而與後句不同韻部,如韋莊《訴衷情》:
燭燼香殘簾未卷,夢初驚。花欲謝。深夜。月朧明。何處按歌聲。輕輕。舞衣塵暗生。負春情。〔二九〕詞中「深夜」僅隨前句「花欲謝」押韻,而區別於後句「月朧明」,即屬於隨韻。因此,「深夜」和「花欲謝」兩句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單元,嵌在該詞的主體韻部之中。「輕輕」一句,與前、後句的韻部都一致,則屬於普通押韻,而不屬於隨韻。
隨韻的二言句實際上成爲了一個轉韻的信號,促成「抱韻」的形成。如上詞的「花欲謝。深夜」爲前後的三言句「夢初驚」、「月朧明」所抱。二言句的存在使得詞中隨韻、交韻、抱韻、疊韻等更易獲得實現,詞調的聲情、節奏也得以調節。
三言句式也常押韻,並且多見本句換韻、從而形成新韻段的形式,卻沒有押隨韻的形式。從上表不難見出,隨韻的應用在《花間集》中已成規模,並成爲了一種二言句的基本體式,爲後世所追隨。
此外,二言句往往帶來聲音的延長,詞文的頓與韻對應音樂上的敦,「表示其爲句中的延長者,或延長爲兩字、三字之長」。〔三〇〕不押韻的二言句,也具有延聲功用,不過所延長的拍值有所不同。《花間集》二言句僅兩例不押韻,張泌《河傳》之「渺莽,雲水」〔三一〕;顧夐《河傳》之「燕颺,晴景」〔三二〕,不僅押韻的二言句延長聲音,逗號前不押韻的二言句也要拖長唱腔。因此,二言句的聲律意義是非常突出的。
二引起、過渡
在結構方面,二言句的功能在於關聯上下詞句,位於詞首的二言句引起下句,位於詞中的二言句則承上啟下。需要説明的是二言句的引起與過渡功能兼具文意與韻律兩方面的結構意義。
詞首的二言單句對下句的引起,如溫庭筠《思帝鄉》的首句爲「花花」,以疊韻形式喚起下句「滿枝紅似霞」在押韻與文意上與之相配合。〔三三〕詞首連用兩個二言句,則以第一句引起第二句,如孫光憲《河傳》以「花落」引起「煙薄」,〔三四〕聲律一致,結構一致。前文所引張泌《河傳》的「渺莽,雲水」,「渺莽」在語意上不具有獨立性,引起後面的「雲水」幫助完足語意,兩句共同完成第一個意象單元「雲水渺莽」。
詞中的二言句主要功用則在於過渡。在八十一個居於詞中的二言句中,包括緊鄰詞首二言句的十七個,如果它們僅僅是普通押韻,那麼其過渡功用僅體現於詞意方面;如果它們是隨韻,則兼具聲律與詞意的雙重過渡作用。以溫庭筠的《荷葉杯》爲例:
一點露珠凝冷。波影。滿池塘。緑莖紅豔兩相亂。腸斷。水風涼。〔三五〕
從聲律來看,「波影」隨前句韻,具有音韻上的順承接續關繫,而又區別於後句韻,與後句具有音韻上的轉換關繫。從詞意來看,「波影」另開一個意象,於前句是並列之中有變化;而「波影」實爲後句「滿池塘」之主語,於後句又是順承關係。二言句「腸斷」同樣押隨韻,具有音韻與文意的雙重結構意義。
由於二言句雙重的上下勾連,更加嚴密了詞調的結構。溫庭筠數首《荷葉杯》中二言句的用法如出一轍,結合其使用習慣,可以更準確地把握其詞意。例如其《荷葉杯》之一:
鏡水夜來秋月。如雪。採蓮時。小娘紅粉對寒浪。惆悵。正相思。〔三六〕
對於其中「如雪」,常見理解是秋月如雪,即將「如雪」與前句「鏡水夜來秋月」進行語意的關聯。楊注《花間集》也列示此種解釋:「如雪:鏡水月華皎潔如霜雪」。〔三七〕如果我們熟悉溫庭筠筆下該調二言句的隨韻用法,解讀時就應當把「如雪」與後文「採蓮時」相關聯,即「如雪」是對「採蓮」的主體——後文所謂「小娘」的描繪。梳理全詞的描寫,「秋月」實已由「鏡水」來描寫修飾,再加以「如雪」,殆無此累贅之筆。與之相對應,「小娘」由「如雪」來形容描寫,又與後文「紅粉」相呼應,當是更爲合理。實際上,該句是從李白《越女詞》化出:「鏡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三八〕因此,詞中二言句「如雪」在語意上是關聯後句無疑。將二言句的功用納入考慮,或有助於辨析詞文的歧義。
由於二言句的順承和轉變作用,使得音韻結構更爲錯落有致。如單調《荷葉杯》共六個詞句,竟換韻兩次。其中第一、二句互押,第四、五句互押,而第三、六句互押,形成了以第三、六句環抱第四、五句的「抱韻」結構,靈動而精巧。
同時,二言句的順承與轉變作用也令詞作的文字結構嚴密而不失生動。回到上文《荷葉杯》(鏡水夜來秋月)詞,「如雪」是視點的第一次轉換,由水月轉到小娘;「惆悵」是第二次轉換,由敘述者的視點轉爲人物視點,由外在描摹轉爲內心描寫。短短一首小令,由景及人,由外而內,層層深入,描寫抒情堪稱搖曳生姿。而對於這樣的詞美呈現,兩個二言句功不可沒。
當然,同樣承擔過渡功能,二言句在詞意上關合前句,或是在關聯前後句上無所謂偏重的情況也是存在的,由韋莊《荷葉杯》(絶代佳人難再得)、〔三九〕顧夐《荷葉杯》(夜久歌聲怨咽)〔四〇〕等詞可以見之。
三意象、情緒書寫
一個雙音節詞構成的句子,自然在書寫上較爲局限。詞的二言句不具備句子的形式,而需要擁有句子的內涵,故其書寫在兩個方面進行拓展:其一是增加書寫的密度與概括力;其二是以組句聯合完成書寫。
組句是詞中短句的常見形式,可是二言句對於組句的依賴和對於其他句式的借助卻較少。例如三言詞句的形式大多數爲組句,《花間集》中含三言句的詞作共計二百八十八首,以兩句或三句連用的三言組句爲常見,達到一百八十六首,而最多的情況是兩句連用的組句、僅第二句押韻,有一百五十八首。〔四一〕除了同一句式的連用、疊用,三言句還常與五、六、七言句搭配成組,共同完成書寫。相比之下,《花間集》中二言句連用的幾率較低,含有二言句的詞作五十一首,僅有十九首存在連用,二言組句最多兩句連用,且幾乎各句均押韻,在韻律與文意上相對獨立,例如「棹舉。舟去。」「無語。無緒。」〔四二〕皆如此。此外,二言單句與其他句式的配合也相對較少,同樣,在獨立押韻的前提下,《花間集》中與前後三、四、五、六、七言句配合使用的二言句大約有三十句,常常用於二言句表達疑問、祈使和否定等語氣時,如「何處」、「知否」、「須勸」、「莫知」、「不歸」等。相對而言,二言單句與三、五、七言句的搭配更多一些,〔四三〕而與四、六言句的配合極少。不同於三言句,二言句以組句形式對書寫空間的拓展有限。
《花間集》的二言句在書寫方面最大的特點卻是高度概括,以濃縮至句子核心的方式展開書寫。蔡宗齊先生提出了一個令體詞的「題評」結構,包括主體意象(題語)和針對主體意象展開的描寫與評論(評語)。〔四四〕其書寫特點也適用於二言句,相比同爲短句的三言句、四言句,殆可成語的二言句做了最大限度的結構省略與修辭簡化,即便如此,《花間集》中的二言句仍具有語意自足的特點,出色地完成了主體意象的呈現和對主體意象的描寫與評價。
主體意象的呈現,或者説意象式書寫是二言句主要的書寫功能,一百零二句中有六十二句屬於此類,通常以偏正結構的名詞和主謂結構的動詞來實現,偏正結構如「宮錦」、「紅杏」、「曲檻」、「雙鳳」等,偏於靜態描摹;主謂結構如「鶯語」、「舟去」、「風颭」、「眉斂」等,偏於動態描寫,帶有敘事性。在中國抒情詩留白與跳躍的書寫傳統之下,二言句獨立呈現意象,且語意基本完足。
對於意象的描寫與評論,二言句主要通過動詞與形容詞來實現,如以「佇立」、「沾泣」、「孤眠」、「相喚」等詞來描繪動態;以「依依」、「迢迢」、「腸斷」、「寥亮」等詞來形容狀態與程度,表達情緒。此類書寫有點染與總結情感的作用,因而以「評語」概括之也是合理的。
二言句將一個標準音步的表意功能做了高效的發揮,其書寫效果可以與三言句略作比較。一方面,由於三言句對於句組有較大的依賴,單個句子的書寫效能並不如二言句,如同樣用於開頭的組句: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溫庭筠《更漏子》)〔四五〕鶯語。花舞。春晝午。(溫庭筠《訴衷情》)〔四六〕湖上。閑望。雨蕭蕭。(溫庭筠《河傳》)〔四七〕第一首的三言組句寫成對偶結構,偏於靜態描摹。第二首的二言組句,結構與聲韻一致,偏於動態描寫,表現力更強。第三首的二言組句卻是結構各異,首句書寫環境,次句描寫人物,兩句之間形成層次,其中第二句押隨韻,又增加了變化,因而比前兩組內容更爲豐富,可興發的空間也更大。
再從同調詞使用的不同句式來比較其書寫效果:
雙臉。小鳳戰篦金颭豔。舞衣無力風斂。藕絲秋色染。(溫庭筠《歸國遙》)〔四八〕金翡翠。爲我南飛傳我意。罨畫橋邊春水。幾年花下醉。(韋莊《歸國遙》)〔四九〕同一詞調,溫詞以二言句開頭,韋詞則選擇三言句,表達效果難分伯仲。細味之下,二言句的書寫自然不如三言句舒展,無法從容使用「翡翠」這樣的連綿詞,略少一點婉轉之度,但也更具概括力,語意更爲自足,興發之力絲毫不遜。
依據漢語韻律句法學理論,韻律可以影響甚至控制句法的構造。〔五〇〕一定程度上,二言句的形成及其書寫受到韻律的影響與制約。前文的押韻、過渡等功能無疑根源於詞樂的要求,然而二言句的書寫功能卻體現了詞人創作的自主性。隨著二言詞句體式化,二言句的書寫功能趨於弱化,而《花間集》所奠定的押韻、過渡功能獲得進一步發揚。值得留意的還有二言句詞尾位置的缺失。三言句常用作詞調收尾,或是一個韻段的收束,唐宋詞中的二言句卻幾乎不作結句,也與《花間集》所奠定的二言句功用特點有關。
三 《花間集》二言句的功用體式及指向
基於上述功用,再結合二言句在詞中的位置,《花間集》的二言句主要形成與完備了單頭二言、雙頭二言和隨韻二言等體式,孕育並指向了換頭二言體式的主流方向。
(一)功用體式
一單頭二言
單頭二言體式指單個二言句在詞首發揮引起功用的體式。該體最早見於《花間集》的四首詞作,《歸國謡》和《思帝鄉》兩個詞調。〔五一〕兩調均爲唐教坊曲,而首見於溫庭筠詞,均以意象引起全詞。孫光憲《思帝鄉》的體式與溫詞相同,以疑問句進一步發揮了二言句詞首的引起功能:「如何。遣情情更多。」〔五二〕「如何」不具備詞意獨立性,須結合下句共同表意,其主要功用在於韻律與詞意的引起。
單頭二言體式在北宋前期詞人,尤其柳永之筆下多有呈現,如《甘草子》、《河傳》,而且柳永將單頭體應用到近、慢體詞,如《過澗歇近》、《郭郎兒近拍》、《洞仙歌》、《木蘭花慢》、《浪淘沙慢》等調。大約從北宋中期開始,直到南宋末,該體式幾乎僅見於《調笑》令,一縷僅存,作品數量卻也不少。《調笑令》在北宋鄭僅、秦觀、晁補之、毛滂等許多詞人的作品中已變成了單頭二言體式,並流傳於南宋。由於《調笑》令與轉踏表演相結合,又汲取了地方戲曲元素,寄身於該調的單頭體二言句獲得較廣泛、長久的流傳。而對於單頭二言體,《花間集》的創體、存體之功不可忽視。
二雙頭二言
兩個二言句並置詞首,形成雙頭二言體式,作爲一個共同單元引起全詞,其中第二句又往往承上啟下。該體式肇始于唐代《調笑》令,而《花間集》中有該體詞作十六首,集中於《訴衷情》與《河傳》兩個詞調。其與唐《調笑》的不同之處在於,《調笑》是疊句形式,兩個二言句相重復,通常同第三句押韻,或是全詞幾乎一韻到底,而《花間集》中的雙頭二言體式,除了一首閻選詞,兩句並不相疊,押韻的情況也複雜很多。少數雙頭二言體第一句不押韻,第二句又有隨韻與不隨韻的類型,不隨韻與唐體相似;隨韻則是對唐體的發展。
《花間集》雙頭二言體對唐代疊句形式的突破,代表了雙頭二言體式在詞文學創作中的實際確立。唐代《調笑》令的二言疊句形式,體現了樂曲的重復,也可能與前文所提聲詩的疊唱表演相類似,總之主要目的在於音樂上的修飾,而《花間集》中的雙頭二言體式在創作上已經有了許多的文字講究與細膩的文學表現。因此,雖然雙頭二言體式非發端於《花間集》,卻由《花間集》獲得了文學體式上的確立。
《花間集》雙頭二言體式首句不押韻和第二句隨韻的方式,均通過體式的確立,進一步強調了雙頭二言句作爲詞首第一個韻律與抒情單元的內在有機結構與相對獨立性,如溫庭筠《河傳》上片:
同伴。相喚。杏花稀。夢裏每愁依違。仙客一去燕已飛。不歸。淚痕空滿衣。〔五三〕雙頭二言句在音韻與詞意上都自成單元。音韻方面,「同伴」與「相喚」二句相互押韻,第二句「相喚」押隨韻,下句「杏花稀」開始換韻,轉入上片的主體韻部,因此詞首二句獨立於主體韻部之外。詞意方面,「同伴」與「相喚」二句有機連結,作爲該詞第一個意象單元,內容已經自足。隨後「杏花稀」一句雖與前句有所關涉,畢竟是新開一個意象單元,視點有所轉變。因此,首二句在詞意上也有相對獨立性。雙頭二言體式如此精妙的結構是從《花間集》才開始出現的。
柳永同樣繼承了《花間集》的雙頭二言體式,其《河傳》、《臨江仙引》皆隨花間樣式。蘇軾雖然繼承了唐《調笑》二言體,又隨《花間集》之二言體創制了雙頭二言不疊句的《醉翁操》,並且得到郭祥正、樓鑰、辛棄疾等詞人的效仿。辛棄疾也「效花間集」雙頭二言體而填寫了一首《唐河傳》。〔五四〕
或許與唐五代詞調音樂的失傳有關,雙頭二言體式在兩宋漸漸式微。儘管如此,《花間集》所反映的其時該體式的盛況,以及流傳于兩宋的情況對於詞體演進的考察頗具價值。
三隨韻二言
前文在「押韻」和「過渡」部分已對《花間集》的隨韻二言體式做了分析,是位於詞中的二言句僅隨前句押韻、後句換韻的體式,體現了二言句的過渡功能。敦煌曲子有三首《定風波》令已經初具隨韻二言體,〔五五〕此後便是《花間集》對該體式進行了充分的發揮,該體式見於《花間集》的二十四首詞,在幾種基本體式中爲最多。
兩宋《定風波》令是隨韻二言體的經典詞調,而花間詞人李珣有五首《定風波》傳世,因此通過《定風波》令的體式演變,也可推及《花間集》對於隨韻二言體式的豐富與完備。
敦煌曲子的《定風波》體式並未定型,或含一個二言句,或含兩個二言句,只能説已具後來《定風波》令隨韻二言體式的雛形。隨著《花間集》時代二言句隨韻功能的發展與鞏固,李珣筆下標準的《定風波》令隨韻二言體出現:
志在煙霞慕隱淪。功成歸看五湖春。一葉舟中吟復醉。雲水。此時方認自由身。花島爲鄰鷗作侶。深處。經年不見市朝人。已得希夷微妙旨。潛喜。荷衣蕙帶絶纖塵。〔五六〕該詞有三個二言句,皆隨前面的七言句而押韻,是隨韻二言體的集中體現。李珣另有四首《定風波》,歐陽炯、閻選、孫光憲各有一首《定風波》,〔五七〕與此體式一致,形成了該調穩固的隨韻二言體式。該調由此前一個、兩個二言句,發展爲三個二言句,至此達到二言句與七言句的最佳配置,成爲了該調在兩宋流傳最廣的一種體式。北宋留下的四十三首《定風波》令,僅有兩首未效該體。
《花間集》雖未收録該調,但對於隨韻二言體有相當充分的展現,足以結合李珣、歐陽炯等詞人的《定風波》一同完備誕生於唐代的二言隨韻體式。《花間集》指示了隨韻二言體式的廣闊前景,偏好隨韻二言體式的蘇軾,其所作九首《定風波》皆隨五代體,進一步固化了該體式,得到許多詞人的追隨。
然而,兩宋詞調的換韻不再如《花間集》那麼頻繁,往往是一韻到底或是分片押韻,隨韻二言體式在其他詞調上就非常少見了。
以上是《花間集》對於二言句基本功用體式的奠定,還有一些二言句的使用形式,因數量極少,如疊句,或是包含於基本體式之中,如疊字,故不做歸納。
(二)體式指向
二言句在《花間集》之後又發展出新的體式——換頭二言體,即二言句位於第二片的開頭,用於詞調的換頭。〔五八〕該體式接替隨韻二言體成爲二言體式的主流。然而,《花間集》所奠定的隨韻二言體式孕育了換頭二言體並指示了二言句體式發展方向。
首先,《花間集》對於換頭二言體的孕育主要表現爲二言句過渡功能的奠定。隨韻二言體具有上下勾連的作用,聲韻與語意的雙重關照,尤其是音韻上關前而語意上關後的常見形式,都爲換頭二言體的基本功能做了鋪墊。只不過不同於隨韻二言體處於詞中的位置,主要起到關聯前後句的作用;換頭二言體處在一個特殊的位置上,承擔著連結上下片的作用,關乎整首詞的結構。故換頭二言與隨韻二言的功能形式有點相似,是基於隨韻二言體式在《花間集》的成熟而形成的重要體式。
其次,花間詞人的創作發出了二言換頭體式的預報。花間詞人歐陽炯,也是《花間集序》的作者留下一首《更漏子》,是已知最早的二言句出現在換頭位置的詞作:
玉闌干,金甃井。月照碧梧桐影。獨自個,立多時。露華濃濕衣。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樣。雖叵耐,又尋思。怎生瞋得伊。〔五九〕二言句「一向」在詞中承擔了換頭功能。與後世慢體詞的二言換頭不同,此爲令體詞,而且歐陽炯的其他《更漏子》詞並未依此體,也未得到後世詞人的仿效,沒有形成該調定式,其意義卻在於預示了即將到來的二言句功用體式的新變。
二言換頭現象經歷了《花間集》時期的偶發狀態之後,在北宋開始規模化發展,共有一百八十三首詞以二言句換頭,除了其中一兩調是令體,如蘇軾《皂羅特髻》,都出現在慢體詞中,可見二言句換頭功能的普遍應用,是隨著慢詞體式的推進與普及而形成的,這也可以解釋爲何《花間集》中沒有換頭二言體式。目前所知最早將二言句換頭應用於慢體詞調並推而廣之的是柳永,留下二十六首以二言句換頭的慢體詞作。北宋也湧現了一批以二言句換頭的高頻詞調,如《滿庭芳》、《喜遷鶯》、《玉蝴蝶》、《木蘭花慢》等,絶大部分換頭的二言句押韻。
南宋時隨著慢體詞調的大盛,二言換頭體式進一步發展,成爲了其時二言句最主要的功用體式。南宋共有八百二十八首詞以二言句換頭,占該時期含二言句詞總量的百分之七十。還可注意到,北宋時一首詞中可有二言句數個,分佈於詞首、詞中、換頭等不同位置,承擔多種功能,而南宋時期一首慢體詞往往僅保留一個二言句,單純地用於換頭。二言句的功用趨於集中、純粹,二言句的應用也越來越體式化。
《花間集》所指示的二言句體式方向,便在於強調其音樂表現,突出其結構功能,換頭二言體因此獲得普遍應用。過片是南宋詞家非常重視的環節,所謂制曲「最是過片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六〇〕這是對換頭在音樂與文字兩個方面的要求。爲什麼換頭會青睞二言句式?根源於音樂上的變化:換頭樂曲的下片會增加兩拍,這增加的兩拍常常就以詞樂上片結束最後兩拍稍做變化(豔拍)而成,置於下片開頭,即換頭。因而換頭重復的只是上片結束的最後兩拍。〔六一〕雙音節音步特點令二言句在拍值與節奏上都比其他句式更易於配合換頭的音樂變化,更易於實現換頭又合尾的音樂結構,而換頭二言體令換頭文字與樂曲的變化對應更爲清晰。因此詞家會傾向於選擇以二言句換頭,展現純熟的過片技法。姜夔的《徴招》、《角招》、《長亭怨慢》、《喜遷鶯慢》、《念奴嬌》、《暗香》、《霓裳中序第一》等諸調即以二言句換頭,其二言句配合著曲體結構的要求和基本法度,牽合詞的上下片,不粘不脫,過渡流暢,有助於全詞有機結構,前後照應。
相比其他句式的換頭,二言句不具有文意的鋪敘推衍之功用,在樂曲與意脈的連貫之外,不需要做過於複雜的考慮。不難發現,南宋之後二言句的表意功能漸漸弱化,句意虛化,表達程式化,相同位置的二言句重復率高,進一步突顯了二言句的體式意義。
結 語
從二言句式的演進看,《花間集》有奠基和原型意義,二言句的基本功用體式,包括單頭二言、雙頭二言、隨韻二言、換頭二言等,都可在《花間集》尋到原型。雖然《花間集》對於二言句功用體式的建構還不完
備但,代表了晚唐五代時期的詞體發展狀貌並,且指向了詞體的新變。
〔一〕如白朝暉《三言句式在詞中的出現及其詞體意義》,《文學遺産》二〇一〇年第五期;蔡宗齊《小令詞牌和節奏研究——從與近體詩關繫的角度展開》,《文史哲》二〇一五年第三期。
〔二〕參王力《漢語詩律學》,中華書局,二〇一五年,第五九四頁。
〔三〕參馮勝利《漢語韻律語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馮勝利《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四〕據《全唐五代詞》和《全宋詞》(含補輯)統計。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全唐五代詞》,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
〔五〕參趙逵夫《先秦文學編年史·前言》,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年,第八頁。
〔六〕劉勰云:「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謡是也」。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卷七,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五七一頁。
〔七〕參趙逵夫《先秦文學編年史·前言》,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年,第八—九頁。
〔八〕如《襄陵操》:「嗚呼,洪水滔天,下民秋悲,上帝愈諮。」郭茂倩《樂府詩集》,中華書局,二〇一七年,第一一九三頁。《箕子操》:「嗟嗟,紂爲無道殺比干。」《樂府詩集》,第一一九五頁。
〔九〕《樂府詩集》卷八十九,第一八二五頁。
〔一〇〕「唐詞未有已帶和聲辭或疊句而依然不歌者」,見於任中敏《唐聲詩》第二章《構成條件》,《任中敏文集》,鳳凰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五二頁。
〔一一〕參見《唐聲詩》第二章《構成條件》,第六六—七一頁。
〔一二〕參見任中敏《唐聲詩》第二章《構成條件》,《任中敏文集》,鳳凰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七一頁。
〔一三〕參馮勝利《漢語韻律語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六一、八一頁。
〔一四〕參馮勝利《論漢語的韻律詞》,《中國社會科學》一九九六年第一期,第一六一—一六三頁。還有馮勝利《論漢語的「自然音步」》,《中國語文》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一五〕如未特別標明,本文對於《花間集》的統計皆依據楊景龍《花間集校注》而完成,中華書局,二〇一五年。
〔一六〕搏拊拍(豔拍)參《唐宋古譜類説》,劉崇德主編《唐宋樂古譜類存》,黃山書社,二〇一六年,第四頁。
〔一七〕《湛江師範學院學報》二〇〇二年第一期,第一一〇頁。
〔一八〕楊景龍《花間集校注》,中華書局,二〇一五年,第二〇六頁。
〔一九〕《花間集校注》,第四三九頁。
〔二〇〕《花間集校注》,第一〇三九頁。
〔二一〕兩首分別見於《花間集校注》,第一二一一、一二〇八頁。
〔二二〕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全唐五代詞》,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
〔二三〕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
〔二四〕考慮到《花間集》的標誌性意義及其影響,儘管其中也收録了唐詞,但詞體顯然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更成熟的詞體階段,故以此爲界。
〔二五〕作者無考,且繫於此。
〔二六〕已除去含和聲辭的《竹枝》與《採蓮子》四首詞(分別作於孫光憲和皇甫松)。
〔二七〕據楊景龍《花間集校注》,排序則依《全唐五代詞》。表中「功用體式」指二言句因其位置與功用而形成的體式,非整首詞的體式。單頭即單個二言句在詞首;雙頭是兩個二言句並置詞首;隨韻是位於詞中的二言句僅隨前句押韻。體式之間有部分交叉,如「雙頭」體的第二個二言句,兼「隨韻」體,則加括注。
〔二八〕楊景龍《花間集校注》中孫光憲《風流子》詞之「歡罷」標逗號,見《花間集校注》第一一八七頁,誤,應爲韻,全詞一韻到底,皆屬《詞林正韻》第十部韻。
〔二九〕《花間集校注》,第四三七頁。
〔三〇〕《唐宋樂古譜類説》,劉崇德主編《唐宋樂古譜類存》,黃山書社,二〇一六年,第九頁。
〔三一〕《花間集校注》,第六五四頁。
〔三二〕《花間集校注》,第九六一頁。
〔三三〕《花間集校注》,第二〇九頁。
〔三四〕《花間集校注》,第一一一〇頁。
〔三五〕《花間集校注》,第二三六頁。
〔三六〕《花間集校注》,第二三八頁。
〔三七〕《花間集校注》,第二三九頁。
〔三八〕楊注也提及這一點。參見《花間集校注》,第二三九頁。
〔三九〕《花間集校注》,第三六五頁。
〔四〇〕《花間集校注》,第一〇五一頁。
〔四一〕根據楊景龍《花間集校注》統計。
〔四二〕分別出自顧夐《河傳》與孫光憲《風流子》,《花間集校注》,第九六六、一一八五頁。
〔四三〕結合《花間集》的句式和位置來看,最常見的形式是二言單句與前面的七言句相配合,或者聯合後面的三言、五言句,相應二言句數量分別爲七句、八句和六句。
〔四四〕蔡宗齊《小令語言藝術研究:結構與詞境》,《文學評論》二〇一七年第二期,第一九二—一九四頁。
〔四五〕《花間集校注》,第八五頁。
〔四六〕《花間集校注》,第二〇六頁。
〔四七〕《花間集校注》,第二二四頁。
〔四八〕《花間集校注》,第一一三頁。
〔四九〕《花間集校注》,第三五三頁。
〔五〇〕馮勝利《漢語韻律句法學引論(上)》,《學術界》二〇〇〇年第一期,第一〇〇—一〇三頁。
〔五一〕另張泌有一首單頭二言體式的《河傳》孤調,疑詞作脫一句二言句,故不將其計入。參《花間集校注》,第六五七頁。
〔五二〕孫光憲《思帝鄉》,《花間集校注》,第一二〇六頁。
〔五三〕《花間集校注》,第二二八頁。
〔五四〕《全宋詞》,第二四七六頁。
〔五五〕分別見於《全唐五代詞》,第八九三、九二二、九二二頁。
〔五六〕《全唐五代詞》,第六一一頁。
〔五七〕分別見於《全唐五代詞》,第四六四、五七五、六四一頁。
〔五八〕後來也有二言句出現在第三疊開頭的,如《蘭陵王》,也歸入此類。
〔五九〕《全唐五代詞》,第四六三頁。
〔六〇〕參夏承燾《詞源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第一三頁。
〔六一〕呂洪靜《論換頭》,《音樂研究》二〇〇二年第三期,第四〇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