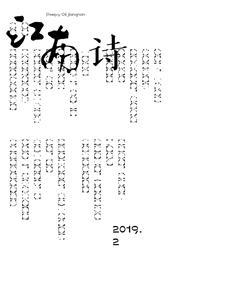蜜炬千枝爛
2019-07-26 01:04:14啞石
江南詩 2019年2期
關鍵詞:人性
在詩中,不是任何力量都能輕易
說出。言語之痛,需要經過
音韻的青色翅膀隱秘地修飾、認同。
譬如,父親去世二十六年了,
幾乎沒夢見他,但最近,
感覺他依然在我身上強烈活動著:
昂著頭,像一輛火車,轟隆,
轟隆地碾壓過鐵軌下潮濕的枕木。
窗外氣氛,模仿他壯年曾遭遇的冰封。
又譬如,人性的泥胎得推進瓷窯,
燒制許久,才能抓住臉的弧形。
美德如花?火焰之手對其精心地捏塑。
一旦形象穩定,我們卻又脆弱,
圣杯,隱匿在瓷器立體的線條之中:
認同啥,你就將開出怎樣音色的喉嚨!
(選自本刊2019年第一期“詩高原”欄目)
蘇野品讀:
這是一首表達言說之難和存在之難的沉郁之詩,又是一首蘊含復雜闡釋可能性的棱鏡之詩。“忠于自我,與詩無達詁,都近于笑話”,“畢竟文字,當它意欲/稱量空中血絲身世,就頗艱難”,啞石這兩句寫于去年的詩,可與此詩互訓互注。前句與“人性的泥胎得推進瓷窯”句群互文,強調意識整肅和權力規訓語境下主體形塑自我獨立性的艱難和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性,更勿論“一旦形象穩定,我們卻又脆弱”;后句表達詩歌言說惡、言說人之苦難的艱難。此詩應該有明確的本事、原型和現實指向性,“最近”“窗外氣氛”以及父親“壯年曾遭遇的冰封”,在歷史、記憶和當下性的維度上都應該生發自具體的爆破點,包含個人的密鑰。“蜜炬千枝爛”為“銀燭輝煌”之意,挪用自李賀《河陽歌》,據姚文燮和王琦注本,結合啞石近期另一詩句“冰封它輝煌它”,詩題飽含濃烈的情欲色彩和對現實文本的反諷之意。
猜你喜歡
雜文月刊(2021年11期)2021-01-07 02:48:01
阿來研究(2020年1期)2020-10-28 08:10:14
攝影與攝像(2020年12期)2020-09-10 07:22:44
文苑(2019年24期)2020-01-06 12:06:58
新產經(2018年3期)2018-12-27 11:14:16
海峽姐妹(2018年4期)2018-05-19 02:12:54
影視與戲劇評論(2016年0期)2016-11-23 05:26:47
工業設計(2016年10期)2016-04-16 02:44:06
人間(2015年17期)2015-12-30 03:41:08
陜西教育·高教版(2015年8期)2015-02-28 15: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