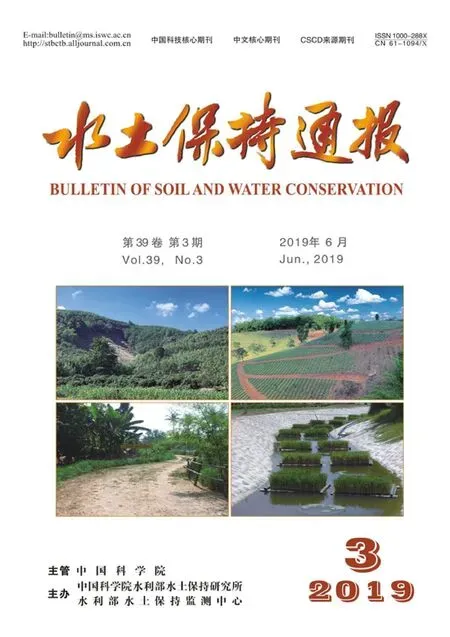基于景觀安全格局理論的壽城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用地評價
張麗芳, 廖 雨, 楊存建, 冉丹陽
(1.四川師范大學 西南土地評價與監測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四川 成都 610068; 2.四川師范大學 地理與資源科學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人類活動是導致土地利用類型發生變化的主要影響因子,對生態用地的安全性也構成一定的威脅。自然保護區作為生物多樣性豐富、生態功能最強、水土涵養能力好、珍稀動植物的天然生存場所。如何協調人類活動用地與自然保護區健康可持續發展是當下面臨的可持續發展的新挑戰[1-2]。
近幾年來對生態安全的保護與關注度一直處于熱點,構建生態安全格局備受中國學者的高度關注,俞孔堅[3]在Forman[4]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景觀安全格局概念,創建識別源地、建立阻力面、構建安全格局的模式。該模式被國內外學者廣泛應用于區域案例的生態安全評價構建,并且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極大的推動了此方法的科學化、成熟化、應用化[5-8]。針對自然保護區的景觀生態安全評價國內也有所研究,胡艷等[9]選取景觀指數,分析了寬闊水自然保護區的景觀格局演變。付夢娣等[10]利用最小累計阻力模型對秦嶺地區的自然保護區進行了網絡構建與優化,確認出秦嶺地區的生態源地面積,對后人規劃與優化保護區提供了參考價值。目前,針對生態安全構建的方法多樣[11],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基于景觀生態安全理論針對自然保護區內的人類活動變化安全與評價的研究較少。
本研究擬以壽城自然保護區2013年0.5 m空間分辨率的有人機航攝影像和2017年2 m空間分辨率的高分一號遙感影像為數據源,采用人機交互式判讀方法提取壽城自然保護區兩期土地利用分類圖層,借助GIS平臺和 Fragstat 4.2軟件,從景觀尺度、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的角度出發,分析壽城自然保護區的景觀空間分布特征,并對不同安全水平下的人類活動用地進行評價與優化。以期為壽城自然保護區的生態功能的最優化、景觀多樣性與人類活動的區域和諧發展而服務,并為壽城自然保護區合理保護生態用地、維護自然保護區安全、維系生物多樣性、合理規劃建設用地提供決策建議。
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壽城省級自然保護區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永福縣北部和臨桂縣西北部,于1982年經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批準建立的,經2017年遙感解譯統計保護區面積范圍為70 139.59 hm2。地理坐標為東經109°38′17″—109°53′36″, 北緯 25°02′16″—25°29′36″,最高海拔1 498 m; 最低海拔179 m,年均溫為17.2 ℃,年平均降水量約為2 500 mm[12]。
保護區內溝壑縱橫,土地利用類型多樣,土地分類標準依據《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遙感監測技術指南(試行)》的通知環辦〔2014〕12號文件,自然保護區土地分類一級分類為耕地、居民點、工礦用地、采石場、能源設施、旅游設施、交通設施、養殖場、道路、其他人工設施(為無法劃分到其余9類的設施用地)等10種一級土地分類,下分41種二級分類,本文按照實際研究需求,按照一級人類活動分類標準并疊加林地、未利用地、河流進行劃分土地利用類型,其中一級分類共計7種,并疊加林地、未利用地、河流3種土地利用類型。
1.2 數據來源
壽城自然保護區2013,2017年土地利用類型研究數據來源于廣西省保護區遙感監測項目。數據基于GIS軟件平臺,采用了2013年0.5 m空間分辨率的有人機航攝影像、2017年2 m空間分辨率的高分一號影像,經過圖像預處理以及人工目視解譯后獲得。全球數字高程數據下載于地理空間數據云網站(http:∥www.gscloud.cn/),數據經過拼接、裁剪得到壽城自然保護區30 m分辨率的DEM數據,運用GIS軟件計算出坡度并進行重分類處理;此外,壽城自然保護區行政邊界、自然保護區邊界等數據來源于廣西省自然保護區遙感監測項目。
2 研究方法
研究根據壽城自然保護區的地理特征,首先選取景觀指數對保護區內的土地利用類型進行景觀格局演變分析。然后以景觀安全格局為理論背景,以MCR模型為依托,識別源地,選取距居民點距離、距河流距離、距道路距離、海拔、坡度等5個阻力因子創建阻力面,利用最小阻力模型得出保護區的不同生態安全水平下的等級最小累積阻力面,與人類活動用地疊加,以此來對保護區內的人類活動用地進行評價與優化。
2.1 景觀格局指數選取
景觀指數是景觀生態學研究的最重要內容,選取高度濃縮景觀格局信息、反映其結構組成和空間配置某些方面特征的景觀指標[13-15],來研究景觀結構組成特征和空間配置關系,是景觀生態學研究中使用廣泛且較為成熟的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結合前人經驗與自然保護區的區域特點,堅持常用、全面、系統等原則,選取了斑塊數量(NP)、斑塊密度(PD)、最大斑塊指數(LPI)、景觀形狀指數(LSI)、聚集度(AI)、邊緣密度(ED)、香農多樣性指數(SHDI)、香農均勻度指數(SHEI)這8個景觀指標,從土地利用景觀斑塊個數及密度、斑塊形狀、斑塊空間結構等方面來描述壽城自然保護區土地利用景觀格局變化特征[16-17]。景觀指數的計算運用GIS軟件平臺,將壽城自然保護區土地利用類型數據轉換為TIFF格式,并將數據加載至Fragstats4.2軟件,得出壽城自然保護區各年各景觀格局指數。
2.2 生態安全格局構建
2.2.1 保護區源地確定 生態源地是指作為區域生態功能最佳、能量與物質流通性好、水源涵養功能強的區域[18-19],是景觀生態安全質量最佳的核心地帶。本研究是基于生態安全格局下對保護區人類活動進行的評價優化。因此,保護區源地的確定優先選取生態服務功能最佳、生態質量較好、受人類活動影響較小的林地與水域。
2.2.2 阻力面構建 生態源地間生物水平方向的空間運動與生態競爭演變過程,主要是克服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各個阻力實現的,阻力面反映了生態用地克服阻力的空間連通性[19]。研究利用地理學中的表面模型——最小累積阻力(MCR)模型建立最小累計阻力面,它反映了從源地出發到達空間的某一個點所克服的最小阻力、成本耗費最小的距離[7]。其公式如下:
(1)
式中:f——區域中任意一點的最小阻力與其到所有源地的距離和景觀特征的正相關關系[8,20];Dij——從空間中的某一景觀i到源地j的距離;Ri——景觀i的阻力值。最小累積阻力模型是根據 Knaapen等人提出的模型和GIS中的成本距離發展得來的[21-23]。該模型主要利用GIS軟件中成本距離工具分析完成。
2.2.3 安全格局構建下的人類活動識別 本研究根據各阻力面與源地進行成本距離分析,劃分出不同等級的生態安全水平用地。然后,將生態安全格局水平圖層與人類活動用地(耕地、道路、居民點、養殖場、采石場、能源用地、其他人工設施用地)斑塊圖層疊加,得出不同安全水平的人類活動景觀安全格局,并對人類活動的發展建設提出相應的優化建議。
3 結果與分析
3.1 景觀指數動態變化
3.1.1 土地利用景觀格局總體變化 通過計算壽城自然保護區2013年和2017年包括斑塊個數、斑塊邊緣密度、聚集度指數、香農多樣性指數、香農均勻性指數等5個景觀指數,來把握壽城自然保護區土地利用景觀格局總體變化特征,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壽城自然保護區景觀多樣性指數
從表1中可以看出壽城自然保護區土地利用斑塊個數和斑塊邊緣密度均呈上升的趨勢,與2013年相比,2017年壽城自然保護區土地利用斑塊個數增加了83個,斑塊邊緣密度增加了0.304 5 m/hm2,表明壽城自然保護區土地利用斑塊形狀趨于復雜,斑塊破碎化程度越來越高。此外,斑塊聚集度指數呈下降的趨勢,表明壽城自然保護區土地利用斑塊在空間分布上趨于分散。壽城自然保護區土地利用景觀香農多樣性指數和香農均勻性指數均呈上升趨勢,說明壽城自然保護區土地利用景觀復雜程度和均勻程度均有所增加。
3.1.2 不同土地利用類型景觀格局變化 為進一步探討壽城自然保護區土地利用景觀格局動態變化趨勢,計算了2013年—2017年壽城自然保護區各土地利用景觀類型斑塊數量及密度、最大斑塊指數、斑塊邊緣密度、斑塊形狀指數、斑塊聚集度等6個指標用于研究保護區的景觀動態變化特征(表2)。
從表2中可以看出,壽城自然保護區道路、居民點、水域等土地利用類型斑塊個數最多,耕地和林地次之,其余地類斑塊個數較少,與2013年相比,2017年壽城自然保護區居民點斑塊大幅度增加,其次為道路、其他人工設施。從斑塊密度變化幅度來看,居民點的斑塊密度增長最為明顯(0.08),道路斑塊次之(0.02)。從最大斑塊指數來看,林地的最大斑塊指數最大,而其余地類最大斑塊指數均不足3,表明林地在壽城自然保護區土地利用類型中占據絕對優勢。從斑塊形狀變化來看,各地類斑塊邊緣密度和除道路外的各地類景觀形狀指數均有所增加,其中居民點斑塊邊緣密度和景觀形狀指數變化最大,分別增加了0.25和1.12,道路的景觀形狀指數下降了0.16,表明道路的通達性有所增強。壽城自然保護區各土地利用類型聚集度指數均呈下降趨勢,表明各土地利用類型斑塊空間分布上趨于分散,斑塊破碎化程度增加。

表2 壽城自然保護區不同用地類型的景觀指數
注:NP為斑塊數量;PD為斑塊密度;LPI為最大斑塊指數;LSI為景觀形狀指數;AI為聚集度;ED為邊緣密度;SHDI為香農多樣性指數;SHEI為香農均勻度指數。
總之,壽城自然保護區受人類活動的影響較為強烈,主要表現為道路、居民點、其他人工設施等人工景觀的破碎化程度增加,空間規模在擴大,而林地、水域等自然景觀趨于萎縮,斑塊個數減少。各土地利用類型空間分布趨于分散,斑塊形狀更加復雜,景觀多樣性和景觀均勻性均有所提高。
3.2 生態安全格局構建
3.2.1 保護區源地識別 本研究根據2017年壽城自然保護區的各個地類的實際分布情況,將坡度分為0°~5°,5~10°,10~15°,15~25°,>25°等5個級別,篩選出保護區內分布在坡度>25°較為連續的林地與水域作為保護區源地。用GIS軟件提取相應圖層,源地面積為29 046.53 hm2,占保護區總面積的41.41%,因其獨特的自然保護區地理特性,生態源地所占比例較大。
3.2.2 阻力面構建研究 基于2017年數據,選取到居民點距離、到道路距離、海拔、坡度、到河流距離5項阻力因子構建綜合阻力面。在參照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19-20,24],結合專家經驗將各阻力因子的相對阻力值劃分為5個等級,并賦予阻力系數。各個因子的相對阻力值系數與權重通過專家打分并結合實際情況獲得(見表3),其中阻力值越大、對生態用地產生的阻力越大,反之,阻力值越小,對生態用地產生的阻力越小。最后,依據表3所建立的各阻力因子權重與指標體系,運用空間分析工具對不同要素的阻力值進行加權疊加分析,最終得到壽城自然保護區綜合阻力分布圖(附圖1)。

表3 壽城自然保護區各阻力面體系、權重及阻力系數
3.2.3 不同安全水平的人類活動用地評價 根據阻力面構建模型所述的阻力模型構建方法,利用GIS軟件將源地、綜合阻力面添加至成本距離工具進行分析,得到綜合阻力面中每個像元到源地的最小累計成本距離,即壽城自然保護區的最小累積阻力面。將最小累積阻力面根據自然斷點法重分類為4個不同安全水平,從而得到壽城自然保護區生態安全優化布局圖(附圖2)。其中,生態安全水平為1級的表示生態安全水平質量最高,為保護區生態功能價值最高的地帶,應該作為保護區的生態核心地帶,優先加強管理與保護。
提取2003年與2017年兩期的耕地、居民點、養殖場、采石場、能源設施、道路、其他人工設施等人類活動矢量斑塊與重分類后的最小累計阻力面進行疊加分析,劃分出4個基于生態安全的不同安全水平的人類活動等級:發展核心區、發展緩沖區、發展優化區、發展限制區(如附圖3所示)。其中生態安全等級為1級的為生態安全用地較好的區域,不適宜人類活動景觀的分布與建設,為人類活動用地的發展限制區;生態安全級別為4的表示生態用地影響較弱,可以優先進行人類活動建設,為發展核心區。
根據圖1可知,2013年—2017年保護區內的人類活動總面積主要呈現增加趨勢,2013年發展限制區面積為232.84 hm2,發展優化區面積為758.10 hm2,發展過渡區為1 203.06 hm2,發展核心區為3 652.66 hm2;2017年發展限制區面積為232.75 hm2,發展優化區面積為763.35 hm2,發展過渡區為1 212.21 hm2,發展核心區為3 670.14 hm2。總體來看,2013—2017年,除發展限制區人類活動面積減少外,其余等級區域的人類活動面積均有增加。為進一步分析2013—2017年的不同安全等級的人類活動用地的具體情況,現對4個級別的人類活動用地進行了統計分析(如表4所示)。

圖1 壽城自然保護區各等級下的人類活動用地面積特征

表4 壽城自然保護區各等級下的不同人類活動用地面積分布情況 hm2
(1) 發展核心區。2013年發展核心區內人類活動總面積為3 652.66 hm2,占當年壽城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總面積的62.43%。其中人類活動用地主要以耕地、居民點用地和道路用地為主,其他人類活動用地面積較小。與2013年相比,2017年發展核心區內人類活動總面積增加了17.48 hm2,居民點用地和其他人工設施用地分別增加了12.53,11.64 hm2,耕地減少了7.98 hm2,表明核心區內人類活動用地變化主要以新建房屋和增加人工設施為主,居民點和其他人工設施的擴張占用耕地的現象明顯。發展核心區主要分布在壽城自然保護區南部以及北部和中部沿河流兩岸,該地區地勢相對平坦、人類活動較為成熟,主要表現為耕地面積廣,人口分布集中,對生態用地影響較小,可在此區域優先進行居民點與工礦用地等人類活動用地建設,作為人類活動重點發展的區域,不建議進行生態功能服務的規劃投入。
(2) 發展過渡區。2013年發展過渡區內人類活動總面積為1 203.06 hm2,占當年壽城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總面積的20.58%。其中人類活動主要為耕地、道路、居民點、其他能源設施、養殖場。與2013年相比,2017年發展過渡區總面積增加了9.15 hm2,耕地和居民用地面積增長明顯,分別為4.12,4.71 hm2,可以看出,發展過渡區人類活動用地變化主要以耕地和居民點的擴張為主,人口向過渡區轉移明顯。發展過渡區主要分布在發展核心區邊緣,是人類活動的過渡地帶,同時也是生態源地恢復、擴展的緩沖地帶,應做好生態修復與環境保護等工作,對于離生態用地較近的采石場、養殖場進行監測與管理,避免人類活動對生態用地產生污染,該區域作為發展優化區域與發展限制區域的搬遷安置點,應合理開發、構建生態屏障、保障人類活動的合理與生態用地的安全。
(3) 發展優化區。2013年發展優化區人類活動總面積為758 hm2,占當年壽城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總面積的12.97%。主要有耕地、居民點用地、道路用地、其他能源設施用地。與2013年相比,2017年發展優化區人類活動總面積增加了5.24 hm2,主要是由居民點用地面積增加造成,表明發展優化區內人類活動有所增強,人口規模呈逐漸擴大的趨勢。發展優化區主要分布在發展核心區和發展過渡區的外圍,作為人類活動的發展優化地帶,是生態源地恢復、擴展的緩沖地帶,該區域建議適當調整優化人類活動用地,禁止耕地的過度開墾,避免因人類的干擾與破壞造成的水土流失、石漠化等問題,在不影響生態用地穩定性的情況下,適當優化土地資源配置。
(4) 發展限制區。2013年發展限制區人類活動總面積為232.84 hm2,占當年壽城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總面積的3.98%,主要為耕地、道路、居民點用地。2017年發展限制區人類活動總面積為232.75 hm2,較2013年減少0.08 hm2,可以看出發展限制區人類活動占地面積變化幅度較小,總體上呈略微下降的趨勢。發展限制區零散分布在自然保護區內,遠離其他發展區,人口較為稀少,該區受人類活動的影響相對較弱,經濟發展方式單一,主要以農業耕作為主。發展限制區作為人類活動的限制地帶,適宜作為動植物的棲息地,是生態源地重點保護的地帶,該區域建議禁止人類活動的開發與建設,對于該區域的耕地等人類活動用地,應做好土地規劃,向發展優化區進行土地轉移,營造該區域優質的生態環境。
4 結 論
(1) 壽城自然保護區2013—2017年受人類活動的影響景觀的破碎化程度增加,景觀類型空間分布趨于分散,景觀多樣性和景觀均勻性均有所提高。人類活動用地面積在發展核心區、過渡區、優化區均有增加趨勢,僅在生態功能最強的限制區內有所下降。總體來看,人類活動限制區內控制的較好,但仍有不足之處,應當繼續加強監管與規劃,對優化區、過渡區的人類活動進行適當的優化與調整,避免人類活動用地對生態用地與自然保護區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干擾與不利影響。
(2) 由于壽城自然保護區自然環境面積范圍較小,從而選取的各個阻力因子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本文利用了兩期較高分辨率的遙感影像,解譯的土地利用數據精度較為精準,研究對保護區進行了景觀指數演變分析,同時借助MCR模型與景觀安全格局理論對自然保護區的人類活動進行了較為合理的布局評價優化,可為其他自然保護區的人類活動評價提供科學的參考。
(3) 本文指標創建的過程中,阻力系數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指標的確定基本是參考前人的研究經驗與專家打分法[25-27]。該方法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得到較為科學、準確的結果,但主觀性強。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綜合考慮更加科學的賦值模型與數學方法來完善指標的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