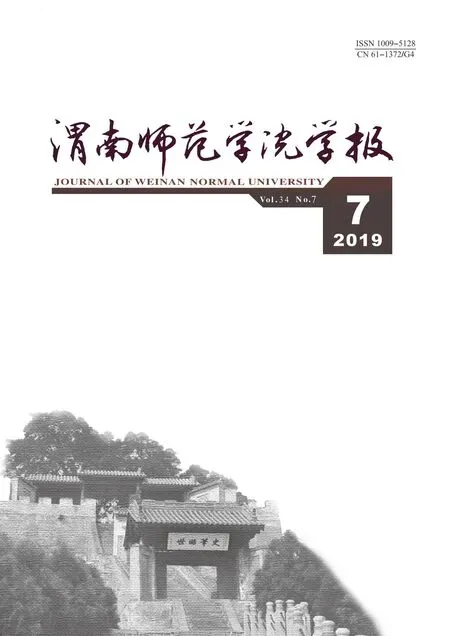晚清陜西創(chuàng)辦新學(xué)過程中的矛盾與困難
——以《秦中官報》為中心
吳 晨 娜
(四川大學(xué) 歷史文化學(xué)院,成都 610065)
《秦中官報》是清末陜西的地方性官報,其前身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創(chuàng)辦的《官報》。光緒二十九年(1903),陜西開辦課吏館,次年在陜西布政使樊增祥的主持下,設(shè)官報局于課吏館內(nèi),由課吏館館員選印《秦中官報》,光緒三十四年(1908)五月停刊。
《秦中官報》最初設(shè)有6個固定欄目:《諭旨恭錄》《秦事匯編》《直省文牘》《外報匯鈔》《藝文存略》《路透電音》。六個欄目內(nèi)容各有側(cè)重,《諭旨恭錄》欄目照發(fā)光緒帝、慈禧的詔令;《秦事匯編》欄目主要收錄陜西省布政使、巡撫等中上層官員對下屬地方官吏呈遞公移文牘的批復(fù),對于個別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會選刊下屬所呈公文的原文。欄目內(nèi)容涵蓋賦稅收繳、辦學(xué)申請、州縣判決詞訟等等大小秦中地方政務(wù);《直省文牘》欄目選登商部、戶部、學(xué)部、政務(wù)處、總理練兵處等政府機(jī)關(guān)及地方要員的各類公文章疏,反映國內(nèi)重要政事;《外報匯鈔》欄目主要轉(zhuǎn)載《北洋官報》《申報》等京津滬粵諸報的文章;《藝文存略》欄目屬于“關(guān)中文錄”性質(zhì),主要發(fā)表陜西官紳的書信文章,其中既有文人雅士所做的詩文,又有各學(xué)堂(以課吏館居多)學(xué)員的優(yōu)秀月課文章;《路透電音》欄目則每日將路透電信轉(zhuǎn)報秦中。“《秦中官報》主要采取內(nèi)部行政派銷的發(fā)行方式,由官報局轉(zhuǎn)發(fā)下屬,分發(fā)各州縣學(xué)堂。而報紙采用繁體豎排版印刷,內(nèi)刊文章由文言寫就,對于普通百姓未免佶屈聱牙,難以閱讀。因此,《秦中官報》的受眾面十分有限,主要面向陜西中上層士紳階級。從《藝文存略》欄目所刊載文章的作者中可以看出,報刊的讀者參與也幾乎全是各級官吏、士紳以及地方學(xué)堂的學(xué)員。
《秦中官報》的一大特點是內(nèi)容以秦中政事為主,非常重視“秦事”。通覽該報,《秦事匯編》欄目占整份報紙的篇幅最多,約為總內(nèi)容的一半左右;此外,它還具有鮮明的官報特質(zhì)。《秦事匯編》欄目所刊內(nèi)容幾乎全是直錄秦中各類奏牘文移,不僅載有地方民事,如民事糾紛、刑事案件的判決詞訟,而且收錄了大量秦中響應(yīng)朝廷開辦新法的政府公文,“對陜西各地興辦教育、官辦企業(yè),發(fā)展手工業(yè)、抗旱賑災(zāi)、鑿井修渠,以及民事訴訟等各類報道,成為今天全面了解晚清陜西地方歷史的重要文獻(xiàn)”[1]。雖然作為官報,它的社會效應(yīng)有限,“不可能像商業(yè)報刊或民辦報刊一樣,按新聞規(guī)律辦事,發(fā)布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新聞,更無法擔(dān)負(fù)起輿論監(jiān)督之責(zé)”[2];但正是由于其官報性質(zhì)和重視秦事的報道特點,它真切翔實地記述了清末陜西的真實面貌,反映了官商士紳的思想動態(tài),成為一扇透視晚清陜西社會的窗戶,生動地展示了陜西近代社會與近代思想生根成長的整體圖景,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興辦學(xué)堂是當(dāng)時的新事新政,為了使秦中士子了解新學(xué)開展?fàn)顩r,推進(jìn)陜西近代的學(xué)堂教育,各地辦學(xué)之事常常見報。興辦學(xué)堂等學(xué)政之事在《秦中官報》的總內(nèi)容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刊載省內(nèi)各類政事的《秦事匯編》欄目中,各地辦學(xué)內(nèi)容所占比例僅次于民事糾紛、刑事案件的占比。在《直省文牘》欄目中也常有陳述他省興辦學(xué)堂各事項的文書以及學(xué)務(wù)處、管學(xué)大臣等中央關(guān)于辦學(xué)的文件。《秦中官報》的《秦事匯編》欄目所刊登的大量陜西各地辦學(xué)狀況的文書,是研究陜西近代教育開辦情況的第一手史料,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關(guān)于清末陜西學(xué)堂的研究多散見于期刊及學(xué)位論文之中。姚遠(yuǎn)先生對陜西學(xué)堂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xiàn),他分析梳理了陜西大學(xué)堂、陜西農(nóng)業(yè)學(xué)堂、法政學(xué)堂、農(nóng)業(yè)學(xué)堂、實業(yè)學(xué)堂等各大知名清末陜西學(xué)堂的源流、發(fā)展、承襲脈絡(luò)及校政辦學(xué)情況。[注]參見姚遠(yuǎn)《西北大學(xué)的源流和承襲》,《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97年第3期;姚遠(yuǎn)、劉舜康、趙弘毅、王周昆《西北大學(xué)的兩個歷史源頭》,《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0年第3期;姚遠(yuǎn)《中國西部最早的高等學(xué)府——陜西大學(xué)堂》,《西安電子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0年第3期;姚遠(yuǎn)、蘇晉生、張惠民《晚清陜西農(nóng)業(yè)學(xué)堂與實業(yè)學(xué)堂考——兼論陜西高等教育的萌芽》,《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自然科學(xué)版)2000年第6期;姚遠(yuǎn)《陜西法政學(xué)堂與西北大學(xué)沿襲關(guān)系考》,《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1年第3期;姚遠(yuǎn)《陜西大學(xué)堂教學(xué)活動考》,《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2年第4期。除了對清末各類學(xué)堂做出介紹性研究之外[注]參見寇猛利《清末民國時期陜西中等教育研究》,陜西師范大學(xué)2012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李志松《論陜西教育的近代變遷》,《教育評論》2012年第5期;張丹《清末陜西教育近代化初探——以陜西大學(xué)堂為例》,《安康學(xué)院學(xué)報》2015年第1期。,其他學(xué)者的文章還以探究知名高等學(xué)堂或新式書院的社會影響及歷史影響居多,指出清末陜西學(xué)堂的建立與發(fā)展對于傳播科技、培育人才、變革教育、啟迪思想的重要作用[注]參見張惠民《味經(jīng)、崇實書院及其在傳播西方科技中的歷史作用》,《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自然科學(xué)版)1999年第1期;吳曉昱《清朝末年陜西新式學(xué)堂的外語教育對當(dāng)今外語教育的啟示》,《西北成人教育學(xué)報》2011年第6期;曾加、劉亮《陜西法政學(xué)堂與近代中國西部的法學(xué)高等教育》,《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2年第3期;張海軒、楊明東《從陜西大學(xué)堂看清末陜西教育的近代化》,《才智》2015年第23期;朱哲《近代陜西新式學(xué)堂與陜西同盟會關(guān)系研究》,西安工業(yè)大學(xué)2016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此外,也有學(xué)者聚焦于清末陜西書院改學(xué)堂的歷史過程[注]參見王磊《晚清陜西書院改學(xué)堂研究——兼談傳統(tǒng)書院的現(xiàn)代價值與意義》,陜西師范大學(xué)2012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潘明娟、張秦川《“關(guān)中書院改建為陜西師范學(xué)堂”的歷史復(fù)原初探》,《唐都學(xué)刊》2013年第4期。。學(xué)界對于清末陜西學(xué)堂的研究,已經(jīng)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尚未形成規(guī)模,從研究對象來看,對于新式書院和高等學(xué)堂的研究成果較多,鮮少有人關(guān)注地方學(xué)堂、中等學(xué)堂及小學(xué)堂的辦學(xué)情況和實操效果。對于《秦中官報》的研究,起步較晚,目前尚未形成規(guī)模,還未有以《秦中官報》為研究對象的專著,研究成果集中以學(xué)術(shù)論文的形式出現(xiàn)。研究角度則多從新聞學(xué)的理論方法出發(fā),評價《秦中官報》的刊物發(fā)展演變史、新聞寫作特點、傳播功能、社會影響[注]參見姚遠(yuǎn)、柏一林、徐懷東《〈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的孕育、誕生及其社會地位》,《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自然科學(xué)版)2004年第1期;劉安琴《〈秦中官報〉的創(chuàng)辦、務(wù)實與社會影響》,《河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農(nóng)林教育版)2005年第4期;田曉光《清末〈秦中官報〉所載詩文介紹與簡析》,《陜西檔案》2008年第6期;嚴(yán)琳、王繼武、易同民《近代陜西高等教育的興起及高校校報的發(fā)端》,《今傳媒》2011年第7期;舒彩紅《清末〈秦中官報〉的報道特點及傳播功能》,《西部學(xué)刊》(新聞與傳播)2016 第2期。;或是通過簡略概括報章內(nèi)容主題,粗觀20世紀(jì)初轉(zhuǎn)型期的陜西[注]參見裴曉軍、李倩《從〈秦中官報〉看清末陜西的近代化》,《唐都學(xué)刊》2013 第2期。。總體來看,學(xué)界現(xiàn)有的相關(guān)研究尚處于薄弱狀態(tài),缺乏歷史學(xué)視野與歷史學(xué)關(guān)懷。
一、購置新式書籍
(一)善后局購置新式書籍
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廷頒布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學(xué)制——壬寅學(xué)制。同年,在陜西巡撫升允的主持下,設(shè)立陜西大學(xué)堂,這是陜西近代高等教育的肇始。光緒二十九年(1903)頒布了癸卯學(xué)制。在清廷的導(dǎo)向下,各地陸續(xù)開辦學(xué)堂。隨著新式學(xué)堂的興辦,陜西省開始采購各類新式書籍以供學(xué)生閱讀研習(xí)。
陜西省購備新書一事,常由善后局負(fù)責(zé)。從1904年2月的《善后局憲札十二府州備價赴官書局購書札》[注]十二府州即清末陜西領(lǐng)七府五直隸州。分別為西安府、同州府、鳳翔府、漢中府、興安府、延安府、榆林府、乾州直隸州、商州直隸州、邠州直隸州、廊州直隸州、鄜州直隸州、綏德直隸州。可見善后局購書一事,是責(zé)令陜西全境參與,不論是否偏遠(yuǎn)貧瘠。一文中可以看出,善后局屢次派人從上海買回經(jīng)史時務(wù)等各類新印書籍,陜西各州縣學(xué)堂可直接赴省城官書局領(lǐng)購,為地方購買新式書籍提供了一個方便可行的渠道。而善后局為各學(xué)堂購備的書籍中有一部分是緊貼當(dāng)時時事潮流的新書。同年4月,秦報《秦事匯編》欄目中的《行官書局飭發(fā)由鄂購回輿地全圖收儲廣售札》再次提到,善后局籌挪款項,從湖北購買了二百四十部鄒氏《中外輿地全圖》以備各學(xué)堂領(lǐng)購。善后局呼吁,“此圖實為精核詳密之本,學(xué)堂士子吏館官員以及各屬設(shè)有中小學(xué)校之處均宜購領(lǐng)以資課習(xí)。爭先快睹,濟(jì)濟(jì)一時,存數(shù)無多,切需從速”。鄒氏《中外輿地全圖》即清末地圖學(xué)家鄒代鈞主編的《中外輿地全圖》,出版于1903年,“是我國最早的教學(xué)地圖集。該地圖集已具有近代地圖集的特點,也是我國較先進(jìn)的一冊世界地圖集”[3]。書中輯入68幅地圖中,包括世界地圖、各洲地圖、各國全圖及群島圖等,內(nèi)容新穎,在資料采用、數(shù)學(xué)基礎(chǔ)及表示方法等方面都具有近代地圖集特點。陜西省購買此書,目的應(yīng)是為各學(xué)堂學(xué)生開闊眼界,普及中國及世界地理知識。為了落實各學(xué)堂購領(lǐng),不久之后又于1904年8月在秦報上刊發(fā)了《善后局通行十二府州由鄂購到鄒印輿地全圖應(yīng)飭屬備價購領(lǐng)札》一文,足見良苦用心。1905年5月秦報中的《札飭十二府州各赴官書局購備刊出學(xué)堂章程文》一文中提到,為了規(guī)范學(xué)堂章程,陜西省從1904年7月開始,精心經(jīng)營數(shù)月,購買日本紙料,籌款將學(xué)務(wù)處咨發(fā)的《奏定學(xué)堂章程》雕版并印刷成書一千余部。“酌定每部收取板資庫平銀一兩二錢,帶套者加銀二錢”,令各州府速即轉(zhuǎn)飭下屬廳州縣赴官書局購取,發(fā)交至各城鄉(xiāng)學(xué)堂,以達(dá)到“官紳之有志立學(xué)者,俾知凡設(shè)益學(xué)堂必有一學(xué)堂之要領(lǐng)”的目的。善后局將《奏定學(xué)堂章程》其雕印成書,顯然是為了更好地傳達(dá)學(xué)堂各類學(xué)務(wù)的具體標(biāo)準(zhǔn),以便各州縣官員、鄉(xiāng)紳辦學(xué)時參考。
(二)州縣領(lǐng)購者寥寥,難見成效
善后局添購新書的舉措,對于地方學(xué)堂教學(xué)來講,本是一樁便利之舉。然而善后局為購買、刊印各類新式書籍花了極大本錢,還屢次下發(fā)札文督促各州縣前來領(lǐng)購,但是實際領(lǐng)購情況卻依然不盡人意。《善后局憲札十二府州備價赴官書局購書札》中寫道:“乃數(shù)月以來,領(lǐng)購者寥寥無幾,或以已經(jīng)購辦借口,或以經(jīng)費(fèi)支絀為詞,其實漠不關(guān)心,所以得緩及緩,以致學(xué)堂雖已林立,至今成效毫無。”為了解決領(lǐng)購者過少的問題,札中更是直接做出了明確規(guī)定:“今與各牧令明定限制,即照本局前次札發(fā)數(shù)目舉要,大縣必須籌集二百數(shù)十兩,中縣百五十兩,小縣亦須百余兩作為購領(lǐng)書籍之資。各就地方情形分別解價赴省領(lǐng)取。”由于前來領(lǐng)購者太少,善后局手中積存了大批書籍,其結(jié)果是購書成本大量積壓,以至于財政虧空。1904年7月的《善后局札十二府州飭屬遵照前札限日攜銀赴省官書局購取時務(wù)各書文》一文中便提到,發(fā)札通飭已經(jīng)兩月,然而“遵辦者僅得數(shù)處,其余若罔聞知”。善后局的書大半為學(xué)堂所備,由于購領(lǐng)者寥寥,“現(xiàn)積壓成本三萬余金”。擬稿者吳廷錫不能理解這種現(xiàn)象,認(rèn)為所規(guī)定各縣購書金額(大縣二百數(shù)十兩,中縣一百五十兩,小縣百余兩)并不算多,“其購價最多者不過二百余金,一州一縣之大,籌此戔戔之?dāng)?shù),斷不致十分為難”。
但地方州縣的基層官吏卻顯然不這么認(rèn)為。有的官吏甚至?xí)ふ腋鞣N借口,企圖名正言順地逃避購領(lǐng)書籍一事。城固縣知縣以前任知縣已經(jīng)派人去川省購買學(xué)堂應(yīng)用各書籍為由,企圖逃避規(guī)定,不去購領(lǐng)書籍;并托詞道待到采辦人返回之時,如果需用各書有缺,再赴省城官書局備價領(lǐng)購。從1904年4月秦報所刊《批署城固縣知縣陳膺臻遵札查明小學(xué)堂應(yīng)用各書已赴川購買稟》中可以看出,陜西布政使樊增祥對待此事的態(tài)度非常強(qiáng)硬,先是指出,自陜西開辦學(xué)堂以來,善后局已經(jīng)先后兩次派人去上海購買各類新式書籍,以備各屬購閱。指斥該縣不來本省領(lǐng)購而前往川省購買的行為“舍近就遠(yuǎn),情理所無”;再是提出,城固縣的學(xué)堂自壬寅以來已經(jīng)開辦了三年左右,而前往川省購買的書籍卻至今未到,與該縣學(xué)堂開辦情狀脫節(jié)甚重;最后列舉其他已經(jīng)購備書籍的地方官員作對比,“如商州尹牧臨潼李令,皆以重金購備多種;而鄜州勞牧,地瘠官貧,猶且捐廉二百金博收群籍”,并直接在批文中對該縣令提出了嚴(yán)厲批評,下達(dá)了最后通牒:“該吏處膏自潤,遇此等事,推之前任,推之邑紳,推之川省,本司生平最恨脫滑取巧之人。仰漢中府轉(zhuǎn)飭陳膺臻,速備五百金專差赴省城官書局購買一切新舊書籍。如一月以內(nèi)不來,定將該令撤任以懲慳猾繳。”
從善后局購書一事中可以看出,陜西省中上層官員心中的引入新學(xué)、創(chuàng)辦新式教育的設(shè)想,在實際操作中遇到了重重困難。一方面,由于時事危急,急需人才,中上層官員充分意識到興辦學(xué)堂,培育人才的重要性。為了盡快達(dá)到培育人才的目的,他們單方面地加大投入,期待能收到成效。善后局積極為了方便各地學(xué)堂閱習(xí)新書、新章程,甚至不惜先行籌挪錢款,從發(fā)達(dá)省份購置各式時興書籍,或是自己主持刊刻辦學(xué)章程。然而對于地方官員來說,興辦學(xué)堂首先需要耗費(fèi)大量財力,而培養(yǎng)人才屬于長久之計,辦學(xué)之益處并不能立刻見效。短期內(nèi)產(chǎn)出幾乎為零,遠(yuǎn)遠(yuǎn)低于投入,在這樣的心態(tài)主導(dǎo)下,他們不以辦學(xué)為急務(wù),也就扯皮推諉,并不十分愿意備齊經(jīng)費(fèi)、購領(lǐng)書籍。
二、地方學(xué)堂的課程
(一)課程設(shè)置
合陽縣縣令仇繼恒所辦小學(xué)堂較有成效,規(guī)劃完備,為全省之楷模,因而被調(diào)任赴課吏館接辦分校事宜。他上書匯報辦學(xué)情況的稟及表折,即《批合陽縣仇令具陳現(xiàn)辦小學(xué)堂情形稟》一文,也刊登于1904年9月秦報,作為陜西省辦學(xué)典范,供其他官員學(xué)習(xí)模仿。
表1是根據(jù)報章原文整理的合陽縣小學(xué)堂原定課程單。
由表1可知,該縣小學(xué)堂分為尋常小學(xué)堂與高等小學(xué)堂,原定每日授課共計8小時。按照規(guī)劃,學(xué)生原本應(yīng)入蒙學(xué)堂學(xué)習(xí)四年后,升入尋常小學(xué)堂學(xué)習(xí)三年,再升入高等小學(xué)堂學(xué)習(xí)三年。但顯然有未入蒙學(xué)堂學(xué)習(xí)即進(jìn)入尋常小學(xué)堂學(xué)習(xí)或未入蒙學(xué)、尋常小學(xué)學(xué)習(xí)即進(jìn)入高等小學(xué)堂學(xué)習(xí)的特例存在。在課程安排上,尋常小學(xué)堂計劃每日學(xué)習(xí)修身一小時,讀經(jīng)二小時,作文一小時,習(xí)字一小時,史學(xué)一小時,輿地半小時,算學(xué)半小時,體操一小時;高等小學(xué)堂計劃每日修身半小時,讀經(jīng)二小時,讀文、作文一小時(單日讀文雙日作文),習(xí)字半小時,算學(xué)半小時,史學(xué)一小時,輿地一小時,理科或圖畫半小時(單日理科雙日圖畫),體操一小時。在科目內(nèi)容上,修身主要是對學(xué)生進(jìn)行道德教育,通過《曲禮》《小學(xué)》等儒家著作向?qū)W生傳授傳統(tǒng)倫理觀念,即“性理通論、倫常大義”;讀經(jīng)要求學(xué)生學(xué)習(xí)《詩經(jīng)》《禮記》等各類儒家經(jīng)典,但只要求略通大義即可,不要求記誦;讀文與作文主要為培養(yǎng)學(xué)生語言組織能力,鍛煉學(xué)生閱讀、寫作能力;習(xí)字一科不僅教授學(xué)生識字,還教之以書法;史學(xué)一科按時間先后順序教授中國史事之大略,但對高等小學(xué)堂學(xué)生要求較高,建議其了解歷史地理、本朝掌故等具體知識;輿地教授學(xué)生地理知識,偏重于介紹本國本省,但對于世界(地球)地理知識也有所涉獵,比重不大;算學(xué)主要教授一些簡單的數(shù)理知識,課本皆國人所作,大多較舊;理科主要傳授生物(動植物)、器具制造法和物理知識,內(nèi)容較為淺顯,課本大多是從國外引進(jìn)或翻譯的新書,但陜西省似乎并未購得應(yīng)用課本;圖畫主要是教學(xué)生臨摹實物模型;體操一科引入日本辦法,課程內(nèi)容為柔軟操、器具操。

表1 尋常小學(xué)堂課程門目年限時刻書籍表
在課程比重上,無論尋常小學(xué)堂還是高等小學(xué)堂,讀經(jīng)一科比重最大,最受重視,所占時間為25%左右;其次是史學(xué)、體操,占比為13%左右。在尋常小學(xué)堂中,修身、作文、習(xí)字較受重視,占比均為13%左右;高等小學(xué)堂則對輿地較為重視,占比為13%。最不被重視的是高等小學(xué)堂開設(shè)的理科、圖畫兩科,占比僅為3%。
在各項科目所列的課程應(yīng)用書籍中,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史、文學(xué)各書占了絕大部分。這些書籍主要為配合修身、讀經(jīng)、史學(xué)、作文等帶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烙印的科目。而帶有近代特征的新興科目,如輿地、理科等,不僅所列書目的數(shù)量較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書籍陜西省其實并未購得,學(xué)堂學(xué)生也就自然無法讀到這些新學(xué)書籍。
(二)缺乏教師、經(jīng)費(fèi),原定課程難以推行
原定課程單表格,開設(shè)修身、讀經(jīng)、讀文、作文、習(xí)字、史學(xué)、輿地、算學(xué)、體操、理科、圖畫等諸類科目,看似涵蓋極廣,兼顧中西,然而實際執(zhí)行情況如何呢?合陽縣縣令仇繼恒在稟文中說明,他從去年春初開始,便急急以興學(xué)育才為先務(wù)。籌備款項,延聘教習(xí),添蓋講堂,置買書籍,嚴(yán)立課程,籌辦“書籍新舊三百余種,講堂新舊二所,新舊齊舍六十四間”,“意欲辦成一完全合格之小學(xué)堂”。開辦小學(xué)堂半年有余,學(xué)生從一開始招之不來,到現(xiàn)在爭先恐后前來學(xué)習(xí),實際在堂住宿學(xué)習(xí)的學(xué)生數(shù)量已經(jīng)達(dá)到68人。學(xué)校設(shè)一位總教習(xí),負(fù)責(zé)教授經(jīng)學(xué)、習(xí)字和作文;設(shè)兩位分教習(xí),其中一位負(fù)責(zé)教授修身和史學(xué)兩科,另一位負(fù)責(zé)教授算學(xué)和輿地兩科。實際上,物理、圖畫、體操并無人教授。至于教學(xué)情況則是,“每教習(xí)每日上堂一次,久者兩點鐘,速者一點鐘。逐日三次,譬如主算學(xué)輿地者,單日算學(xué)雙日輿地,余以類推”。因此,報刊上所載的兩幅細(xì)致完備、規(guī)畫甚詳?shù)脑ㄕn程單,只能說是一個美好的愿景。現(xiàn)實中,地方辦學(xué)仍然困難重重,即使重視教育、踏實肯干如合陽縣縣令仇繼恒者,在“人才物力均有所限”的情況下,也只能“略加遷就,曲與融通”。
陜西布政使樊增祥對本篇稟文的批示中提到,陜西辦學(xué)有一大難處,即經(jīng)費(fèi)不足。“以書院改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恒虞不足,就地籌捐,苦無為炊之米”。由于經(jīng)費(fèi)窘乏,開始興辦學(xué)堂雖然已經(jīng)兩年有余,“雖實心辦理者亦自有人,而齊舍租立經(jīng)費(fèi)無著者又比比皆是”,辦學(xué)效果并不理想。陜西省原本就士風(fēng)樸塞,人民見聞不廣,“所以俗儉民窮,人無遠(yuǎn)志”。因此他認(rèn)為,對這些“耳目囿于鄉(xiāng)鄙,心力盡于時文”的局于舊學(xué)的古板鄉(xiāng)紳來說,如果廢八股講時務(wù),就會導(dǎo)致“怯者不肯來,來者不可學(xué)”的局面。這位心系地方教育的一省藩臺,雖然他主持創(chuàng)辦了《秦中官報》,為閉塞的陜西省打開了一扇接觸外界新事與新知的窗戶,期望能培育出兼知本省政要和中外時局的見聞廣博的有用之才,但是在他的心目中,這份對培育人才的期許,仍然輸給了在新舊融匯相爭的多變時局中堅持傳統(tǒng)學(xué)問最為優(yōu)秀的是非之辯。這份被奉為典范的小學(xué)堂課程及書目表,經(jīng)過悉心規(guī)劃,且被陜西省藩臺推崇為“皆如吾意中所欲言”,從中折射出的卻是清末辦學(xué)過程中根深蒂固的矛盾:雖然中上層官員認(rèn)同清廷政策,重視開辦新式教育,以培養(yǎng)兼通中西的可用人才為一大急務(wù),但是實際上仍然對于西學(xué)的引入存在著很大疑慮。在“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方針的指導(dǎo)下,課程設(shè)置壓倒性的偏于傳統(tǒng)經(jīng)史文學(xué),而帶有近代特征的地理、生物、物理等學(xué)科并沒有得到認(rèn)真落實。再加之陜西省地處偏僻,財用緊張,許多新式課程應(yīng)備書籍一時間難以置辦,陜西省各學(xué)堂學(xué)生能接觸到的新知識實際上極為有限。
三、地方辦學(xué)經(jīng)費(fèi)的籌措
(一)各地辦學(xué)經(jīng)費(fèi)的來源
興辦學(xué)堂的學(xué)務(wù)工作,除了擬訂章程、購置書籍之外,還需要租賃或改建校舍、延請教習(xí)等等,這些工作無疑需要大量經(jīng)費(fèi)。清末陜西各地的辦學(xué)經(jīng)費(fèi),大多數(shù)來源于地方自籌。為了響應(yīng)興辦學(xué)堂的號召,籌款活動在各地普遍展開,地方官吏想方設(shè)法多方籌措。
全省籌措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的方式各不相同,并沒有統(tǒng)一的規(guī)范。《秦中官報》的《秦事匯編》欄目中就刊登了數(shù)十篇反映地方籌措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的公文,各地的籌款方式幾乎各不相同。如1904年11月的《批沔縣勸集殷本開質(zhì)提息充作學(xué)費(fèi)稟》,沔縣提出勸捐購買股票,并以股票利息充作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在《批藍(lán)田縣胡令請以長解屯更二成銀發(fā)典生息撥濟(jì)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稟》一文中,藍(lán)田縣提議將原應(yīng)積谷備荒的款項作為本金生利,作為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但被陜西布政使樊增祥批為“巧取茍安”,嚴(yán)厲駁回;《批宜川縣林令岐饒請抽收船鈔充作小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稟》一文顯示 ,宜川縣無資可籌,只好擬請抽收船鈔,將經(jīng)費(fèi)攤之于“船戶粟商股子人等”; 時有弊政,即“驛站馬料在征購中的流弊。各地驛夫名額多被虛報冒領(lǐng),實際在驛服役的不過十之二三。地方官上任伊始,首先打聽郵驛經(jīng)費(fèi)的多寡,有利可圖則笑逐顏開”[4]35。從1905年4月的《批臨潼縣李詳請將號豆折價歸作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由》文中可知,臨潼縣將遺留弊政——號豆整改:將其折價歸入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而號需之豆,由地方官自行捐廉,達(dá)到了既籌措到了辦學(xué)經(jīng)費(fèi),又不加重民眾負(fù)擔(dān)的效果,受到了藩臺樊增祥的贊譽(yù);《批武功縣稟開辦學(xué)堂無資請收回籽種錢文作為經(jīng)費(fèi)一案由》中,武功縣懇請將渭河南岸的二十余頃新灘地畝每年所征收的六百余串錢永歸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被陜西巡撫曹鴻勛駁回;7月的《批宜君縣稟抽收煙苗稅錢按年收作蒙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一案由》中,宜君縣將煙苗稅錢抽取三百六十串撥作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批長武縣稟籌辦蒙小學(xué)堂章程并常年經(jīng)費(fèi)由》中,長武縣為了興辦學(xué)堂,清民糧,墾荒地,裁戶首,并以有余而補(bǔ)不足,為學(xué)堂籌集到了經(jīng)費(fèi)。
還有一部分辦學(xué)經(jīng)費(fèi)來源于地方鄉(xiāng)紳的捐獻(xiàn)。1904年7月的《批咸寧縣民人劉溶以南五臺地畝懇祈收入學(xué)堂以資膏火呈辭》,咸寧縣民人劉溶,耄年好善,曾將田產(chǎn)捐給佛寺。但因寺內(nèi)僧侶戒規(guī)不嚴(yán),蕩耗廟產(chǎn),現(xiàn)請將捐于佛寺的田產(chǎn)充歸學(xué)堂之費(fèi)。據(jù)陜西布政使樊增祥批示,不僅準(zhǔn)予將該寺現(xiàn)有地產(chǎn)充歸學(xué)堂,還要清查該寺之前抵押的一百余畝地產(chǎn),將來仍歸學(xué)堂取贖。該縣官吏舒某曾在驅(qū)逐該寺“野僧”后,又撥給其十五畝地,樊增祥批示將此地一并歸入學(xué)堂,由學(xué)堂招佃取租,不準(zhǔn)撥給僧人。1905年3月的《行知準(zhǔn)禮部咨山陽縣程祝氏賞給樂善好施字樣以示旌獎文》中,山陽縣創(chuàng)辦小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不足,號召該縣鄉(xiāng)紳量力捐助。已故四川布政使程豫的孀媳程祝氏,將其祖產(chǎn)一塊值銀一千兩的田地捐作小學(xué)堂常年經(jīng)費(fèi)。為旌表其行為,準(zhǔn)給“樂善好施”字樣以示旌獎[注]關(guān)于對樂善好施行為的表彰,道光二十八年清廷定例,各省樂善好施者,原系有力之戶,均令自行建坊,毋庸給予坊銀。此事便是遵循道光二十八年的成例,賜予程祝氏“樂善好施”字樣,令其自行建坊。。除了捐贈田產(chǎn),也有鄉(xiāng)紳為學(xué)堂捐贈書籍。如1905年4月和1905年6月先后刊登于《秦中官報》的《批咸陽縣稟邑紳李舒馨捐款購書歸入學(xué)堂懇請立案由》和《批咸陽縣稟紳士李舒馨捐款進(jìn)書充歸學(xué)堂立案由》兩篇文書提到,光緒初年曾任山東省福山縣令的咸陽人李舒馨,他向咸陽縣的書院學(xué)堂捐贈了數(shù)十種經(jīng)史書籍。他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書捐贈咸陽縣的渭陽書院:“光緒辛丑歲(1901)大饑,出巨金賑鄉(xiāng)里,又以二十四史、九通及新書多種,捐庋渭陽書院,以餉寒唆。”[5]266
(二)籌措辦學(xué)經(jīng)費(fèi)中的問題
地方在籌措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的事務(wù)中,效率較低,問題不斷,困難重重,常生弊政。以醴泉縣為例,該縣曾經(jīng)先后數(shù)次請示或報告該縣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籌辦的各類事項。1904年6月《批醴泉縣千令長華呈遞勸捐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捐戶清冊》一文,醴泉縣的前任官吏在學(xué)堂初設(shè)、縣內(nèi)百姓尚未見到辦學(xué)益處之時,便勸捐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借“一視同仁”之名,“不分士商農(nóng)工,不分貧富,一概派捐”;勸捐過程中,捐戶清冊撰寫不清,只記錄為“某堡某村捐錢若干”,并無姓名可考。這些做法導(dǎo)致勸捐事務(wù)秩序混亂,縣內(nèi)“劣衿惡約藉此苦擾”;經(jīng)辦者貪污經(jīng)費(fèi),“上下其手,多少任意”,給醴泉縣縣民造成了極大負(fù)擔(dān),民怨沸騰。1905年4月《批醴泉縣請擬撥存米平糶余款以作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并豁免捐輸稟》中,從陜西巡撫升允批示中也可以看出,醴泉縣在自行籌措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的過程中存在著較大的管理缺陷:“學(xué)堂捐款派及下戶辦理,實屬不善。究竟是否有捐無收,抑系有收無交,其間有無蒙混侵蝕情弊,仍應(yīng)詳細(xì)訪查稟明,核辦至里。”面對這種情況,巡撫只得應(yīng)允將存米平糶所得余款撥作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并免除醴泉縣的部分捐輸,以支持該縣的辦學(xué)事業(yè)。此外,1905年2月的《批醴泉縣舒請將減收米錢撥充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稟》顯示,醴泉縣還將減收米錢撥充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今于每兩收錢九十文內(nèi)酌減二十文,且以買朱盈余之?dāng)?shù)撥作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1905年4月的《批醴泉縣舒稟請將善堂生息撥作小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由》中,醴泉縣為移緩就急,縣令舒某擬將該縣善堂自制棉衣所得之款全部撥歸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而每年應(yīng)散棉衣之費(fèi)由地方官自己貼錢,捐廉給發(fā)。大學(xué)堂盛贊該縣令“樂善好施”,“擴(kuò)充學(xué)堂,固屬要政;施散棉衣,亦屬善舉”,但表示對該縣這一善政的前景并不看好,“設(shè)或奉行日久,地方官不肯解囊,則施散棉衣一事勢必至有名無實,嗟彼窮黎,其何以堪!”
綜上所述,一方面,地方為學(xué)政籌措經(jīng)費(fèi)的過程十分艱難,大部分經(jīng)費(fèi)都是從地方稅務(wù)、公款、公產(chǎn)中撥調(diào),以濟(jì)急緩。一些心系學(xué)務(wù)的地方官吏甚至要捐出自己的養(yǎng)廉銀來支持學(xué)務(wù),然而這部分金額畢竟為數(shù)不多,捉襟見肘。各地籌措經(jīng)費(fèi)的方式方法也不盡相同,這也導(dǎo)致辦學(xué)經(jīng)費(fèi)收入來源多種多樣,十分繁雜,并無定制,亦不規(guī)范。開辦學(xué)堂的初心雖善,然而籌措辦學(xué)經(jīng)費(fèi)一事卻成了加劇地方官吏貪污腐敗、加重百姓負(fù)擔(dān)等種種惡性現(xiàn)象滋長的溫床。另一方面,興學(xué)堂育人才本身就是一件見效極慢,必須長遠(yuǎn)建設(shè)的大事,比起鄉(xiāng)紳捐獻(xiàn)、地方官捐廉等不能確定的短期收入,更加需要來源穩(wěn)定的長期經(jīng)費(fèi)。地方所采用的籌款之法有的確實可以堅持一時,但卻不是長遠(yuǎn)之計。如何獲得穩(wěn)定的經(jīng)濟(jì)支持,這個問題像山一樣壓在地方學(xué)務(wù)的籌辦之路上,想要腳踏實地地興辦學(xué)務(wù),只能想辦法盡量在不擾民生的前提下解決長期經(jīng)費(fèi)問題。對于本就財用匱乏的陜西省來說,籌措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是清末新政出給每位地方基層官吏的一道難題。正如《批臨潼縣李詳請將號豆折價歸作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由》中布政使樊增祥所說,“籌款難,籌款而不病民尤難,籌款不病民且能利民尤難之難”。
四、結(jié)語
在陜西省興辦新學(xué)堂、培育新人才的過程中,省城的中上層官員和地方的基層官吏在某種意義上并非一心同體。
中上層官員的社會地位較高,因此,他們或多或少心懷著培育人才的社會責(zé)任感。再加之積極迎合清廷新政,他們對興學(xué)堂、育人才的學(xué)政之事十分重視,以辦學(xué)為急務(wù)。在他們心中,興辦新式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人才,廣開民智。但實際上,深層目的并非如此簡單。一方面,清廷正處于內(nèi)外交困、列強(qiáng)環(huán)伺、時事嚴(yán)峻的危急態(tài)勢之中,急需一批能承擔(dān)起興國救亡責(zé)任的有用人才作為中流砥柱力挽狂瀾;另一方面,培育人才也是一種控制思想的過程,出于維護(hù)統(tǒng)治的需要,他們主動抑制那些他們所認(rèn)為的“激進(jìn)觀念”。即使引入新知識,他們也小心翼翼、酌情考量,將西學(xué)作為中學(xué)的從屬。
地方官吏的社會地位比中上層官員較低,他們每天需要處理的政事多是地方各類民事。在他們的心中,一切以生計為重。陜西省地遠(yuǎn)民窮,受生產(chǎn)力限制,辦學(xué)困難良多。首先,學(xué)堂經(jīng)費(fèi)難以籌集。若要依靠勸捐攤派,則“蚩蚩者未見其益,先有捐錢之事,而滋多口所謂少見多怪也”,加重轄區(qū)內(nèi)百姓負(fù)擔(dān);而鄉(xiāng)紳捐獻(xiàn)、官吏捐廉,又只能解一時之急,并非長久之計。其次,想要辦好學(xué)堂,需要購買大量書籍、擬訂具體章程、建設(shè)學(xué)舍操場、延請新式教習(xí)、招募學(xué)堂學(xué)生,投入大量的財力、精力、人力。然而辦學(xué)一事,成效較慢,付出與回報并不能成比例,兩相權(quán)衡,他們自然偏于先理民事,再談辦學(xué)。所以對待赴省官書局購書一事,就能緩則緩。生產(chǎn)力低下,占有的經(jīng)濟(jì)文化資源匱乏,這就是陜西省之所以 “士守橫編,商無遠(yuǎn)志”的根源,也是陜西省和東南地區(qū)發(fā)達(dá)省份的差距所在。
在這些基層官吏隊伍中,個別心懷社會責(zé)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地方官員,心系教育,也確實為了創(chuàng)辦新學(xué)投入了大量精力、財力、人力,如合陽縣縣令仇繼恒。但終究受個人才學(xué)見識所限,客觀資源條件所限,辦學(xué)結(jié)果也是有限的。大部分的官員主要還是為了自己的政績才開辦學(xué)堂,缺乏實打?qū)嵧度朕k學(xué)的氣魄,所以即使創(chuàng)辦了學(xué)堂,也是徒有空殼,收獲甚微。
對于陜西省地方辦學(xué)的種種困難,陜西中上層官員其實心知肚明。如陜西布政使樊增祥,他懂得地方辦學(xué)“經(jīng)費(fèi)恒虞不足,就地籌捐,苦無為炊之米”之難,也看到了“是以新章誕布兩載于茲,雖實心辦理者亦自有人,而齊舍租立經(jīng)費(fèi)無著者又比比皆是”的現(xiàn)實。他一方面認(rèn)為興辦新學(xué)的難處皆不足為難,成事在與人,“所難者仍在有本有文,實心辦事之地方官。官得其人,不學(xué)可教之使學(xué),無師則身自為師”;但另一方面,他不對基層官員是否能辦好地方學(xué)務(wù)做硬性要求,對興辦學(xué)堂不利但治理民事有方的官員表示理解,認(rèn)為“學(xué)術(shù)雖差而能盡心民事,則猶有可取”。在中上層官員的認(rèn)知中,辦學(xué)雖為一大急務(wù),但仍可妥協(xié)于民事。
清末陜西省興辦新學(xué)過程中,中上層官員與基層地方官吏,由于立場不同,對待辦學(xué)的態(tài)度不同,兩方認(rèn)知中的學(xué)務(wù)緩急程度也不同。造成雙方矛盾和辦學(xué)困境的原因,固然有財用匱乏、文化資源緊缺之故,但歸根結(jié)底,從中上層官員到基層地方官吏,他們或多或少都戴著功利性的“有色眼鏡”來看待“興學(xué)堂,育人才”的大政方針,真正關(guān)注“人”(或者說“國民”)的素質(zhì)的比重很小。他們處于不同的立場,雙方都受限于各自所處的客觀環(huán)境。即使中上層官員意識到普及新式教育的重要性,以辦學(xué)為急務(wù),積極組織,也不能說他們就是目光長遠(yuǎn),心系民眾;換言之,基層官吏逃避責(zé)任,不愿投入,也不能一味地批判其“短視”。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見效較慢的長久大計,急功近利的態(tài)度是不可取的。如果沒有關(guān)注個體、以人為本的情懷,缺乏傾注心血、不計成本的魄力,美好的心愿終究會輸給現(xiàn)實,其結(jié)果不過如清末陜西省辦學(xué),學(xué)堂林立,成效甚微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