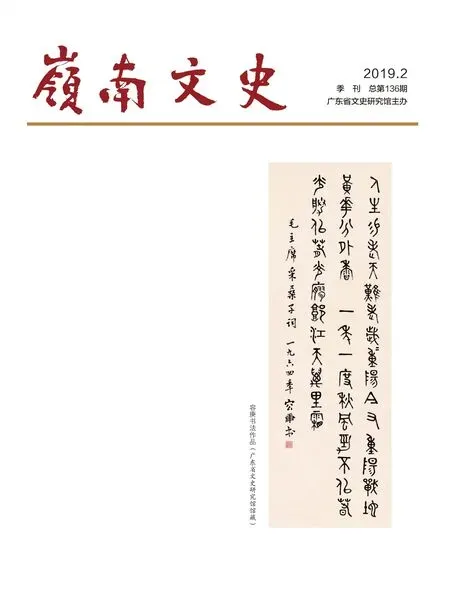三元里抗英斗爭研究七十年
秦利國
三元里抗英是鴉片戰爭時期廣州三元里民眾抗擊英國侵略者的重大事件,是鴉片戰爭時期民眾反抗侵略者的典范,一直被后人所稱頌,被認為是中國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的開端,在鴉片戰爭史和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年間,中國史學界對它展開了不斷深入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是研究鴉片戰爭史和晚清史的學者所繞不開的課題,取得了顯著成果。
一、三元里抗英斗爭資料整理
鑒于三元里抗英斗爭事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科學界首先進行了有關此事件的史料搜集與整理工作。1953年廣東省文史研究館成立,旋即成立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史料組,“通過多種渠道和多種形式廣泛搜集包括清代官書著述、人物事略傳記、社學、社會流傳詩歌、外人記載、調查訪問實錄等有關史料。”[1]直到1956年,該館根據所搜集的資料內部編印了《廣東人民三元里抗英斗爭簡史》。在此基礎上,該館在1959年正式編輯對外公開出版發行《三元里抗英斗爭史料》(中華書局)。“全書共22萬余字,6個部分,而最重要的有三個部分,即三元里抗英斗爭史料,社學及平英團抗英斗爭史料,以及手工業者參加抗英斗爭史料。應當指出,本書所收入的清方檔案和私家著述,除有一部分與《鴉片戰爭》重見外,其余都是難覓的未刊資料,有一定的史料價值。”[2]此書在當時引起了較強烈的反響。后來,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將一部分資料移至《中國近代史資料》,197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修訂本。
20世紀50年代初,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史學會主編出版了一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為該叢刊之一,1954年由神州國光社出版。書中有大量關于三元里斗爭的一手資料,包括《夷氛聞紀》《籌辦夷務始末》《英軍在華作戰記》等。此套書在當時及其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學者們研究這一事件的主要依據,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是此書搜集的資料大多是以中方資料為主,關于英國方面所記述的材料則很少,這難免給三元里斗爭的研究帶來缺憾。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有關鴉片戰爭史資料的大量出版,有關三元里斗爭的資料收集也不斷豐富。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為進一步拓展鴉片戰爭史的研究,在1983年編譯了《鴉片戰爭史料選譯》(中華書局)一書,該書總共選譯了58篇資料,都來自傳教士在澳門創辦的《中國叢報》。此書翻譯的主要是報刊材料,而對于英國方面檔案資料的翻譯則沒有。
199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胡濱先生譯注《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則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本書包括英國藍皮書有關鴉片戰爭資料和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有關鴉片戰爭資料兩部分,基本反映了鴉片戰爭全過程,對英國制訂侵華的經過作了較詳細的說明。全書大約80萬字,其中也涉及到三元里人民抗英方面的有關資料。這些有關英國方面資料的出版,對當時中國史學界研究三元里抗英斗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1987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將其所藏的有關鴉片戰爭的清政府檔案資料出版,名為《鴉片戰爭檔案史料》,200多萬字。這套叢書不僅促進了鴉片戰爭史的研究,而且對三元里抗英斗爭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深化作用。步入新世紀以后,由于研究時段的逐漸下移,包括鴉片戰爭在內的晚清史研究逐漸淡出了史學研究者們的視野,因此相關的資料的整理、出版工作也逐漸減少。
二、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研究
隨著上述資料的先后整理與出版,從20世紀50年代起,不少學者對三元里抗英斗爭這一事件開始進行研究。最早對此一事件進行系統研究的是中山大學陳錫祺教授。他在1956年出版的《廣東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一書中,詳細敘述了這次斗爭的前因后果,著重介紹了三元里人民如何準備戰斗、戰斗的經過以及三元里戰斗對后來廣東人民反侵略反投降斗爭的影響。[3]但是此書由于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再加上史料搜集的局限,許多事實在今天看來并不完全真實。
這一時期學界關于三元里斗爭研究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三元里抗英斗爭的領導問題上,包括三元里抗英斗爭的領導者是誰、三元里抗英斗爭是群眾自發的還是有組織的領導、社學在其中有沒有發揮作用等問題。在50年代,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組織人力搜集三元里抗英斗爭的史料時,組織人員親自到三元里進行實地調查,搜集到一些當地民眾所回憶的口述資料。[4]依據這些資料,他們認為農民韋紹光是此次抗英事件的領導人,參加斗爭的主體是當地農民和打石、絲織工人,部分愛國士紳也發動社學參加了斗爭。[5]這一觀點在改革開放之前,在學界一直占據著主流。如陳錫祺教授的《廣東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一書中就指出,三元里的抗英斗爭是由農民韋紹光等發動起來的,而且是經過宣傳鼓動有一定組織形式的人民反侵略武裝。[6]他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中,同樣強調了人民群眾在三元里抗英斗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7]而李龍潛等人則在1955年發文指出:“三元里人民反英斗爭正是廣東人民反抗英國侵略者的愛國主義的自發斗爭。”[8]劉焜煬在給《廣東三元里抗英斗爭》一書的書評中也指出:“三元里的抗英斗爭,是工農勞動人民與地方士紳的一種自發的聯合行動,說哪一個階級領導了這次斗爭,都是缺乏科學依據的。”[9]何若鈞在1962年的文章中認為,社學在三元里抗英斗爭中并沒有起過組織和領導的作用,但他承認士紳的地位及社學的固有影響在動員群眾方面的積極作用。[10]但是,這些不同的聲音在當時并未引起學界的應有重視。
這一時期,學者們對三元里抗英事件的意義也進行了闡述,但大多在強調人民群眾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有意抬高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陳錫祺教授指出,三元里抗英斗爭“是廣東人民對外國侵略者長期積憤的爆發,是拯救祖國解廣州之圍的斗爭”。它的勝利“完全證明中國人民有力量擊敗任何敢于來犯的侵略者。”[11]趙矢元在1962年的文章中也指出,“三元里抗英斗爭是近代中國人民自發的武裝反殖民主義斗爭的第一聲,它是中國人民反帝斗爭的光輝前導,它激勵了人們在近百年民族危難時刻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意志和勝利的信心。”[12]
總之,這一時期關于三元里斗爭的研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研究歷史,階級性比較明顯,突出強調人民群眾在三元里抗英斗爭中的作用。這一時期研究還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研究內容、主題比較單一,并且緊隨政治形勢的發展,具有極強的時代特色。
三、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研究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思想的解放,國內學術研究不斷拓寬視野,逐漸多元化。在此背景下,有關三元里抗英斗爭的研究也進一步深化,而此前的一些研究結論也逐漸得到進一步的補充與修正。
首先學者們仍然圍繞三元里抗英斗爭的領導問題逐漸展開。1979年卞哲在《讀書》雜志上發表《研究和編寫歷史必須實事求是》一文,對“文化大革命時期史學界存在偽造歷史的現象,對踐踏實事求是學風的做法進行批判。此文指出,三元里抗英雖然是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第一個英勇戰斗,但“三元里抗英畢竟是人民自發的局部地區的斗爭,對整個戰爭的結局不可能起決定性作用。”“三元里的抗英斗爭是以農民群眾為主要力量,但是不能否認地主階級在當時起了組織領導作用。”[13]隨后,陸力在《讀書》雜志第8期發表文章,對此種觀點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地主階級在三元里抗英斗爭并沒有起到組織領導作用,說卞哲是“揭橥反對‘唯成分論’,但反到隔壁去了,變成另一種‘唯成分論’。”[14]田用針對陸力的觀點,在1980年又撰文參與此次爭論中。他直接指出三元里抗英斗爭的領導人是舉人何玉成。[15]之后卞哲又發文來反駁陸力的觀點,指出三元里抗英斗爭領導者多是地主階級的愛國士紳。[16]
這些爭論無疑進一步深化了三元里抗英斗爭的研究。卞哲的觀點打破原有的“禁區”,得到了當時學界的認同。后來林增平教授在1980年的文章中也指出,長期以來“一些著作、教材,隱諱真實的史料,牽強附會地引用不完全可靠的傳聞和訪問記錄,把三元里抗英寫成了由農民領導、農民組成的一支有組織的武裝。”他認為“三元里抗英的主力確實是農民,也無疑應高度評價,但首倡的確為愛國的地主士紳,則是事實。”[17]吳杰在1983年也指出,三元里抗英斗爭是自發興起的,“在斗爭的過程中,舉人何玉成聯絡各鄉,領導和組織鄉民共同抗英,對斗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18]廣州史學界在1991年舉行了紀念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15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學者們就三元里抗英斗爭的領導、性質等問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認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是各階層愛國群眾的聯合斗爭,是反侵略的聯合陣線。”“在三元里抗英斗爭前,已經有人在策劃組織人民的反抗斗爭,三元里人民遭到騷掠,實為一個導火線。愛國士紳何玉成等人的領導組織作用不可否認。韋紹光作為一個青年農民不可能成為這場大規模斗爭的領導者是顯而易見的,但韋紹光作為發難者,其功亦不可沒。”“從本質上說,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是一場各階層愛國群眾的自發斗爭。”[19]1994年,姚敬恒在文章中也指出,“三元里抗英是廣州北郊農民反抗英軍侵略暴行的武裝自衛斗爭”,與社學無關,更不是由社學組織領導。[20]劉寶軍在2004年也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其主要觀點與以上學者的觀點相似,不再贅述。[21]李穗梅則認為,社學在此次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指出,“正是社學的發動與組織,三元里的地理與人和的優勢才在這場戰役中發揮出來。”[22]美國學者魏斐德在1988年出版的《大門口的陌生人》[23]中文版一書中也指出,三元里抗英斗爭“既非純粹自發,也非農民領導,它是團練組織中的一類,依賴于士紳們謹慎而得到官府準許的領導。”[24]
這一時期關于三元里斗爭研究的最前沿的成果當屬茅海建教授在1995年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的《三元里抗英史實辨證》一文。該文利用中西方檔案,從考證的角度入手,對三元里抗英斗爭的起因、過程、結果進行了研究,糾正和補充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結論。如就前文提到的所討論的三元里抗英斗爭的領導問題,作者認為此一問題在今天看來已經失去了意義,重要的在于“通過領導人的辨認,弄清參加這一事件的主體。”參加抗英的組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鄉紳、官府和普通民眾都參與其中,這三類組織界限很難明確劃分。作者還對中文文獻內一些基本事實進行考證,中文文獻記載此次戰斗斬獲了英軍軍官伯麥和霞畢,作者通過對中英文獻的考證指出并沒有此事。作者還就中英文獻所記載的殲敵人數進行考證。他從軍事學的角度認為三元里抗英斗爭雖然有意義,“但其作用有限,其戰果大小的分歧對評價此次事件并無決定性價值。”[25]關于三元里之役英軍死亡多少及其中文文獻中所記載的被擊斃的英軍軍官霞畢是誰等問題,趙立人教授也在1993年進行了考證,所得結論與茅文大致相似,但此文要比茅文更早,特此說明。[26]
這一時期,由于意識形態對學術研究的影響逐漸減弱,因此,學者們從對三元里抗英斗爭的評價也更為客觀。長期以來,三元里抗英斗爭被認為是近代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的第一次群眾愛國行動,此說受到學者們的質疑。茅海建認為三元里民眾抗英斗爭雖然值得稱頌,“但將之提升至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精神展示,則脫離了當時的時代。”[27]美國學者魏斐德也指出,在三元里這樣的農村“很難發現強烈的民族意識”。在廣東省,他們有著“強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緒。”[28]李磊同樣也認為,“對三元里人民抗英用‘愛國精神’評價,可以理解,然而不合乎歷史實‘情’,違背了歷史真實性的原則。突出歷史教育功效的同時還應尊重歷史本來的面貌。”[29]但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不同看法。李錦全就茅海建上述提出的看法進行反駁,他認為“三元里群眾反擊英國侵略者是一場即是保家又是衛國的斗爭是不容分割的。”充分體現了嶺南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30]王明前則認為三元里抗英斗爭在以保衛家鄉為行動主旨的同時,也不自覺地承擔起反侵略的歷史責任,并不必苛求是否具有近代民族意識。[31]
步入21世紀以后,對三元里抗英斗爭研究方法更為多樣,內容更為多元。曾維用社會學的方法分別從三元里與清政府、三元里與英國侵略者之間的關系的角度探討三元里斗爭發生的原因,[32]進一步豐富了前人的研究結論。他在2010年所寫的碩士論文《三元里民眾抗英事件新探》可以說是新世紀以后對此次事件本身最為系統的研究。此文運用社會學的方法,結合文獻考證對此次事件的起因、過程、結果、影響以及評價五個方面進行了論述。[33]還有一些學者研究武術在三元里抗英斗爭中所起的作用。[34]趙亮從教學的角度探討這一事件,他指出“由于一些具體學術爭議在網絡背景下的泛社會化而對教學工作提出了挑戰。這就要求‘三元里抗英’教學應在順向追蹤與逆向觀照的雙重維度展開。有關此事件的教學技術探討,提示在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教學中,應注重對近代國難頻仍的背景下,民眾生存生活狀態和行為選擇的考察,確保相關史料利用的確度、信度與導向,從而誘發學生積極思考國家命運與個人命運的關系。”[35]
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后關于三元里抗英斗爭的研究,從研究主題上看更為多樣,學者們不僅對三元里本身事件進行研究,而且對其相關問題也進行了研究。從研究方法上看逐漸淡化對此事件政治性質的判斷,突破原有的意識形態的影響,運用多種方法,特別是微觀的考證與實證的研究,對此次事件發生的具體過程進行細致的還原,尤其是茅海建教授的研究。當然,由于此次事件的重要性,相關研究眾多,筆者難免會掛一漏萬。但是以上的研究成果足以反映出新中國成立七十年間關于三元里抗英斗爭研究大體趨勢與問題。
四、不足與展望
總體上看,新中國成立七十年,關于此次事件的研究以20世紀80年代為界分為兩個時期。在80年代以前,著重于肯定民眾反侵略斗爭的意義,歌頌民眾不畏強暴英勇反抗的精神,帶有極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很多的研究結論并不符合歷史事實。80年代之后,隨著研究角度的不斷更新、視野的不斷拓展,對之前的研究結論進行修正與補充的同時,還開拓出不少新的內容,提出了眾多的新觀點。作為一次地方性的事件,能有如此眾多的研究成果,足見此次事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但步入21世紀以后,關于此一事件的研究逐漸淡出學者們的視野,在中國知網中輸入“三元里抗英斗爭”主題詞,所出來的文章最晚的一篇是在2015年,而且這一年只有這一篇,還不是三元里抗英斗爭的研究,只是與此相關的。[36]這雖然不能說明學者們近年在這一問題研究上停滯,但至少可以說明這一事件的研究熱度在逐漸下降。
今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致信祝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強調“希望我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繼承優良傳統,整治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著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力,推動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展,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切實增強做好新時代中國歷史研究的責任感使命感,研究好中國歷史、廣東歷史。例如如何深化三元里抗英斗爭事件的研究,成為學術界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首先,從資料的使用上,三元里抗英斗爭涉及到中英雙方,在當時雙方都記述下了這一事件,因此在資料的使用上必須運用雙方資料互相印證才能梳理出此次事件的本來面貌。但是從以上介紹的文章中看出,幾乎所有的文章在資料使用上都是用中文資料,只有茅海建教授的《三元里抗英史實辨證》一文運用有少量英文檔案。即便是中文材料,大多都是使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三元里抗英斗爭史料》和《鴉片戰爭》兩類書。要想進一步深化三元里抗英斗爭的研究,必須在資料方面有所突破。前文可以看出,就英文檔案的資料翻譯出版工作仍然非常滯后。針對以上缺陷,在科技不斷進步、全球交流越來越頻繁的今天,必須深挖有關三元里抗英斗爭的外文資料。面對晚清史研究的下行趨勢,朱滸教授在2017年《史學月刊》所組織的筆談文章中強調晚清史研究的“深翻”。所謂“深翻”,其中一個方面就是“需要深入勘查以往研究賴以立論的資料基礎,找出其資料上的局限與運用上的缺陷,繼而再重審舊資料、挖掘相關新資料,通過對新舊資料的融會貫通,最終形成對相關史事的準確解讀。”[37]這對進一步深化三元里抗英斗爭的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其次,在研究的主題、方法、視角上仍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深化的地方。雖然改革開放以后有關這一事件的研究在研究方法、視角上逐漸多元化,但是從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真正有影響、突破性的著作并沒有。這提醒學術界要想進一步在這一事件的研究上取得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必須在這些方面下功夫。如三元里抗英斗爭作為一個地方性事件,如何一步步被國家塑造成今天大家都熟知的歷史事件,它是如何傳播,在傳播的過程中國家與地方社會是如何互動。對這些問題可以運用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等方法對這一事件展開研究。羅志田在研究“五四”時的歷史記憶問題時,指出“雖然,‘五四精神’不斷被提及,我們歷史記憶中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呈現出一種明顯的斷裂意味,這一運動與后之歷史發展的關聯,除了一些經特別選擇而得到反復強調的面相,仍然模糊。”[38]事實上,三元里抗英斗爭存在同樣問題。在今天,“三元里精神”不時被提及,在不斷強調這種精神的同時,往往忽略眾多的其他事實。因此,人們也可以從當下興起的記憶史學的角度來對此問題進行研究。再如,可以轉換研究視角來對這一事件進行研究,三元里抗英涉及到中英雙方,可以把它放置到中英關系史中來考察,同時也可以運用全球史的觀點來研究。總之,在史學方法、視角不斷推陳出新的今天,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即是深化這一事件研究的需要,同時也是時代的要求,這樣才能看到關于三元里抗英斗爭的不同面相。
第三,要進一步深化這一事件的研究,必須擺脫固定的思維模式。三元里抗英斗爭是一次政治性質的事件,一直被國家當作民眾愛國主義的典范被寫進教材,這種做法從宣傳角度說是正確的。但是,在學術研究時必須從事實出發考察這一事件。其次,三元里抗英斗爭作為一次反對英國侵略者的地方性事件,在筆者看來,現在并不一定需要爭論三元里斗爭的本身,雖然求真是史學工作者的終極目標,從另一方面說,每一個時代都有切合每一個時代的歷史學,所以,更應該探討的是為什么三元里抗英斗爭,能被如此重視,如何將它的問題意識切合現實的需要。
注釋:
[1]廖獻周、呂器:《深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史的研究——為紀念館慶45周年而作》,《嶺南文史》1998年第2期。
[2]莊建平:《鴉片戰爭資料簡述》,《歷史教學》1988年第11期。
[3]參見陳錫祺:《廣東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廣東人民出版社,1956。
[4]參見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史料》,中華書局,1978。
[5][25]茅海建:《三元里抗英史實辨正》,《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
[6]陳錫祺:《廣東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第24頁。
[7][11]陳錫祺:《鴉片戰爭時期廣東人民的反侵略斗爭——紀念廣東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120周年》,《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1年第2期。
[8]李龍潛、盧權、吳祖塘:《廣東三元里人民反對英國侵略者的斗爭》,《歷史教學》1955年第8期。
[9]劉焜煬:《“執挺以撻堅甲利兵”!——評介“廣東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讀書月報》1957年第2期。
[10]何若鈞:《鴉片戰爭時期廣州人民的反侵略斗爭不是社學領導的》,《學術研究》1962年第2期。
[12]趙矢元:《三元里抗英起義及其歷史意義》,《歷史教學》1962年第6期。
[13]卞哲:《研究和編寫歷史必須實事求是》,《讀書》1979年第2期。
[14]陸力:《關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的領導問題》,《讀書》1979年第8期。
[15]田用:《何玉成冤詞——三元里抗英斗爭領導問題的我見》,《史學月刊》1980年第1期。
[16]卞哲:《答陸力同志》,《讀書》1980年第2期。
[17]林增平:《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江西社會科學》1980年第00期。
[18]吳杰:《三元里抗英斗爭組織者考》,《歷史教學》1983年第9期。
[19]駱驛:《繼承反侵略斗爭傳統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紀念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150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開放時代》1991年第5期。
[20]姚敬恒:《廣州三元里抗英斗爭考》,《貴州文史叢刊》1994年第6期。
[21]參見劉寶軍:《三元里抗英斗爭領導問題之我見》,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22]李穗梅:《論鴉片戰爭時期廣州民眾抗英斗爭的漸進》,《廣東史志》2001年第4期。
[23]此書為作者的博士論文,在20世紀60年代已出版。
[24][28][美]魏斐德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新星出版社,第45、65頁,2014。
[26]趙立人:《鴉片戰爭考釋兩則》。《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7]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313頁,2014。
[29]李磊:《三元里評價合理不合情》,《歷史教學》2010年第19期。
[30]李錦全:《鴉片戰爭時期嶺南人士的愛國情懷》,《嶺南文史》1999年第3期。
[31]王明前:《鴉片戰爭前后中國沿海的地方軍事化與紳權伸張》,《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32]曾維:《從兩種關系看三元里抗英事件》,《社科縱橫》2009年第2期。
[33]曾維:《三元里民眾抗英事件新探》,四川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4月。
[34]陳燕、翟波宇:《基于三元里抗英斗爭研究清代民間武術》,《蘭臺世界》2014年第7期。
[35]趙亮:《近代中國國難史教學技術探討》,《歷史教學》2014年第16期。
[36]檢索時間:2018年8月9日16點20分。網址: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
[37]朱滸:《晚清史研究的“深翻”》。《史學月刊》2017年第8期。
[38]羅志田:《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復旦大學出版社,第116頁,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