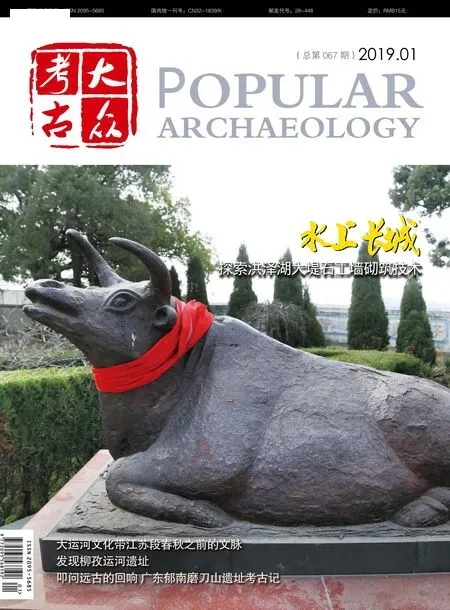方興未艾的中國大運河考古
考古學的新發現一是通過田野發掘獲取,二是通過對當代社會提出的新問題、新理念做出的回應所獲取。中國大運河考古同時具備這兩方面特點。在中國古代的工程創造中,有兩項作品聞名世界,一是東西走向崛起于地上的長城,一是南北走向深鑿于地下的大運河。它們一剛一柔,幾乎都起源于2500年前左右的東周時代,作為文化遺產形態,則一直保存到當代乃至未來。不過,大運河與長城不同的是,直到今天,它的大部分河段還是活態的,持續滋養著運河兩岸的千家萬戶。
東周至南北朝時期,大運河更多呈現的是局域性運河的形態,隋唐時期開始形成真正全國性的南北大運河,當時它西抵長安,北通涿郡,南達杭州,全長2700多公里,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連接了華北、黃淮和長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了長安—洛陽為軸心的全國性水運物流網。到北宋,這個水運中心東移首都東京(今開封);南宋又以杭州為大運河中心,杭州至寧波的浙東運河同時得以繁榮。元明清三代,大運河直接從河北入山東,南接江蘇,形成了以北京中心、全長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運河體系。可以認為,2000多年來,大運河使得中國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海上絲路和陸上絲路、人工河道與天然河道、北方區域與南方區域、經濟基礎和文化創造相互溝通、融合,為保障國家治理系統的安全和國土統一作出過難以想象的貢獻。不過,在傳統理念中,大運河是一項偉大的水運事業,人們看中的是它的運輸和水利價值。近30年來,它博大而深厚的文化價值才得到初步認知,被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形態而呈現于世人眼中。導致這種理念產生的重要原因,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文化線路”遺產實踐。1993年,“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次年,“文化線路”世界遺產專家會議在馬德里召開,“文化線路”作為一種新型文化遺產的學術概念、定義、判斷標準等形成了學術共識。2005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15屆大會在西安召開,通過了《文化線路憲章》(草案)。此后,大運河申遺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在國家文物局的主導下,配合申遺的大運河考古進入了大面積開展的新時期。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順利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但是大運河考古卻并未終結,2017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批示:“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此后,由8省市共同參與的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拉開帷幕,大運河考古又承擔了新的歷史使命。
大運河考古作為一項專題性考古,涉及面寬廣,包括大運河河床本體、河防工程、船閘、堤壩、分水樞紐工程,大運河涉及的城鎮、鄉村、碼頭、橋梁、沉船或船舶、倉儲設施、關防設施、宗教設施、管理設施,大運河上豐富多彩的運輸物資如糧食、陶瓷、木材、鹽茶、磚石、文化用品等,以及大運河涉及到的人物遺存、中外文化交流遺跡遺物等。考古研究的目標至少應包括大運河的歷史、文化、交通、工商業、水利、科技、生態環境、宗教、外交等以及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利用等諸多方向。從學術史角度而言,大運河考古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已經開始,如1969年與大運河直接相關的國家倉儲遺存——洛陽隋唐含嘉倉遺址的發掘,1999年在濉溪柳孜村發現隋唐大運河河道、沉船、陶瓷器等遺物;2004年,我們也主持了唐宋大運河重鎮泗州城址的考古勘探等。但是,主動的、系統的大運河考古還是在國家文物局主導的大運河申遺后才逐步深化的。近年來,各地考古單位對宿州西關步行街汴河遺址、宿州老環城路內宋代碼頭遺址、泗州城遺址、汶上南旺分水樞紐工程及分水龍王廟遺址、隋唐洛口倉遺址、中牟官渡鎮汴河河段天然“水柜”遺存、靈壁隋唐運河遺址、高郵大運河故道平津堰遺址等進行了發掘。這些大運河考古項目不僅揭示了大運河的形態演變和復雜內涵,而且以許多前所未知的內容展現了大運河所長期孕育的有關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成就,為全面真實地向世人展現大運河文化的源遠流長、深厚博大提供了獨特的材料和視角,一批建立在考古發現基礎上的博物館、遺址公園也應運而生。
當然,千年流淌的大運河積淀了太多的歷史內涵和文化篇章,迄今為止的大運河考古在數千公里長的運河線路上還僅僅是九牛一毛,隨著對作為文化線路類世界遺產保護及研究事業的不斷發展,隨著大運河文化帶及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不斷深入,大運河還會給考古人提出無數的問題,呼喚有志者去發掘去探討去展現。或者說,大運河考古作為大運河歷史與文化認知及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的基礎性、細節性、深厚性、實證性的科學事業,理應得到政府、社會、專業等各方面的更多支持和推進,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運河考古真可謂方興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