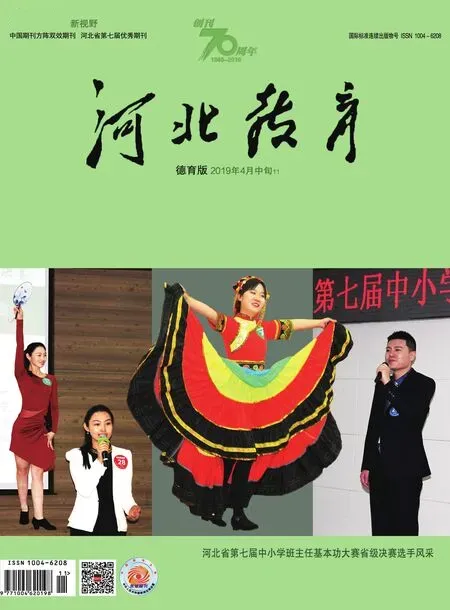“一代文人有厄”
——王冕的詩意與失落
○徐新武

提起王冕,我們當不陌生。小學語文課本上早就有那首家喻戶曉的《墨梅》詩,那句“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也是我們認識王冕高潔品性的最初印象。而在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王冕的形象更加生動豐滿,他是吳敬梓一生致力效仿的賢達,是一個官場士林的積極逃遁者。
在小說“楔子”部分,吳敬梓以詩意的語言讓王冕出場。王冕從小生長在諸暨縣的一個小鄉村,七歲亡父,母親無力繼續供養他讀書,便給鄰居秦老放牛寄生。他放牛讀書的地方,草樹連天,湖水彌漫,宛似古畫。一日,恰是黃梅天氣,王冕疲倦,有些煩悶。須臾,濃云密布,大雨下來,王冕看見“那黑云邊上,鑲著白云,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山上,青一塊,紫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里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這完全是以一個孩童之眼來觀看自然之美,而環境的美是與人情的美相聯系的,王冕的慧性和純粹也透漏出來。從此得錢不再買書,而“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自然不久,這荷花畫得“精神、顏色無一不像”,畫畫的名氣漸長,生活也充裕起來。
與他人皓首窮經不同,王冕不到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王冕讀書既不為做官,也不為結交各類朋友,讀書時看見《楚辭圖》上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時節,乘一輛牛車載了母親,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著鞭子,口里唱著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玩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群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這完全是魏晉名流放誕任性、追求自我的作風,他效仿志行高潔的屈原,樂在享受生活,并不在意他人眼光。《論語·先進》篇記載孔子和眾弟子談論志向,其中曾晳(又名曾點)說自己的理想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不由喟嘆“吾與點也”。曾晳還只是想著自己能夠在暮春閑暇時,與大人小孩一起游于沂水,吹著暖風,歌詠而歸,而王冕是真正把這種詩意的“理想”落實到日常生活當中。
諸暨縣的時知縣得知王冕大名后,便拿著他的花卉冊頁去討好上司危素。這危素得知故鄉有如此賢士,想要結識,時知縣自然想到這是一個很好的表現機會。高傲又諂媚的時知縣是那個時代官僚階層的一個縮影。王冕隨即表現了不合作的態度,閉門外出,他深知“時知縣倚著危素的勢,要在這里酷虐小民,無所不為。這樣的人,我為甚么要結交他”,隨后擔心危素惱怒,遂辭別老母,遠避濟南,靠問卜賣畫為生。
在山東王冕又遭遇黃河大水,流民四散,而預感“天下自此將大亂”,便返浙回鄉。后朱元璋來會,一方是真儒,一方是豪杰,卻相談甚歡,朱問如何服民心,王冕只道“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這種仁義治國的道理早就是老生常談,而在王冕說來,卻有足以動人的真誠和力量。隨后朱元璋定鼎天下,朝廷征聘他出來做官,他連夜逃往會稽山,后得病離世。吳敬梓在文末嘆惋:“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王冕自然是不屑于此類對“參軍”官銜的附加,恐怕他只愿在塵世的嘈雜中做一個凡夫俗子,讀書作畫,如此而已。
王冕并不離經叛道,也不是刻意與別人相異,他對生活和現實有著透徹明白的理解。王冕對古代賢人隱士的追摹,是因為他心中有一個尚未失落的理想。他詩意而執著,就像孔子一生致力于對上古三代禮法社會的恢復與建設,雖然無望,卻積極而堅定。他能和朱元璋坐而論道,也能全身而退,他積極逃遁,卻不遠離人間煙火,并不算嚴格意義上的“隱士”。然而王冕詩意棲居的社會土壤畢竟沒有了,他只有恪守內心的召喚,才不會被混亂的士林裹挾而去。
吳敬梓筆下的王冕,其形象大多承襲自明代宋濂寫的《王冕傳》,而刻畫更為細密深入。吳敬梓有意在小說的開頭就塑造這么一位“狂士”,正是為了突顯書中整個士林階層人文價值的失落和混亂。在科舉取士的僵化教條下,讀書人只憑此一條晉身之路,自然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正如商偉在《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一書中所評,“八股取士制度造成了不擇手段的競爭、偏狹、瘋狂、人格破產、以成敗論人和唯官是從的勢利心態、官場腐敗與價值失落,以及文人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制度性的言行不一、名實不符和表里分離。”這種文人生活普遍失范的荒謬現象,不正是“一代文人有厄”的最好體現么?
王冕之后,科舉制度所籠罩下的士林社會,無論是在小說還是現實中,都以群魔亂舞的姿態,上演著種種鬧劇和丑劇。而王冕的清醒之處在于他看到了:科舉制度一旦固化,士人為了仕途名利自然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必然會導致士林社會價值觀的變異,從而漠視自我修持的價值以及對社會的責任和關懷。王冕的失落之處也在于“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所以他只能優游狂傲,保持自我的一份獨立與持守,顯得悲哀又孤獨。這是制度性的社會文化悲哀,是科舉制度模式化以后所導致的士林價值的集體潰敗,對此王冕無能無力,只能高標自我。
閑齋老人說《儒林外史》的主旨是“以辭卻功名富貴、品第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很明顯,王冕正是吳敬梓所要致力塑造的“中流砥柱”。然而現實社會中能有幾個“王冕”存在?宋濂的《王冕傳》記載: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之“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高庭下,備奴使哉?”。王冕寧愿躬耕南畝,讀書自樂,也不與官場合作,顯示了其對仕途決絕的對抗態度。
王冕的生活有多詩意,他在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就有多失落。換句話說,吳敬梓筆下的王冕有多詩意,他所依存的士林社會就有多混亂。王冕所堅守的真“士”的社會土壤已經逐步被侵蝕了,他的一切看似悖反常知的行為,都類似一種孤勇的反抗,他清醒而痛苦,“詩意”恐怕也只是世俗的附加。在小說的最末,吳敬梓借用一首詞結尾,中有兩句“把衣冠蟬蛻,濯足滄浪。無聊且酌霞觴,喚幾個新知醉一場”。清醒的吳敬梓無論如何“濯足滄浪”,也沒能活成王冕那樣,一代代文人的厄運,就這樣持久地上演,并最終消散在歷史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