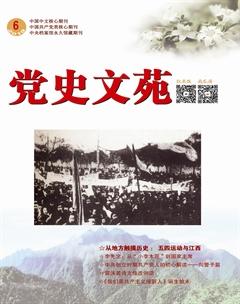郭沫若詩(shī)文修改例話
朱永芳
學(xué)富五車、才高八斗的郭沫若,無(wú)論是作詩(shī),還是寫劇本,常常是“妙思泉涌,奔赴筆下”。就是這么一個(gè)才子詩(shī)人、文壇巨擘,也是非常重視修改這一重要環(huán)節(jié)的。他寫《孔雀膽》“雖然只費(fèi)了五天,但改卻費(fèi)了二十天以上”。寫《蔡文姬》“費(fèi)了七天工夫。但其后在上海,在濟(jì)南,在北京,都修改過(guò)多次”。而劇本《武則天》自初稿發(fā)表的近兩年半的時(shí)間里,則“進(jìn)行了很多次的修改”。他認(rèn)為“文章寫好后,要翻來(lái)復(fù)去地推敲一下”,要“多讀幾遍,多改幾遍”。這是他的經(jīng)驗(yàn)之談,也是他的成功要訣。郭老有關(guān)修改的“理論”與實(shí)踐,再次雄辯地證明了認(rèn)真細(xì)致的反復(fù)修改對(duì)于精品佳作的“出爐”,是何等的重要與必要。才情橫溢、著作等身的郭老在為我們創(chuàng)作了數(shù)量可觀的經(jīng)典的同時(shí),也給我們留下了不少修改佳話。
1942年春夏之交,郭沫若的大型歷史劇《屈原》在山城重慶公演,反響強(qiáng)烈。作為編劇的郭沫若自然要常去觀摩。在劇本上演三四次后的一個(gè)晚上,他與扮演屈原侍女嬋娟的張瑞芳在后臺(tái)談起了第五幕第一場(chǎng)中嬋娟滿懷憤懣痛斥背叛老師的宋玉的一句臺(tái)詞:“宋玉,我特別的恨你,你辜負(fù)了先生的教訓(xùn),你是沒(méi)有骨氣的文人!”郭沫若說(shuō):“在臺(tái)下聽(tīng)起來(lái),這話總覺(jué)得有點(diǎn)不夠味。似乎可以在‘沒(méi)有骨氣的下面再加上‘無(wú)恥的三個(gè)字。”張瑞芳沒(méi)有馬上回答。她站起來(lái),學(xué)著舞臺(tái)上的動(dòng)作和各種語(yǔ)氣表演了一番,最后搖頭道:“好像還是不大夠味兒!”“還是不大夠味兒?”郭沫若似乎有點(diǎn)為難了,他一時(shí)實(shí)在找不出更滿意、更恰當(dāng)?shù)脑拋?lái)代替它。正在一旁化妝的張逸生(劇中釣者的扮演者)插話說(shuō):“‘你是不如改成‘你這。‘你這沒(méi)有骨氣的文人!那就夠味了。”郭沫若聽(tīng)了大受啟發(fā),覺(jué)得這一個(gè)字真是改得非常恰當(dāng)。從語(yǔ)氣的角度來(lái)說(shuō),“你是沒(méi)有骨氣的文人”只是單純的敘述語(yǔ),缺乏強(qiáng)烈的感情色彩。而改為“你這沒(méi)有骨氣的文人”,則成了堅(jiān)決的判斷句,省略了“你真該死!”“你真不是東西!”或“你真是禽獸!”之類極度強(qiáng)烈的語(yǔ)句,就像是指著宋玉的鼻子痛罵他的卑劣無(wú)恥一樣,當(dāng)然比一般的陳述句感情強(qiáng)烈而語(yǔ)氣有力。改“是”為“這”,的確增強(qiáng)了語(yǔ)勢(shì)。同年5月30日,郭沫若在《瓦石札記·一字之師》一文中特地記載了這段修改佳話,附在《屈原》劇本之后,盛贊張逸生為“一字之師”。
6月26日,郭沫若應(yīng)邀從重慶天官府到北碚去觀看《屈原》演出。他抱起自家插花用的大瓷瓶,準(zhǔn)備給劇中的嬋娟當(dāng)?shù)谰哂谩M局胁磺捎鲇辏s到劇社,詩(shī)興頓生,脫口吟出一首打油詩(shī)。詩(shī)曰:“不辭千里抱瓶來(lái),此日沉陰竟未開(kāi)。敢是抱瓶成大錯(cuò)?梅霖怒灑北碚苔。”演員們聽(tīng)后,有人風(fēng)趣地向他建議說(shuō):“兩個(gè)‘抱瓶重復(fù)了,不太好。不如把第三句改為‘敢是熱情驚大士。”理由是郭“把觀音大士驚動(dòng)了, 所以才下雨啦”。飾演嬋娟的演員張瑞芳也插嘴道:“這‘怒字太兇了一點(diǎn)。”郭馬上高興地表示:“好的,我要另外想一個(gè)字來(lái)改正。”趁演員出場(chǎng)之際,他提筆沉吟:先是將“怒”字改為“遍”字,似覺(jué)不妥;繼而改為“透”,仍感不好;最后決定改為“惠”字。張瑞芳下場(chǎng)一看,連連稱贊說(shuō):“對(duì)啦,這個(gè)字改得蠻好蠻好。”過(guò)了不久,雨停了,《屈原》順利地演出五場(chǎng)。郭非常高興,風(fēng)趣地說(shuō):“農(nóng)人劇人皆大歡喜,惠哉,惠哉。” 一個(gè)“惠”字很好地表現(xiàn)了觀音大士賜予的恩惠,這樣與第三句的感情基調(diào)協(xié)和。“作詩(shī)安能落筆便好?”郭沫若精心選詞的改詩(shī)逸事,再次為“好詩(shī)是改出來(lái)的”作了一個(gè)形象注腳。
1962年夏,郭沫若收到四川省中江縣(現(xiàn)屬德陽(yáng)市)黃繼光紀(jì)念館籌委會(huì)邀請(qǐng)其為烈士題詞的信函。收到邀請(qǐng)函的他很快完成了對(duì)聯(lián)創(chuàng)作:
血肉作干城,烈愾在火中長(zhǎng)嘯;
光榮歸黨國(guó),英風(fēng)使天下同欽。
上聯(lián)的最末兩字原為“永在”,寫好后作者發(fā)覺(jué)上聯(lián)里出現(xiàn)了兩個(gè)“在”字,不妥,需要改。郭老感到“永在”是死字眼,而英烈是永遠(yuǎn)活著的,永遠(yuǎn)在呼嘯前進(jìn),于是改作“長(zhǎng)嘯”。這一改就使全句變活了。郭老對(duì)此修改還比較滿意。
對(duì)聯(lián)寫出來(lái)了,匾額寫什么呢?郭老為此煞費(fèi)苦心,頗費(fèi)周章。他起先想用“永垂不朽”“浩氣長(zhǎng)存”“氣壯山河”等現(xiàn)成詞語(yǔ),覺(jué)得這些太俗套、缺乏新意,棄而不用。接著想了個(gè)“藩翰中朝”,又感到“藩翰”(喻捍衛(wèi)王室的重臣)雖典雅,但生僻,圈去未用。后又改為“火中鳳凰”“青年師表”“人民模范”,又覺(jué)空而不切。再又改為“血鑄和平”“國(guó)際英雄”,依然覺(jué)得和聯(lián)語(yǔ)扣合不緊,也不稱意。就這樣,郭老前前后后共擬了20多個(gè),最后才確定用“凱歌百代”作為匾額。這四個(gè)字既通俗易懂,又意味深長(zhǎng):寫出了黃繼光精神的內(nèi)涵和深遠(yuǎn)影響,與聯(lián)語(yǔ)珠聯(lián)璧合、相得益彰,起到了畫龍點(diǎn)睛的作用。郭老手書的那四個(gè)雄勁豪放、蒼勁有力的鎏金大字——“凱歌百代”至今仍然在紀(jì)念館黃繼光雕像后面的白色照壁上熠熠閃光。郭沫若精益求精,不厭其煩,琢磨推敲題詞的佳話確實(shí)值得我們大書特書。
古人云:“世人之著述,不能無(wú)病……有不善者,應(yīng)時(shí)改定。”文章不厭百回改,像郭沫若這樣才思敏捷的大手筆猶能“不以一時(shí)筆快為定,而憚?dòng)趯腋摹保螞r我們這些初學(xué)者呢?郭沫若一絲不茍、不憚屢改的寫作精神值得我們大家學(xué)習(xí)。要想詩(shī)文寫得好,多寫多改不可少。“改之又改,方成無(wú)瑕之玉。”請(qǐng)記住郭沫若的諄諄告誡吧——“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鐵杵是可以磨成針的。”
責(zé)任編輯 / 陳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