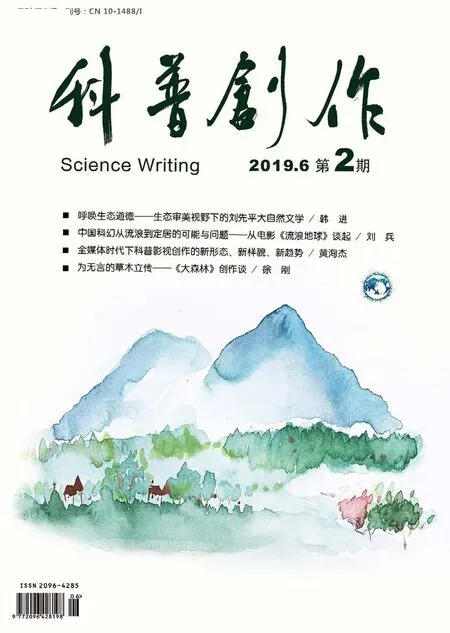為無言的草木立傳
——《大森林》創作談
徐 剛
一、帶著蘆蕩風雨的氣息

圖1 《大森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5月), 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我的自然文學創作自1988年于《新觀察》發表《伐木者,醒來》始,2017年出版的《大森林》,可稱是尾聲了。從頭至尾恰好30年,彈指一揮間啊!于今想來,所謂其始其尾均是相對而言的。自命運把我——一個小小的生命精靈,降生在長江邊緣的大蘆蕩邊開始,因為自幼失怙,少小時便與守寡的母親一起,面對著崇明島西北角的農田與荒野。我記事時是在20世紀50年代,那時我家鄉的蘆葦比莊稼多,荒野比農田多,不僅缺吃的還缺柴火。七八歲時,我便于秋冬時節,跟母親一起到“北海”邊沿蘆葦一望無盡處拾柴了——干枯的、折斷的蘆葦——農人稱之為蘆柴。“北海”是我母親和鄉人留下的名字,其實是長江流經崇明島時一分為二的北支,我上了初中讀鄉土地理時才知道。我曾經問過母親和鄉人,何以稱之為北海?所答皆同:大水就是海,有莊子遺風矣!
小時候崇明島上的氣候,與今天大不相同,夏秋多雨多風暴,冬日則冰天雪地,間有西北風。我打小就愛下雨的日子,聽雨、看雨,綿綿細細的春雨秋雨也好,能把楊樹按在地上的疾風暴雨也好,我都會在家門口呆看呆想:誰在天上潑的水?雨點怎能連成線?風為什么把雨絲折彎……只要風雨小了點,我便會跑出屋去,沐浴風雨,在鄉間的泥濘小道上奔跑,加上我自小好胡思亂想,母親曾擔心過,“這兒子會不會有什么精神病?”
其實就是對風雨敏感一點而已,如今想來少小時大自然的一切賜予,都會留跡于心中,濕漉漉的雨,浩然茫然的大蘆蕩,冬天被雪覆蓋的曠野,還有透風漏雨的茅屋,母親紡紗時如歌的紡車聲和幽明的燈……在某種意義上,寫作就是掏心窩子。倘若找到了能讓你掏心掏肺的題材,你不掏就不得安寧的題材,以及表述的語言,而這些題材和語言,甚至還有濕漉漉的、搖曳生風的感覺,那就是詩和文章了。翻檢舊作,1982年2月,應《雨花》之約,我第一次上黃山,一步步拾級而上,爬上了天都峰。我寫了《綠色抒情詩·五首》,以及《黃山請給我一滴綠》,其中有云:
黃山,請給我一滴綠
從松葉上淌下一滴綠
從草葉上滾下一滴綠
哪怕從生長苔蘚的濕土中
擠出一滴綠……
我是干渴的乞討者
我不缺水
我渴求綠!
還有:
黃山松,你真是萬古不朽的嗎
永恒的生命既然不屬于我
也就不會屬于你
你有松濤百里
為什么沒有一句最珍貴的寄語
世間頌歌太多
何不贊美新綠?
(見拙著《徐剛詩選》,作家出版社2014年11月。)
二、鉤沉與感悟:詩意的寫作
就這樣,我帶著蘆葦的氣息,于1987年寫了《伐木者,醒來》后一發而不可收,《流水不再浪漫》《沉淪的國土》,寫三北防護林體系工程的電視專題片《綠色長城》《中國風沙線》《綠色宣言》《水啊水》《中國,另一種危機》《黃河萬里獨行客》《大壩上的中國》《長江傳》《地球傳》等。由于2010年國家林業局邀我采寫林業改革事宜,一年中從一處大森林,踏進另一處大森林,其間構想,開始了《大森林》的寫作,2017年5月出版第1 版。引出了這么一串并不完整的書目,我是想說,30年就這樣過去了,有了關于自然文學創作的一點體會:積累和堅守。
積累之謂也,當然離不開知識的積累,比如:森林是怎樣形成的?這些資料均能查到,但你用什么樣的筆觸去使用這些資料,卻有講究。我的做法是先走心再走筆,凡是走過心的、心靈浸泡過的,就會“筆端常帶著感情”(梁啟超語),就會有非凡之想,可以說這是思想,但又不是一般的思想,是包含有哲思與文思的“我之思”。如我在《大森林》中寫蜘蛛,這最早出現于石炭紀森林中的動物。“誰能猜測造物者因何造蜘蛛,又因何造出這網羅天下之‘網’?倘說遠古大森林的出現似有方向、似有期待的話,這些古老的蜘蛛古老的網,其指向更為明確:億萬年后,華夏民族的人祖爺伏羲法蜘蛛而織網,開創了人類的漁獵時代。蜘蛛吐絲,懸空織網,編織之類的創造,其為始也。”這一段話并無驚人之語,但卻有我思之所在,且事關古人類生存發展的里程碑之一:從編織麻草不再樹葉蔽體,一直到后來的綢絹錦繡絲綢之路,物質和技術的進化之路,人類文明之路也。
自然文學的創作,不僅僅是見山寫山、見樹寫樹。自然文學的創作必須是詩意的寫作,它是直面現實的,它又是浮想聯翩的,它是敘述簡潔明了的,它又是抒情濃淡自如的。如果我們目中只有眼前的樹,所得的便是膚淺,何以故?一切歷史皆需要鉤沉。森林樹木,陸上生態中樞,大地歷史之主要篇章也。在地球形成、有了草木之后,至石炭紀,“大地上的森林有了大約8000 萬年的相對穩定的氣候、環境,當時地球可稱為森林地球。可是不久便風云突變,火山爆發,地震不斷,山岳或者抬升、或者沉淪,沙漠出現,冰川緩慢而堅定地闖進熱帶,大約到2 億2000 萬年前,石炭紀森林完全毀滅”。這是我在《大森林》中一節關于石炭紀森林的敘述,這些陳述是為煤炭作鋪墊的。大地要造煤了,大地怎樣選煤?大地為誰造煤?煤是這樣煉成的:“石炭紀的林地很多在泥濘沼池中,林木倒地便會下沉,成為泥炭。又因地質運動河流沖擊,這些泥炭越陷越深,越埋越黑,成為褐煤,再經過反復增壓、擠壓,成為無煙煙煤。0.3 米厚的煙煤,至少需要6 米厚的植物層擠壓而成。”這些數據與材料均可查得,但我已經不自覺地帶進了跨學科的寫作中,我重新如中學生一樣讀自然、地理,面對那些我向來認為與文學無關的數字時,忽然覺得數字是可愛的。自然、地理的歷史才是人類物質文明的根本,而“毀滅為創造之初,創造為毀滅之始”,則是我自己的語言,其中有對大自然、大森林在大尺度宇宙空間,在大地之上的火與水的反反復復地錘煉、重壓及擠壓的敬畏。
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生活自然文庫》稱:“雖然近到60年以前仍有科學家認為,煤炭不是由植物形成的,”后來更多證據表明“石炭紀廣袤茂密的森林,幾乎是全部近代工業用煤的原始來源”。作為替代木柴的一種來源,它的問世即意味著一場重大的能源革命的開始,而能源革命以煤炭推動蒸汽機為代表,其轟鳴聲則又宣告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開始。當時正流亡國外的康有為先生在參觀了蒸汽機后認為,中國積弱而不振、而落后、而被列強欺凌,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工業化,而大聲呼號:“汽機力即國力”(《康有為全集》,人民大學出版社)。南海先生,先知也!
為了證明石炭紀森林的繁榮旺盛,世界植物學家皆以中國為例:“中國所產的煤層,有的厚度超過120 米,相當于2440 米原始植物質的厚度。”也就是說120 米厚的煤層的形成,所需林木為2440 米的厚積。如前文所述,一片森林被埋沒后又有新的森林出現,再埋沒,再新生,如是往復。植物質厚積的過程,也是壓力增大的過程,因而變質,因而成煤。當煤作為能源而燃燒時,我們當能讀出它野性的張揚,那是埋沒、擠壓積蓄幾億年之久的激情與能量的釋放啊!它推動著這個世界的飛躍,也見證了人類貪婪無度之后的污染。我在《大森林》及別的書中曾一次次地呼喚:“人啊,你要小心翼翼地接近輝煌!”
我僅僅是在寫樹和森林嗎?非也,我同時也在寫人和社會。我在告誡自己也奉獻給讀者:倘若你曾被埋沒、被擠壓,那就應該獲得恭祝,因為所有這些經歷都是你的財富,你有福了!
人類的歷史通常是被人類自己夸大的,自我夸大的極致,就是不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大地之上,我們不過是萬類萬物之一,可是我們自認萬物之靈,肆意妄為。生物學家說,把地球上植物發生、發展,直到人類出現的歷史,濃縮在一天之內,以最早的微生物發生于午夜為起點,當一天的時間過去六分之五,即晚8 時左右,古海洋中藍綠藻完成了光合作用的程序繁殖旺盛;晚9時以前植物登陸;晚10 時左右石炭紀森林盛極全球;晚11 時以后,始有開花植物發生;午夜結束前十分之一秒時,人類的歷史才告開始。
植物的漫長歷程啊!
森林的艱難時世啊!
沒有這漫長而艱難的歷程,沒有萬類萬物的開拓先行,哪有人類文明史可言?
我曾行走在原始的、人工的、氣象萬千的大森林中,我能感到林中路的神秘和艱難,會想起海德格爾筆下的“林中路”:“路是樹的古名,林中有許多路,這些路多半隱沒在人跡不到之處,叫林中路。每個人各奔前程,但都在同一處森林中。只有從事林業的人及護林員認得這些路,他們懂得什么叫誤入歧途。”在井岡山一處茂密的不見天日的次生林和人工林交織的林地中,我跟著護林員,默念著林中路的那些詩思與哲思編織的語言,我不知道海氏所說的“路是樹的古名”有無出處?倘有,出于何處?但細想之下,這些都不重要了,大哲所言莫不是提醒世間:人啊,只有樹才是引領者,有樹便有路。
三、和實生味
馮友蘭先生有名言傳世:“和實生味,同則不繼。”這里的“和”意指和合、相雜,比如糖和醋共用,能出糖醋味的美食如糖醋排骨之類,但若鹽里加鹽,則除去咸味無他味。我真正感覺到,而且日益強烈地感覺到“和實生味”的美妙,是在自然文學寫作過程中,且始于無奈和彷徨:通常的以水論水,以樹論樹,以山論山,寫不下去了,沒有詞語和文采了。“窮者變,變者通,通者久”(《易經》)。我是在創作實踐中體會到:大地上的一切,都是血脈相連的啊!我們的知識卻是被割斷的,以文理科劃分,文學創作又被分割成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體裁。而我的寫作涉及學科多,使我不得不求變,不得不從頭學起,如生態學、環境學、史地學等。奧爾多·利奧波德《沙鄉年鑒》中的“土地倫理學”,對我的觸動首先是良知和靈魂的,其次才是知識創新結構的:把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倫理學,推向大地之上的所有生命,推向大地的邊緣,那是一種何等美妙的升華!我在寫《大森林》的過程中,清醒地認識到我不是在寫小說,面對大地的過去和現在,我把歷史和地理與森林,以及人類出現之后的森林文化糅合在一起,又汲取了西方自然文學的精華,構建了一個穿越森林創生、人類創生、森林文化創生,以及時代演化的框架。這是足以讓我放縱思絲、聯想天地、敘述古今,而又須落筆謹慎、情動心動的框架。我很難敘述那些對森林、山區、沙漠的感悟,是怎樣從心頭到筆下流出的過程,幸運或者痛苦?艱難或者愉悅?還是兼而有之?過去只是想象沙漠,真正面對騰格里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時,沙丘、沙鏈、沙山、沙海給我的震撼與感慨難以言表,這是大地的一部分啊,這里也有農人在種草種樹……沙漠學家告訴我先有山后有沙漠,沙,細小的、其直徑介于0.05 毫米到2 毫米之間的沙礫,它們渴望過重新高大嗎?只要有樹木和草的陪伴,它們就會如此安詳地鋪陳。懷想當初,沙是風與水的杰作。有時我會在戈壁灘上流連忘返,那些巨石,是誰在什么年代擺放的?為什么排列成此種形態?中國西部大戈壁上的石頭陣,會使人想起造物主的沙盤……奇妙的是這些亂石一律不再嶙峋,所有的棱角都在風吹日炙中光滑圓潤。
風與水揉搓著,揉搓著嶙峋,揉搓著巨大,揉搓成細小。
我身在沙漠,我腳下的沙丘,我口袋里不知何時造訪的沙礫,它們已經存在千百萬年了。
蒼涼就是歷史。
感覺蒼涼就是感覺歷史。
誰不與蒼涼和歷史同在?
歷史的蒼涼是有溫度和色彩的,在大漠中有各種沙生植物,有胡楊,有“三北防護林”,有戈壁亂石底下冒出的一棵、幾棵野草,開著黃色、紫色、白色的小花,這就是大森林啊,大森林氣象萬千之一端。
30年行走大地,與草木為伍,尤其是《大森林》的寫作實踐,使我認識到中國自然文學的開拓意義,是對“文學是人學”的突破:文學不僅是人學,還是大地自然之學,追根溯源,甚至可以說首先是大地自然之學,是對人類中心說在文化上的“反動”。這一切,在我寫《伐木者,醒來》時,從未思及。因為堅守,因為堅守時的困惑,因為在寂寞中向著小草、樹木、山澗的傾訴,而有所思、有所悟,然一旦見諸文字便心有愧疚:樹無聲,草不言,水不語,它們參與人類的生存和死亡,卻不以奉獻為奉獻,存乎天地之間,只以溫柔面世,沉默而高貴也。
我希望并且正在渺小自己。我只是自然文學作者中之一員,躬奉其盛而已。我心里永存的是大地上的風景,中國的風景,人類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