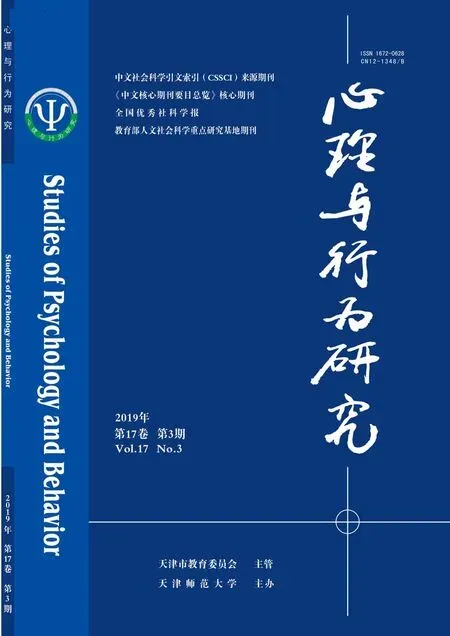信息框架及個體情緒誘發對大學生捐助行為的影響 *
張聚媛 許 瀟 劉勤學
(青少年網絡心理與行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人的發展與心理健康湖北省重點實驗室,心理學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武漢 430079)
1 引言
捐助行為是一種典型的以他人受益為目的,不以物質獲得和聲譽回報為目的親社會行為,即是一種超出了親屬關系之間的互助行為(Fehr &Fischbacher, 2003; Nowak & Sigmund, 2005)。一般認為其包括捐款行為和非金錢性質的幫助行為——比如投入時間進行幫助的行為(Kim, 2014)。徐麟(2005)認為,慈善捐贈行為是奉獻社會的自愿行為,其核心是通過某種途徑自愿地向社會及受益人提供無償社會救助。故研究捐助行為對于解決賑災、扶貧、助學、助弱等問題,維護社會穩定和諧有重要意義(林志揚, 肖前, 周志強, 2014)。
國內外對于捐助行為的研究方向不同,國外的研究主要是對于捐款意愿的研究,具體來說是選擇捐錢還是捐時間(Chatterjee, Rose, & Sinha,2013; Kim, 2014)。如Chatterjee 等人(2013)的研究提出捐贈的錢數會影響個體的意愿;而有研究證實了道德認同會削弱對時間捐贈的厭惡感(Reed,Kay, Finnel, Aquino, & Levy, 2016);Kim(2014)則是探究了公益廣告策略對捐助意向的影響。國內主要關注于對企業捐贈與個人捐贈的大數據調查,如關注“512”地震中社會責任與經濟動機對企業捐贈的影響(盧現祥, 李曉敏, 2010)、探討期望績效對企業捐贈行為的影響(王菁, 程博, 孫元欣, 2014)或者是調查區域內居民的捐款數量(劉鳳芹, 盧瑋靜, 2013)。總體來說,國外的研究方向側重于意愿調查,國內的研究側重于數據調查,國內外對于捐助行為的研究缺乏科學嚴謹的定量的實驗研究。
另外,影響個體捐助決策的因素眾多,如國家的慈善政策、文化、捐贈者自身的經濟條件、個性特征、捐贈對象的特點甚至慈善機構的募捐策略。相對而言,提升慈善機構的募捐策略對促進捐贈行為是更加便捷可行的(陳劍梅, 傅琦,2016)。Levin, Schneider, 和Gaeth(1998)認為人們對公共事件的認知和判斷明顯受信息呈現方式的影響。
然而捐助情境中語言文字不同的表述方式會形成不同的信息框架,使受眾有不同的行為傾向。這種現象被稱為框架效應。其中框架是指決策者對特定問題的選項、結果和結果可能性的感知(于會會, 徐富明, 黃寶珍, 文桂禪, 王嵐, 2012)。Tversky 和Kalmeman(1981)借助“亞洲疾病問題”首次向世人驗證了框架效應的存在,即個體面對獲益框架時傾向于風險規避,而面對損失框架時傾向于風險尋求。對此,Kahneman 和Tversky的預期理論給出了解釋,認為這是由于個體的決策是基于得失框架的相對知覺。另外Levin 等人(1998)對框架效應的大量跨學科研究進行元分析后,進一步提出框架效應分為三種互相獨立的類型,即風險框架效應、特征框架效應和目標框架效應。風險框架效應是指,對于實質相同的信息,個體面對其獲益框架時傾向于風險規避,而面對其損失框架時傾向于風險尋求;特征框架效應是指,采用積極框架或消極框架描述一個事物的某個關鍵特征,會影響個體對該事物的喜愛程度,而且個體一般偏愛用積極框架描述的事物;目標框架效應是指信息是強調做某事的獲益,還是強調不做某事的損失,會影響信息的說服力。Tversky 和Kahneman 提出的框架效應即屬于風險框架效應。但目前框架效應大多是經濟行為學的研究領域,探討個體面對獲益框架時傾向于選擇無風險的選項,而面對損失框架時傾向于選擇有風險的選項的偏好(于會會等, 2012)。但是在沒有利益目標的情境下,文字框架的改變是否也會對公眾的決策造成影響,研究結果尚不明確(杜秀芳, 王穎霞, 趙樹強, 2010)。捐助行為屬于典型的利他行為,而框架效應強調的是個人利益的獲得與損失,屬于利己主義,是利他主義的對立面(劉明威, 2013),故在兩種完全不同的利益背景下,框架效應是否依然存在,是本研究探討的問題。目前的研究多基于受贈者的角度出發,強調災難對受贈者的受災情況的不同表達方式,對捐助者產生的影響,比如謝曄和周軍(2012)采用自編的玉樹震后的校園捐贈行為的情境材料,通過對災后人們死亡和幸存人數的不同表述,形成了得失框架,證明了風險框架的存在。如果從捐助者的角度來看,根據目標框架效應,捐贈行為本身帶給捐贈者的得失可能依然會影響信息的說服力。因此,本研究假設1:在捐助情境下,框架效應仍然存在。
另外,目前人們對于積極框架和消極框架在捐助情境中的說服力仍然存在爭議。Maheswaran和Meyers-Levy(1990)證明積極框架相比消極框架更具有說服力。相反,Abhyankar, O’Connor 和Lawton(2008)的研究證明了消極框架比積極框架更能促進人們的親社會行為。因此,不同信息框架下的捐助情境對捐助行為的影響可能不同,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其作用呢?有研究發現由情緒性材料喚醒的個體情緒狀態會影響個體的認知決策。比如前人的研究發現框架效應的形成是由于情緒對認知努力的影響(Kuo, Hsu, &Day, 2009);前人研究發現,當重大事件發生后(比如癌癥)產生的強烈情緒會影響個體的認知能力(Slovic, Finucane, Peters, & MacGregor, 2007)。過去的很多研究認為,情緒是助人行為的前提(Salovey, Mayer, & Rosenhan, 1991)。但以往研究中不同情緒狀態對助人行為的影響卻存在爭議。根據情緒維持假說,積極情緒狀態下,人們為了延續這種好心情,會做出更多的助人行為(劉明威, 2013)。例如,Cavanaugh, Bettman 和Luce(2015)的研究通過考察不同積極情緒程度下被試的親社會行為傾向,發現積極情緒對親社會行為有很好的預測作用;國內的李穎和羅滌(2013)的研究也證明了積極情緒與親社會行為存在正相關。但也有研究認為消極情緒狀態下,被試更容易做出助人行為。如Forgas(2002)通過誘發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考察被試在簡單請求任務和復雜請求任務的測試表現,結果發現在消極情緒的誘發下被試更愿意接受請求任務。
調節匹配理論認為,調節聚焦與信息框架的匹配可提高說服效果,調節聚焦可以是長期的也可以是暫時啟動的,當被啟動的調節聚焦與不同的信息框架相匹配時,個體對于決策后的感覺越好(Cesario, Higgins, & Scholer, 2008)。另外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調節匹配會影響個體的動機(Higgins, 2000)、情緒(Idson, Liberman, &Higgins, 2004)、說服(Zhao & Pechmann, 2007)、談判(Appelt, Zou, Arora, & Higgins, 2009)和領導(Stam, van Knippenberg, & Wisse, 2010)。所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對調節匹配理論與決策領域進行相關研究。其中有的研究將實驗情境設定為捐助行為,通過對過去捐助情境的瀏覽和回顧,可以發現情境一般分為兩類:災后重建和幫助他人度過危機(戴鑫, 周文容, 曾一帆, 2015)。故對于受眾來說兩種捐助情境也形成了兩種不同的信息框架,一種是消極框架,一種是積極框架(施卓敏, 李璐璐, 吳路芳, 2013)。而不同的信息框架會對已經進行過初步情緒喚醒的被試,產生第二次的情緒喚醒,即消極信息框架會喚起消極情緒,積極信息框架會喚起積極情緒。那么兩種情境下,情緒的啟動與信息框架的情緒喚起是否有匹配作用?因此基于調節匹配理論提出我們的假設2:積極信息框架下(也就是在積極的情境材料誘發下),被試中被情緒喚醒的個體在積極情緒狀態下比消極情緒狀態下更傾向于進行捐助行為,而消極信息框架下(也就是在消極的情境誘發下),被試中被情緒喚醒的個體在消極情緒狀態下比積極情緒狀態下更傾向于進行捐助行為。
2 實驗一:積極框架和消極框架對捐助行為的影響
2.1 被試
選取武漢某師范院校非心理學專業大學生87 人,男33 人,女54 人。年齡17-29 歲。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視力正常或矯正視力正常,無腦外傷及身心健康問題史,未參加過類似的心理學實驗。
2.2 實驗設計
本實驗采用兩因素被試內設計,實驗設計為2(框架效應: 積極框架, 消極框架)×4(平均金額:500 元, 1000 元, 1500 元, 2000 元),把被試行為意向的人數分布作為因變量衡量指標(段錦云, 朱月龍, 陳婧, 2013)。被試需要完成不同金額下的不同試次,一共20 個試次。
2.3 實驗材料和工具
2.3.1 自編假設捐助情境中框架效應材料
實驗材料是根據Tanner,Medin 和Iliev(2008)改進的風險決策范式以及劉明威(2013)的自編利他框架效應情境材料進行相應的改編得到的。在不同實驗處理中,捐助情境一致,都被設置成地震捐款情境。區別在于不同的實驗組中言語暗示線索是不同的。
在積極框架組的捐助情境材料中選項如下(示例):
A(保守):捐款200 股,一定獲得1646 元;
B(風險):不捐款,30%可能獲得3088 元,70%可能獲得1028 元。
在消極框架組的捐助情境材料中選項如下:
A(保守):捐款200 股,一定損失411 元;
B(風險):不捐款,30%可能獲得3088 元,70%可能損失1030 元。
2.3.2 計算機
2G 內存,1G 獨立顯卡,14 英寸液晶電腦顯示器。
2.4 實驗程序
每個被試都單獨在計算機上完成所有情境測試題。被試到達實驗室后,在主試的幫助下,進入實驗。被試需按照指導語的提示,根據實驗情境以及錢數做出選擇,獨立完成實驗。實驗結束后,被試會得到一份小禮物。
2.5 結果
我們對捐助情境下的框架效應進行檢驗,采用成對樣本t 檢驗,在積極框架下選擇風險組和在消極框架下選擇保守組與在積極框架下選擇保守組和在消極框架下選擇風險組相比差異顯著,t(86)=2.10,p<0.05,d=0.22。因此存在框架效應,假設1 得到驗證。
3 實驗二:情緒與信息框架的匹配性對大學生捐助行為的影響
3.1 被試
采用招募的方式,選取36 名武漢某師范院校的大學生,男生12 人,女生24 人,悲傷情緒組18 人,快樂情緒組18 人。被試要求同實驗一。
3.2 實驗設計
本實驗采用兩因素混合設計,2(情境: 積極信息框架, 消極信息框架)×2(情緒: 快樂, 悲傷),材料中的金額則是從1-100 元,時間是從1-100 小時中做選擇(根據預實驗結果, 除去了極端值1 和100)。被試被隨機分配到不同情緒誘發組,快樂情緒組18 人,悲傷情緒組18 人。每組被試在看視頻前需要進行篩選,抑郁量表得分≤14,述情障礙量表得分≤66 分;符合要求的被試觀看情緒喚醒視頻,視頻觀看完畢,會對主觀情緒進行評分,接著分別閱讀兩個自編情境材料,當被試閱讀完每一個情境材料后需要回答以下5 個問題:①面對以上情境,你更會捐錢還是捐時間(二選一)?②如果你只有100 元可以用于捐錢,你會選擇捐多少錢?③如果你真的捐了這么多錢,你此刻內心的感受是怎樣的(1-7 點評分, 1 代表一點兒也不開心, 7 代表十分開心)?④如果你只有100 分鐘可以用于捐時間,你會選擇捐多少時間?⑤如果你真的捐了這么多時間,你此刻內心的感受是怎樣的(1-7 點評分, 1 代表一點兒也不開心, 7 代表十分開心)?
3.3 實驗工具
3.3.1 自編情境材料
情景一(積極信息框架):希望工程之建設圖書館活動,為農民工子弟帶來知識。情景二(消極信息框架):抗災救災之幫受災居民走出困境。兩個實驗情境材料均由真實公益廣告改編而成。
3.3.2 抑郁量表
采用由Beck 編制,王振等人(2011)翻譯的《貝克抑郁量表第2 版》,這是應用最為廣泛的抑郁癥狀自評量表之一,在各種疾病人群和普通人群的抑郁癥狀評估中均得到應用,BDI-Ⅱ中文版的Cronbach α 系數為0.94,各條目間的相關系數在0.18~0.71 之間。
3.3.3 述情障礙量表
采用由Taylor GJ 編制,袁勇貴等人(2003)翻譯的《述情障礙量表》,TAS-20 量表共20 個條目,按1-5 級評分,TAS-20 具有良好的心理測量特性,Cronbach α 系數在0.58~0.74, TAS-20 各分量表的分半相關系數在0.56~0.80。
3.3.4 情緒主觀報告問卷
采用靳霄(2009)編寫的《情緒主觀報告問卷》,刪除與此次誘發情緒類型無關的2 個條目,形成包含6 個情緒條目情緒主觀報告問卷:快樂、恐懼、憤怒、幸福、緊張、悲傷等,對各項目按Liker 的9 點計分方式評分,從0(一點也沒有)分到8(非常強烈)分,分數越高代表被試體驗到該情緒的強度越高。
3.3.5 情緒誘發視頻
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喚起視頻來源于徐鵬飛、黃宇霞和羅躍嘉(2010)編制的《中國情緒影像材料庫》,該材料庫包括可誘發憤怒、恐懼、悲傷、快樂、厭惡和中性等6 種情緒類型的影像片段共30 個,每種情緒類型5 個。其中快樂情緒喚起采用《別拿自己不當干部》中的片段,片長2 分22 秒;悲傷情緒喚起采用《媽媽再愛我一次》中的片段,片長2 分16 秒。
3.4 實驗程序
每個被試到達實驗室后,會填寫一份調查問卷,符合標準的被試可以進行正式實驗。在主試的指導下,觀看誘發愉悅情緒(或悲傷情緒)的電影片段“別拿自己不當干部”(或者“媽媽再愛我一次”)。
情緒誘發之后,請被試填寫情緒主觀報告問卷,共六種情緒,采用九點計分,分數越高被試的情緒體驗越好。之后,被試需要根據指導,認真閱讀并填寫自編情境材料。實驗結束后,贈送被試一份小禮物。
3.5 結果
3.5.1 情緒誘發結果
首先對被試的情緒主觀報告結果進行統計,快樂情緒體驗組和悲傷情緒體驗組的情緒誘發效果如表1 所示。

表 1 情緒誘發效果的描述性統計
由表1 可知,快樂情緒組被試的快樂水平為5.39,達到了比較強烈的程度,憤怒情緒組的悲傷情緒水平為6.72,接近9 點量表“7”的很悲傷程度。將快樂情緒組被試的快樂情緒和悲傷情緒得分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快樂情緒和悲傷情緒之間的差異顯著,F(1, 17)=6.19,p<0.001,d=0.99。把憤怒情緒組被試的憤怒情緒和愉快情緒得分之間進行t 檢驗,結果表明憤怒情緒和愉快情緒的差異顯著,F(1, 17)=19.54,p<0.001,d=0.39。結果說明視頻能成功地誘發出愉快和憤怒情緒。
3.5.2 不同信息框架下捐助行為的差異比較
進一步對不同捐助行為(捐款/捐時間)在不同框架下進行差異檢驗。結果發現在積極信息框架下,被試更愿意捐時間,X2=(1, N=35)=12.79,p<0.001。在消極信息框架下,被試間無差異,X2=(1, N=35)=0.02,p=0.900。
3.5.3 不同情緒狀態對不同捐助行為的影響
被試被引發的情緒(快樂、悲傷)為組間自變量,被試所面臨的積極信息框架和消極信息框架為組內自變量,捐款數額、捐款愉悅度、捐時間長度、捐時間愉悅度以及捐助行為傾向為因變量。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的結果發現,僅僅在捐款愉悅度上信息框架存在顯著主效應,F(1, 34)=5.05,p<0.05,情緒也存在顯著的主效應,F(1,34)=5.74,p<0.05,信息框架與情緒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F(1, 34)=5.05,p<0.05。

表 2 不同情境中不同情緒下捐助行為的描述性統計
進一步進行簡單效應分析,對消極信息框架下捐款愉悅度的進行差異比較,t(34)=-3.20,p<0.05,在消極信息框架中,被引發悲傷情緒的人(M=5.56, SD=0.78)比被引發快樂情緒的人(M=4.44,SD=1.25)捐款后的愉悅度更好。
4 討論
實驗一的結果表明,在捐助情境下,框架效應依然存在。這與Levin 等人(1998)提出的目標框架效應一致,即指目標強調做某事獲益或者不做某事的損失,都會影響信息的說服力。也就是說,對相同客觀信息采用不同的表述,顯著影響了個體的行為決策(Bazerman, 2006),即不論在利他主義還是利己主義的前提下,理性決策均會受到框架效應的影響。前人的研究發現,強調災難中喪生者的數量會增強個體的捐贈意愿(謝曄,周軍, 2012)。而本研究中則發現,捐助情境中強調捐贈者的行為會使受贈者生活的更好時,捐助行為會受到促進,可能是對受助者的積極影響使捐助者產生了更強烈的共情。并且有研究表明,情境中的因果關系會對共情產生積極影響(陳武英, 劉連啟, 2016)。所以這指引了捐助類情境在日后編輯中,一方面可以強調受贈者受到的傷害,另一方面則可以強調捐助者的捐助行為對受贈者的積極影響。國內不少研究表明共情與利他行為、助人傾向等呈顯著正相關(丁鳳琴, 納雯, 2015;何寧, 朱云莉, 2016)。而國外相應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如Batson 等人(1995)認為,共情能促使個體構建自己同他人的情感體驗、他人幸福感的普遍聯系,是助人行為的源泉。
實驗二的結果表明,在積極信息框架下,人們更傾向于捐時間而不是捐錢,而在消極信息框架下沒有顯著差異。這與Kim(2014)的研究結果相符,在為了幫助受助者并使其更好的情況下,人們更愿意做志愿者,在為了使人們脫離困境的情況下,人們更愿意捐款。另外據馬斯洛需要理論,積極信息框架下的個體處于高級需要層次,而消極信息框架下的個體處于基本需要層次,所以人們在消極信息框架下應更愿意捐錢(Maslow,1954)。而我們的實驗結果與前人的研究并不完全一致,在積極信息框架下,人們更傾向于捐時間,這與前人的研究相一致,而在消極信息框架下沒有顯著差異,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不相一致,可能存在以下原因:(1)有研究表明,道德認同的激發會削弱個體的時間捐贈厭惡感(Reed,Aquino, & Levy, 2007),雖然兩種情境下被試的道德認同感都被激發,但在積極信息框架下,更強調捐助行為產生的積極結果,從而更大程度上激發了捐助者的道德認同。所以在積極信息框架下,人們更傾向于捐時間,而在更需要脫離困境并且基本需要急需滿足的消極信息框架下,被試的捐助傾向依然沒有顯著差異。(2)積極信息框架下,強調的是受贈者的獲益,而消極信息框架下,強調的是其損失。根據框架效應,捐助者消極信息框架下更趨向與風險趨避,而選擇捐時間相較于捐錢更具風險(Tversky & Kalmeman, 1981)。所以,導致積極信息框架下,捐時間的被試所占比例更多。(3)可能因為我們的實驗被試群體是大學生,而西方研究者的被試是社會人士,由于大學生時間觀和金錢觀與社會人士不同,從而導致研究結果有差異。
本研究還發現,在消極信息框架下,個體在悲傷情緒誘發下比快樂情緒誘發的捐款愉悅度更好,而在積極信息框架下,個體在悲傷情緒的誘發下與快樂情緒的誘發在捐款愉悅度上無顯著差異。雖然研究結果在具體數量上都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在愉悅度上存在顯著差異,根據Ferster 和Skinner(1957)的強化理論,好的感受體驗能夠促進未來該行為的發生,因此更好的捐款體驗將促進人們未來的捐助行為的發生。本研究結果與Higgins(2000)提出的調節匹配理論是一致的,當個體追求目標的策略方式支持個體當前的調節定向,個體傾向于選擇與當時調節定向匹配高的策略方式,也就是說當個體的情緒與個體所處的情境相促進,那么就能夠感受到調節匹配的作用,調節匹配越高,個體對所相匹配的情境感覺越好,對不匹配的情境感覺越差。此外,Isen 和Patrick(1983)的情緒維持假說也有相似的觀點,即在消極情緒的誘發下,人們為了擺脫這種情緒,更愿意做出改變,而在積極情緒的誘發下,人們為了維持這種情緒而不愿改變,但這只能解釋消極信息框架中的結果,然而在積極信息框架中沒有顯著差異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1)Bless,Schwarz 和Wieland(1996)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積極情緒下被試采用自上而下加工,易受已經形成的認知圖式的影響,不易受材料本身的影響。而在消極情緒下,人們采用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更注重對事物本身性質進行加工,受材料本身的影響較大。故在消極情緒下,材料中信息框架對被試的影響更大。(2)Forgas(2002)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在積極情緒下人們由于不需要激活更多的認知資源而感覺到安逸,而在消極情緒下,決策者為了擺脫當前這種消極情緒,會對已有的認知資源進行精細的加工,從而更容易受到信息框架的影響。(3)這與主觀期望愉悅理論也是相符的,捐助者捐助是為了獲得捐助后的主觀愉悅感,即捐助決策帶來的正性情緒與負性情緒之間的差值。在消極情緒的情境下,捐助行為能夠增加主觀愉悅感;而在積極情緒的情境下,雖然主觀愉悅感依然會增加,但是由于邊際效益遞減,其增加程度不如在消極情緒狀態下增加的程度高(謝曄, 周軍, 2012)。(4)由于自編情境相對于真實情境來說生態效度低,在積極信息框架下難以模擬真實情況,因此可能會導致結果與前人研究存在差異。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調節匹配的角度考量了情緒及信息框架對捐助行為的影響,并提出了自己的猜想,這對公益廣告的設計提出了新的理念,即在負性信息框架下,比如賑災情境等,可以采用能夠誘發人們悲傷情緒的公益廣告,更好地促進人們的捐助行為,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但是本研究還存在以下局限:第一,本研究僅考察了情緒與情境的調節匹配,并未對其機制進行深入探究,未來研究可以從由不同情境引發不同心境的角度來探究對捐助行為的影響(寇彧, 唐玲玲, 2004)。第二,本研究僅對于情緒和信息框架對捐助行為的影響進行探討,并未對其他的因素——比如說道德認同對捐助行為的影響(Reed et al.,2016)做出探討,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情緒和道德認同的激活對捐助行為的影響進行探究。第三未來研究還可以基于行為實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多層面的人腦紋狀體對于捐助行為決策的影響(王曉利, 2016)。
5 結論
通過不同的情緒誘發以及不同的信息框架,探究對于大學生捐助行為的影響,結論如下:(1)在捐助情境下,框架效應顯著,即在不同的信息框架會影響個體的行為傾向。捐助情境的積極表述方式會使個體更愿意冒險,而消極表述方式會使個體更加保守,這與前人的某些研究結果相符。(2)當個體處于消極情緒狀態下,消極信息框架會使個體產生更多的捐助行為,并有更好的心理體驗。而處于積極情緒下的個體,則不受信息框架的影響。(3)在不同信息框架下,個體的行為傾向也存在差異。在積極信息框架下,人們更傾向于捐時間而不是捐款;而在消極信息框架下,在捐款或捐時間傾向上沒有顯著差異。但這一行為傾向,并不受個體所處情緒狀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