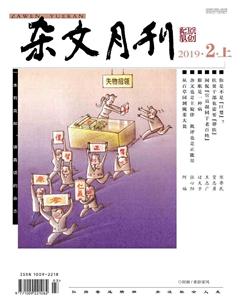舌尖上的“鄉”味
禾刀
這本書至少有三個時間段不宜閱讀:肚子餓了,夜半三更,再就是遠離家鄉之時。
本書雖與飲食相關,但絕非獵奇,所見之物大都極為尋常,像白菜、番薯葉、南瓜葉、馬齒莧、豆腐、土豆、鯰魚,還有與飲食相關的茶葉、酒、稻谷都是常見之物,沒有一樣是珍稀或“高貴”的。尤其是對于那些來自農村的人而言,這些飲食熟悉得令人幾乎從不怎么在意,一旦提及,往往會陡然涌出一股濃濃的鄉味來。
俗話講,民以食為天。雖是日常之物,但農人對于食物始終心存敬畏,哪怕極為普通的蔬菜,農人們常常會以一雙雙巧手,做出許多花樣來。以番薯為例,他寫了番薯的隨遇而安,順時度勢地旺盛生長。他寫了番薯葉化成農村餐桌上的菜肴。其實周華誠還漏掉了番薯稈。在筆者兒時的農村記憶中,番薯稈不僅可以清炒,還可以腌制,都是不錯的菜肴。
周華誠說,“一餐一飯,內里都藏著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可以是名不見經傳的草木,也可以是司空見慣的動物。周華誠的別致之處在于,他總能在尋常之中發現不尋常。許多作品常常把南瓜當成災荒之年的充饑之食,而在周華誠這里,“南瓜煮飯”不僅有一種特有的香味,曬干后的南瓜干,“加適當比例糯米粉及油鹽醬醋生姜辣椒等十余種花樣”,再蒸熟再曬干。這一趟下來,繁瑣是繁瑣,但南瓜干頓時實現華麗轉身,變得高大上起來。還有一些人吃田螺,居然把里面的肉先挑出來,和著豬肉剁碎再塞進田螺,這樣煮出來的螺絲沒了田螺的腥味,豬肉的味道中也多了一些野性。
確切地講,并非是越繁瑣味道就越好,但繁瑣自有繁瑣的道理。繁瑣里面不僅有農人們的汗水,還蘊含著他們把生活日常過得更為精致的影子。農人炒菜對火候的把握全憑經驗,但對于菜肴的準備工作大都一致。記得老家過去逢年過節辦喜事做的魚糕、魚面的配比早就人所共知,但廚師就是廚師,家常就是家常,味道差別遠不止一兩個檔次。
印象中,小時候家家戶戶每年都要做很多干菜腌菜醬菜,一開始是因為蔬菜稀缺,尤其是冬季受氣候影響蔬菜的生長難以滿足飯碗。后來分田到戶,菜地多了收成也好,雖然不用再做過去那么多,但老一代人還是喜歡折騰。一個村子就是一個舞臺,干菜腌菜醬菜做好了,左鄰右舍端著飯碗相互品嘗,說是取長補短,但每家還是各有千秋。
鄉味不會一成不變,時間常常成為鄉味的佐料。最典型的當數清代文學家周容寫的《芋老人傳》。同樣是煮芋頭,味道天壤之別。芋頭其實還是芋頭,只是食客品味不再是以前的品味了。過去在鎮上上高中時,條件大都不太好,那時嘴饞的同學拿著好不容易攢到的幾個零錢,到路面攤上點上碗包面(餛飩),頓覺勝過天堂。現如今,同學群里總在討論鎮上哪家包面如何如何正宗,但每次去吃,雖然餡比以前更多,做工更精致,可就是吃不出當年的那種美味來。
周華誠談到了一個令人心酸的現象,就是過去在鄉村的酒席上,常見人為吃幾碗大塊肉而打賭。那是在糧食稀缺的年代,越是稀缺的食物越有人打賭。大家肚子里缺少油水,偶爾碰到葷腥,沉睡已久的味蕾如久旱逢甘霖轉瞬被激活,饞勁頓時便沖昏大腦。
周華誠的文字非常美,這種美不是緣于寫作技巧,而是他對生活細致地觀察。他說“在城里是會忘了季節的”,生活在鋼筋水泥森林之中,四季越來越像是一種沒有溫度起伏的“定色”;他說“煮起一鍋羊肉,然后等雪來”,下雪天是吃羊肉的最好時節,就著滾燙羊肉的暖氣,勝過身上的十件皮衣;他說“飲茶之人,可以從一杯茶里品出蘭香,聽見流泉”,吃茶之人不在于解渴,而在細品慢咽中琢磨茶葉背后的空谷幽靈;他說“小地方的好處,就是可以容忍一兩個傳奇人物的存在”,相較于大地方處處講禮節講規矩,小地方的人則快意豁達;他說“麻糍的滋味,更多的是思鄉滋味”,無論是清人回味的那盤芋頭,還是小時印象中堪稱人間美味的包面,如果沒有“鄉味”的底子,再好的美味都會顯得過于淺薄而經不起咀嚼。
時下常見一些人疲于追尋所謂的美食,但觥籌交錯后,只是扔下一片胡亂饕餮的狼煙。周華誠筆下的草木之所以變得那么美味,當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因為里面浸潤著我們的生活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