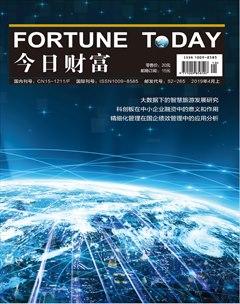成都周邊地區土地規模化經營中的農民地權保護調查
吉媛 楊靜
我國農民地權易受侵害長期惹人關注,土地權利模糊被公認為罪魁禍首。農地權利“物權化”則被認為是解決這一難題的必由之路。然而成都實驗表明,確權頒證后,農民的土地權利仍然有受到侵害的可能,農地權利主體的自由意志仍然會讓位于政府推動的土地規模集中的政策意圖。因此政府主導的土地流轉可能是造成農民地權被侵害的主要誘因。
一、 問題的提出
2003年,成都市正式決定實施“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戰略。自此,成都市開始了“城鄉一體化”的改革試驗(以下簡稱成都實驗)。雖然成都市的實驗是從統籌城鄉的整體視角出發的,但其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必然是農村土地制度,而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成為其他改革推進的抓手或前提。正如有學者評論那樣“成都實驗走出了一條既能滿足城市化用地需要又能相對有效防止征地沖突的農村土地產權市場化創新之路,其基本思路就是‘管住規劃,放開產權”。成都實驗之所以要“管住規劃”,是為了防止土地流轉過程中出現的異化現象,確保土地用途管制不被破壞。而“放開產權”的目的是為了構建一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農地產權制度,為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以及農村房屋產權流轉創造前提條件。2013年成都基本完成了確權頒證的工作,農村土地也的流轉也開始加速。那么,這一過程中農民地權保護如何呢?本文的研究正是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二、土地流轉中的“行政”色彩是農民地權的潛在威脅
在成都實驗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作為實現農業規模適度集中的重要手段,是成都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在成都實驗中是通過目標責任制等管理手段納入了市、縣、鄉政府以致村組考核體系的。以2007年為例,成都市當年確定了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60萬畝的目標,共涉及226個鄉鎮,并將目標任務全部分解落實到村組,由專人負責,并實行目標考核。不難看出,成都市農地流轉帶有較強的“行政”色彩。根據張洪松(2010)的調查,雖然近年來成都市的農用地流轉面積持續增長,但僅有56.64%的農戶傾向于流轉其土地。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成都市的土地流轉需要政府在背后推動,因為如果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來進行土地流轉的化是不可能達成政府土地流轉目標計劃的。由此成都實驗中的土地流轉并非市場自發形成,即便農地流轉可以為傳統農業帶來資本、技術、企業家才能以及規模效益等要素的注入,但其收益仍然不足以激活市場的自發需求。這也反映出了成都試驗中土地流轉的內在動因主要還是政府的強力推進。這就必然使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更多的服從于政府的需要,而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意志則必然處于次要的位階。
三、從農地流轉的糾紛數據看農民土地權利的保護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按照政策的邏輯,成都的土地流轉是建立在確權頒證的基礎之上的。而確權頒證實際上是《物權法》將土地承包經營權等農地產權納入物權范疇的一個自然延伸。而《物權法》之所以要將農地產權納入物權的保護范疇,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對抗其他勢力對農村土地權利的侵害,其中政府一直被認為是侵害農民土地權利的主要勢力之一。而成都實驗的邏輯卻出現了令人尷尬的局面,即政府通過確權頒證確立農民的土地權利之后,又通過行政手段大力推進了土地的流轉,雖然政府推行土地流轉的目標取向之一是為了增加農民的土地收益,僅就這一點上來看,是可能獲得多數農民支持的。但在如此大的土地流轉規模之下,農民因土地流轉而發生的糾紛并未明顯增加。根據張洪松(2010)的調查,在其調查的總樣本中堅決反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農戶只有4.59%。而自2005年以來,成都市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面積的平均增長速度為47%,僅2006年度和2007年度,成都市土地流轉面積凈增數就達到了38.4萬畝和81.87萬畝。而如果按照我國農村戶均10畝地的水平來匡算,2006年度和2007年度成都市土地流轉凈增面積涉及農戶約為3.8萬戶和8.2萬戶。涉及規模如此龐大農戶的土地流轉,所產生的土地流轉類糾紛在兩年間僅出現了7例,低于土地承包類糾紛和征地補償類糾紛。這從側面反映出,即使確權頒證后,政府行政手段加上村社自身的傳統權威體系仍然可以有效的運作。在這個意義上來看成都實驗中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益的增加本質上是在政府主導下的一種利益的輸送。雖然這種利益輸送對統籌城鄉發展以及提高農民收入而言具有無可爭辯的積極意義,但距離農民土地權利的完全保護仍有距離。因為,雖然政府主導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政策目的與農民利益的取向基本吻合,但如果一項涉及農民勞動力再生產資源配置方式轉變的政策能符合99.9%的受眾的支持,顯然不太符合常理。而本文基于張洪松(2010)的調查數據所進行的匡算,在兩年、涉及近12萬戶農村居民的土地流轉中所產生的土地流轉類糾紛僅為十二萬分之七。顯然,對成都試驗中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所呈現出的這種整齊劃一的結果有必要保持謹慎的態度。
四、結論
成都市“確權頒證”、“還權賦能”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尷尬之處在于,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破除農地產權模糊弊端進而解放農民因地權保護不足而無法釋放的土地流轉需求,但在“確權頒證”改革后,仍然需要通過行政手段來推動土地的流轉,這在某種程度上又與農民的土地權利產生了沖突。可見,土地權利清晰與否并非是制約農地流轉的主要因素。成都實驗表明,農民土地權利“物權化”并非是保護農民權利的靈丹妙藥也非必要。(作者單位:1.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機關黨校、2.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機關黨校)
本文系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機關黨校校級一般調研課題《成都周邊地區土地規模化經營中的農民地權保護調查》的研究成果(課題編號:SCJD2018DY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