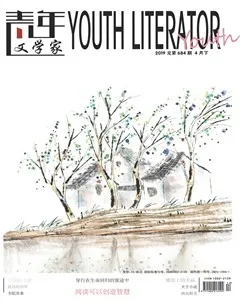“在京異鄉者”的生存困境書寫
路瑤
摘? 要:小說《出京記》的最大亮點是以外地人身份去書寫外地人在北京的生存困境。作者有意選取了異鄉者與北京人的不同角度,反映了以武月月為代表的“在京異鄉者”的身份感模糊和歸屬感缺乏的窘況;并通過家庭和工作的雙重壓力,集中體現了這一群體的生活困境。以二元的結構、譏諷的筆調呈現出了精妙的困境書寫手法的同時,也存在著同類型小說的困境模式。值得肯定的是,《出京記》還原了“異鄉者”在北京的真實生活和真實情感、對社會與生活的全力追尋和敏銳反應,有著不容抹殺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荊永鳴;身份困惑;生活矛盾;困境敘事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2-0-03
荊永鳴作為眾多書寫“外來者進京”中的一員,雖起步很晚,但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他筆下對生存困境的書寫,與“老北京”的老舍不同,也與鄧友梅、陳建功等“京味小說”作家不同。他通過一個外來人的視角,以自身的經歷與體驗,對當下現實進行觀察和表現,獲得了更多的讀者共鳴。以描寫“在京異鄉者”的困境來表達中心主題,也并非荊永鳴獨創,但是,荊永鳴能夠在這些作品中脫穎而出,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必定有他的獨特之處。本文將針對小說《出京記》中的困境書寫展開討論。
一、身份的困惑
英國學者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寫到:“新的經濟自由使數億中國人過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榮的經濟大潮中,一個已經困擾西方世界長達數世紀的問題也東渡到了中國那就是身份的焦慮。”[1]的確,當下國民身份的焦慮已經越來越突出,“在京異鄉者”表現得尤為明顯。荊永鳴不僅準確捕捉到了這一社會現狀,還通過三個人物,不同角度加深了身份困境的窘迫性。
其一,是初出茅廬的外地人武月月。她的身份一直得不到他人的認可是她最大的困擾。月月自幼父母雙亡,為躲避嫂子的逼婚利誘,她背井離鄉,試圖在北京找尋屬于自己的幸福。月月與大部分懷揣夢想進入北京的打工妹一樣,她到處漂泊,從底層服務性行業做起。“做保潔,當保姆,最初還在郊區一個木工廠里干過幾天小工,搬木頭,每天扎得滿手都是刺兒!”[2]但是她沒有放棄,終于借著她出色的工作能力,精明的辦事技巧在飯館踏踏實實的干了下去。然而,在北京打拼的月月,在生活逐步步入正軌的同時,遇到了歸屬感缺乏的問題,從而陷入身份感模糊的困境中。廣告公司老板提出為她遷戶口這件事,正式激起了她內心對擁有“北京身份”的一種向往。就連桂萍也看得出“她總是把眼光放在城里人身上……找個城里的男朋友,名正言順。”[3]月月對自我發展有著清晰的規劃,她只是在隱約地尋找著城市提供的這種可能性,希望通過獲得城市戶口,成為真正的城市人,然而憑借一己之力去解決這一困境顯然是不可能的,婚姻成為她實現自我身份確定的最快途徑,此處并不是指武月月的戀愛帶有了絕對功利的色彩,而是指與楊浦這樣一場付出真心的戀愛,同時使得她獲得了身份上的轉變。
其二,是立足異鄉的過來人鐘鳴。當鐘鳴得知月月與北京人楊浦戀愛以后,他對妻子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是:“高了吧?”、“你得考慮到兩個人的身份,武月月畢竟是鄉下人。”[4]飯館老板鐘鳴的態度交織著多重的聲音。首先,他作為武月月在北京最親近的人,不免發出身份懸殊、不相配的感嘆。其次,他作為同在北京打拼的外地人,經歷過和月月同樣的身份困惑與掙扎的過程,卻也仍不看好月月與楊浦的結合。再次,他作為作者的發聲者(有評論者認為小說中的鐘鳴有著荊永鳴的影子,同是多年“飄”在北京,同是依靠開飯館為生[5])暗含著作家對這一群體的困境認知。暫不論故事的講述者與作者之間的遠近關系,多重的親密關系依然無法打破這種身份的桎梏。
其三,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婆婆。她介意武月月只是一個鄉下人,沒有“北京人”的身份,成為婆婆心中拔不去的一根刺。婆婆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甚至還是自稱有著愛新覺羅血統的旗人,自認高貴的血統,讓她無法去接納一個外地來的兒媳婦。盡管武月月工作熱情、踏實肯干;生活上也井井有條,孝順公婆,也入不了婆婆的眼。即使是婆婆最終接受了武月月進家門,她也不愿風風光光的大辦婚禮,只請了幾桌親戚草草了事,為的是不失她這個“身份”。
總之,一方面,武月月已經脫離鄉村的生活,在北京打拼,原有的故鄉身份和屬性已經在模糊、淡化。另一方面,武月月卻并未被納入這一北京人的身份當中,婚姻關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身份困惑。在確立身份歸屬的過程中,武月月無法獲得一種身份的認同感。武月月的生活現狀改變了,在享受著城市現代文明的自由之時,歸屬感的匱乏和身份感的模糊困境卻是一直伴隨著她存在的,而且伴隨著鐘鳴、婆婆等形象逐漸加深。
二、生活的窘境
如果說身份的變更是能否決定你在城市立足的第一步,那么生活問題則是決定你能否長久在城市生活的因素。然而在月月這里,荊永鳴緊緊圍繞工作與家庭這兩組日常化的窘境去展示了這一生存困境的難題。
第一組生活化的窘境便是武月月工作成就感的匱乏。工作上的困境可謂是每一個在北京生存的外地人所要面臨的問題,月月也是如此。對于月月來說,她的工作仕途并不順利。首先是頻繁地更換工作。從武月月進京以來,她到處漂泊,從最底層服務性行業做起。“做保潔,當保姆,最初還在郊區一個木工廠里干過幾天小工,搬木頭,每天扎得滿手都是刺兒!”[6]僅僅是飯館小妹的工作,也更換過多家飯館。其次是繁重的工作壓力。武月月在飯館工作時候,時常會遇到挑刺的顧客。在武月月擔任售樓顧問的工作時候,除了工作淡旺季的工資差異,還有繁重的工作帶來的巨大壓力。“二十幾層的高樓,一天要爬四五次!遇上拿不準主意的客戶,磨磨嘰嘰,那簡直是一種折磨。武月月接待過一位男客戶,他想買一套頂樓,二十八層。他自己角角落落地端詳了兩遍……帶著老婆、孩子、親戚不停地看,最后還把同事拉過來幫他參謀。幾天下來……武月月爬了十多次!兩條腿腫得像棒槌,夜里又脹又痛,覺都睡不成。”[7]再次是工作所引起的家庭紛爭。一次月月在酒店大堂和客戶談生意,不巧被丈夫碰到,這一次引起了丈夫對她婚姻忠誠度的懷疑。愛人的不理解與埋怨給武月月帶來的傷害更甚于工作的重壓。多重壓力的交織對武月月能否繼續在北京實現她的夢想,追尋她的幸福,打出一個大大的問號。
第二組生活化窘境即月月家庭存在感的缺失。月月的原生家庭并沒有給予月月在成長中應有的幸福感,武月月出生于河南農村,十六歲父母雙亡,同哥哥一起相依為命。然而,哥哥并沒有起到長兄如父的作用,兄嫂試圖利用月月的幸福去換取自己的利益。沒有父母、兄弟的關懷,“家”是孤獨的,而這一份孤獨恰恰說明了她存在感的缺失。也正因如此,再后來嫁給楊浦之后,她曾試圖去彌補這一缺陷。但是沒想到的是,月月在這個全新的家庭之中,更是沒有任何的話語權力。在楊浦家得到八十多萬的拆遷補償款之后,武月月好心提出了買新房子給公公婆婆住的建議,但她在這個家中并沒有發言的權利,這一想法也未能實現。在這個家中,公公無聲的反抗成為以不變應萬變的生存法則。公公和月月一樣,在這個家庭中也是一個“外來人口”,“老頭的‘根兒在山東,祖祖輩輩是農民。”用老太太的話說:“也不是玩兒不到一塊兒,而是文化上有差異,根兒就不一樣。”[8]公公“即使在家,也向來不大言語,甚至不笑,更不參與家人對任何事情的討論。大多時候他都是以一種無聲形式存在著。”[9]即使公公婆婆發生爭執,婆婆破口大罵,公公也絕不會反擊一句,沒有言說權利的公公似乎成為武月月的未來,想要在這個家中生存,沉默就是萬金油。
無論是工作上的重壓還是家庭中的煩悶,武月月都沒有宣泄的出口,她是孤獨的,沒有人能理解她真正內心的感受,更沒有人去溫暖她。故事僅僅是以一個旁觀者的口吻去敘述五月月日常瑣碎的生活壓力,也從側面表現出對身處現實困境中的小人物在面對生存問題時的舉步維艱,個體的孤獨及無助。荊永鳴不僅用冷酷的筆觸寫出了月月現實生活中的困境,更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寫出了月月精神上的困境。
三、“困境”的書寫模式
小說的創作是指向文化精神的內涵的,以生活與藝術相結合的手法,用想象的表現方法詮釋世界的意義,尤其是展示那些從生存困境中產生的、人人無法回避的問題。荊永鳴在展示這一困境上就采取了獨特的敘事模式。
首先,是“二元三人”敘事結構的運用。“二元三人”模式是一種高超的技藝方法,這一模式應用在小說的表現之中也同樣精彩。在小說《出京記》之中,二元模式并不是絕對的對立,人物之間也絕不是善與惡、正與邪的對立,而是以月月、楊浦、婆婆為主,形成一個三角狀、相對穩定的對峙格局。但在這部小說中的二元對立模式是雙重的,一是婆媳之間的矛盾,二是農村與城市之間的矛盾,農村媳婦與城市婆婆之間的矛盾的雙重的。一次,武月月一不小心“熗鍋時把蔥花炸煳了”,婆婆陰郁著臉,引發了一場婆媳之間的罵戰。
“多大個屁事兒,至于嗎?”武月月不吭聲,他便心煩意亂地吩咐道,“行了行了,你去問問媽,還吃不吃飯,不吃收碗去!”
“愿意去你去,我不侍候了。”武月月憋著一肚子委屈。
婆婆……高揚著臉:“說誰呢?”
楊浦看見老太太掛著一臉的挑釁,他想息事寧人:“行了媽,您煩不煩啊?”
……
老太太一生氣,楊浦更生氣。他是因為武月月進一步激發了母親的憤怒而生氣。他沖著武月月勒令道:“給我閉嘴,不吱聲你會死呀!”[10]
這你一言我一語之間,婆媳的矛盾已經發展到熾熱的程度,然而楊浦這個中間人物,看似在“左右安撫”,在二人之間進行調停和斡旋。但兩邊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實則加劇了婆媳之間的沖突斗爭程度。在《出京記》中,荊永鳴已經將這種模式熟練運用在這個家庭的矛盾戰線上,將武月月的生存困境展示得淋漓盡致。
其次,是譏諷的敘事筆調。反諷作為一種敘事手法在中國文學中由來已久,荊永鳴在《出京記》中運用反諷的手法揭示生存困境的原始圖景可謂信手拈來。當月月還在鐘鳴的飯館工作時候,“有一天,是武月月生日……陳五湖做了一大桌子菜……就在筵席即將開始的時候,陳五湖像個魔術師似的,突然亮出了一手絕活兒用雙手把一只金色的鳳凰放到了桌上。”一只金色的鳳凰,一個從農村來到北京實現的夢想的女孩,她經歷了種種困境與磨難之后,還是一只“鳳凰”嘛?月月的生活以還鄉而告終,這一只從遠方而來的“鳳凰”終其選擇以一種“凡鳥”的姿態還鄉,可謂諷刺意義十足。月月的夢想就是“發誓不回去”、“要在北京有全新的生活”。相比在經歷過這一次次磨難之后,作者借月月這一“金鳳凰”的生活經歷向讀者說明了這一真實、殘酷的現實世界。
在一次遛狗的過程中,月月的疏忽可能引起了小狗的意外懷孕,婆婆對她破口大罵,楊浦對她大打出手。這只是家里的一只小狗,而且還是可能會引起懷孕。而她,是這個家庭的一個成員,是一個人,是一個活生生為這個家庭付出又無怨無悔的人,她又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是婆婆對她的改造,得到的是丈夫的冷淡,得到的是家庭的冷漠與不信任。她也懷過孕,她也在盡自己的努力去討好他們,融入他們,但顯然這是不可能的,楊浦的那一巴掌將月月徹底打醒了,她終于明白面對這樣一個“大事做不來小事不屑于做”的丈夫,面對這樣一個不認可她的家庭,在北京,顯然不是她的容身之處。這是現實困境所給她的一記響亮的耳光,也是作家筆下譏諷筆調的精彩呈現。
但在另一方面,荊永鳴的困境模式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首先,是老舍京味模式的模仿。《駱駝祥子》曾經被看作那個時代個人奮斗無法成功的典型案例,如果僅此而已就是對經典的稀釋,當我們今天重又在城鄉沖突的語境下審視這部作品時,它所包含的容量再次令人驚奇。月月通過婚姻在城市立足的途徑不正是祥子所走的道路嗎?二人在生存困境上的相類與最終選擇的雷同都在延續著這一模式在文學形式上的重演。其次,是荊永鳴主題相似的類同。荊永鳴是近年來堅持寫“外地人”系列的作家之一,而且他的外地人多集中在北京發展、生存,他的《北京時間》、《北京候鳥》、《大聲呼吸》難免落入同樣的敘事套路,《出京記》也無法逃脫個人寫作模式的弊病。
荊永鳴的“外地人在北京”系列就描寫了這么一批背離了鄉土、在城市中尋找生路的農民。他們在進入城市之前都曾經描繪過美好的未來生活圖景,但是,在城市中等待他們的,并不是夢想中的幸福生活,而是冷眼、欺侮、驅逐和敵意。《北京候鳥》中,來泰在車站拉貨時被保安毆打;《白水羊頭葫蘆絲》中,馬歡被年輕的城管員扇了一耳光;《走鬼》中,民生打妹妹的那一巴掌,以及《保姆》中伸向水秀胸膛的那雙枯萎的手,這些侮辱都如同悶頭一棍,將這些外地人的美好夢想一下子擊得粉碎。在現實的沖擊下,他們才認清了自己在城市中的位置,明白了現實并不如夢想那么美好。
結語:
小說以武月月回鄉生活為結束,當武月月明白了這是一場無謂的掙扎的時候,一切都成為過去了。小說似乎是對人生的一聲悠長的感慨或嘆謂,大有過來人“何必當初”的慨嘆。但是,《出京記》不是一部宗教小說,既不是勸善懲惡,也不是明清白話小說的喻世明言。它首先是一部敘述日常生活的小說,是一部用細膩真實的筆致介入當下社會生活、揭示社會整體狀態的小說。作為描寫“外地人在北京”的中心主題,這些都并非荊永鳴的獨創,但是,荊永鳴的“外地人”系列有著與眾不同的獨特魅力,他不僅揭示了鄉下人進城所面臨的普遍問題,同時也從這些生活的表面提煉出更為深刻的人性意義。
參考文獻:
[1](英)德波頓(Botton,A.)著;陳廣興,南治國譯.身份的焦慮[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1.
[2][3][4][6][7][8][9][10]荊永鳴.出京記[J].十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2):37.40.40.37.53.50.49. 58.
[5] 孟繁華.新文明的構建與都市景觀[J].當代作家評論,2014,(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