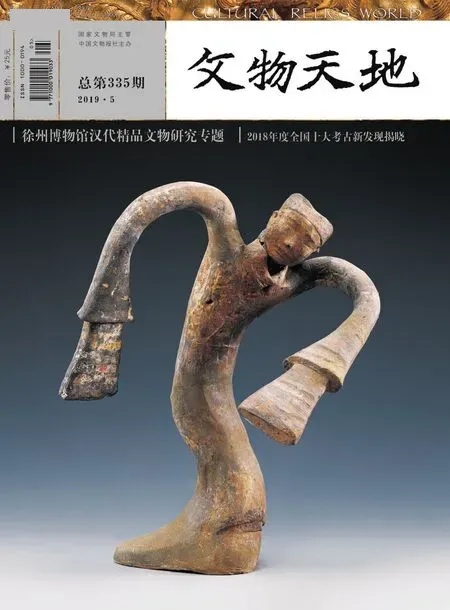徐州漢代銅鐵器珍品散記
文/張譯丹
徐州之所以具有濃重的漢文化氣息,正是源于其兩漢時期的地位。作為兩漢楚國和彭城國統治的中心區域,400多年的發展在這里留下了各類漢墓千余座,出土文物數萬件(套),為徐州博物館藏品夯下堅實的基礎。其中漢代銅鐵器數量尤為可觀,富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從一個側面揭示了中國古代銅鐵器的發展規律,為今人了解兩漢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等開啟了一扇亮窗。透物見史,如果說兩千多年前徐州地區青銅器的余暉依舊璀璨,那么通過這些珍貴的物證,更能看到鐵器的蓬勃發展,并幫助我們得以探究漢人的物質文明。

圖一 明光宮趙姬鍾

一、徐州出土漢代銅鐵器概況
上世紀50年代伊始,徐州地區在徐州博物館等單位的主持下,發掘了千余座漢代墓葬,雖多數被盜擾,但還是出土了數量相當的銅鐵器,總體保存狀況銅器優于鐵器,這也符合鐵器易銹蝕不易保存的特質。現將同時出土銅鐵器的各類漢墓以表格形式呈現,其他零星出土的漢墓在此不贅述。

徐州出土銅鐵器較多的漢墓
從品類上分,銅器主要有七類,大致如下:一是炊食器,包括鼎、釜、甑、染爐、鍪等;二是酒器,包括鍾、鈁、壺、盉、勺、鐎等;三是盥洗器,包括盤、匜、盆等;四是兵器,包括戟、矛、戈、鈹、劍、弩機、箭鏃等;五是日用器,包括鏡、燈、熏爐、鎮、帶鉤等;六是銅印;七是其他諸如車馬器、計量器、樂器、文具等。鐵器主要有三類,一是生產工具,包括臿、削、錛、?、鏟、鐮、錐等;二是生活用器,包括鎮、燈、書刀、烤爐、鼎、鐎、熏爐等;三是兵器裝備,包括劍、環首刀、戟、戈、鈹、鏃、甲、胄等。
二、從銅鐵器珍品中領略兩漢徐州冶金業原貌
兩漢400余年正處于中華文明史上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徹底轉變的歷史性時期,而徐州地區沉寂地底的這些器物,恰恰折射出那個青銅器與鐵器并存交織、此消彼長的時代,還原了兩千年前冶金業興盛的風貌。青銅時代在謝幕之前,展現了它最后的繁華,從考古發掘實物來看,品類齊全、珠璣紛呈,凸顯出徐州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而中國古代冶鐵是獨立起源的,為世界上最早出現和使用鐵器的國家之一。徐州蘊藏豐富的鐵礦資源,其開采歷史可追溯到漢代,盡管出土的漢代鐵器數量和種類不如銅器,但極具地域特色,尤其鐵質兵器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也印證了“徐州自古兵家必爭之地”的獨特面貌。現將徐州出土的銅鐵器珍品略作鋪陳,從中亦可滴水辨海,一葉知秋。
“明光宮趙姬鍾”(圖一),出土于徐州東洞山楚王后墓,高44、腹徑33.5厘米。銅鍾乃漢代最常見的盛酒容器。該器造型簡潔素雅,腹部兩側有對稱的鋪首銜環,平底矮圈足,整體素面,口、頸、腹部飾有三圈帶狀素面紋。圈足外側有刻銘“明光宮趙姬鍾”6字,實際上該墓一共出土了刻有“明光宮”字樣的銅器10件,通過銘文可以明確地告訴今人墓主人為趙氏名姬。姬是古代君王之妻的別稱,“明光宮”位于西漢長安城內,《漢書·武帝紀》記載太初四年(前101)“秋,起明光宮”。值得深究的是墓中還陪葬刻銘文“王后家盤”的鎏金銅盤,種種證據表明“趙姬”應該在長安城內的明光宮生活過,后來嫁到楚國成為了王后,這批“明光宮”器皿應是來自皇宮的媵器。

圖三 錯金鑲嵌寶石瑟枘

圖四 銅豹鎮


圖七 楚太史印

圖九 蘭陵之印
“趙姬沐盤”(圖二),是迄今出土的最大的一件西漢鎏金銅盤,直徑達到了68.5厘米,來自徐州東洞山楚王后墓。盤腹部有陰刻隸書“趙姬沐盤”四字銘文,結合前面所述“明光宮趙姬鍾”,表明這是楚王后趙姬的沐浴用器。此外,墓里還出土有相當一部分沐浴用具,包括銀鋗、銀鑒、銅扁壺、搓石等,展現了西漢楚王宮奢靡的生活畫面,也為今人了解那個時代背景下的沐浴文化提供了極具禮,起草重要文告、文件,管理禮制的官印;“楚食官印”是管理楚王及屬下飲食的官吏;“楚太倉印”應為楚國控制糧食的總倉庫。二是反映楚國軍隊建制的印章,如“楚司馬印”(圖八)系都尉屬下,主管軍政諸事;“楚騎尉印”系楚國管理騎兵的主要官吏;“楚中司空”掌管軍事工程之事。三是楚國屬縣職官。《漢書·楚元王傳》記載,“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二國,立賈為荊王,交為楚王。網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三十六縣具體名稱,史料無載,但從獅子山墓出土的“蘭陵之印”(圖九)“符離丞印”“武原之印”等可明確得知當時楚國轄36縣中17縣的準確名稱。
鎏金獸形銅硯盒(圖十),東漢,長25、寬14.8厘米,徐州土山一號墓出土。這是目前漢代出土的最具“創意”的文具,古人文房中盛硯臺的專屬盒子。盒形似一只匍匐爬行的蟾蜍,以上下顎交接處為界,分為蓋、身兩部分,并以子母口相合。神獸頭生雙角,肋生雙翼,張口嗔目,狀極兇悍,既有寫實的手法,又有夸張的成分,背部有一小圓鈕,方便開啟,而其下顎部則被巧妙地設計成貯水的墨池。硯盒表面金光閃閃的工藝為鎏金工藝,始于戰國時期,是我們祖先的獨創,在地下逾千年而不脫落,完整如新,屬一件難得的漢代鎏金工藝佳作。此外,硯盒器身均勻鑲嵌有綠松石、青金石、紅寶石等交相輝映,熠熠生輝,是漢代鎏金與鑲嵌工藝的完美結合。打開盒蓋,里面置有一石硯和一磨硯的小圓石,出土時,硯堂上尚有墨痕,證明其為墓主人生前實用硯。

圖十 鎏金獸形銅硯盒

圖十一 銅牛燈

圖十二 鐵札甲

圖十三 鐵胄

圖十四 環首刀

圖十五 玉劍格鐵劍
銅牛燈(圖十一),高26.5、長21厘米,徐州睢寧劉樓東漢墓出土,是漢代釭燈中的杰出代表。此燈取俯首翹尾青牛的形象,牛身為燈座,牛背上是可以旋轉的燈罩,能調節燈光照射方向和防御來風,燈罩上有蝙蝠展翅狀頂蓋。最精妙之處在于,銅牛兩角做成圓筒形煙道與頂蓋相連,當點燃油脂時,煙塵可以通過頂蓋進入煙道再進入空心的牛腹,牛腹注水,靠水過濾煙塵以保持室內清潔,減輕空氣污染;同時,牛腹內的水冷卻了燈具的溫度,可讓燃油完全燒盡而不把油烤干,起到省油的作用,堪稱兩千年前的環保燈,集造型和功能之大成,匠心獨運。
鐵札甲(圖十二),高72、寬68厘米,來自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時已銹蝕散亂,經修復后由836片甲葉組成,重16.5千克,由肩甲、披搏、身甲、裙甲四部分構成,目前這種形制的札甲僅在內蒙古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出土過。西漢諸侯王墓中大都隨葬精堅的鐵鎧,這件鐵札甲是當時楚國兵力強盛的象征,表明蓬勃興起的鋼鐵業將漢代軍隊鑄成為那個時代所向披靡的鋼鐵雄師。
鐵胄(圖十三),高42、直徑27厘米,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漢時也稱兜鍪,外觀如“風”字形,由胄體和垂緣兩部分組成,出土時銹蝕散亂,修復后共用甲120片,重4.7千克,最大限度保護人體的頭,頸部,與獅子山兵馬俑坑出土的跽坐甲胄俑相似,是我國修復的第一頂西漢實戰鐵胄。其和前面介紹的鐵札甲應是一套,為楚王作戰時所穿戴,威武了得。
環首刀2件(圖十四),分別長97、98厘米,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環首刀誕生于我國漢代,是當時最先進、殺傷力最強的近身冷兵器,西漢始普及,最初作為騎兵的劈砍武器來取代原本的漢劍,徹底取代長劍則在東漢末年。這也是人類史上具有非凡意義的一種兵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環首刀將匈奴打敗,并間接促成了當時歐亞民族大遷徙。還需一提的是徐州漢墓發現了大量的“書刀”,作為當時文房用品,造型為“環首刀”的縮小版,一文一武彰顯出此地尚武崇文之風。
玉劍格鐵劍(圖十五),長5.3、寬3.9厘米,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鐵劍已銹蝕殆盡,唯留玉劍格內殘余部分,玉劍格雕琢極為精美,這種保存狀態出土的實例全國僅此一件。從獅子山出土銅鐵兵器的比例,結合全國西漢墓的考古發現,可以證明鋼鐵兵器取代青銅兵器的進程比過去所認識的提早近兩個世紀。徐州具有豐富的鐵礦資源,《漢書·地理志》記載:楚國的彭城、下邳、臨朐縣設置有鐵官,這些鐵器有可能是本地產品,在徐州利國驛曾發掘古煉爐遺址可以確證,遠在秦漢之際,銅山利國已開始采礦冶鐵,所以徐州漢墓出土優良的鐵質尖兵銳器就不足為奇了。
“五十煉”鋼劍,長109、寬3.1厘米,徐州曹山東漢墓出土。此劍挺直端正,柄上有麻織物痕跡,原有苧胎髹漆鞘,已朽附劍上。劍柄正面錯金隸書銘文:“建初二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煉□□□孫劍□”,劍格一面陰刻隸書“直千五百”四字。通俗一點說,是一把公元77年一位來自成都的叫王愔的工匠鍛打了50遍的鋼劍,售價1500五銖錢。這把鋼劍系用生鐵鍛造再反復鍛打滲碳而成,是對成語“百煉成鋼”的最好詮釋,工藝水平之高,實為罕見,對研究中華民族冶鐵史尤其是巴山蜀水與中原徐方經濟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義。
三、徐州銅鐵器的工藝特色
徐州出土的漢代銅鐵器是反映當地漢代物質文明的重要組成,兩漢時期天下富足,海內清平,而崇文重藝之風體現在銅鐵器上則表現為注重務實和精益求精。
青銅器失去了禮器這個顯赫的身份,由“家國重器”蛻變為“生活之器”,一切以生活實用為目的,器物不加雕飾,渾樸自然。上述的“明光宮趙姬鍾”“趙姬沐盤”等器形單純樸素,簡潔洗練,凸顯“簡”為風尚。同時漢代銅器格外注重裝飾技法,鎏金與鑲嵌、細線與刻鏤中極盡奢侈,如前述“鎏金獸形銅硯盒”“錯金鑲嵌寶石瑟枘”等又盡顯繁華之美。此外青銅鑄造工藝仍在攀升,“銅牛燈”“鎏金銅熏爐”結構細膩復雜,想象力和創造力空前絕后。
而漢代徐州鐵器也迅速崛起,以雷霆之勢取代銅器,先民們積累的豐富的冶煉金屬的經驗,讓這里的冶鐵業站在了較高的起點上。首先是大量農具和生產工具的鐵質化,極大促進了徐州兩漢時期農業和各項手工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另外大量各類優質鐵兵器也昭示了徐州屬于較早完成鐵器替代銅器的地區之一。至遲到西漢中葉,灰口鐵、鑄鐵脫碳鋼興起,隨后又出現生鐵炒鋼(包括熟鐵)的新工藝;東漢時期,炒鋼、百煉鋼繼續發展,這些無不在中國古代冶煉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
四、結語
縱觀徐州漢代銅鐵器珍品,作為當時社會發展的重要載體,為我們清晰勾勒出古徐州的冶金業發展水平,青銅器的“樸素精巧”和鐵器的“精堅鋒銳”無論是在考古、科技還是藝術價值上均具備“地域特色、國內著名、國際影響”的特點,無不向今人傳遞著漢人求真篤實、吐故納新的精神。
[1]馬曉輝:《徐州出土的漢代青銅器賞析》,《文物世界》2004年第2期。
[2]尹釗、岳凱等:《徐州漢代鐵兵器賞析》,《東方收藏》2015年第4期。
[3]南京博物院:《銅山小龜山西漢涯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
[4]徐州博物館:《徐州石橋漢墓清理報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5]徐州博物館:《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文物》1989年第2期。
[6]徐州博物館:《徐州繡球山西漢墓清理簡報》,《東南文化》1992年Z1期。
[7]徐州博物館:《徐州九里山西漢墓發掘簡報》,《考古》1994年12期。
[8]徐州博物館:《徐州后樓山西漢墓發掘報告》,《文物》1993年第4期。
[9]徐州博物館:《徐州韓山東漢墓發掘報告》,《文物》1990年第9期。
[10]徐州博物館:《徐州西漢宛朐侯劉埶墓》,《文物》1997年第2期。
[11]徐州博物館:《徐州東甸子西漢墓》,《文物》1999年12期。
[12]王愷、邱永生:《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8期。
[13]徐州博物館:《江蘇銅山縣鳳凰山西漢墓》,《考古》2004年第5期。
[14]徐州博物館:《徐州拖龍山五座西漢墓的發掘》,《考古學報》2010年第1期。
[15]徐州博物館:《碧螺山五號墓》,《文物》2005年第2期。
[16]徐州博物館:《江蘇徐州市顧山西漢墓》,《考古》2005年12期。
[17]徐州博物館:《徐州賈汪官莊漢墓群發掘報告》,《東南文化》2008年第6期。
[18]徐州博物館:《江蘇徐州蘇山頭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5期。
[19]徐州博物館:《江蘇徐州市翠屏山西漢劉治墓發掘簡報》,《考古》2008年第5期。
[20]徐州博物館:《徐州黑頭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年11期。
[21]劉尊志:《江蘇徐州后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