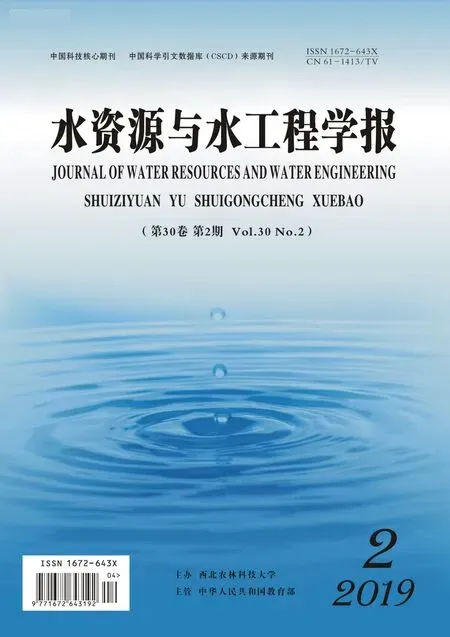江淮生態大走廊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吉婷婷,王細元
(1.淮陰師范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江蘇 淮安 223300;2.淮河生態經濟帶研究院,江蘇 淮安 223300;3.淮陰師范學院 城市與環境學院,江蘇 淮安 223300)
1 研究背景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是區域發展的重要支撐,協調城市化與生態環境關系是學術界和政府部門普遍關注和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1-2]。我國是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國家,對城市化與生態環境關系的研究一直持續,研究的內容也逐步精細化,涉及到不同的時空尺度[3-4]。從理論層面探討到實踐實證分析[1,5-6],從評價指標遴選到模型構建與優化等方面都進行了大量分析[7-9]。從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的時空特征到兩者協調發展的質量演進[1,10-11]、從耦合關系影響要素分析與協調發展模式的探討等都開展了諸多研究[12-14]。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研究還集中在耦合關系的演進趨勢、影響要素、耦合機理、動態模擬和路徑選擇等方面[2,4,6,10]。
江淮生態大走廊是近年江蘇省政府著力打造的區域性發展規劃,在這一規劃驅動下,對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的先行評估尤為重要。但是,目前從規劃視角下對該區域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的研究尚未展開,基于此,本文擬探討二者的耦合關系,解析其影響因素,以期為區域規劃的科學實施提供參考依據。
2 研究區概況
江淮生態大走廊位于南水北調東線長江與淮河流域之間,是以京杭運河為主干線,以南水北調東線輸水線路所流經的地級市為范圍的區域,包括揚州、泰州、淮安、宿遷、徐州5市(圖1)。2016年,區內土地面積42 697 km2,人口3 169萬人,地區生產總值19 757億元。
江淮生態大走廊是江蘇省政府實現蘇中、蘇北綠色發展的區域性戰略規劃,既是現實需要,也是探索新型城鎮化發展下GDP和生態財富同步累積的重要途徑。江淮生態大走廊建設有著明確的近期和遠期目標:到2020年,南水北調東線區域生態環境顯著改善,基本形成空間利用集聚高效、生態環境良好、產業結構優化、區域互聯互通的生態經濟走廊;到2030年,沿線區域社會經濟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格局全面形成,成為南水北調工程生態環境治理的樣本區。
3 數據與方法
本文以江淮生態大走廊淮安、揚州、泰州、宿遷和徐州5市為研究區域,時段為2012-2016年,數據來源于相應年份《江蘇統計年鑒》以及各市統計年鑒和環境公報等。通過構建耦合度評價指標體系,運用耦合度與協調度模型,測度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

圖1 江淮生態大走廊位置范圍示意圖
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解析影響耦合關系的主要因素,以各市平均的耦合度與協調度為母序列,以各市2012-2016年指標的平均值作為灰色關聯分析序列。灰色關聯分析方法詳見文獻[15]。
3.1 指標體系
遵照科學性、可獲得性及可操行性原則[7,9,14],從人口城市化、經濟城市化、空間城市化和社會城市化4個方面選取11項指標,構建城市化評價體系;從水資源水平和生態環境壓力兩個方面選取6項指標,建立生態環境評價體系。綜合指標體系見表1。
3.2 數據處理
3.2.1 數據標準化處理 對原始數據標準化處理,并基于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分析。標準化具體方法如下:
(1)對指標值越大越有利于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采取正向型指標計算公式:
(1)
(2)對指標值越小越有利于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采取逆向型指標計算公式:
(2)

3.2.2 指數的計算 基于上述各評價指標標準化值和權重,利用加權求和法計算城市化指數f(x)和生態環境指數g(y)。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T=αf(x)+βg(y)
(3)
(4)

(5)
式中:T為城市化和生態環境的評價指數;wi,wj為各指標權重。xi和yj分別為城市化和生態環境的單項指標。α和β是待定系數(本文認為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同等重要,因此取α=β=0.5)。

表1 江淮生態大走廊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
3.2.3 熵權重方法 本文指標體系的權重采用熵權重方法,熵是對不確定性信息的一種度量,可計算熵值來判斷一個事件的隨機性及無序程度,也可用熵值判斷某個指標的離散程度。熵權重法步驟[16-17]如下:

(2)數據的非負數化處理。對矩陣中高優和低優指標分別進行歸一化變換,即:

(6)

(7)
(3)計算第j項指標下第i個市(縣)占該指標的比重Pij:
(8)
(4)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ej:
(9)
式中:k>0,k=1/ln(n),e≥0
(5)計算第j項指標的差異系數。對于第j項指標,指標值Xij的差異越大,對Xij的作用就越大,熵值就越小。定義差異系數νj為:
νj=1-ej
(10)
(6)計算熵權重wj
(11)
3.3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模型
3.3.1 耦合協調模型的建立 參考相關文獻并慮到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作用的特性,構建耦合協調度模型如下[7,9,14]:
(12)
(13)
式中:C(0 3.3.2 耦合類型的判別 參考已有文獻[9,12,14],依據耦合度C值,對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類型從無序到有序耦合共劃分為4個階段,具體階段劃分及閾值見表2。 3.3.3 協調類型的判別 考慮耦合協調度D的值,將城市化系統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劃分為4個階段[12],具體見表3。 2012-2016年間,江淮生態大走廊各市城市化指數總體為升高趨勢(圖2),為穩定提升的城市化發展過程。近5年,指數均值最高的為揚州市的0.5132;最低為泰州的0.4609。盡管城市化指數都呈線性增加趨勢,但各市增長幅度略有差異,其中淮安增長速度最大,而揚州最小。 表2 江淮生態大走廊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類型的階段劃分及閾值 表3 江淮生態大走廊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度發展階段劃分及閾值 圖2 2012-2016年江淮生態大走廊各市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指數變化過程 大走廊平均的城市化指數也表現為較突出的線性增加趨勢(圖3),由2012年的0.2505增加到2016年的0.7849,增長幅度偏大,近5年增長了0.5344,表明區域城市化水平的總體提升。 與城市化指數變化不同,研究區生態環境指數的變化在不同地區存在一定差異(圖2)。可以發現,隨著城市化指數的逐漸增加,不同地區生態環境指數亦為增加趨勢。 近5年間,淮安、宿遷和徐州3市生態環境持續增加(圖2),在2016年為最大,但指數最低年份都出現在2013年,有較大的波動,且這3個地區變化過程較為相似。揚州和泰州生態環境變化過程較為相似,這兩市2012-2015年間生態環境指數都為持續增加,但在2016年卻為減小過程。江淮生態大走廊內淮安、揚州、泰州、宿遷和徐州5市的生態環境指數10 a線性增長率分別為2.408、0.851、1.268、2.043和2.144,淮安最大,揚州最小。 而從研究區的平均狀況看(圖3),生態環境指數總體在增加,由2012年的0.2326增加到2016年的0.7961,增加幅度為0.5635,幅度偏大。其中,2013年為指數最低時期。 由此可見,江淮生態大走廊地區生態環境與城市化在變化時序上具有較好的同步性特征,且都呈升高趨勢,表明城市化過程中,生態環境壓力不斷升高,其對生態環境的脅迫效應也較突出。 從江淮生態大走廊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度與協調度變化(圖4)可以看出,耦合水平和協調度可以劃分為兩類,其一為波動型耦合關系,即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變化過程波動較大的類型,包括淮安、宿遷和徐州3市;其二為平穩型耦合關系,即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變化過程較為平穩的類型,包括揚州、泰州兩市。 圖3 2012-2016年江淮生態大走廊平均城市化與生態環境指數變化 圖4 2012-2016年江淮生態大走廊各市的耦合度與協調度變化過程 5.1.1 波動型耦合關系 波動型耦合關系的淮安、宿遷和徐州3市中,耦合度與協調度都表現為明顯的2013年低值時期,淮安、宿遷和徐州的耦合度分別為0.1274、0.0666和0.3108,都屬于低水平耦合類型,協調度則分別為0.1274、0.1005和0.2368,屬于低協調階段;而其余年份,3市耦合度與協調度指數都較高。可見,在城市化過程中,這3個地區盡管生態環境壓力偏大,但仍具有較好的容量。 5.1.2 平穩型耦合關系 揚州與泰州兩市的耦合度與協調度變化趨勢與過程波動較小,更為平穩(圖4),且同步性較好,屬于平穩型的耦合關系。近5年間,揚州與泰州兩市耦合度始終較高,揚州市始終處于高水平耦合階段,泰州僅在2012年耦合度為磨合階段,其余皆為高水平耦合。 而在耦合協調度上,揚州與泰州兩市的變化過程為總體穩步增加(圖4),其中2012、2013年為高協調階段,2014年以后,皆屬于良好的極協調發展階段。 從江淮生態大走廊耦合關系的平均狀況上看(圖5),耦合度與協調度均呈線性增加過程,10 a線性增長率分別為0.733和1.567,除2013年為頡頏階段外,其余年份均為高水平耦合階段,總體為趨向高水平耦合的發展趨勢。 圖5 2012-2016年江淮生態大走廊平均耦合度與協調度變化過程 在耦合協調度上,江淮生態大走廊地區平均的協調度總體不高,2012-2014年為失調協調發展類型,其中2013年是協調度最低的年份,僅為0.2859。進一步還可發現,2013年是耦合度與協調度均最低的年份,表現為頡頏階段的中度失調衰退類發展。這一特征與前述淮安、宿遷和徐州3市在2013年耦合度值明顯偏低的綜合影響有關。但到2015、2016年,江淮生態大走廊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均轉變為高協調發展的耦合類型。 采用灰色關聯方法,獲得耦合度C和耦合協調度D分別與城市化指標的灰色關聯矩陣(表4)。 表4 江淮生態大走廊耦合度、協調度與城市化指標的灰色關聯系數矩陣 從耦合度C與城市化指標體系的灰色關聯度(表4)可以看出,人均用電量、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口(常住人口)、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位列前5位的指標,表明這些指標對耦合度影響程度偏大。人均用電量是表征社會城市化的重要指標,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反映了空間城市化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是經濟城市化的指標,而人口(常住人口)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屬于人口城市化的指標,可見,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度受城市化不同結構體系及指標的綜合影響。 而在城市化指標對協調度D的影響上(表4),人均建成區面積、萬人擁有醫院床位數、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是位列前5位的指標,也涵蓋不同結構城市化的核心影響要素。特別是人均建成區面積、人口(常住人口)以及建成區綠化覆蓋率3個因素,突出地反映了空間城市化與人口城市化對協調度的影響。 可以發現,在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上,不同城市化結構的要素對耦合協調度的變化起著系統而綜合性的影響,應當系統考慮城市化中人口、經濟、社會、空間城市化的綜合發展,尤其應當注重空間城市化、社會城市化指標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可能影響和壓力脅迫。 耦合度C與生態環境指標的的灰色關聯度見表5。由表5可以看出,人均水資源量是最為突出的因素,其次為人均SO2和人均氨氮的排放量。人均水資源量為正向指標,有利于提升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度,而人均SO2和人均氨氮的排放則不利于耦合度。 表5 江淮生態大走廊耦合度、協調度與生態環境指標的灰色關聯系數矩陣 協調度D與耦合度C類似但又有所區別,協調度與生態環境指標的關聯度上(表5),人均水資源量也同樣是最為重要的因素,其次則為人均SO2和人均COD的排放量,也反映了區域水環境和大氣環境的壓力。因此,從耦合度、協調度與生態環境系統指標關聯度綜合來看,水環境與大氣環境是直接決定耦合度及協調度發展質量高低的重要因素。 運用耦合度與協調模型和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探討了江淮生態大走廊地區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主要結論如下: (1)2012-2016年間,江淮生態大走廊城市化指數和生態環境指數總體上呈線性增加過程,且增長幅度較大。5個地市城市化指數的變化過程高度類似,但生態環境指數變化過程有一定差異,但二者總體同步性特征較好。 (2)江淮生態大走廊5個地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可以劃分為兩類,其一為波動型耦合關系,包括淮安、宿遷和徐州3市;其二為平穩型耦合關系,包括揚州、泰州兩市。 (3)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度與協調度均呈線性增加過程,除2013年為頡頏階段外,其余年份均為高水平耦合。2012和2013年為中、低協調發展階段,2014-2016年為高協調或極協調發展階段。其中,2012年與2015年為環境滯后類型,2013、2014和2016年為城市化滯后類型。 (4)城市化在空間城市化、社會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方面的不同結構指標是影響耦合關系的主要因素,而水環境和大氣環境是影響耦合關系的主要生態環境因素,包括人均水資源量、人均SO2排放量、人均氨氮排放量和人均COD排放量等。4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指數變化特征
4.1 城市化指數變化



4.2 生態環境指數變化
5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
5.1 不同地市的耦合關系


5.2 江淮生態大走廊平均的耦合關系

6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的影響因素
6.1 耦合關系的城市化影響因素

6.2 耦合關系的生態環境影響因素

7 結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