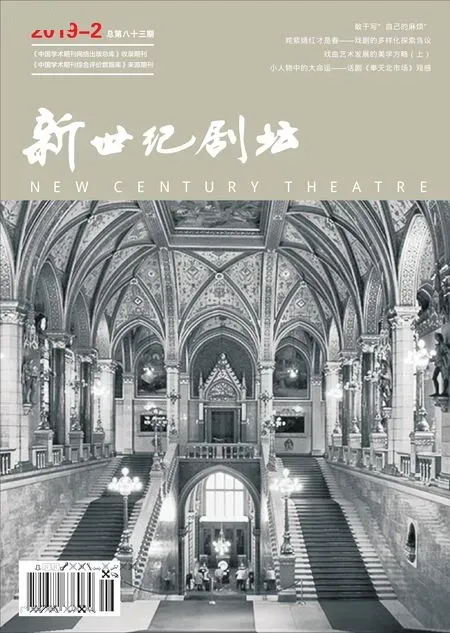從小說到戲劇
——王安憶對張愛玲《金鎖記》的改編研究
王雨晴
文學名著被搬上戲劇舞臺并不罕見,因為名著可為劇本的文學性提供先天保障,名著的影響力更為戲劇增添商業價值。“張愛玲熱”現象的出現表明其作品的文學性與影響力在影、視、劇等領域的影響。張愛玲小說改編為話劇的作品有1987年陳冠中和2005年毛俊輝分別導演的《傾城之戀》、2004年林奕華執導的《半生緣》、2007年田沁鑫導演的《紅玫瑰與白玫瑰》。

《金鎖記》書影
引人注目的是被稱為“張愛玲后又一人”的王安憶將張愛玲最負盛名的小說《金鎖記》改編為話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王安憶說,“戲劇是文學的寶塔尖,一個作家沒寫過戲劇總是不完整的”,因此她開始了戲劇的初次嘗試。“《金鎖記》是我最初想要改編的作品,因為我很喜歡戲,很想找一個對象來做一個戲,就像文本上的游戲一樣的。”[1]王安憶認為《金鎖記》是張愛玲最好的一部小說,并且從戲劇性、體量來講,都非常適合改編成多幕劇,這是她選擇《金鎖記》的原因。王安憶雖把這稱為游戲,但三次易稿可見她對作品的珍視。2004年,由黃蜀芹執導,話劇《金鎖記》于上海話劇中心首演,演出后卻反響平平。2009年,導演許鞍華——曾經將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和《半生緣》搬上大銀幕的電影導演與香港焦媛實驗劇團合作,將臺詞改為粵語,增加詩意和陌生化,同時運用電影手法,將聲光電技術靈活運用到舞臺中,再次將王安憶改編的話劇《金鎖記》呈現給觀眾。王安憶評價道:“黃蜀芹的版本寫實,許鞍華的版本則更寫意。”
從小說到話劇的一大跨越就是對“舞臺”的把握,但本文主要將研究重點放在對劇本的改編,即從張愛玲的《金鎖記》改編為王安憶的《金鎖記》的過程。王安憶通過剪裁增補情節和外化人物性格,使《金鎖記》的基調從“蒼涼”變為“明亮”,在背靠原著與忠于自我間找到平衡。任何作品皆有得失兩面,從中發掘改編創作的啟示才是意義所在。
一、創作觀之反轉:從“蒼涼”的張愛玲到“明亮”的王安憶
身處“舊的東西在崩壞,新的在滋長中”的時代下的張愛玲,早在18歲寫作的散文《天才夢》里就以一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表達她對人生的看法,同時也預示出她作品的底色。在《自己的文章》里她說,“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2]張愛玲是用冷眼看人世的悲觀主義者,她的性格尖銳而“刻薄”,以至于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時代對立起來,從而走向虛無。張愛玲筆下的故事多是世俗的人用世俗的眼光過著世俗的人生,但張愛玲本人卻是脫俗的,她用華靡的文章寫出的是人生素樸的底子。
《金鎖記》被傅雷稱為“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夏志清更是將其贊為“中國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短篇小說”,由時年23歲的張愛玲在1943年創作于上海。在不足四萬字的中篇體量里,張愛玲將三十年的故事寫出三生三世之感,講述了主人公曹七巧嫁給殘疾的落魄豪門子弟,在金錢枷鎖與情欲焚燒之中,逐漸異化為扭曲變態的惡魔的女性悲劇。曹七巧的悲劇批判了封建社會制度對女性的戕害,在更深層次上又暴露出金錢欲望將人性異化的殘酷。話劇卻將色調由“蒼涼”變為“明亮”,王安憶說,“到最后,整個演出和《金鎖記》原來的氣質完全不一樣,它變得非常響亮,很熱烈。”[3]話劇《金鎖記》采用開放式結構,共兩幕各三場戲,按照時間順序上演七巧個人的悲劇及其一手造成的長安的悲劇。王安憶改編《金鎖記》時年過半百,與張愛玲23歲時的愛憎分明不同,王安憶有著中年人的溫厚寬容。王安憶不尖銳也不“刻薄”,她是溫柔且慈悲的。王安憶說自己喜歡“朗朗乾坤的東西”,因此她把張愛玲冷冽森然的筆調弱化,增添了些許光亮。
把王安憶和張愛玲聯系在一起的人是王德威教授,他在看過王安憶的《長恨歌》后發表文章《張愛玲后又一人》,從此王安憶便和張愛玲“牽扯上”了。但王安憶本人對此總是斷然否定。“我有很多否定的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我和她的世界觀不一樣,張愛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熱眼看世界。”[4]張愛玲對她的時代是絕望的,“人是生活于一個時代里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5]而作為“共和國兒女”的王安憶并不會認為時代有多么壞,用她自己的話說,她比較容易妥協,比較樂觀主義或犬儒主義,“我會順應我所在的環境,我比張愛玲好商量。”[6]王安憶絕非張愛玲的傳人。王安憶將小說比作“心靈世界”,著眼于個人與歷史的關系,將日常生活作為起點,意在挖掘人生意義,直奔人類的心靈深處,這范圍要比女性、上海、市俗更大,使其作品的內涵豐富廣闊。而張愛玲的世界很小,小到她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世俗生活,經過對男男女女愛恨情仇剖析,走向荒謬無奈的虛無。她能把人性寫得無比深刻,只有悲劇才能承擔起人性刻骨的蒼涼。張愛玲的世界觀注定了作品的“蒼涼”與虛無,王安憶的作品則充滿“明亮”和飽滿的生命氣息。

話劇《金鎖記》劇照
影響作家創作的因素復雜多樣,時代背景、成長經歷、性格特質、理想信念等等不勝枚舉。因此,二人對《金鎖記》的看法亦有所不同。“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所以我的小說里,除了《金鎖記》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7]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是極端病態的,正因此才極端覺悟,這便透出極端蒼涼之感,得以在人心中留下更深長的回味。而王安憶卻從曹七巧的報復中看出了悲壯,“我覺得曹七巧的報復在《金鎖記》中非常悲壯”[8]。悲壯帶給人一種刺激性和沖擊力,能強烈的抨擊人心,終究是灼熱的,而蒼涼則是一種令人愈想愈瑟瑟發抖的揮之不去的余味。冷眼看世界的張愛玲,筆下的《金鎖記》也是蒼涼的,而熱眼看世界的王安憶卻為《金鎖記》增添一抹明亮之色。冷與熱、絕望與希望、蒼涼與明亮,這既是二人的不同,也是小說與話劇的不同。
二、劇本之再造:從內斂的小說到外化的話劇
王安憶把這次改編看作是練習“寫作‘強烈’”,認為最大的挑戰便是“將藏著的推到表面”。的確,張愛玲的意識流手法為小說布下謎團,故事的情節和線索、人物的情感思想和語言、結構和風格皆是內斂含蓄的。王安憶承擔起解謎的任務,通過增減情節線索、暴露人物性格、強化戲劇沖突的改編,將張愛玲隱藏起來的情緒外化,把謎底呈現給觀眾。
(一)增刪情節,線索簡明
王安憶在故事線索上做了幾個加減法。首先制造出一個非常外化的情節——姜季澤盜取宣德爐被曹七巧識破,七巧出于對季澤的感情選擇隱瞞,這里二人的感情曖昧模糊,當季澤在分家產時將此事栽贓給七巧,七巧才驚覺季澤的虛情假意。這個情節把七巧與季澤的感情由曖昧轉為荒謬,背叛感破滅了七巧曾經對季澤懷抱的幻想,季澤虛偽自私的一面暴露無疑。“等于說把他們之間的關系來了一個激化的處理。”[9]于是小說中曖昧的暗示在話劇里浮出水面。
其次是一個減法,王安憶把長白的整條線索減去。原著中長白這條線刻畫出七巧一步一步走向瘋狂變態。七巧對兒子長白的感情有種恐怖的褻瀆,為留住身邊唯一的男人,她變著法哄長白抽鴉片,徹夜同床逼兒子說出與兒媳的私事,再大肆添油加醋到處宣揚。在她日益惡劣殘忍的折磨下,最終逼死兩任兒媳。據王安憶說,刪去這條線一是出于空間和時間的考慮,很難安排那么多線。于是話劇只留七巧和季澤、七巧和長安兩條主線,這使情節更加集中。二是出于王安憶個人的考慮,“我個人和張愛玲有些地方不太相和,可能我是共和國的人了,喜歡那種朗朗乾坤的東西,覺不覺得她有時候挺森然,挺曖昧的。”[10]王安憶同情曹七巧的命運,所以不愿用“這么陰毒的表現”。因此,刪去長白的戲使話劇剪去過多線索的枝蔓,從而保證主線突出、沖突明確。

話劇《金鎖記》劇照
三是把長安的戲加長。話劇把第二幕的故事集中到長安身上,圍繞長安與童世舫從相識相戀到最終被拆散展開。王安憶把小說簡略的一句“他們繼續來往了一些時”擴為一場戲,改變小說中二人“很少說話”,增加對白,使長安與童世舫的戀愛過程完整豐滿,從而加強觀眾對七巧惡言惡語拆散二人的同情和憤怒,以及強化七巧殘忍變態的人物形象。原著則圍繞七巧對長安的影響展開,從長安十三四歲寫起,以七巧灌輸長安提防男人、強迫長安裹腳、因一條褥單導致長安退學、耽擱長安的婚事、唆使長安抽鴉片等,勾勒出曹七巧的惡母形象。話劇把長安的成長經歷分散在回憶中,在戲劇情節高度集中的前提下,做到與原著的細節保持一致,保證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可以說,補充長安的情節使話劇比小說更完整詳細。
此外,王安憶還填補了幾處細節。安排代替新郎的姜季澤把七巧背上臺,“賣弄著健康和力氣”的姜季澤令七巧“滿意”,這與七巧揭開蓋頭后的“不解而害怕”形成對比,既埋下七巧對丈夫二爺的怨,也種下七巧對三爺季澤的情。另外,王安憶根據張愛玲弟弟張子靜的回憶,把分家后七巧和長安的家安排在一個小學校的樓上,因此話劇中出現三處讀書聲,王安憶表示希望用小孩子的讀書聲沖淡一點戲劇沖突的緊張感。可以看出王安憶對細節的重視。
(二)暴露性格,內心外化
曹七巧是《金鎖記》的靈魂人物。張愛玲把曹七巧視為她筆下唯一“徹底的人”。王安憶將曹七巧的“徹底性”歸因于“原始性”,她在接受采訪時曾說“在張愛玲所有的小說人物里,曹七巧是一個最原始的人”。這一原始性通過情欲表現出來,正如傅雷在《論張愛玲小說》中指出“情欲”在《金鎖記》的重要作用。曹七巧和張愛玲筆下的其它人物一樣經歷社會的教化,但她的獨特之處在于未經教化磨滅的情欲的原始力量。王安憶抓住了這一點,極力展現七巧對季澤的追求,把小說中似有若無、忽遠忽近的曖昧,變為步步緊逼、夸張露骨的求愛。小說里七巧對季澤的感情是因對死人一般的丈夫的恨之后抓住的一根稻草,話劇則因季澤背七巧入府這一細節的補充,使七巧對季澤的一見鐘情先于對丈夫的恨意,這一點可以從七巧對季澤說出“誰讓你背我的呢?你背我進這姜家的門,我就是你的人了!”看出。于是七巧的情欲從深處被挖掘到舞臺上。
姜季澤是七巧情欲的寄托,卻將這情欲無情熄滅。小說里季澤雖曾動過心,但頭腦始終清醒,“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季澤對七巧的撩撥和調情更多出于一個花花公子的慣性,輕佻、虛偽但不至于可恨。王安憶則鋪設宣德爐一案暴露出季澤的無賴,在季澤虛情假意哄七巧賣田時,徹底斷絕七巧的一絲癡望。王安憶把小說中七巧的心中所想變成臺詞,這是話劇的特點,這一改變雖對七巧百轉千回的細膩心思有所削弱,卻增強了戲劇沖突的張力。
長安是七巧情欲幻滅后復仇的對象。母親殘酷的壓迫令長安將犧牲視作習慣,甚至自我催眠為“一個美麗的,蒼涼的手勢”。更殘忍的是長安耳濡目染七巧的行事作派,“言談舉止越來越像她母親”、“誰都說她是活脫的一個七巧”。王安憶終究比張愛玲仁慈,她保留了長安對愛情的追求和對光明的向往。王安憶寫了一場只有長安和童世舫兩個人的戲,這是她在這部話劇里打開的一絲光亮。兩個年輕人內心糾結、掙扎、矛盾,最后終于堅定相擁,其中不乏令人松一口氣的幽默。比起小說里童世舫內心將求婚看作他割舍自由送上的一份厚禮,話劇里二人的臺詞將內心剖白,使二人的感情更為真誠純粹。
(三)高潮迭起,風格改變
張愛玲曾說“人生總是在走向下坡路”,小說的基調仿佛如出一轍。曹七巧逐漸淪為金錢奴隸、喪失人性、湮滅靈魂的一生,留下蒼涼的余燼。小說首句“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與尾句“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寥寥幾筆“月”的意象,勾勒出蒼涼的色調,可嗅出一絲《紅樓夢》的余韻。并非真刀真槍明目張膽的沖突碰撞,而是綿里藏針笑里藏刀的隱隱作痛。合上小說,這悲劇令人唏噓,卻唯有苦澀無奈。反觀話劇落下帷幕之時則令人心潮澎拜,胸中似有憤激之怒火熊熊燃燒。正如王安憶所說,《金鎖記》變得非常響亮與熱烈。一方面,戲劇沖突尖銳,幾乎每場戲都有高潮,令人時刻保持緊張感;另一方面,以七巧和長安雙雙精神失常為結尾,使矛盾沖突到達頂點,制造出震撼感和沖擊力。此外,受演員表演、舞臺設置、服裝道具等多種因素影響,話劇的最終呈現經過各環節的詮釋難免與原作偏離。王安憶曾說自己出于私心希望能給整個故事增添一抹亮色,因此她的《金鎖記》是透著一絲光亮的。小說雖給人暗無天日的絕望,仿佛在地獄深處被黑暗吞噬,但話劇卻尚存一絲希望,于黑暗中投射一束微弱但明亮的光。于是,小說斂筆營造的蒼涼無奈的氛圍,被王安憶袒露外化的改編所沖淡,在絕對的冷色中摻入暖調,調和出一種微亮漸暖的風格。
三、改編《金鎖記》得失與啟示:背靠原著,忠于自我
在某些方面,改編比原創的難度更大,且戲劇更是“戴著鐐銬跳舞”的藝術。小說家王安憶初涉戲劇的“游戲”結果是得失兼具的。
首先,對于體裁的改編是成功的。在王安憶看來,從小說到戲劇的挑戰在于,“寫小說是在一個單純的時間流程里面寫,……我們可以自由地調度,調度到任何空間、任何時間,在文字這個境界里面它是很自由的。戲劇卻沒有這樣的自由。第一,時間和空間都是受制約的,……第二個挑戰就是你所有的故事和情節以及人物都只能用一個方式來交代,就是對話。”[11]這剛好體現出體裁轉換上的成功。一方面,小說可以借用藝術手段營造出細節與復雜的想象空間,但戲劇必須憑借舞臺上實實在在的演出打動觀眾。特別是張愛玲運用蒙太奇、象征、心理分析等多種藝術手法,為《金鎖記》開拓無限想象空間,這為改編增加了難度。王安憶化虛為實,按照時間線索重新編排時序,對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進行剪裁加工,使話劇情節線索明晰、戲劇沖突尖銳、人物形象飽滿。另一方面,小說與戲劇的差異在于,小說重敘述,戲劇重展現。小說文本是敘述者的話語,而戲劇敘事的主要方式是臺詞,即故事中人物的話語。王安憶將小說對人物的心理描寫改為臺詞,基本做到合情合理、不過分突兀。
其次,對于人物變化層次的展現是失敗的。作為張愛玲筆下最復雜的人物,曹七巧這一角色的舞臺塑造是話劇呈現的最大難關。張愛玲的語言技巧是耐人尋味的關鍵,在看似無心的白描語言中,曹七巧一步一步走向變態瘋狂的深淵,小說的悲劇性層層深入,令人不禁顫栗。曹七巧“因極端病態而極端覺悟”,其中體現著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即由陰騭到跋扈、由控制到宣泄、由抱怨到絕望。小說里的曹七巧的變化既可恨又可憐,話劇則無法令人對其心生憐憫。原因在于王安憶忽略了變化過程的層次,使結尾處高潮成為悲劇的最強音。另外,話劇中飾演曹七巧的演員只表現出一氣呵成的張揚與刻薄,原因既有演員表演的不足,也有臺詞設計的欠缺。
除此之外,對于戲劇節奏的把握有得有失。小說閱讀和觀看舞臺演出在接受方式上的差異決定節奏的重要性,讀者可隨意控制閱讀速度、順序、斷續等,觀眾則只能一氣呵成地被舞臺引導,可見恰如其分的節奏調度是戲劇成功的一大關鍵。張愛玲的敘事節奏得益于暗示、蒙太奇、心理分析等技法的運用,詳略得當又韻味無窮。然而“月亮”“鏡子”“酸梅湯”等意象暗示出的想象空間,鏡中人的轉換等電影化描寫手法,在話劇舞臺上是很難實現的。對于時空變換的展現,王安憶通過服飾變化試圖反映出家道中落和時代變遷,設置陽臺上的傭人小雙,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交代情節變化,既方便了幕與幕之間的分隔與補充交代細節,又淡化了緊張感,使節奏張弛有度。然而,對于長安與童世舫的戲份的增添,在互表心意的過程中臺詞略顯重復拖沓,使話劇節奏由緊張突入緩和,雖有“讓觀眾松一口氣”的考慮,但從話劇整體節奏來看卻是弊大于利的。
綜上所述,話劇的二度創作是比較成功的。改編之大忌是完全照搬原著,如果人們對小說和話劇產生完全一致的感受,便會失去二度創作的意義。再創作不能失去自我,這是王安憶對改編的態度。王安憶的改編既抓住原著精髓,又融入個人闡釋。從淺層批判金錢與情欲對靈魂的扭曲,到深層揭秘女性人格悲劇,最后延伸到人類生存困境,這是不變的主題內核。變化在于,王安憶基于個人理解和他人回憶,增刪故事情節,暴露人物內心,改換風格色調,使話劇體現出王安憶的個人創作特質,并非將小說原原本本地搬上舞臺,從而為話劇《金鎖記》注入新的生命力。
結 語
文學與戲劇的雙向運動既有必然性也有必要性,戲劇對文學作品的改編普遍存在脫離原著精神、缺乏內涵創新、迎合大眾犧牲文學性等缺失。王安憶改編《金鎖記》的過程為小說的舞臺移植提供了有價值的啟示。改編作品應在背靠原著的基礎上,注入改編者的靈魂,并擴大作品的闡釋空間。同時,小說改編為戲劇要注意適應性,一是如何能將小說特有的表現方式呈現在戲劇中,二是如何選擇適合改編的作品。王安憶曾說,“當我們在詮釋張愛玲的時候,張愛玲離我們越來越遠,但是好在張愛玲的東西有那么多的空間,夠我們走得很遠。”[12]好的作品,一定是經得起反復咀嚼的。
注釋
[1][3][9][10][12]王安憶.改編《金鎖記》[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3):60-63
[2][5][7]張愛玲.張愛玲散文全編[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111-113
[4][6][8][11]王安憶.張愛玲之于我[J].書城,2010(0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