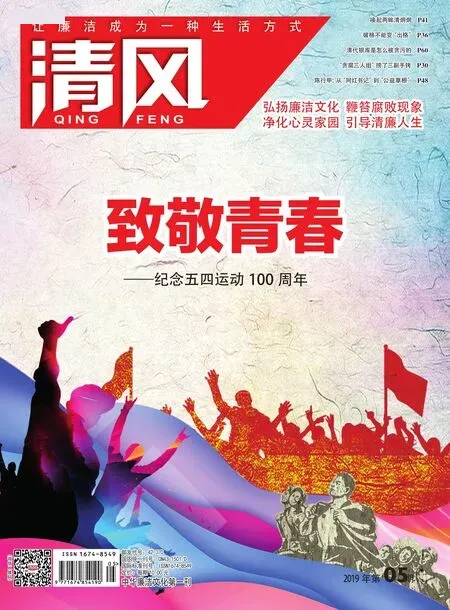烽火歲月家國情
文_本刊記者 化定興

1931 年,日本策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后,中國東北興起了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軍的斗爭。以日軍1937 年7 月7 日炮轟宛平縣城和進攻盧溝橋為標志,中國開始全面抗戰。1945 年,經過14 年的斗爭,抗日戰爭最終取得勝利。這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
在這一艱苦卓絕的斗爭中,許多青年志士展現出了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反映出了濃濃的家國情懷。
“愿拼熱血衛吾華”
戰爭是無情的,時刻面臨著犧牲的危險。在抗日戰場上,八路軍犧牲的最高將領當屬左權。1905 年3 月12 日,左權出生于湖南省醴陵縣新陽鄉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在縣立中學讀書時,左權通過閱讀《新青年》《向導》等進步讀物,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萌生了改造社會的志向。1924 年春,左權進入廣州陸軍講武學校,后轉入黃埔軍校,1925年2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左權英勇善戰,深得毛澤東等的贊賞。周恩來稱他“足以為黨之模范”,朱德贊譽他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抗戰爆發后,左權擔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協助彭德懷指揮了著名的百團大戰。左權在寫給母親的信中說:亡國奴的確不好當,在被日寇占領的區域內,日人大肆屠殺,奸淫擄搶,燒房子……實在痛心。……日寇不僅要亡我之國,并要滅我之種,亡國滅種慘禍,已臨到每一個中國人民的頭上……我軍在西北的戰場上,不僅取得光榮的戰績,山西的民眾,整個華北的民眾,對我軍極表好感,他們都喚著“八路軍是我們的救星”。我們也決心與華北人民共艱苦,共生死。不管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準備不回到黃河南岸來。我們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當局對我們仍然是苛刻,但我全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準備將來也不要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準備還吃草。
1942 年5 月,瘋狂的日寇對太行抗日根據地進行鐵壁合圍大“掃蕩”。5 月25 日下午,日寇的一發炮彈落在左權的身邊,左權不顧危險,高喊:“大家臥倒——”接著第二發炮彈又來了,不幸的是,左權的頭部、胸部和腹部都中了彈片,犧牲時年僅37 歲。
左權犧牲后,朱德題寫了悼念詩:“名將以身殉國家,愿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但此時,左權遠在湖南的老母親并不知道這一噩耗。新中國誕生前夕,人民解放軍揮師南下,朱德親自命令南下部隊路過醴陵時,要列隊去看望老人。因為,左權19 歲離開家鄉后,與母親再未相見。當隊伍進入醴陵縣境時,《左權將軍之歌》響徹云霄,成千上萬的戰士對老人喊道:“左權沒有回來,我們都是您的兒子!”老太太這時才明白自己日思夜想、日夜牽掛的小兒子已經殉國了。
不過,這位堅強的老人沒有慟哭,她沒有讀過什么書,就請人代筆,寫下了這樣的話:“吾兒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兒。現已得著民主解放成功,犧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兒有知,地下瞑目矣!”
“我以我血薦軒轅”
在抗戰的烽火歲月里,“母親教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是現實寫照。而走上戰場時,很多人都是青春正茂,但他們的名字并不都像左權一樣響亮。湖南沅陵縣盤古鄉耍溪村有一位抗戰老兵,名叫頓 志 成。1942 年8 月,20 歲 的頓志成被抓去當壯丁,邊走路,排長邊教用槍。到達貴州黃平,編入軍長牟廷芳指揮的國民革命軍94軍121 師361 團2 營6 連,未經訓練直接上了火線,先后參加湘西會戰、收復桂林等幾十次大小戰役,后升任中尉排長。
1945 年,日軍為占領湖南芷江飛機場,維護湘桂和粵漢鐵路交通,集結七個師團七八萬兵力,向湖南西部發起進攻。94 軍奉命從黃平、鎮遠火速馳援,策應74 軍主力,解圍湘西重鎮武岡,加入湘西大會戰。“那是場惡戰,團長陣亡,我撿得條命!”頓志成回憶說。一次在花橋戰斗中,日軍占據橋頭,架設兩挺重機槍日夜把守。那次戰斗打了一天一夜,死傷無數。頓志成手腳兩處被子彈打穿。
1945 年8月,侵華日軍繳槍投降,94 軍由廣西柳州機場空運到上海,接受上海、天津地區日軍投降,121 師2000 多人先期趕到,奉命接防繳械物資。頓志成清楚記得,在上海吳淞口接管機場時,剛下飛機,他看到一架日本軍機螺旋槳啟動,日本軍官駕機準備起飛逃跑。當時正在患重感冒的他,立即端起沖鋒槍掃射,打爛駕駛艙玻璃,日本軍官害怕了,無奈下了飛機。
像頓志成這樣的人還有很多,他們籍籍無名,卻拋頭顱灑熱血,把青春獻給了國家。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大學學生苗可秀投筆從戎,在對日作戰中成長為威震遼南的義勇軍將領。1935 年,苗可秀在作戰中受傷不幸被捕,英勇就義。在遺書中,苗可秀叮囑弟弟:“凡國有可慶之事,弟當為文告我;國有可痛可恥之事,弟亦當為文告我。”“不要忘了我們要做新中國的主人,要做重整山河的圣手。”陳翰章是東北抗日聯軍第1 路軍第3 方面軍指揮,中學畢業時他發誓:“為了祖國,我一定投筆從戎,用我手中的槍和我的鮮血、生命來趕走敵人!”1940 年,他在作戰中被敵人包圍,面對敵人“陳翰章,投降吧!給你大官做”的喊叫,用“死也不當亡國奴”回答敵人,壯烈犧牲。
這些人不是不愛惜生命,但在國家危急存亡之際,他們挺身而出,踐行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諾言。
“河山北顧淚常俱”
身處亂世,前線的戰士奮力抗敵,而中國的學人也齊心協力,展現了他們的血性與風骨。1937 年11 月1 日,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但由于日軍的步步緊逼,長沙臨時大學分三路西遷昆明,1938 年4 月,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這座臨時大學從1937 年11 月1 日建立到1946 年7 月31 日停止辦學,前后共歷時8 年11 個月。
三校合并之初,彼此尚有一些矛盾。當時,清華校長梅貽琦任命聯大各學院院長、系主任時偏向清華,這讓北大師生很不滿。有一天,蔣夢麟有事到暫留蒙自的文法學院去,北大多位教授群議分校。當時,錢穆認為國難方殷,大家應以和為貴,他日勝利還歸,各校自當獨立。蔣夢麟后來采納了錢穆的意見。為了融洽兩校關系,蔣夢麟主動放棄了一些權力,他讓梅貽琦負責聯大的內部事務,自己主管相對次要的聯大對外事務。
校長們能夠齊心協力,任教的老師諸如華羅庚、陳省身、王力等也憑借堅強的意志和赤子之心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為中國培養了諸多人才。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西南聯大卻成為展現民族精神的高地,知識救國的典范。西南聯大總共招生不過8000 余人,但培養出了鄧稼先、楊振寧、朱光亞等一大批優秀學生。他們中的多位1949年后當選國家兩院院士,有2 人獲得諾貝爾獎,5 人獲得科學進步獎。“兩彈一星功”勛專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聯大的學人。
身處戰火洗禮之下的西南聯大,不僅面臨生活物資短缺、教學條件艱苦等困難,還不得不時刻躲避日軍的瘋狂空襲。但正因這種特殊的環境,讓愛國精神在西南聯大的學子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學校組織各種形式的抗戰宣傳和教育活動,喚起學生團結奮進、保家衛國的愛國情懷,并先后涌現出三次從軍高潮,有不少學生自告奮勇要求參軍。
“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這是昆明巫家壩空軍航校大門入口處的對聯,一共有12 位聯大學生走入這個大門。抗日戰爭開始后,日本軍隊占盡空中優勢,中國飛行員大量犧牲,當局決定從大學生中錄取飛行員,聯大學生積極報名,最終有數十人通過嚴苛選拔成為飛行員,駕駛戰斗機參與對日作戰,或駕駛運輸機穿越舉世聞名的“駝峰航線”運送戰略物資,其中至少七人壯烈犧牲。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在西南聯大就讀時,尚未畢業就自愿報名參軍,給美軍在華作戰的飛虎隊做翻譯。也正是因為從軍,梅祖彥最終沒能拿到西南聯大的畢業證書。而當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是空軍飛行員,在淞滬會戰中犧牲。
不管是努力學習文化知識,還是棄文參軍,都體現了那一代青年人的愛國情懷。從北京準備南遷時,教授吳宓寫道:“鳥雀南飛群未散,河山北顧淚常俱。”的確,在國家危難之時,身處象牙塔的人并未作鳥獸散,而是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至于為何“淚常俱”,無疑是因為他們對腳下的這片土地愛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