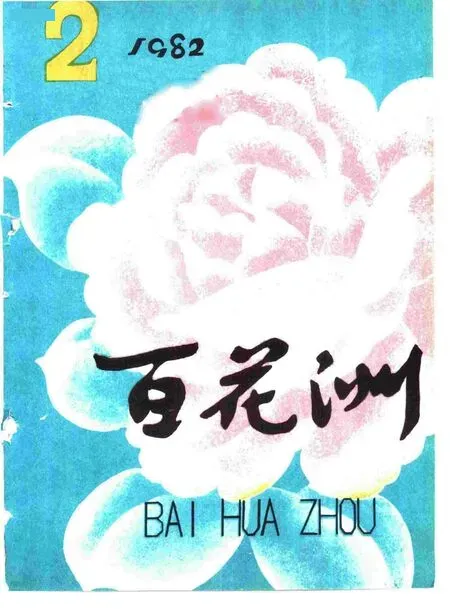自覺
提云積
所有的故事從一座塔開始。
他與他們簽訂了君子之盟,盟約僅憑口語,無文字傳世,只是后人的虔誠與謹慎的記錄。我是閱讀者,字里行間能感知到他的威勢。當然,他的威勢含了慈悲、關懷、安詳。他寄希望于他們能達到自覺,對他的善意不假絲毫的疑慮,他的胸懷暢達,世人卻不能解。
一片亙古平原,介于河流之間,肥沃、豐饒。一座繁華都城,安居了他們。糧食可以自足,風物可以放眼。子民生活安穩,繁衍生息;動物歡躍,自建王國,與人類各自祥安;植物開花結果,描摹春去秋來。
平原的風吹過很多年,大河的水浩蕩過很多年,世人的心磨礪過很多年。風吹著吹著不見了蹤影,水流著流著歸了大海,心磨著磨著就變得殘缺。貪婪及一切欲望開始萌芽。他們開始想建一座塔,以避難的名義,試與天齊,或誓與天齊。這是最初,也是最原始的改造自然之舉。
現世的我們不能洞窺他們所居時代的富足與發達,也不能描述其時的浮華與驕奢。總之,塔層層堆積,高可比浮云。他知道他們想到天上來,這是忤逆了他的旨意。天與地,神與人,遙視可及,卻不能達。懲治的手段簡單,隔閡了他們的語言,心也變得遙遠,頭腦走了不同的陌路,都作鳥獸散。塔還在,傳世的書本里的記載,塵世不再。
故事極簡,后世的讀者皆明了君子之盟的履行只是靠他與他們的自覺。現代哲學為自覺定義,其是人類在自然進化中通過內外矛盾關系發展而來的基本屬性,是人的基本人格。很難想象,也不難想象,如果人類放棄了自覺,單純地依靠外力強其履行一定的義務,或者遵循一定的道德規范,其所承受的心理是怎樣的一種狀態,承載其的社會又會是怎樣的形態。
他給我說起自覺的時候,是在一個下午。對于自覺的理解,憑借自己不甚醒知的大腦,感覺應是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的過程。一個點是起點,一個點是結果。過程是自覺的漸趨朗清。當然,對“自覺”一詞每人的理解不同,我后來求證過多人,與詞典的解釋有出入的答案很多。此時,他給我說到自覺無關土地的生存狀態,只是一次游歷,他所說的自覺偏向于結果。游歷的目的地不遠,就在村莊后面的海邊,海是渤海,此處因為居萊州地域名萊州灣。
聚會是他工廠里的工人發起的,工人們晚上去海邊燒烤,作為一廠之主,他也受邀參加,他與兒子一起去。自家的皮卡車,車廂里裝了啤酒及一應燒烤用具,工人們拼車,一行二十余人,傍晚時分到了海邊。男性工人支架燒烤爐,點火,安裝餐桌;女性工人打下手,準備燒烤用料,分揀餐具。收拾停當,炊煙升起,杯盞滿盈。坐具不夠,男性工人都有了自己的馬扎,女性工人有的站著,有的四處尋找石塊充當臨時坐具。他作為一廠之主已經有工人給他在餐桌的主位上安置了馬扎。此時是一個看點。他把自己的馬扎讓給了女性工人,自己去尋來一石塊,鋪上從啤酒箱上撕下來的紙殼安坐。他的兒子效仿他,也把馬扎讓給了女性工人,那些女性工人客氣地謙讓著。后來,那些男性工人都把自己的馬扎讓給了女性工人,有的尋石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他說這就是自覺。這是古人說的“見賢思齊”,也是古人說的“德不孤,必有鄰”。從一個小馬扎看日常生活習慣,男人在家里是主導地位,從未想過女人在家庭的位置,生活的一些細節帶到社會上來,就會看出女性居家的從屬地位。他說,他不喜歡說教,身教是最好的。他的舉動不但影響了自己的兒子,還影響了工人,想必他的工人從中受到啟發,也會去影響別人。這是自覺的延續。他還說那晚燒烤結束,沒用他的身教,工人們都自覺地把垃圾清理干凈。
去他的工廠時秋日剛始,工廠在村莊的北面,緊挨著村子,目測占地有五六畝的樣子,工廠的大門向東,門前是一條穿村而過的馬路,向北不遠便是一條省道,省道向東連接著一條國道。過了門前的馬路便是一處空地,空地向北相鄰的是他的另一個車間。由此向東便是一處更大的空地,有十幾畝的樣子,空地向北、向東則是即將成熟收割的玉米、大豆。空地以前也是耕地,也生長各式糧食作物。現在只有西南角種植了幾壟蔬菜,它們皆旺盛生長。暗綠色的白菜還沒有卷心,呈開放的姿態直面天空;蘿卜、芹菜枝葉婆娑。它們在此,證實了泥土的養育功能是多么強大。
從去年開始,他把這片土地從本村村民手里流轉過來,準備建一個更大的工廠。我們巡查到這里時,他正在向這里運送土石方,給他下達了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通知書,他沒有繼續施工。我們給他講明如何辦理用地指標的流程,他說想想辦法。后來再經過這里,看到土地空置,也問詢過他,他說正在辦理。他的用地指標有無辦理下來并不得知,2014年度的衛片執法檢查卻走到了前面,這塊空置的土地,以及土地上堆放的砂石被衛星清晰地勾勒出來。這里作為地級市的督辦清理壓占項目,列于重點監督檢查范圍。這也是我和同事來此的目的。
這是第二批拆除(清理)耕地非農化項目。這之前已經完成了第一批,第一批相對比較順利,違法占地行為規模小,大多是一些臨時搭建、臨時壓占,易于清理拆除。進行衛片拆除(清理)之初,領導者的指導思想是由易到難,由點帶面,依次推進。不知道與他前面說到的自覺有無相通之處。
他的閱歷注定他不是一個難纏的人物。在我們來之前,負責人對他曾有過一次約談,大體講明政策與法律,他不做辯解。后來聽負責人說起他,說他是開明的人,能分清形勢,不是一個單純的生意人,或者不是一個滑頭的生意人。清理壓占也不是難事,難的是如何給當事人做思想工作,我和同事比較慶幸,他在此處的清理壓占行為由我們來做監督。我們只需要給推土機與挖掘機司機講明工作步驟,應如何清理即可。
堆積了近兩年的砂石土堆已經長滿荒草,時至深秋,荒草幾近衰敗,枯黃的葉子中透出些許綠意,終不像春夏之時綠得肆無忌憚。我們過去時卻驚飛了在荒草里覓食草籽的一群麻雀,它們應該是屬于一個家族,翩然驚飛時看出這個家族的龐大,有上百只的樣子。起初,它們肯定是被嚇著了,驚飛時毫無章法可循,陣容雜亂,嘰喳有聲,忽而東西,忽而上下,在空中繞了幾個圓圈后,在一只麻雀的帶領下紛紛落在東面的玉米纓穗上,是否在偵察我們進一步的行動,不得而知。俄頃,一只麻雀沖向天空,一聲鳴叫,其他的麻雀跟著沖飛起來,幾聲呼哨,在土堆上空打了一個旋子,迅即降落到空地西南角的那片菜地里。想必麻雀們對于飽腹的草籽尚存絲絲念想,那片荒草曾經是它們的樂園,有溫飽,有安逸,還有不愿舍棄。
不愿舍棄的豈止它們,我想應該還有他,只是他沒有表現出絲毫的不舍,他的認知告諭他必須配合我們的工作,沒有絲毫妥協的余地。鏟車和運輸車輛開了過來,機器轟鳴,煙囪冒著黑色的油煙。土堆很快地被撕裂了一個口子,濕潤的泥土氣息沖了出來,我能聞出氣息的慌亂,它們成團倉皇奔逃出來,瞬間包圍了我。它們被禁閉的時間太久了,久到忘記了它們泥土的身份,它們的生機被人為地禁錮,一旦得到釋放,它們此時的歡悅誰能得知?
一種褐色帶了油亮的光澤,在泥土氣息的裹挾下一并沖了出來,光澤帶了誘惑,我知道這是植物最希求的光,與太陽光不同,它能照亮泥土內心的暗夜,如果它們是一片泥土,會長出什么樣的莊稼,只能由我信馬猜想。
空地東面的玉米行將成熟,路北是葉子逐漸萎黃的豆稈,太陽光暖暖地照射下來。擇一處比較干燥的田壟隨意安坐,背依著玉米形成的屏障。隨手扯了玉米須拿在手里揉捻,玉米的清香氣息,與源源不斷地從玉米地里竄出來的野草的氣息混雜在一起,恍然覺得這就應是田野獨有的味道。此刻,我只想靜靜地待在這里,用心感知它們給我無邊的安寧。祈愿面前的空地能趕上不停行走的季節,如它們一般,用成熟,以及豐收還泥土最本真的樣貌。
不久,他邀請我們去他的辦公室稍做歇息。辦公室在路西的廠區里,從外面也看不出什么特殊之處,就是村民普通的住宅。一張紅木做的茶桌旁圍坐了三人:他,我,我的同事。我們俱不作聲,對于面上的話題前面幾乎已經說透。他麻利地沖泡著茶水,有一瞬,我竟似聽到小溪從春天的泥土上流過的聲音。水汽從每人面前的玻璃杯里升起來,剛描摹出一段曲線便沒有了影蹤,獨留了春日的氣息,讓我恍若置身在盛大的春日里。下午的陽光已經變得淡漠,有光從房子南側的窗戶穿進來,自顧撲在屋內的地面上,沒有了熱烈,只是幾片碎縷,光線淡黃,似乎為了無視我們的存在,自顧靜寂地照著面前的塵世。房子南面是一個狹長的院落,靠窗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樹,已經高過窗戶,樹葉綠中透著墨色。石榴還沒有開裂,只是一個渾圓的果實,泛著清淡的光澤,如一只碩大的眼睛,沉默中夾雜了疑問面對我無聲的觀望。
屋內氤氳著藏香氣息,應該是從里屋傳出來的,在這間屋子的里間供奉著一尊財神像。這間屋子我并不陌生,去年因為他的非法占地行為多次進來小坐,也知道主人的習慣,每日上香,日日祈禱,不知這是否也是一種自覺行為。此時藏香摻和了茶香,濃烈、清淡交雜,竟使腦子放緩了運轉速度,時間與世間的美好應是如此吧。不思不想,忘卻紛爭,忘卻傷痛,或者是忘卻工作的疲累。生活的各種繁忙、混亂、不易,都在此刻得以放下,只要一點兒光,一點兒香,一點點兒的清心寡欲。
室內墻壁懸掛了幾幅字畫,鐘馗出游圖懸掛在東側墻上。鐘馗著紅袍,束黑腰帶,目瞪欲裂,手舞寶劍,足蹈虛空,面相不足以刻畫,觀者的認知決定了鐘馗相貌的惡與善、陋與帥。蝙蝠繞身,一只蝙蝠在鐘馗的劍柄上停留。此時我單純地以為這是另一個世界執法者應有的形象。西面墻壁是一幀清人進士張自超書寫的條幅:“明月照積雪,平疇交遠風。”應是張的真跡,以前多次觀瞻,不識真況味,只覺語句與含義的精妙。后來查了百度才知是一副拼湊的聯句。一為謝靈運的《歲暮》,一為陶淵明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各取其一,意境便大不同。雪夜,雪野,清冷的月光無邊無際地揮灑,月光下的雪野,雪光迢遙,夜在雪光的盡頭,風從未知的宇宙深處踽踽獨來,月光下的村居,一盞淡黃的燈光,透射進雪地。冷與溫,寒與暖,層次分明。一“照”一“交”,時光任意縱橫。縱可涵蓋,橫可無垠。當然,這是古人的意境,今人識得此中況味須得不著邊際地想象,沒有古人真實的眼觀、形象的描述。這也是自覺,是古人的自覺,自然自得,是一種精神境界的升華。
茶過幾盞,他說到如何品茶,不識茶味如我者,渾然懵懂。品茶程序繁雜,要摻雜個人的感知,這點感知是從內心生發出來的真況味,早年喜歡一首簫曲《苦雪烹茶》,開曲是幾縷清音,清是相對,是物我兩忘的意境,是自我的慎思,是天地之間的獨行者,這清便生雅,生思,生定。接之便是悠遠的長調,遠到無邊無際,遠到可以孤寂,遠到周身可以隨處安歇。如此者,必有閑適之心境,當下蕓蕓眾生,極難再尋此雅致,熙攘碌碌皆為欲利往來。
屋外天光開始晦暗,茶味漸寡,工人陸陸續續地下班,我們也該回程,告訴他,明日我們再來。他送我們出來,在大門處跟他握別時,竟發現了大門南側種了幾株柿子樹。它們還不是大樹,它們還小,還不足以撐起一樹風雨。它們作為景觀植物于此,已經失卻了早年我們對作為經濟作物的它們寄予的期望。進門的時候沒有發覺它們的存在,不知道是不是柿子在漸暗的天色里變得明亮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柿子累累,在秋風里散發著清暖的色調。這必是泥土在盛秋時所寄望的色調。在我的感知里,它們應該屬于田野,一爿不大的果園,柿子、蘋果,或者其他的果實類作物,在秋天的眼眸里,各自祥安一隅,用心描摹秋天的各種姿彩。
一個下午的工作量,面前這片被壓占的土地已經開始露出原始的輪廓,夕陽下的泥土依舊靜默,看不出喜悲,秋風開始追逐遙墜的太陽。回到單位,天色已經完全黑了下來,另一個組的同事還沒有回來,不能先走,只能是等,也不能閑坐,隨手處理一些信訪材料。
同事們回來時,外面的天光完全歸于黑暗,馬路對面樓房的霓虹燈開始閃亮,它們勾勒出整座樓房的外形,閃爍的霓虹燈如同一條條排列整齊的貪吃蛇,首尾相連,一條吃掉一條,色彩不斷變換,樓房隱在霓虹燈炫目的光線里,它們原本的樣貌被強勢地剝奪了。疾馳而過的車子,帶動空氣發出陣陣刺耳的聲響。回來的同事說他們遇到了阻力。下午的時候,他們和當地政府的工作人員去了當事人非法占地建筑的現場,當事人和他們見面后只一句話:“我有精神病,你們看著辦。”再沒有其他的言語。
非法占地建筑與前面說到的他的非法壓占,有相通之處,也有著本質的區別。相通的是當事人的行為都是對土地的非法侵害。不同的是非法壓占對泥土造成的危害小,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耕種。非法占地建筑已經形成事實,是一種根源性的破壞行為,即使能恢復耕種,受損的泥土在短時間內也不能得到徹底的復原,如同一個人破損了元氣,想達到赤子狀態,必要經過極長的保養時間才行。
這樁違法占地案子,從一開始我們就忽視了一個人物。他的老婆,此處有必要對她多交代幾筆。近五十歲的農村女人,看面相或許能再大一些,生得黑且瘦,戴一副黑邊無框近視眼鏡,臉頰窄而尖,顴骨略高,給我的感覺不是鼻子架住了眼鏡,而是得益于顴骨。眼光頻閃,不能專注于和她交流的人,她的嘴唇薄,泛著青紫色,牙齒錯列。她說話的時候,幾乎看不到嘴唇的翕動,語速能配合著面部表情時快時慢。身骨略瘦,不是單薄,是硬,一種由身體內里生出的硬。因為他們的違法占地,以后又見過幾次,她給我的感覺一直沒有改變。
事實已經形成,現狀擺在這里,他也再不能自圓其說。再次下達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通知書,告知其下午到分局做一個問詢筆錄。
當日下午剛上班,從辦事大廳的窗口看到一輛黑色別克車開進了院子,別克車在門廳前急速地畫了一個半圓,黝黑的漆色在太陽底下晃出一道耀眼的光斑射進了辦事大廳。車子在院子里停了好長時間,兩側的車門才打開,他和他的老婆,那個黑且瘦硬的女人,一起下了車。他走在前面,他老婆在后緊隨,他不時地回頭和老婆交流著什么。
他坐在同事的面前,對于同事做的相關問詢,他依舊囁嚅,要么就回頭看一眼他老婆,他老婆再對同一問題重新做一次說明。筆錄做完,雖說是向他了解有關情況,但基本上是他老婆做了全部的說明,違法占地行為觸及不多,說得最多的是他們家的窘境。兒子正在上高中一年級,眼睛因視網膜病變嚴重影響視力,可能會有失明的危險,去了國內許多知名的眼科醫院求醫,效果一直不明顯,花費已經是天文數字,能不能不處罰,或者是少處罰。同事表現出無奈,法律的剛性誰也不能逾越,只能是讓他們先回去,處理的進展情況會及時通知他們。并再次叮囑,不要再組織施工,最終受損失的是他們自己,誰也不能代替,他們皆連聲應諾。
日子平白無奇,流水一樣。他違法占地案子的處罰程序按照每一個時間節點,一步一步,緩緩而來。在這個時間段里,他照例不聽勸阻,下達的停工令根本不存在一般。在處罰決定書下達之前,他的鋸房已經落成。我們再去的時候,鋸房里已經安裝了大型鋼鋸,門框上系了紅綢布,他用一種審視我們的眼光探問我們:我已經建成了,你們還有什么辦法?我們的程序沒有任何的閃失,也不存在任何的漏洞,看著他的違法占地建筑成果,我們只能是等,再等一個期間的終止,可以把這個案子移交法院申請裁決。
我曾經想過,如果沒有我們的執法,當事人的建筑進度會不會沒有這么快?我們的介入,給當事人造成了一種緊迫感,這種緊迫感不是法律的剛性帶來的,而是來自他們想要盡快地建筑成型,使法律在他們的違建面前退步。日常和同事交流,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這么多年的執法監察工作,你看看,我們做了什么?”我不解。他繼續說:“從面上講,我們對每一宗違法占地案都處理到位了,這有我們百分百的立案率作為證據。但是再進一步的結果是怎樣的?要求拆除的,拆除了嗎?要求沒收的,沒收了嗎?我們缺失的不是監管力度,而是執行力度。如果僅僅是停留在自行拆除的層面,試問一下,哪一個當事人能讓自己的血汗錢毀在自己的手里?多年前的執法手段明顯不能與形勢相符,造成了今天的被動局面,自覺對不對?這個概念應該沒有任何的錯誤,執法機關,執法者,都寄希望于當事人的自覺,在利益面前,換句話說,在當下的社會大環境下,誰能有這個覺悟?當事人沒有自覺性,只能由法律的剛性來理順這個問題,而目前恰恰缺少的就是法律的剛性。是什么原因造成法律剛性缺失?大家都明白,每一個人的心里都裝著一個現成的答案,無須問詢任何人。你、他、我,都有這樣一個答案。
平淡的是時間,跌宕的是過往。新一輪的疑似圖斑核查又要開始了。時間已近陽歷的年底,一場風雪過后,很快就是陽歷新年。新年后第一日上班,車下高速公路,晨靄還在,馬路上的車輛已經多雜起來,我坐在副駕的位置上,一只麻雀出現在我的視野,它自顧在路邊蹦跳,全然不顧來來往往的車流。它是一只落單的麻雀,我們的車子從它的身邊駛過,也沒有驚飛。路兩邊是擠擠挨挨的廠房,間或一處村路,可以看到遠處的田野,墨綠的麥苗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