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眼中的中國細節
鄒經
1928年,史沫特萊跨越蘇聯邊境,進入中國東北,1941年返回美國,在中國駐留12年。《中國的戰歌》是史沫特萊在中國12年的親歷親聞,《中國在反擊》則是這期間的日記信札,她主動活動于戰區,眼見的多是苦難。而她寫這一切,并不是叫苦。史沫特萊說:“我在過著我這一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日子。我寧愿選擇每天一碗米飯的這種生活,也不想要‘文明社會能夠給我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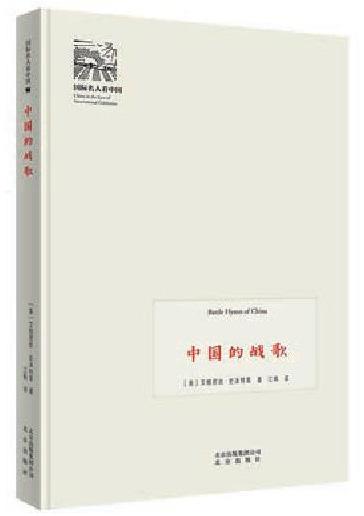
閱讀史沫特萊的場景,不是咖啡館,而是野外。史沫特萊是裸露于野地的石頭,生活本身的風雨打磨,柔脆的部分剝蝕凈盡,剩下最剛健的部分,是石頭的骨,粗礪參差,傷痕歷歷外顯。因為來自大地,所以對大地上普通人之不可遏止的同情,不是意識形態的外露,而就來自她的現場觀察。
“大地的女兒”,是史沫特萊為自己尋找的絕好象征,她的文字,不是對美的求索歷程,而是實感經驗的詳細記錄,多從生活現象入手。雖然史沫特萊往往做不到存而不論,一論就顯其天真,但這天真,也無可辯駁證明著她內在的真。
她年輕時當過速記員,女招待,剝煙葉女工,圖書推銷員,時有挨餓的體驗,她的經歷使她自然地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呼聲滿懷同情,但她的天真和經驗,又無法被完全馴服,所以也始終作為黨外人士而存在。所以,在關于中國的記錄上,我們也許可以更為信任史沫特萊,因為她的所蔽之處,我們完全明了,“圖像去噪”后,歷史中人的細節,我們可以看得更清。
例如,內陸人民的本來生存狀態。中國的廣大群眾缺少一切——糧食、衣物、住房、教育、醫療照顧,他們甚至不知道吃飽肚子是什么感覺或什么意思。延安的大多數農民,不知道北平、天津或上海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日本人是什么人,自八路軍在這一帶建立根據地,這里的農民才開始受教育。當然,教育不可避免地與救亡需求、戰爭時事有關。例如士兵每天上政治課、識字課和寫作課。在識字階段,就注入意識形態教育,所以“從戰士到小鬼,人人都準確地知道打擊什么和為什么而戰”。八路軍各部隊都設有政治部。這些政治部都有自己的演劇隊、演講人和組織工作者。一支軍隊,就是一個戰斗的、組織的、宣傳的、寫作的、演說的龐大群體,不斷動員人民起來斗爭。
八路軍的宣傳能力,從下至上,有土壤,有方法。史沫特萊記錄了一場“宣傳戰”。八路軍為日本士兵準備的日文小傳單,上面寫的是:“我們八路軍是日本勞動人民的同志。我們不殺俘虜,我們寬待俘虜。快過來吧,弟兄們。我們要和你們握手。”一下子拉近了雙方的距離,即便無法感動敵人,也在原則問題上立于正面的一方。而朱德和彭德懷簽署的一份宣言,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導之以利,號召日本士兵調轉槍口對準本國的軍閥,和中國弟兄聯合在一起為日本人民的自由而戰。“不為一個無用的階級消滅自己有用的軀體”。不得不說,這種設身處地的勸說方式,繼承了《左傳》《戰國策》的立言傳統,深得實踐心理學精髓。
相反,日本人向中國軍隊散發的傳單:“一、消滅共黨分子;二、日本人給東亞帶來和平;三、山西的中國軍隊抵抗不了日本,全中國人民也辦不到,所以,必須投降。”行文粗鄙,邏輯斷裂,直如法院傳票,簡直不像是曾誕生過紫式部、夏目漱石的國度。史沫特萊敏感抓取的此類細節,豐富了我們對抗日戰場的多元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