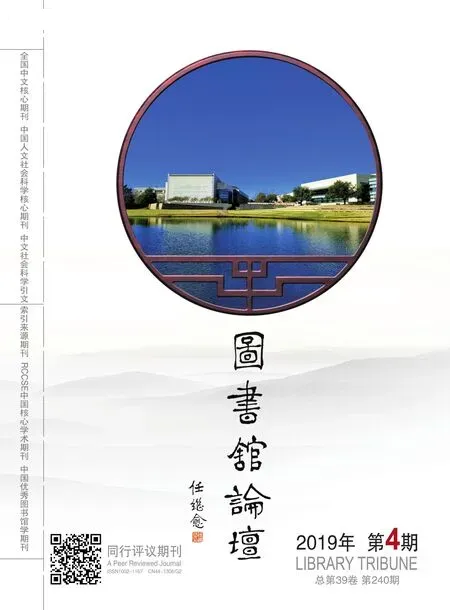宋元時期陶瓷文獻分類方法探討*
陳 寧,曹 之
1 古代陶瓷文獻概況及稀少原因考察
我國古代包含陶瓷文獻在內的科技類文獻,與經部、史部、集部等類文獻相比,少得可憐。梁啟超曾言:“做中國學術史,最令我們慚愧的是,科學史料異常貧乏。”[1]而作為古代手工技藝之一的陶瓷制作,相關著述更是鳳毛麟角。直到宋元時期,我國才出現第一篇紙質陶瓷專論之作《陶記》;明代中晚期才出現第一部陶瓷專著《陽羨茗壺系》;而整個古代陶瓷專論之作和陶瓷專著加起來不過20 余種。這與我國近萬年的陶瓷生產發展歷史相比,很不相稱。由于陶瓷相關文獻中論及這一問題的史料極少,筆者將它放在數量相對較多的科技類文獻中來探討,以此推測古代陶瓷文獻稀少的原因。通過考察分析,造成古代科技類文獻(包括陶瓷文獻)稀少的原因可歸結為四個方面。
(1)作為古代立國之本的儒家思想安貧樂道,不重視科學技術和經濟建設,這在儒家經書《論語》中就可找到許多證據。《論語·里仁》 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2]32《論語·子路》言:“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3]117-118孔子認為“喻于利”者為“小人”,只要抓好“禮”“義”“信”就可以了,不必抓什么農業生產。古代深受這一思想影響,導致文史類著述豐碩、科技類著述稀少的局面。
(2)古代部分統治者大興文字獄,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古代統治者以功名利祿為誘餌,把知識分子引入鉆研儒家經典的死胡同,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青燈黃卷,皓首窮經,脫離生產,脫離實踐,厚古薄今。如果當時這些掌握著能文識字技能的知識分子能夠致力于科技生產,科技類著述會大量增加。
(3)古代統治者輕視科學技術。歷代王朝缺乏鼓勵人們進行科技生產及其研究的機制,科技生產及其相關研究與升官發財毫無關系。宋代學者沈括在《夢溪筆談·序》中言:“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噱,不系人之利害者。”[4]明末科學家宋應星在《天工開物·序》中亦言:“丐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5]科技生產在古代常被視為“不系人之利害”“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的事情。“有識”之士“棄暗投明”,很少關注科技生產,更不愿“出力”做研究。《漢書·樓護傳》中就記述了有醫學之才的樓護“棄醫從經”之事:“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由是辭其父,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6]樓護本有醫學之才,后來“長者”覺得他大材小用,勸導他改學經傳,果然成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
(4)古代知識分子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觀念影響,視科學技術為“雕蟲小技”,不屑于從事這方面的實踐和研究,動手能力差,有的甚至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錯過了發明創造的機會。美國學者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中言:“一旦穿上了長衫,就拋棄了體力勞作……他們認為用雙手勞作的都不是讀書人……這種手與腦的分家,與達芬奇以后的早期歐洲科學先驅者們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對照。”[7]這種長期脫離生產實踐的做法使知識分子對“雕蟲小技”毫無興趣,當然也就無所作為。豈不知這些“雕蟲小技”往往包含著可以解開宇宙奧秘的大道理,往往關系著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古代無視這些“雕蟲小技”,注定他們與許多發明創造無緣,更少有人付諸熱情,投身到科技生產的實踐和研究之中,自然也就不會產生多少科技著述。科技研究是系統工程,就像接力賽跑一樣,承前啟后,代代相傳;科技著述是承上啟下的接力棒,沒有這個“接力棒”,就會失去攀登科技高峰的良機,就要走許多彎路。明末以后中國科技日漸落后,也許正是科技類著作稀少導致的結果。
概言之,我國古代受各種因素影響,文人學者大多“不屑于”科技、工藝、器物之類的文獻著述,而諸如陶瓷之類的手工藝人又大多不識字,無法將自己的技藝和思想付諸文字,筆之于書,他們只能通過口口相傳、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承其技藝和思想,這導致這幾類文獻編撰數量稀少,而作為古代手工技藝之一的陶瓷制作著述更是鳳毛麟角。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需要整理、挖掘和利用好陶瓷文獻。本文以宋元時期陶瓷文獻為例,探討它們在古代文獻分類體系中的分布狀況,并對各類陶瓷文獻的史料價值作簡要評析;以此為基礎,建構符合這一時期陶瓷文獻實際狀況的分類方法。
2 宋元時期陶瓷文獻分類方法建構的依據
成書于清代乾嘉時期的《景德鎮陶錄》有言:“從來紀陶無專書,其見于載籍者,或因一事而引及一器,或因一器而引及一事,或因吟賦而載一二名。”[8]從現有陶瓷文獻整理成果來看,我國古代陶瓷文獻史料的分布狀況確實如此。我國古代不僅在陶瓷文獻編撰數量上稀少,而且在陶瓷史料分布上也比較零散,多是一些只言片語,少則一兩句,多則數十言,成系統的陶瓷專論之文甚少。就宋元時期而言,陶瓷文獻史料的分布情況更是如此。這一現實狀況是我國古代陶瓷文獻分類方法建構的基礎,也是本文研究過程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關于古代陶瓷文獻分類方法的探討,最早見于1993年傅振倫在《景德鎮陶瓷》第三卷第四期發表的《中國古陶瓷文獻學(二)》(以下簡稱“傅文”),但一直未引起學界的關注。可能是由于這一工作需要大量的整理實踐作為基礎和支撐,之后鮮有學者再有論及。傅文鑒于陶瓷文獻極其分散的狀況,將其分成了十三類,分別是正史類、政書類、雜史或專史類、地理或方志類、類書類、詩文集類、格致之書類、金石類、名窯資料類、圖錄類、筆記雜說類、中外文化交流類、其它類[9]。不過傅文中并未言明如此分類的依據,也沒有考慮到古今陶瓷文獻的差異性,而是將古今陶瓷文獻全部囊括其中。其實,該分類法不僅不能囊括古今所有的陶瓷文獻,就連古代陶瓷文獻也未能全部囊括其中。比如,古代陶瓷專論文獻分布比較集中的譜錄類文獻,卻只能錄入“其它類”,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整體而言,傅文第一次提及我國古代陶瓷文獻的分類方法,其開創之功不可抺殺。其中提及的一些類目,如政書類、地理類、類書類、詩文集類、金石類等是值得今人借鑒和參考的。當然,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尤其是針對本文研討的宋元時期的陶瓷文獻,至少有四點值得探討和商榷。
(1)個別類目劃分過于細化,如正史類、雜史或專史類等,這兩類古代陶瓷文獻并不多,無需如此細化分類,可以考慮借鑒當前比較科學的劃分類別,統歸入“歷史類”。這樣該類收錄的陶瓷文獻相對多些,不僅可以支撐這一類別,還方便世人查找。還有格致之書類、筆記雜說類,可以統歸入“雜家類”,這樣既符合古代文獻的分類習慣,也方便世人查找。
(2)有些涵蓋重要陶瓷文獻的類目沒有設置,如譜錄類、六經類、小學類、目錄類等。這些類目都是涵蓋比較重要陶瓷文獻的類目,需要強化和凸顯其重要性,不可混入“其它類”中。
(3)個別類目的名稱不太適用于古代陶瓷文獻分類,如名窯資料類、圖錄類、中外文化交流類等。這幾類若用于當前陶瓷文獻的分類尚可,但在古代陶瓷文獻中或者數量十分稀少,或者根本沒有。比如,專門論述名窯資料的陶瓷文獻,大多收錄在譜錄類文獻中,幾乎沒有專論名窯資料的陶瓷文獻。需要說明的是,傅文中“圖錄類”文獻下羅列的明代項元汴的《歷代名瓷圖譜》,其實是近人托古的一部偽書,不能當作古代陶瓷文獻看待。
(4)整個分類體系的邏輯性稍顯不足,有些類目設置的標準不太統一,這使人們在實際的陶瓷文獻分類過程中,由于類目之間的界限不夠清晰,往往會產生困惑,甚或無所適從,不知道將其歸于何類。比如,地理或方志類與名窯資料類,名窯資料類與圖錄類、格致之書類與筆記雜說類等,在實際分類過程中就有可能會出現交叉的情況。即使是交叉收錄,傅文中也沒有提及以“互見”或“互著”的方法來進行完善和補充。
有鑒于此,筆者以自己歷時六年參與組織編纂的《中國古代陶瓷文獻影印輯刊》作為參照對象,通過對其中宋元時期陶瓷文獻的分類羅列和歸納分析,以求更加具體直觀地反映出這一時期陶瓷文獻的實際分布狀況。然后在傅文陶瓷文獻分類法的基礎上,汲取其優點,完善其不足,并通過借鑒傳統四部分類法,尤其是借鑒《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分類法的類目設置,再結合當前比較科學的文獻分類法,建構較符合宋元時期陶瓷文獻實際存在狀況的分類方法。具體而言,筆者將這一時期陶瓷文獻分成了十類:六經類、小學類、歷史類、地理類、政書類、目錄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詩文集類。
3 宋元時期陶瓷文獻分類方法的具體建構
3.1 六經類
六經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后來出現了大量有關六經的各種注釋類文獻,并把這些注釋類著述納入“六經”的范圍之中。本文所指的六經類文獻,就是有關六經的各種編撰形式的著述。其實這類著述中的陶瓷史料不多,內容多有雷同之處,宋元時期的這類著述即是如此。今舉其要者,如表1。

表1 宋元時期“六經類”重要陶瓷文獻一覽表
此外,六經各類文獻的多寡情況有所不同,以易類、禮類文獻居多,詩類、書類、樂類文獻較少,而春秋類文獻基本沒有。從表1看出,這類文獻主要是對《易經》《尚書·禹貢》《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樂書》等的一些陶瓷相關字句進行闡釋。以《易小傳》為例,“卷一下”就對“有孚盈缶”之“缶”字作了闡釋,其文略云:
缶,質素之器,圓虛而應者也。凡親比之道,茍有由中之信,初不待豐其禮、盈其器也。故圣人復假象以兼明之,猶如祭祀之器,以瓦為缶,中有玄酒之盈,則可以通神明之德。君子充誠信之實,圓幾善應,為比之首,則可謂得比之道,是以有孚缶,貴誠也。[10]
值得一提的是,禮類文獻中的《周禮》不僅提及當時“陶正”的職責范圍,還明確“陶人”“旊人”的生產分工,以及各種禮儀用器(包括陶瓷器)的形制、規格、功能、用途等。這些內容對于認識上古三代的陶瓷生產管理情況具有參考價值。尤其是對“陶人”“旊人”的全文錄載和相關注解是研究當時陶瓷工匠生產分工的重要史料,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由于“六經”問世較早,孔子整理于春秋末年,當時成熟瓷器尚未產生,陶器也不是王侯貴族禮儀和生活用器的主流,故而相關記述少。而宋元學者只是據文注釋略作提及,但有些史料,如《周禮·冬官考工記》中有關“陶人”“旊人”的記載是研究當時陶瓷工匠生產分工的重要史料,在此類陶瓷文獻整體稀少的情況下,顯得彌足珍貴。鑒于此,筆者將六經類文獻獨列為一類,以體現其重要性。
3.2 小學類
關于“小學”的含義,古今看法有所不同。本文采用《總目》的劃分方法,將“小學”獨列一類,并將其收錄文獻的范圍涵蓋到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三類。今舉其要者,如表2。從表2看出,小學類文獻主要是對陶、瓷、窯、瓦、坯、缶等字詞的讀音和含義進行解釋說明,對了解和認識這些字詞的含義本源、演變脈絡和使用情況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作為陶瓷史論研究的輔助性材料。
3.3 歷史類
這里所言的歷史類文獻是指記述某人、某事、某時、某地或某國歷史情況的文獻,包括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雜史類、傳記類、史鈔類、史評類等。今舉其要者,如表3。從表3可以看出,歷史類文獻主要記述古代有關陶瓷發生的一些事件。這類文獻中的陶瓷史料從多個角度記述了與陶瓷器物和生產貿易相關的歷史,對研究我國古代陶瓷生產管理的發展演變,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表2 宋元時期“小學類”重要陶瓷文獻一覽表
3.4 地理類
地理類文獻尤其是地方志涵蓋內容廣泛,常被譽為“地方博物之書”“一方之全史”“地方百科全書”等,故而這類文獻中大多囊括有陶瓷史料。今舉其要者,如表4。從表4看出,地理類文獻中的陶瓷史料頗為豐富,涉及內容較廣,如《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城志》《嘉泰吳興志》《元一統志》等記述了宋元時期各地名窯的產瓷貢瓷情況,《諸蕃志》《島夷志略》等記述了宋元時期中國與多個國家和地區之間包括陶瓷器在內的貿易往來情況,《淳熙三山志》記述了曾在福州南臺設立的主造磚瓦的“窯務”的沿革情況,《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則記述了宋代宣和時期徐競出使高麗時的所見所聞,其中就錄載了高麗青瓷(如尊、爐之類)的生產情況等。《至順鎮江志》卷十八錄載了元代景德鎮監陶官堵閏的生平事跡,其文云:“堵閏,字濟川,金壇人……至順二年七月,奉命督陶器于饒,行次三衢之常山,以病卒。”[11]這一史料對于整理研究元代監陶官的生平事跡和監陶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地理類文獻尤其是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在宋元陶瓷史料整體匱乏的情況下,數量較多,內容廣泛,對古陶瓷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章宏偉將地理類文獻同“廿四史”“九通”之類的文獻作比較,僅就其中的陶瓷史料而言,他認為地理類文獻的地位和作用,要比“廿四史”“九通”之類的文獻重要得多。這是由于“廿四史”“九通”之類的文獻是以王朝為中心,只記載有利于維護統治和服務秩序的事實和言論,很少關注平民的生產生活;地理類文獻則是以社會為中心,舉凡地理概貌、山川物產、民俗風情、人物藝文等,不詳于“正史”記載的,幸得以這類文獻保存下來[12]。可見這類文獻的史料價值是非常高的,理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并加以充分的挖掘和利用。

表3 宋元時期“歷史類”重要陶瓷文獻一覽表

表4 宋元時期“地理類”重要陶瓷文獻一覽表
3.5 政書類
政書的編撰,源于正史中的“志”,而后獨立成書,其內容主要是介紹歷朝歷代政治經濟方面的典章制度。《總目》設有“政書類”,隸于“史部”之下。本文仿《總目》之例,將此類的陶瓷文獻也獨列為一類。今舉其要者,如表5。

表5 宋元時期“政書類”重要陶瓷文獻一覽表
從表5中看出,這類文獻主要記述宋元時期與陶瓷相關的職官設置、器用制度、生產貿易、建筑規格等,還涉及與陶瓷燒造有關的法律規定。比如,《通制條格》卷八“器物飾金”條記載:
至元八年十一月,尚書省欽奉圣旨,節該今后諸人,但系磁器上并不得用描金生活,教省里遍行榜文禁斷者。[13]
又卷十六記載:
大德八年正月,欽奉詔書內一款:國家財賦,自有常制。比者諸人妄獻田土、戶計、山場、窯冶,增添課程,無非徼名貪利,生事害民。今后悉皆禁絕,違者治罪。[14]
可見這類文獻中的陶瓷史料,對于了解我國古代的器用制度,認識古代建筑所用磚瓦的規格,探知陶瓷相關的典章制度,研究各個時期的陶瓷生產貿易狀況等,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目前這類史料整理的并不多,挖掘的更不夠,常被學界忽視,利用者較少。鑒于此,筆者盼望有志于此的學者,能全面收集和整理這類文獻中的陶瓷史料,并予以充分地挖掘和利用,以更好地解決陶瓷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豐富和完善陶瓷研究中的相關內容。
3.6 目錄類(金石類文獻入此)
關于“目錄”一詞的連用,最早當起于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圖書之時[15]6,劉氏父子因此而編撰的《七略》《別錄》是目前我國有稽可查的最早的圖書分類目錄和提要目錄。漢代,“錄”的含義覆蓋“目”,故“目錄”常被簡稱為“錄”。后來隨著文獻增多,著錄“旨意”的目錄越來越少,遂將“錄”之名統歸于“目”,于是有篇目而無“旨意”者也稱為“目錄”。久而久之,連只記書名而不錄篇名者,也冒稱“目錄”之名了[16]7。宋元時期,目錄類文獻編撰數量稀少,涵括陶瓷史料者更是鳳毛麟角。據筆者考察,目前涵括陶瓷史料的目錄類文獻只有宋代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其中收錄了《營造法式》《呂公窯頭坯歌》等與陶瓷相關的著作,對其卷數、作者、編撰過程、內容概要等給予說明。以所錄《營造法式》為例,其文云:
《營造法式》三十四卷,將作少監李誡編修。初熙寧中,始詔修定,至元佑六年成書。紹圣四年,命誡重修,元符三年上,崇寧二年頒印。前二卷為總釋,其后曰制度,曰功限,曰料例,曰圖樣,而壕寨、石作、大小木、雕、鏃、鋸作、泥瓦、彩畫、刷飾,又各分類,匠事備矣。[17]
目錄是我國古代圖書的清單,盡管其編撰數量稀少,但其中錄載的陶瓷史料,尤其是有關陶瓷專論文獻的著錄文字,對于梳理和研究我國古代陶瓷文獻的編撰數量、內容體例、史料分布、存佚狀況等具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金石類文獻是指專門匯錄鐘鼎、碑刻、金石、磚瓦等載體上文字圖案的文獻。關于它的分類著錄,古代目錄不盡一致。比如,《隋書·經籍志》 《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將其統歸入“小學類”,而《宋史·藝文志》將其改入“目錄類”,隨后漸成定例。《總目》亦是依從《宋史·藝文志》之例,將其歸入“目錄類”,不過編排方式有所改變。它將金石類文獻全部析出,獨成“金石”一類,不再像《宋史·藝文志》那樣將此類文獻雜糅于目錄類文獻之中,而是附于經籍類文獻之后。這可能是由于《總目》編撰者已經認識到如此劃分的不合理性,正如他們在“目錄類”小序中言,將“金石之文”附于經籍類文獻之后,只是為了“并列此門”,但“別為子目,不使與經籍相淆焉”。由于涵蓋陶瓷史料的這類文獻比較稀少,筆者依從《總目》之例,將其與目錄類文獻合并成“目錄”一類,并將兩類文獻作以區分排列,將金石類文獻排列在經籍類文獻之后。
金石類文獻最早始于南朝梁元帝蕭繹集錄碑刻文字而作的《碑英》。宋代漸有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等著述相繼問世,搜討和著錄金石之文獻漸多,但整體數量仍然稀少,涵括陶瓷史料者更少。據筆者考察,此類文獻中涵括陶瓷史料者,主要有趙明誠的《金石錄》、洪適的《隸續》、陳思的《石刻叢編》等,其內容主要是對古代磚瓦上的文字進行考證說明。這對于了解古代磚瓦的收藏演變,認識古代磚瓦的文字或圖案裝飾,考訂一些文字的源流變化,補正歷史研究中的部分錯漏等,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3.7 譜錄類
在四部分類法中,譜錄類收錄的文獻較為龐雜,覆蓋內容廣泛。《總目》在該類小序中闡述了該類設置的原因和收錄文獻的大致范圍:“古人學問,各守專門,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隸。六朝以后,作者漸出新裁,體例多由創造,古來舊目遂不能該(同‘賅’),附贅懸疣往往牽強……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創立‘譜錄’一門,于是別類殊名,咸歸統攝,此亦變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諸雜書之無可系屬者。”可見,譜錄類是一個辨體類目,只認體裁,不看內容。如此收錄文獻,似乎不盡合理,但是為了遵從古代文獻的分類習慣,方便查閱,筆者依從《總目》之例,按照其著錄規則,編排涵括陶瓷史料的相關文獻。根據《總目》的類目設置,譜錄類下又設器物、飲饌、草木禽魚三小類,而宋元時期涵括陶瓷史料者主要是器物和飲饌兩類文獻。今舉其要者,如表6。

表6 宋元時期“譜錄類”重要陶瓷文獻一覽表
從表6看出,飲饌類文獻只有《茶錄》一種,主要記述宋代瓷器在飲茶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比較各地瓷盞的優劣,其文云:“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斗試家自不用。”[18]可見,古人在飲茶器具選用上是十分考究的,這也是我國古代飲茶文化的一個重要反映。
與飲饌類文獻相比,器物類文獻不僅編撰數量較多,而且涵括的陶瓷史料豐富。宋元時期這類文獻所錄載的內容大多是古代磚瓦的大小規制、功能用途及其演變情況,其重要性尚不突出。但是到了明清時期,陶瓷專論文獻漸趨增多,陶瓷專著也開始出現,如明代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清代吳騫的《陽羨名陶錄》、朱琰的《陶說》、藍浦的《景德鎮陶錄》等,大都歸于此類。正是由于這些陶瓷專論文獻和陶瓷專著的出現,使得后來此類的重要性異常凸顯,是陶瓷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3.8 雜家類
所謂“雜家”,《漢書·藝文志》有云:“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19]可見,在漢代,雜家可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縱橫家、陰陽家、農家等八家分庭抗禮,平等視之,它們合起來稱為“九流”。但是到了明清時期,各種官私目錄將“雜家”視作“無所不包”的大雜燴。僅就宋元時期而言,此類文獻涵括陶瓷史料者頗多。今舉其要者,如表7。

表7 宋元時期“雜家類”重要陶瓷文獻一覽表
這類文獻由于內容龐雜,涉及面廣,時常會有論及陶瓷的相關記述,盡管這些記述大多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但是某些史料的可利用價值頗高。這些史料對于古陶瓷研究的發展,起到了較好的推動作用,尤其是對古陶瓷研究中某些問題的解決,起到重要的補充作用。比如,《東坡志林》卷五錄載了宋代景德鎮監陶官余獻策的相關事跡:“近者余安道(指余靖)孫獻策榷饒州陶器,自監榷得提舉,死焉。”[20]這則史料為全面了解宋代景德鎮監陶官的監陶情況提供了線索,但是很少被學界關注和提及。又如,《老學庵筆記》卷二記述了北宋時期宮廷用瓷由定器改用汝器的原因和耀州窯仿燒余姚青瓷的情況:“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余姚縣秘色也。然極粗樸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21]這兩則史料是考察宋代定窯、汝窯、耀州窯瓷器生產狀況的重要參考資料。在宋元時期,類似這樣明確記述窯口生產的資料鳳毛麟角。

表8 宋元時期“類書類”重要陶瓷文獻一覽表
3.9 類書類
所謂類書,是指根據編纂的目的,將所需的資料從各類文獻中輯錄出來,然后按照一定的方式編排的圖書。由于類書的內容較為龐雜,含有經、史、子、集各部內容的成分,人們無法確定它應統歸于何部,這給古代四部分類法劃分圖書門類時帶來了不少麻煩。《總目》編纂者在“類書類”小序中就曾言道:“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有鑒于此,筆者不再設四部,而將諸如“類書類”這樣的類目,獨列為一類,避免了它們“無部可歸”的尷尬。同時,由于類書類文獻涵蓋內容比較廣泛,宋元時期此類文獻中涵括陶瓷史料者較多。今舉其要者,如表8。
從表8看出,這類文獻根據編纂體例的需要,將各種文獻中的陶瓷史料匯集在一起,并編排在相應的類目中,為讀者查檢和利用這些陶瓷史料提供了便利。同時,這類文獻在編排和錄載陶瓷史料時,大多標明來源出處,為讀者核實這些陶瓷史料的內容提供了線索。而其中錄載的已佚文獻的陶瓷史料,幸賴此類文獻的流傳而得以保存。比如,作為宋初著名類書之一的《太平御覽》,首次將“磚”“瓦”“琉璃”作為獨立的條目,匯錄了《詩經》《禮記》《史記》《漢書》《古史考》《博物志》《漢武故事》《燕丹子》《說林》《大秦記》《靈鬼志》《南州異物志》等文獻中的相關描述,尤其是《說林》《大秦記》《靈鬼志》《南州異物志》等當今難以覓見的文獻,其中錄載的陶瓷史料幸賴此書而得以流傳,可見其史料價值之高。由是亦可觀之,宋元類書中涵括的陶瓷史料,在當時陶瓷史料整體稀缺的情況下,顯得彌足珍貴。這些史料對于了解和認識我國宋元及其以前的陶瓷生產和使用情況,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3.10 詩文集類
詩文集類,在《總目》中隸屬四部之“集部”,主要收錄詩文之類的文獻。這類文獻涵括的陶瓷史料頗為豐富。從目前發現的史料來看,漢代鄒陽《酒賦》最早錄載了吟詠陶瓷的詩句:“醪醴既成,綠瓷既啟。”[22]到了唐代,涵括陶瓷史料的詩文漸多,還出現了專論陶瓷的詩文,如陸龜蒙的《秘色越器》、徐夤的《貢余秘色茶盞》、杜甫的《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等。到了宋元時期,這類文獻的編纂繼續發展,數量相當可觀,其中涵括陶瓷史料者也比較多。今舉其要者,如表9。
從表9中看出,此類文獻中涵括的陶瓷史料內容十分豐富,涉及了官方所需磚瓦的制作來源,各種瓦硯的形制特點,多件陶瓷器物的風格、用途,陶瓷工匠的窮苦生活,陶瓷器物的生產貿易等等,有詩有文。限于篇幅,筆者僅以陶瓷相關的詩歌資料為例加以說明。這類詩歌資料或僅有寥寥數字,對陶瓷只是略作提及,整體價值不高,但偶爾也有一些可參引的詩句,如《鄱陽集》卷三錄載的《送許屯田》中有“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23]之句,反映了宋代景德鎮青白瓷燒造的美妙釉色;或通篇論及陶瓷的,如《滏水集》卷六錄載的《汝瓷酒尊》,形象地描述了宋代汝窯酒尊的形制和釉色:“秘色創尊形,中泓貯醁醽。縮肩潛蝘蜓,蟠腹漲青寧。巧琢晴嵐古,圓嗟碧玉熒。銀杯猶羽化,風雨慎緘扃。”[24]又如《宛陵集》卷四錄載的《陶者》,則反映了宋代陶瓷工匠雖勤奮勞作,卻過著十分窮苦的生活,暗諷了那些富貴之家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生活:“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25]由此可見,這類文獻不僅編纂數量較多,而且史料價值頗高,是陶瓷研究者不可忽視的重要參引對象。但當前學界尚未給予足夠的關注和重視,對這類文獻的挖掘、整理和利用的程度不夠。

表9 宋元時期“詩文集類”重要陶瓷文獻一覽表
綜上所述,筆者在傅文陶瓷文獻分類法的基礎上,通過借鑒《總目》分類法的類目設置,再結合當前比較科學的文獻分類法,根據宋元時期陶瓷文獻的實際存在狀況,將這一時期陶瓷文獻分成了上述所列的十類。如此分類,基本上反映了宋元時期陶瓷文獻的分布狀況。但需說明的是,這十類文獻并不是宋元時期陶瓷文獻的全部,一些醫家類、儒家類、小說家類、藝術類的文獻亦涵括陶瓷史料,如宋代吳彥夔的《傳信適用方》記述了定瓷粉末入藥用的情況,朱長文的《墨池編》記述了古代瓦硯的形制和裝飾特點,洪邁的《夷堅志》記述了潼州陶匠梁氏、蕭縣陶匠鄒氏、鄱陽陶器店主張點魚、景德鎮瓷器販商黃廿七等人的相關事跡等。但這幾類文獻不是涵括陶瓷史料者的數量太少,就是涵括的陶瓷史料取自傳聞,內容多不可信,或只作簡單的功用提及,價值甚微,尚不足以單列一類。
此外,尤值一提的是,我國第一篇陶瓷專論著作《陶記》也出現于這一時期。但是,由于它迄今尚未發現獨立成書的版本,只見載于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年間編纂的《浮梁縣志》中,故而無法將其歸入這一時期陶瓷文獻的分類體系中,只能單獨列出,適當加以簡述。從正文內容來看,《陶記》只有短短的1000 余字,但其涉及面十分廣泛,對作者生活時期的景德鎮瓷器的原料制備、裝飾技法、燒造工藝、產品種類、銷售市場、匠籍制度、工匠分工、稅課收入等均有一定的文字描述,在當時陶瓷史料比較匱乏的情況下,這則專論當時景德鎮制瓷業的史料顯得彌足珍貴,參考價值極高,常被傳抄轉引。《陶記》的問世,不僅開啟了陶瓷專論文獻編纂的先河,為陶瓷專著的編纂提供了思路,而且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出現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對我國陶瓷史研究的發展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4 結語
整體而言,我國古代陶瓷文獻不僅數量相對稀少,而且分布極其分散。筆者根據自己多年來整理古代陶瓷文獻的實踐成果,在借鑒以往有關陶瓷文獻分類方法的基礎上,以宋元時期為例,建構出一套符合宋元時期陶瓷文獻實際存在狀況的分類方法,即前面所列的十類。從其中涵括的陶瓷史料來看,各類陶瓷文獻的編撰數量和價值高低是有所不同的:就編撰數量而言,以詩文集類最多,六經類、地理類、雜家類、類書類次之,其余各類較少,以目錄類最少;就史料價值而言,研究角度不同,價值也略有差異,但在陶瓷史料極其稀少的情況下,每條史料都有可能解決陶瓷研究中的一些疑問,需要全面挖掘和充分利用。
筆者建構的這一套分類方法,不僅為世人查找陶瓷文獻、搜集陶瓷史料提供一定的線索和方向,而且還為其他專題文獻,尤其是與陶瓷文獻相近的玉器類文獻、銅器類文獻,甚至范圍更廣的工藝類文獻、藝術類文獻、科技類文獻等分類方法的建構都提供了有資可鑒的思路和方法。當然,本文研討的對象主要是宋元時期的陶瓷文獻,筆者后續將以此為基礎,逐個時代地對陶瓷文獻進行拓展整理實踐和歸納分析研究,以探求中國古代陶瓷文獻分布狀況的演變,進而建構出一套更加宏觀、系統、完善的陶瓷文獻分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