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時錦記
2019-04-15 03:02:32莫諾
美文
2019年6期
莫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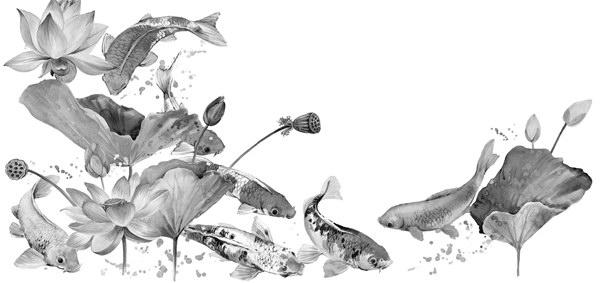
這世間,從來如此——再濃重的筵席,也敵不過天高云低,晚來風急。
桃紅柳綠,旦夕翻身之間,才驚覺,這一朝年歲竟業已見底,仿佛踮腳便能張望到來年沉甸甸的日子。
二0一八,紅塵滾滾,上帝收走了好些人。
而我仍是這俗世里一枚敲鐘的僧。
此間年月,雖故事無多,卻心有所感。是以歲月為憑,時令為證,紙筆為記。
驚蟄
江南春雨,總是綿長的。
自菲律賓旅歸后,這雨便似個碎嘴寡婦,未有停歇之意。一連十余日,陰云蓋頂,仿佛厄運即臨,盤踞天幕,不肯退去,斜風細雨,總在街頭巷尾過市招搖。起床掀開窗簾,又是一個灰頭土臉的陰雨天,心情就難免跟著灰敗了幾分。尚未出門,整顆心便已淋濕了半截。在如此天氣里待久了,多多少少都會叫人憋出些心理上的病來。
由此,便格外眷戀起東南亞春日的爽朗——即便是雨,那也是淋漓酣暢的雨。
去年春日在甲米,是領教過這雨勢之迅猛豪爽的,那雨鋼炮似的毫無預兆地砸落下來,若非盔甲傍身,凡身肉體定是扛不住這般猛攻的。不出半刻鐘,整個奧蘭小鎮,由海灘至長街,霎時空無一人。人群撤離之速度,好似行軍蟻覓食。
我和友人自沙灘急奔上來,擠在街角店家屋檐避雨的人堆里。我專情于檐外雨之暴烈迷人,只見那碩大雨點砸在瀝青路上,似銀幣落地,乒乓作響,滾動如珠。不遠處,海面起了大片雨霧,迷蒙如一道閨閣簾幕。如此,更遠處的山就猶如躲在那閏閣簾幕后的秀女,原本粗曠的野山頓時便顯得清秀端莊起來。……
登錄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