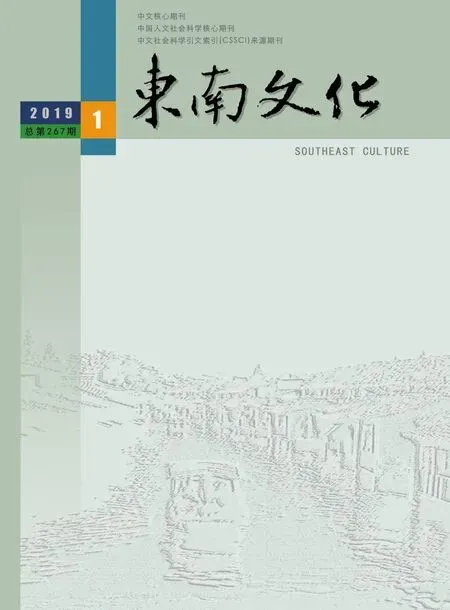試析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遺存及其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的關系
白國柱 余 飛 劉海峰
(1.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24;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合肥 230601;3.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 江蘇南京 210044)
內容提要:一直以來,學界對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遺存認知較為模糊,概因處于該時間段的遺址雖為數不少,但文化層卻多單薄,資料也零碎。但從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可知,寧鎮地區自良渚文化后至點將臺文化之間并非空白。近年來,安徽當涂船里山、江蘇鎮江馬跡山等遺址均發現有后良渚階段遺存的地層堆積或遺跡,遺物也較豐富。結合以前的發掘和調查資料,可以發現這類遺存不僅與以太湖流域為分布中心的同時期考古學文化關系緊密,而且與淮河流域、滁河流域甚至海岱地區的龍山時期諸考古學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寧鎮地區,一般是指以寧鎮、茅山等山脈為主體的丘陵區,其核心地帶為這些山脈所包圍的區域,域內涵蓋秦淮河、姑溪河兩大水系;其西部、北部以長江為界,南部以青弋江下游入江地帶至胥河一線(古中江)為界,東部大致以茅山山脈為界。它的東北緣地帶,情況則有些特殊。寧鎮山脈一直往東延伸到江蘇武進孟河鎮,進入太湖流域區;而屬太湖流域的香草河,向西可溯源至江蘇句容邊城鎮,進入寧鎮核心區。這個地帶,屬溝通南北的地理要沖,位置相當重要。寧鎮山脈東北側與太湖流域重疊區域,暫劃至寧鎮地區進行研究。
早在20世紀50年代,南京博物院便對寧鎮及鄰近地區遺址進行了普查[1],為之后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奠定了基礎。以往對寧鎮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多為三分法,主要以魏正瑾、張敏、張之恒為代表,其劃分法依次如下:
(1)北陰陽營期→昝廟期→昝廟二期[2];
(2)丁沙地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城頭山—朝墩頭文化遺存期[3];
(3)北陰陽營期→昝廟一期→昝廟二期[4]。
有學者持有其他認識,如紀仲慶的四期說[5]、谷建祥的五期說[6]和以陳國慶為代表的二期說[7];另有劉建國在魏正瑾分期基礎上提出的寧鎮地區東區三期說[8]。
以上諸說,末期年代并無晚于良渚者。張敏等學者認為寧鎮地區良渚文化與青銅文化之間存在缺環[9],這個缺環即后良渚階段。囿于資料限制,之前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遺存的文化面貌并不清晰。自1999年以來,上海廣富林[10]、浙江湖州錢山漾[11]遺址全面發掘后,先后提出“廣富林文化”[12]“錢山漾文化”[13]的認識,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末期形成良渚—錢山漾—廣富林的文化序列,然后是青銅時代的馬橋文化。有學者指出,寧鎮地區同時期遺存是王油坊類型南下的產物[14]。近些年,伴隨調查、發掘的增多,寧鎮地區也發現或辨析出許多后良渚階段遺存,其是否有明確的文化歸屬,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的關系又是如何,則有待于進一步的認識、探討。
一、寧鎮地區已發現的后良渚階段遺存
寧鎮地區已發現的具有后良渚階段遺存的遺址,目前至少有21處,主要分布于秦淮河、姑溪河流域,胥河、東北臨江地帶也有分布。這些遺址周邊水網多較發達,交通便利。
(一)典型遺址
這類遺址資料多較豐富,一般有保存較好的地層,層位關系清晰或遺物較典型,如安徽當涂船里山[15],江蘇鎮江馬跡山[16]、南京太崗寺[17]和高淳朝墩頭[18]等。
1.船里山遺址
位于安徽省馬鞍山市當涂縣姑孰鎮松塘村尹家自然村。安徽省文物考古所2014年發掘,發現后良渚階段遺存[19]。其中T1⑥出土的遺物特征相近,年代屬龍山晚期。其他探方,如T2⑤、T3⑤應屬二里頭文化早期,混有少量龍山晚期遺物。所見龍山時期陶器,鼎或罐的頸部多有變長趨勢,腹徑多大于口徑;側扁三角形鼎足(圖二︰4—6)多見,足尖一側多見按捺,足側面或微內凹,足跟外側或有1~2個按窩。其他典型遺物有斜弧腹陶缽(圖二︰1)、淺斜腹陶器蓋(圖二︰2)和半月形石刀(圖二︰7)等。發掘之前考古人員曾對遺址進行過調查,采集到1件魚鰭形足(圖二︰3)。鼎足一側偏厚,一側偏薄,足面有刻劃槽,其年代應為龍山早中期。
2.馬跡山遺址
位于江蘇省鎮江市京口區五鳳橋高架與丁卯橋路交界處東側,往北近200米即為京杭大運河。1980年、2014年各進行過一次發掘,其中第二次發現有新石器時代末至商周時期遺存[20]。發掘者將其劃分為三期:第一期以⑦層、H47為代表,年代為龍山末期;第二期以⑥層為代表,年代為夏時期;第三期以②、③、④、⑤層及⑤層下遺跡為代表,年代為西周晚至春秋前期。在對材料進行分析后,筆者認為不同探方層位并不統一,其第一期遺存可再行劃分。原ⅡT0103⑦、ⅠT0302⑥、ⅠT0303⑥、ⅡT0101⑥、H35、H47等應屬崧澤時期,而ⅠT0201⑥、ⅡT0301⑥、ⅡT0302⑥、ⅡT0303⑥和ⅠT0101⑤等則屬龍山時期。從遺物形態判斷,ⅡT0201⑤應屬二里頭文化偏晚至二里崗下層之間,而ⅡT0202⑤卻為晚商,可見不同探方⑤層年代并不相同。遺址龍山時期地層、遺跡多直接疊壓于生土層或崧澤文化層之上,后被更晚者疊壓或打破。流行腹部較突出的罐形鼎(圖三︰1、2),許多鼎足側面多微內凹,足尖、足跟外側常作按捺處理(圖三︰8—11);其他常見器物如子母口盒(圖三︰3)、敞口斜腹杯(圖三︰4)、大捉手器蓋(圖三︰5)、粗柄圈足盤(圖三︰6)、細高柄凸棱豆(圖三︰7)、半月形石刀(圖三︰12)等。這些遺物,年代屬龍山文化晚期。
3.太崗寺遺址
位于南京市西善橋村太崗寺南側的臺地上,距長江夾江南河約1.2千米。南京博物院1960年對其進行發掘,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遺存[21]。發掘者將文化層分為上、下兩層,上層厚0.8~2.5、下層厚2.5~5.4米。對資料進行分析后,筆者認為下層至少存在崧澤、龍山兩個時期遺物,而且后者可再劃分。典型陶器有深鼓腹側扁三角足鼎(圖四︰1)、高頸扁鼓腹壺(圖四︰2)、斂口扁腹缽(圖四︰3)、弧壁單耳杯(圖四︰4)和細長頸捏流鬶(圖四︰5)等,其中杯、鬶年代偏早,鼎、缽和壺年代偏晚。從鬶的形態來看,流的開口處外撇稍小、頸部稍內曲且把手位于頸和足交界處偏上;其應處于這類長頸鬶發展的早期階段[22]。與之類似者有安徽蚌埠禹會村JSK5︰1[23]、錢山漾T1001⑨B︰50[24],年代同屬龍山早中期。曲壁單耳杯在寧鎮、太湖地區十分少見,它似乎來源于淮河中游甚至偏北的魯豫皖交界處。從安徽蘆城孜[25]、山東尹家城[26]同類遺物的發展規律來看,它的年代應與這件長頸捏流鬶同時。以上所見鼎、缽、壺等,可在河南王油坊[27]、江蘇南蕩[28]、上海廣富林[29]找到原型,年代均為龍山晚期。綜上分析可知,太崗寺后良渚階段遺存可分兩期,第一期為龍山早中期,第二期為龍山晚期。
4.朝墩頭遺址
位于南京市高淳固城鎮檀村東南側,東臨沛溪河,南距胥河1.5千米。1989年,南京博物院、高淳縣文保所對其進行了發掘[30]。遺址地層堆積共5層,發掘者將其劃為三大文化層,分三期。其中第一期以④、⑤層為代表,年代為崧澤晚期至良渚早期;第二期以③層為代表,年代為龍山晚期;第三期以②層為代表,年代為周。由于該遺址材料未完全發表,筆者僅能分析已公布的龍山時期材料,根據出土遺物判斷,第二期遺存的年代仍有早晚之分。如袋足鬶(圖五︰5),頸部粗矮;它與太崗寺細長頸鬶年代相近,屬龍山早中期遺物。就目前資料顯示,這種鬶并未延續至龍山晚期。另外幾件器物,如扁鼓腹鼎、垂腹鼎、細高柄豆、弧腹盆(圖五︰1—4、6)等,年代為龍山晚期,形態與馬跡山者幾無差別。由此可知,朝墩頭后良渚階段遺存也可分兩期,第一期以鬶為代表,第二期以鼎、豆、盆為代表,年代分別為龍山早中期和龍山晚期。
(二)其他后良渚階段遺存
除以上典型遺址外,寧鎮地區發現有后良渚階段遺存的遺址還有17處。其中秦淮河流域有5處,分別為南京的北陰陽營[31]、前崗[32]、曹家邊[33]、老鼠墩[34]以及鎮江句容東崗頭[35]等;姑溪河流域有7處,均分布于安徽當涂縣,分別為錘墩山[36]、楊塘墳[37]、四維村[38]、船頭村[39]、朱崗渡[40]、張家甸[41]和窯墩[42]等;胥河附近有1處,為高淳薛城[43];東北臨江地帶有4處,分別為南京點將臺[44],鎮江丹徒團山[45]、斷山墩[46]和丹陽后彭[47]等。這些遺址,大多經過調查,部分經過發掘,遺物較混雜,以陶器最為多見。陶器以鼎為主,以鼎足居多(圖六︰1—4、7—21),其他器形有豆(圖六︰5)、鬶(圖六︰6)等。經分析后,發現許多遺址存有龍山早中期、龍山晚期兩個階段遺物,也有遺址僅居其一。這些遺物中,如腹徑極大的垂腹鼎、高頸鬶、條形堆紋足、刻槽足、足尖對捏的寬扁足等,年代均偏早;而扁鼓腹鼎、腹徑稍大于口徑的垂腹鼎、細高柄豆、各種形態的高瘦側扁足等,年代則偏晚。
二、分期與年代
以上所見的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遺存可分為兩期。
第一期:未見典型單位。多為調查采集遺物,發掘出土者大多見于晚期地層、遺跡[48]。陶器以鼎、鬶為主,其代表的文化因素復雜。流行腹徑極大的垂腹鼎(圖六︰3),多為寬沿。鼎足形態多樣,主要為側扁形足(圖六︰9、12、13、18、19),也有部分魚鰭形足(圖六︰16、20)、條形堆紋圓錐足(圖六︰7),少量舌形足(圖六︰10、11)、扁圓錐足(圖六︰14)。足多素面,足跟處多有按窩。有紋飾的足,常見刻劃紋,其中縱向刻槽偏多,也有呈“八”字形者;足的長寬比相對較小,足尖多進行按捺,對捏現象常見。所見鬶均為細長頸,敞口不是特別明顯,頸部或飾縱向刻劃槽(圖四︰5);頸部靠下部分多較細,鬶耳上部多位于頸部,下部多位于袋足上。本期所見魚鰭形足、索狀堆紋圓錐足、舌形足、細長頸鬶的時代特征明顯,屬龍山早中期。
第二期:有典型單位。以馬跡山ⅠT0201⑥、ⅡT0301⑥、ⅡT0302⑥、ⅡT0303⑥和ⅠT0101⑤為代表,不見典型遺跡。該期遺物較多,主要為陶器、石器,少量玉器。陶器以鼎、豆、盒、壺、杯等較為多見,石器以刀、錛、鏟和鏃等多見,玉器僅見鑿。鼎的形態多變,其中以深鼓腹(圖四︰1)、扁鼓腹(圖六︰1)為多,垂腹者(圖六︰2)相對較少。鼎的紋飾均為繩紋,多見于腹底或偏下腹處。流行形態較高、較窄的側扁足,足外緣根部或有按窩。其他典型器,有細高柄凸棱豆(圖五︰2)、直口盒(圖三︰3)、扁腹高頸壺(圖四︰2)、敞口斜直腹杯(圖三︰4)、單耳杯(圖四︰4)等。以上所見器物,年代均屬龍山晚期。
三、文化因素分析
由上可知,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遺存主要為陶器、石器,其文化因素劃分為如下幾類。
A類:以對捏足尖的素面寬扁足和橫剖面呈近三角形、表面有縱向劃槽的舌形足(圖七︰1、2)為代表。這兩種鼎足,寧鎮地區數量不多,更不見于以太湖東南為分布中心的錢山漾文化。地理位置接近的滁河流域有類似遺存,但目前文化面貌仍不算清晰[49]。在進行更多分析后,可知這種因素以淮河中游最為發達,有學者將該區域龍山時期遺存稱之為“禹會類型”[50]。筆者認為,該文化因素應是由禹會類型經滁河流域傳播而來。
B類:以腹部有凸棱的直口盒(圖七︰3)為代表。這種陶器,盛行于海岱龍山文化,也常見于造律臺文化[51]和南蕩類型[52]。一般認為,分布于里下河地區的南蕩類型,是造律臺文化南下的結果。而寧鎮地區所見的這種文化因素,并不見于以太湖流域為分布中心的廣富林文化,其直接來源應該是南蕩類型。
C類:以敞口斜腹杯、大捉手斜直腹器蓋(圖七︰4、5)為代表。這類陶器,以斜直腹為特征。類似的陶器以海岱龍山文化多見;造律臺文化、南蕩類型中雖然也不缺乏,但卻不盡一致。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應是造律臺文化特別是南蕩類型資料尚不完善所致。C類因素與B類因素存在一定相似性,如果將來資料健全,二者可以合并。
D類:以大垂腹鼎、細高頸袋足鬶、足面有斜向劃槽或條形堆紋的錐形足等(圖七︰6—9)為代表。包含這種因素的陶器,禹會類型和錢山漾文化中均有發現,但稍有區別。如錢山漾文化流行腹徑、口徑比偏大的垂腹鼎,禹會類型雖然也見垂腹鼎,但腹徑、口徑比明顯要小;而寧鎮地區所見鼎的形態,更接近錢山漾文化。細長頸袋足鬶的紋飾特征,也類似錢山漾文化的做法。錐形足在淮河中游和太湖流域均多見,但裝飾做法卻有區別[53]。條形堆紋或索形堆紋飾是淮河中游龍山時期常見紋飾,同時期的太湖流域少見;斜向刻槽或“八”字形刻槽裝飾則與之相反,以太湖流域多見,淮河中游少見。
E類:以魚鰭形足(圖七︰11)為代表。包含該文化因素的陶器,以太湖流域最流行,寧鎮地區數量變少,滁河流域更少,淮河中游基本不見。
F類:以足尖對捏、足面有縱向刻劃槽的側扁足(圖七︰12)為代表,屬寧鎮地區特有因素。它有別于太湖流域常見的魚鰭形足,是A類因素中對捏側扁足與E類魚鰭形足結合的產物。
G類:以半月形石刀(圖七︰13)為代表。這種石刀更扁,有別于進入夏商時期以后偏胖的形態,刃部也多內凹。這種因素并不見于南蕩類型或其他北方龍山文化,而是多見于廣富林文化。
H類:以深圓鼓腹鼎、扁鼓腹鼎、細高柄碗形豆、矮圈足盤、扁腹高頸壺和單耳杯等(圖七︰14—20)為代表。該因素陶器數量較大,與南蕩類型、廣富林文化所見者幾無差異。
四、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遺存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的關系
(一)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一期
筆者將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一期所見的主要陶器與錢山漾文化、禹會類型及滁河流域同期遺存進行了對比。發現四個區域陶器的主要器形均可互見,具有許多共同特征(圖八︰1—5、8—10、12—14、20、21)。幾種陶器中,以鬶的區別最小,幾乎不見形態差異;但鼎的變化較大,尤其是鼎足(圖八︰6、7、15—19、22—28)。
由相關研究可知,龍山文化禹會類型是在大汶口文化尉遲寺類型[54]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繼承了其部分文化因素,如刻槽舌形足、側扁足和鴨嘴形足等;新出現各種形態的索形堆紋足、按窩足。細長頸袋足鬶、斜向刻槽紋并非淮河中游土著因素,屬南方文化系統產物。而錢山漾文化除繼承良渚文化因素外,在形成過程中受到了更多外力沖擊,如鴨嘴形足、索狀堆紋足、對按窩足、舌形足等的出現。包含以上特征的鼎足,淮河中游及偏北地區均非常發達。良渚文化晚期,淮河下游地區文化版圖發生了較大變動,陶器的變化非常劇烈。如江蘇阜寧陸莊[55]、東園[56]等良渚文化分布區已經出現刻槽側扁足、刻槽舌形足和鴨嘴形足,“T”形鼎足外緣越變越窄演變為扁三角足,翅形足則過渡到魚鰭形足。魚鰭形足并非良渚文化孤立發展的產物,它的形態類似于禹會類型中外側緣弧凸的側扁足,它很可能便是在與北方文化系統碰撞過程中所產生的。滁河流域情況要模糊一些,但可以作大致的判斷。以南京牛頭崗為例,遺址除各種形態的鼎、袋足鬶等外,還存在數量較多的禹會類型陶器[57]。也可發現少量錢山漾文化典型器,如魚鰭形足鼎等。至寧鎮地區,魚鰭形鼎足、斜向刻槽紋因素增多,但仍遠比太湖流域少;對捏足尖的側扁足、縱向刻槽的舌形足因素仍得以保留,至太湖流域則無覓蹤跡。
(二)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二期
如果僅從目前公布材料看,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二期遺存與南蕩類型、廣富林文化的共性大于差異。陶器的主要器形,如鼓腹鼎(圖九︰1—3、8—10、15—17)、細高柄豆(圖九︰4、11、18)、高頸扁腹壺(圖九︰5、12、19)、單耳杯(圖九︰6、7、13、20)等均可互見,制作技術、裝飾特征也相近。盡管如此,仍然存在一定的地域差異,具體如下:(1)地理位置越偏南,南蕩類型等北方龍山文化因素越弱。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二期遺存中缺少了南蕩類型常見的袋足甗,至太湖流域器類則繼續減少,如直口盒、斜直腹杯、斜直腹器蓋等,但選擇性地保留了仍具有直腹特征的單耳杯。(2)南蕩類型、廣富林文化均有一定數量的小件骨器,寧鎮地區暫未發現。考慮到南蕩類型的主要來源是造律臺文化,而造律臺文化的骨器、蚌器較為發達,這種因素也是由北往南漸弱。(3)南蕩類型中存在少量的石器,至寧鎮地區石器器形、數量均增多,且出現了小件玉器;至廣富林文化玉石器則更發達,甚至出現了具有禮器性質的石琮、玉琮[58]。半月形石刀是寧鎮地區、太湖流域的共有因素,但太湖流域在數量上遠比寧鎮地區為多;而南蕩類型中未見。
五、結語
由上分析可知,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遺存可劃分為兩期。第一期遺存與禹會類型、錢山漾文化均存在一定的共性,也存在一定差異。如禹會類型文化因素越接近錢山漾文化分布中心區變得越少,反之錢山漾文化因素越接近禹會類型中心區則變得越少。寧鎮地區位于二者的過渡地帶,其文化特征摻雜了禹會類型、錢山漾文化的核心要素,但卻又與二者不完全相同。有學者將這種情況稱為考古學文化的“漩渦地帶”,是文化與文化之間碰撞、分化、滲透、融合的結果[59]。第二期遺存與南蕩類型、廣富林文化之間的共性更多,但在寧鎮地區本地顯示的特征并非是某種考古學文化的整體遷移,而是摻雜了很多土著文化因素。因此,并不能將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遺存歸屬到以上考古學文化中的任何一種。筆者建議將張敏先生所劃分的“城頭山—朝墩頭文化遺存期”里面的良渚文化遺存剝離出來,并以朝墩頭遺址年代屬龍山早中期、龍山晚期的遺存作為寧鎮地區后良渚階段的典型代表。建議沿用已有稱謂,稱其為“朝墩頭類型”。而此朝墩頭類型,便是后來點將臺文化[60]的先驅。
[1]a.曾昭燏等:《江寧湖熟史前遺址調查記》,南京博物院編著《南京附近考古報告》,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b.尹煥章、張正祥:《寧鎮山脈及秦淮河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普查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1期。
[2]魏正瑾:《寧鎮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點與分期》,《考古》1983年第9期。魏先生后來觀點發生了一些改變,他將寧鎮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同樣劃分為三期,認為第一期以北陰陽營第四層墓葬為代表;第二期以營盤山、城頭山遺存為代表;第三期以朝墩頭下層、昝廟良渚墓葬為代表。具體詳參魏正瑾:《長江下游寧鎮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及其東漸》,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411—412頁。
[3]張敏:《寧鎮地區青銅文化研究》,高崇文、安田喜憲主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248—250頁。
[4]張之恒:《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84—189頁。
[5]紀仲慶認為第一期以北陰陽營H68、H70遺存為代表;第二期以墓葬區遺存為代表;第三期以太崗寺下層和北陰陽營居住區墓葬遺存為代表;第四期以良渚時期遺存為代表。可參紀仲慶:《寧鎮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與相鄰地區諸文化的關系》,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4—43頁。
[6]谷建祥認為第一期以丁沙地早期、北陰陽營第一期和薛城下文化層遺存為代表;第二期以北陰陽營二期及薛城中期遺存為代表;第三期以北陰陽營三期、昝廟下層及太崗寺同類遺存為代表;第四期以城頭山下層、營盤山墓地、朝墩頭一期及薛城晚期遺存為代表;第五期以北陰陽營四期、朝墩頭二期、太崗寺和昝廟的同類遺存為代表。具體參鄒厚本主編《江蘇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第59—65頁。
[7]a.陳國慶、許鵬飛:《淺析寧鎮地區北陰陽營文化和薛城文化遺存》,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邊疆考古研究》第18輯,科學出版社2014年;b.許鵬飛:《寧鎮地區及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
[8]劉建國:《淺論寧鎮地區古代文化的幾個問題》,《考古》1986年第8期。
[9]a.同[3],第249頁;b.張敏:《20世紀江蘇考古工作的回顧與21世紀的展望》,《東南文化》2005年第3期。
[10]a.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區廣富林遺址1999~2000年發掘簡報》,《考古》2002年第10期;b.周麗娟:《廣富林遺址良渚文化墓葬與水井的發掘》,《東南文化》2003年第11期;c.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區廣富林遺址2001~2005年發掘簡報》,《考古》2008年第8期;d.王清剛:《2012年度上海廣富林遺址山東大學發掘區發掘報告》,山東大學2013年碩士論文;e.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區廣富林遺址2008年發掘簡報》,上海博物館編《廣富林考古發掘與學術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f.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市松江縣廣富林新石器時代遺址初探》,《考古》1962年第9期。
[11]a.丁品、鄭云飛等:《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第三次發掘》,《中國文物報》2005年8月5日第1版;b.丁品:《湖州市錢山漾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馬橋文化遺址》,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館:《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第三次發掘簡報》,《文物》2010年第7期;d.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館:《錢山漾——第三、四次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12]a.張忠培:《解惑與求真——在“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末期文化暨廣富林遺存學術研討會”的講話》,《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b.宋建:《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末期考古學研究的新進展》,《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c.翟楊:《廣富林遺址廣富林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d.陳杰:《廣富林文化初論》,《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e.欒豐實:《試論廣富林文化》,徐蘋芳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徐蘋芳先生紀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3]a.《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暨錢山漾遺址學術研討會在湖州召開——“錢山漾文化”正式命名》,《中國文物報》2014年11月18日第1版;b.宋建:《“錢山漾文化”的提出與思考》,《中國文物報》2015年2月13日第6版;c.曹峻:《錢山漾文化因素初析》,《東南文化》2015年第5期。
[14]谷建祥、申憲:《王油坊類型龍山文化去向初探——江蘇境內王油坊類型龍山文化遺存分析》,蔣贊初主編《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當涂縣文物管理所:《安徽當涂船里山遺址發掘報告》,《東南文化》2018年第3期。
[16]a.鎮江博物館:《鎮江馬跡山遺址第二次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5年第1期;b.鎮江博物館:《鎮江馬跡山遺址發掘報告》,鎮江博物館編著《鎮江臺形遺址》,江蘇大學出版社2015年。
[17]江蘇省文物工作隊太崗寺工作組:《南京西善橋太崗寺遺址的發掘》,《考古》1962年第3期。
[18]a.谷建祥:《高淳縣朝墩頭新石器時代至周代遺址》,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b.同[14]。
[19]同[15]。
[20]同[16]。
[21]同[17]。
[22]高廣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論》,《考古學報》1981年第4期。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館:《蚌埠禹會村》,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66—167頁。
[24]同[11]d,第70—71頁。
[2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州市文物管理局等:《宿州蘆城孜》,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38—140、171—175頁。
[26]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158—163頁。
[2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商邱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河南永城王油坊遺址發掘報告》,《考古》編輯部編《考古學集刊》(第5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28]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揚州博物館等:《江蘇興化戴家舍南蕩遺址》,《文物》1995年第4期。
[29]同[10]。
[30]同[18]。
[31]南京博物院:《北陰陽營——新石器時代及商周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32]曾昭燏等:《江寧湖熟史前遺址調查記》,南京博物院編著《南京附近考古報告》,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
[33]南京市博物館、江寧區博物館:《江寧湖熟曹家邊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南京博物院編著《穿越宜溧山地——寧杭高鐵江蘇段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3年。
[34]同[32]。
[35]南京博物院、鎮江博物館等:《句容東崗頭遺址——2005年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8—23頁。
[36]郭小敏:《姑溪河流域先秦遺址初探》,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37]同[36],第18、19頁。
[38]同[36],第19、20頁。
[39]同[36],第21、22頁。
[40]中國國家博物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當涂縣姑溪河流域系統調查簡報》,《東南文化》2014年第5期。
[41]同[40]。
[42]同[40]。
[43]a.南京市文物局、南京市博物館等:《江蘇高淳縣薛城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0年第5期;b.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市高淳區文化廣電局:《南京高淳薛城遺址2010年發掘簡報》,南京市博物總館、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編著《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第四輯),文物出版社2016年。
[44]筆者曾對該點將臺遺址進行調查,并于地表采集到側扁三角鼎足8件(均不完整),其中4件保留有足尖,足尖明顯外撇、靠外側處有按捺現象。這些鼎足,有較寬、細高兩種。足多素面,部分足面有稍內凹的處理,其中1件有縱向的多道凹槽。橫剖面形態也有兩種,一種為扁圓形,一種為外側緣突變薄。采集的這些鼎足,均屬后良渚階段,但有明確的早晚關系。早在1973年,南京博物院便對該遺址進行過發掘,當時也出土有后良渚階段遺物,但并不典型。具體參見南京博物院:《江寧湯山點將臺遺址》,《東南文化》1987年第3期。
[45]團山考古隊:《江蘇丹徒趙家窯團山遺址》,《東南文化》1989年第1期。
[46]鄒厚本、宋建等:《丹徒斷山墩遺址發掘紀要》,《東南文化》1990年第5期。
[47]江蘇省文物局:《江蘇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新發現》,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48]經正式發掘出土的后良渚階段遺物的遺址有老鼠墩、太崗寺、曹家邊、船里山、窯墩和東崗頭等,其中前兩處遺址所見遺物僅有大致單位,后幾處遺物則是出于偏晚地層。
[49]滁河流域存在類似遺存的遺址有肥東大城頭和南京牛頭崗。a.安徽省博物館:《安徽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b.王光明:《牛頭崗遺址早期陶器與禹會村出土陶器之初步比較》,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廳等編著《禹會村遺址研究——禹會村遺址與淮河流域文明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4年;c.華國榮:《南京牛頭崗遺址的發掘》,國家文物局主編《2003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4年。
[50]韓建業認為這種以垂腹鼎、高領罐、假圈足扭器、假腹高圈足簋、長頸壺、淺盤等為特征器的禹會龍山遺存,或可稱“禹會類型”,并認為其年代為龍山前后期過渡階段或稍偏晚,具體可見韓建業:《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9頁。筆者認同將禹會龍山時期遺存單劃為一個類型的觀點,并認為可將袋足甗、實足鬶、袋足鬶、深鼓腹罐補充入內。鼎的形態多見側扁足,足跟、足尖多經按捺處理。除此之外,足面縱向刻槽的舌形足(或正裝足)、多樣的縱向索狀堆紋足均較發達,也可見到少量鳥首形足、斜向刻劃紋飾的舌形足或鴨嘴形足。禹會類型分布范圍北部至少已到北淝河,南部至少到瓦埠湖水系,東部可能到泗縣一帶,西部暫不清晰。
[51]造律臺文化是指以永城王油坊、永城造律臺、宿州蘆城孜等地龍山時期遺存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之前也有王油坊類型或造律臺類型的認識。稱王油坊類型的,如a.吳汝祚:《關于夏文化及其來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b.欒豐實:《龍山文化王油坊類型初論》,《考古》1992年第10期。稱造律臺類型的,如a.嚴文明:《龍山文化和龍山時代》,《文物》1981年第6期;b.李伯謙:《論造律臺類型》,《文物》1983年第4期。
[52]關于南蕩類型的認識,可參考a.張弛:《中國史前農業、經濟的發展與文明的起源》,《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b.張敏:《南蕩遺存的發現及其意義》,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大象出版社2003年;c.宋建:《從廣富林遺存看環太湖地區早期文明的衰變》,上海博物館編《長江下游地區文明化進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年。
[53]刻劃槽的作風盛行于良渚文化并被錢山漾文化所繼承,后者更為多樣,出現了斜向或“八”字形刻槽。北方龍山文化中流行在舌形足面飾縱向刻槽的做法,可能也是受良渚文化影響所致。斜向或“八”字形刻槽飾在禹會類型中僅見2例,分別見于長豐古城和泗縣大郭。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豐縣文物管理所:《安徽長豐縣古城遺址發掘報告》,《文物研究》(第19輯),科學出版社2012年;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泗縣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遺址調查報告》,《東方考古》(第10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
[54]a.苗霞:《大汶口文化尉遲寺類型及其年代與分期》,《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6期;b.梁中合:《尉遲寺類型初論》,吉林大學考古學系編《青果集:吉林大學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紀念文集》,知識出版社1998年。
[55]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鹽城市文管會等:《江蘇阜寧陸莊遺址》,徐湖平主編《東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發現60周年紀念文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
[56]南京博物院、鹽城市博物館等:《江蘇阜寧縣東園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2004年第6期。
[57]同[49]b。
[58]廣富林考古隊:《2012年上海廣富林遺址考古或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2013年6月21日第8版。
[59]高蒙河:《試論“漩渦地帶”的考古學文化研究》,《東南文化》1989年第1期。
[60]a.張敏:《試論點將臺文化》,《東南文化》1989年第3期;b.毛穎、張敏:《長江下游的徐舒與吳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9—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