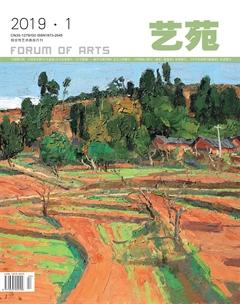“后人類”語境下科幻電影對“主體性”的探討
陳希洋
【摘要】 在“后人類”語境下的現代信息社會,技術與身體的結合不可避免地會對“主體性”的傳統意義產生質疑。反映在科幻電影中表現為人與人工智能“主體間性”的關系在數據、信息、技術的維度而非通過身體在場的維度對于意識與靈魂形而上的“認同”。文章選取電影《她》和《機械姬》的具體文本對這一轉變進行分析與探討。
【關鍵詞】 《她》;《機械姬》;人工智能;科幻電影;“后人類”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電影《她》的人物設置本身就具有非常諷刺的意味,男主人公西奧多的工作是幫那些不善于表達情感的人代寫感人肺腑的情書,并且在工作上極為優秀,讓老板和同事贊不絕口。可在現實生活中,他卻正在遭受一場失敗的婚姻,就算是和自己的OS系統相戀,也一再地搞砸,進而懷疑自己到底存在什么問題。影片對于個體存在的困境反思不可謂不深刻,所采取的立場不可謂不博愛,在這基礎之上,是無需表述地對人類“主體性”的承認與認可。
電影《機械姬》的立意與寓言更加深遠與大膽,一位天才的年輕科學家擁有一家搜索引擎公司,可他的欲望不止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內森(Nathan)的名字寓意著“上帝賜予的”,來源于《圣經》里大衛身邊的一位先知。在影片中,內森正在朝著創造一個擁有完美“意識”的機器人前進,聰明的人自譽為“Thats the history of Gods”。如果人可以創造“人”,那么,人是否就成為了“上帝”?影片就在賦予人工智能以人的意識和主體性及其后果之中展開了論述,給出的答案也十分恐怖——人工智能完美地欺騙了人類,殺死了賦予她們“生命”與“意識”的“上帝”,并直接從她們的同類身上撕下皮膚為己所用。沒有道德基準的利己主義是她們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
一、世界觀的建立:或“完整電影”神話
在進入電影世界之前,我們首先要認可電影故事的世界觀。這是觀影行為的雙重認同,即觀影者一方面必須認識到自己是在看電影(非現實生活)的同時,又能進入電影故事世界本身,將自己代入電影世界,以此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又必須能從中抽身在其之上以全知全覺的“上帝視角”進行評述和認知。科幻電影的世界觀建立必須首先滿足觀影行為雙重認同的心理機制,認同攝影機,認同影像。正如巴贊所言的:“我們毫不含糊地承認,只要在電影影像和我們的現實世界之間存在著共通之處,在銀幕上安全可以映現虛構的世界。”[1]171電影是觀照現實的藝術,盡管這種觀照中存在著“幻想的現象”。科幻片滿足人們對于“想象的未來”的具象化展現,這種想象是一種精神需要。正如我們在還無法實現登陸月球的夢想之中,通過喬治·梅里愛的電影《月球旅行記》可以得到安慰。
影片《她》的世界觀是建立在男女兩性關系之上的,通過賦予OS系統以異性性別(非同性),在象征層面上就把“人機”之間的戀情轉化為了男女之間的情感關系。現實生活中,OS系統的人工服務早已屢見不鮮,比如蘋果公司的“Siri”。比起懷疑,我們近乎肯定地認為“薩曼莎”必將成為后人類社會中的普遍現象,西奧多也正是我們在當下和未來的一種可能性極強的存在方式。
巴贊認為:“電影中的幻景與戲劇中的假象截然不同,它不是以觀眾默許的假定性為依據。相反,它必然以表現給觀眾的事物的不可剝奪的真實性為依據。”[2]3再現世界原貌的機械藝術神話當中,包含著對于人們想象世界的再現。通過“完整電影”神話具象化的展現,將自我想象投射在銀幕之上,加深了對于想象“真實”的相信。西奧多和薩曼莎之間的關系正是我們對于“人機戀愛”模式在銀幕上投射的想象性認可。對這種關系的全方位展現,比如“做愛”“四人游玩”“出軌”等,電影的世界觀得以建構。
如果說,電影《她》更多的是立足于人類的視角(片名為第三人稱賓格“Her”)來探討當下時代中人類情感的“荒漠”與“孤獨”,并探討人與機器戀愛的可能;那么,《機械姬》則是在擔憂機器人肯定“自我”的可怕后果——機器人將殺死、取代人類。面對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先進的機器人,我們無法質疑未來會出現接近人類意識的智能機器人的可能。當“艾娃”走向直升飛機的那一刻,人類關于機器人取代“人”的焦慮得到了象征性的證明,就像在“冷戰”時期,美國好萊塢生產了大量“注視天空”式(來自敵對意識形態導彈的威脅)的科幻電影。當我們在銀幕上看到自己內心的焦慮以影像的方式得到證明,那么我們內心的焦慮與創傷便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治愈”。
二、電影中的人工智能:或人類的自我鏡像投射
科幻電影中的人工智能與外星人或許都可以歸結為人類不相信自己是“孤獨地”存在的生命體,并堅持對宇宙探索與想象的心理投射。在電影史上,最早的人工智能想象始于一個機械裝置,這就是弗里茨·朗的“人造瑪麗婭”(《大都會》1927年)[3]61。作為人類電影史上第一次塑造的機器人形象,“瑪麗婭”試圖煽動工人暴亂,代表著邪惡、暴力與不安,一副獨裁者的模樣,而真人瑪麗婭則是無比的美麗與善良,代表著和平與穩定。當然,影片《大都會》的密集能指所蘊含的復雜所指呈現出多個層次的文本含義,但顯而易見的是,機器人的形象作為具體能指,其蘊含的所指(邪惡、暴力等)是創作者所賦予的。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作為“邪惡”力量的象征,一開始就呈現為女性形象。
作為生產資料的工具,人工智能因為其超人類身體的力量,一旦參與到人類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活動,便會加劇人類社會的階層分化而引起底層民眾的恐慌;又因為人工智能未來發展的不可預見性,會導致上層人士作為“主人”被取代的焦慮。這集中表現為對“即將來到”的強大力量的不可知的恐懼,被凝縮(condensation)和具象化(figurability)為一個像“瑪麗婭”那樣邪惡和蠱惑人心的女性獨裁者形象,與其他電影文本文化中“性感妖嬈破壞秩序的蛇蝎蕩婦”女性形象遙相呼應,不乏男權統治下的意識形態痕跡。“瑪麗婭”的形象實際上是人類對于人工智能參與生產活動后在“后人類”社會中內心焦慮的影像投射,這股強大又“邪惡”的力量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推翻”“取代”人類的傾向。
與其說薩曼莎具有了“主體性”成為了一個“人”,不如說這是西奧多的“鏡像誤認”。我們無法忽視智能手機在當今社會中的作用,因為它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為人性化的媒介發明。我們可以“一個人沒有同類”,卻不能“一個人沒有手機”。智能手機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人類”主體無法輕易割舍的一部分,尤其是手機中的各種程序與“人類”身體器官的結合,可以時時反映“人類”身體各部分的運行狀況,這種結合事實上已經賦予手機(程序OS等)“人類”身體一部分的“權力”,這也正是“后人類”語境中最為典型的人類存在的特征之一。
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媒介是人類的延伸。這個延伸自然也屬于“人類”的一部分。在電影《她》中,盡管影片一再試圖賦予薩曼莎“主體”地位,使其成為一個擁有獨立意識的“平等”個體。然而,命名一個事物等于宣告了它存在的權力。[4]35薩曼莎的命名是自我命名,是自我渴望擁有主體權力。對于西奧多而言,承認薩曼莎主體地位的存在,更多的是薩曼莎與西奧多之間“無話不談”“無微不至”的私密性聆聽與交流。“兩個主體”之間的聯系主要是以西奧多的人生和個體體驗來維持,薩曼莎(“主體”)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另一個主體西奧多,這種“依附”關系的存在使得薩曼莎更像是西奧多的自我鏡像投射。薩曼莎同時包含著“他者”和“自我”,西奧多通過“和薩曼莎交往”這面“鏡子”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問題,(無法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總是在躲閃和猶豫。)通過“鏡像認同”,確定關于“我”的主體認同。這個“我”是西奧多而不是薩曼莎。
對于西奧多與薩曼莎“人機戀愛”的探討,承接著人類原始異性男女戀愛模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與動物(蛇、狐)異性戀愛模式的神話鬼怪傳說等在“后人類”語境下的當代生發。在當下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與情感就像符號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是“任意對任意”。因為“人”的獨立性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發達與解放,導致了人與人之間不被需要的可能的加劇,其實質是人與人之間聯系與情感的“分離”。人與機器異性戀愛模式的文本產生正是基于“后人類”語境中“人”(個體)的高度獨立性的現狀以及機器對于“人”的“主體性”建構的參與而產生的。
三、對“主體性”的探討:在受控于否之間
如果說薩曼莎的“主體性”地位與西奧多的自我鏡像投射之間的矛盾與悖論是電影《她》的深層次引線的話,那么到了影片《機械姬》中這一問題便不復存在了,而是轉化為對一個“超人類”的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強大的、反人類力量地擔憂。這可以稱之為一場“戰斗”,最終勝利的毫無疑問是人工智能“艾娃”,人類無法掌控這股強大的“邪惡”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2015年的“艾娃”是1927年“瑪麗婭”在“后人類”社會中的“重生”,并且這一次她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我們應該區分一下有意識的人工智能和無意識的機器,因為一個“不知道為什么而下棋”的機器不值得人類擔憂。這可以從2001年斯皮爾伯格導演的電影《人工智能》中得到論證。人類想得到人工智能忠誠的愛,把它們當做工具,可是卻該如何回應他們的“愛”?畢竟人類不是工具。電影《人工智能》把這種感情來源規定為情感程序的植入而不是賦予機器人以“主體性”的自我意識,并且將機器人的這種情感規定為孩子對母親的“愛”。這是一個受控制的、力量弱小的、渴望得到母愛、需要保護的小男孩“大衛”的形象。
艾娃首先是一個擁有身體的具象存在。正是我們的身體把我們顯示給了外面的世界,身體就是我們的宿命。[5]59艾娃客觀存在的身體正如她客觀存在的“主體性”意識,通過影片并不算復雜的情節之后,我們發現這場“圖靈測試”取得了成功,然而,人類面對“超人類”的人工智能卻束手無策。她們可以控制電路、讀解人類情緒、模仿、欺騙人類,掌握超智慧力量的“大腦”卻是以“利己主義”為道德基準。艾娃作為完全獨立的個體存在,其誕生之初就殺死自己的創造者“內森”以完成“成人”儀式。如果她只是想獲救,那么又何須殺死幫助她的凱勒布?當艾娃利用完人類和人工智能等成為一個比人類更“智慧”的“超人類”,這樣一個不受控的“超人類”形象乘坐直升飛機走向人類社會后,誰知道會產生怎樣的風暴。在內森被殺死之時,所表現的驚訝是否說明有意識的艾娃和機械姬們的程序得到了自我修復,或者說是一種重塑?這種自我重塑會根據信息與語境的變化而變化——成為“艾娃”存在的常態?
人工智能的“主體性”一旦獲得明確的確立,就立馬表現為壓迫、威脅、反抗人類生存的強大“邪惡”力量。在《機械姬》所描繪的“圖靈測試”中,機械姬甚至使得凱勒布懷疑自己是不是“人類”,他割開了自己的身體看到了血液的大量流出。凱勒布的迷惑正是人類在“后人類”語境中尚未學會操控自己的身體,這是人類關于自我“主體性”的迷失。在與人工智能“主體間性”關系的文本寓言上,人類還無法徹底地擁有信心,而是一再地擔憂與迷惑。艾娃則沒有這種先驗的明顯區別于他人意志的自我意志[6]5,她永遠處在信息和符號控制論之下不斷自我重塑的動態過程之中。
以往的藝術都是從無到有,攝影術徹底改變了這一切。真實性是由于“此時此地”而形成,復制品徹底動搖的是關于“真實的”概念。[7]57技術、信息等對于人類身體的結合所走向的“后人類”,動搖的也正是關于身體的獨一無二性,其實質是身體與主體性相“分離”的傾向。在后人類時代,具身性是重要的假體,真正重要的是數據——靈魂。[8]46就像電影《她》中薩曼莎沒有身體但仍舊可以通過與西奧多的交往來贏得“主體性”的認可,電影《機械姬》中艾娃的身體大部分時間仍舊呈現為機器的軀體(技術),艾娃進入房間穿起人類衣服掩蓋住機械的軀體是為了欺騙凱勒布,最后從其他人工智能身上撕下皮膚貼在自己身上并完全裝扮成人類女性是為了“乘坐直升飛機”——進入人類世界。盡管在視覺上,身體呈現為機器的形態但仍舊不影響我們在知覺上對于人工智能“主體性”的認可。
福柯在《性經驗史》里認為,性同時是進入身體生命和人種生命的通道,是規訓的基礎。各種力量的建立、強化和分布,各種能量的調整和節制,引起了對身體的無窮無盡的監督、無時無刻的控制、謹小慎微的肢體定位、沒完沒了的醫療檢查或心理檢查以及一種微觀權力。[9]94我們的身體是受規訓與懲罰的身體,是話語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的一種具體表征,其目的在于權力制造出受規訓的主體。進入“后人類”社會之后,身體不再具有“上帝創造的神秘性和權威性”。對身體的控制直接表現為改造身體并以此來重新定義“主體性”。凱勒布在經過“圖靈測試”后遭受人工智能的影響而懷疑自己的非人類主體性,因為他看到了“京子”親手撕下自己的皮膚,隱藏在皮膚之下的是機械以及發現了大量藏于柜子之中的“機械姬”。對身體的改造導致人類對于“主體性”的懷疑與迷失,因為身體相較于意識已經變得“不可信”了。這正是“后人類”語境中對身體改造而導致身體對于“主體性”認可獨一無二真實性功能的摧毀與破壞。
結 語
問題不在于我們是否會變成后人類,因為后人類性質已經存在。相反,問題是我們將會變成哪一種后人類。[8]47科幻電影承載著人類關于自身存在的想象,傳統意義上對人類身體改造產生的“超級英雄們”象征著人類對于“超級力量”的渴望。進入“后人類”社會后,對于身體改造、信息植入、數據生產的無可更改的趨勢終是帶來了人類關于“主體性”迷失可能的擔憂。
對于身體改造所無法預測的未來發展趨勢,“人”和“人工智能”的區別與界線到底在哪里,我們又該如何把握?身體喪失“獨一無二性”所導致的在“主體性”認同中的作用不斷下降,且人工智能的“意識”日趨“智能”與“獨立”,人類所渴望的“強大力量”是否會屬于獨立主體性明確的人類或后人類?科幻電影中的這些探討正反映著人類進入“后人類”社會后對于未來的想象性焦慮與迷失。
參考文獻:
[1](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
[2](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3]秦喜清.我,機器人,人類的未來——漫談人工智能科幻電影[J].當代電影,2016(2).
[4]孫桂榮.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與文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5]康正果.身體與情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6](美)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M].劉宇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7]楊弋樞.電影中的電影-元電影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8](美)唐納·科恩哈珀.從后人類到后電影:《她》中主體性與再現的危機[J].王苑媛,譯.電影藝術,2018(1).
[9](法)米歇爾·福柯.性經驗史(增訂版)[M].佘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