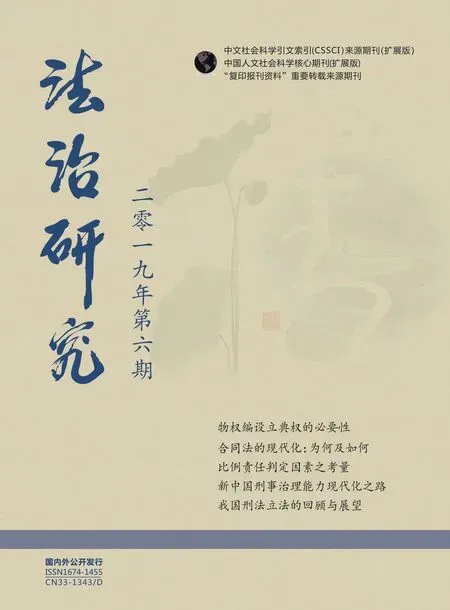從《殘疾人權利公約》看我國新成年監護制度*
李 霞 陳 迪
一、引言
2017年3月頒布的《民法總則》設專節17個條文對監護制度作專門規定,還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法律行為、代理等10個與成年監護制度直接相關的條文。成年監護制度主要是對精神的、心智的、肢體的殘疾人,以及部分高齡者民事權利的保護。民事權利作為人權重要組成部分,《殘疾人權利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已經為該類殘疾人的權利保護提供了基本標準,其中第12條就是針對成年人行為能力和監護的規定。我國早在2008年就作為締約國第一批簽署了《公約》,因此,作為保護殘疾人的人權重要內容的成年監護制度,從立法、法律解釋和法學研究等,都應以《公約》尤其是第12條為標準,這也是中國自愿履行國際義務的承諾。
二、《公約》對成年監護法的倡導標準
(一)肯定殘疾人的民事行為能力,廢除無行為能力制度
《公約》第12條提出,締約國應當確認殘疾人在生活的各方面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legal capacity)。從體系解釋即結合《公約》第3項各國應為殘疾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協助的表述可知,法律能力包含了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但這里主要是指行為能力。①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之成年監護制度》,載《月旦法學雜志》2014年第10期。《公約》肯定殘疾人具有與正常人一樣的法律能力,因此,要限制殘疾人的行為能力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經過司法審查;第二,根據司法審查結果劃定殘疾人行為能力的限制范圍,而不能一刀切地剝奪其從事所有法律行為的能力。
因此,各締約國不得再保留傳統民法中的無行為能力制度。因為無行為能力制度的法律后果,在于被宣告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后,成年被監護人的行為能力一刀切地受到限制,在任何場合一律沒有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②龍衛球:《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頁。這顯然是與《公約》要求相反的。
(二)尊重余存能力,支援自我決定
《公約》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出,確認個人的自主和自立,包括自由作出自己的選擇,對殘疾人至關重要。因此,尊重自我決定是《公約》的基本精神。社會經驗表明,殘疾人并非一概全無行為能力,例如心智障礙癥狀較輕者,完全可以從事日常生活相關的法律行為,只是重大事件可能判斷力不足而需要支援。③郭明政:《禁治產與成年人監護制度之探討》,載《固有法制與當代民事法學:戴東雄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三民書局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頁。更重要的是,“殘疾”如果成為社會對殘疾人的標簽并據此剝奪其行為能力,則將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令許多本具有余存能力的殘疾人因長期禁止參與社會生活,缺乏鍛煉意思表示的機會而逐漸喪失余存的能力,近似于習得性無助。④see :B.Winick,The Side Effects of Incompetence Labelling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Psychiatry,Public Policy & Law,Vol.1,1995,p.437.也就是說,殘疾人不僅有條件實現自我決定,而且自我決定的能力在得到社會認可和肯定后還能夠不斷增強,反之則不斷喪失。
尊重自我決定在成年監護制度中包含兩個方面的權利:一方面是本人拒絕干預自我決定的權利,即監護只在必要時設立,并且監護人的權限必須限制在必要范圍之內,達成對本人最少限制,確需干預本人自我決定的,必須符合妥當、必要、均衡的要求,⑤李霞:《民法典成年保護制度》,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118頁。這也被稱為“最少限制原則”。另一方面是本人要求支援決定的權利。《公約》第12條要求各締約國通過政策和法律來采取適當措施,便利殘疾人行使法律能力,并且這些措施應當符合本人具體情況,適用時間盡可能短。在監護制度上,就是要求提供多元化的措施來支持、保障本人實現自我決定,包括意定監護以及輔助、保佐等法定監護措施。⑥李霞:《成年監護制度的現代轉向》,載《中國法學》2015年第2期。
(三)保障程序參與的訴訟權利
《公約》第13條規定,締約國應確保殘疾人與其他人平等有效獲得司法保護,為殘疾人提供程序便利,使他們在訴訟中能夠直接或間接參與訴訟。《公約》對殘疾人程序權利的強調有著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兩個方面的依據。就前者而言,公約執行委員會在2012年發表的評估報告指出,一些國家正是由于法律程序設計不完善,本人難以反駁鑒定機構關于本人欠缺行為能力的意見,因此本人實際上是從鑒定意見作出時而非法院裁判時就已經被剝奪了法律能力尤其是行為能力。⑦MDAC,Reports on Guardianship in Russia and Hungary.就后者而言,公正的司法程序應當尊重程序參與人的人格尊嚴。根據程序公正的“尊嚴價值理論”,⑧陳瑞華:《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評馬修的“尊嚴價值理論”》,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對參與人來說,否定的訴訟結果并不意味著尊嚴受損,但如果參與人在程序中沒有對否定性結果進行申辯、抵制的權利,則必然意味著尊嚴受到侵犯。因此,在監護程序中必須賦予本人以足夠的程序性權利,包括為其指定訴訟代理人,通過聽證、庭審等程序聽取他的意見等。否則,監護宣告一旦作出,本人在程序中完全沒有表達意愿的機會。
至此可見,《公約》要求締約國的成年監護制度承認本人實施法律行為的能力,尊重其自我決定的權利,保障本人直接或間接參與監護訴訟,從而引申出成年監護制度的四個基本原則:能力推定、支援自主決定、最少限制和最佳利益。⑨李霞:《成年監護制度研究:以人權的視角》,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版,第80~86頁。這種監護模式有別于過往被稱為醫療監護模式的一刀切剝奪本人行為能力的做法,是《公約》締約國在制定成年監護制度時必須遵循的要求。
三、《民法總則》成年監護制度與《公約》的距離
《民法總則》監護制度專節和法律行為、代理等10個與成年監護制度直接相關的條文,與《公約》有較大差距。
(一)保留了陳舊的無行為能力(禁治產)制度
無行為能力制度,目前已不符合《公約》廢除無行為能力制度的要求。令人遺憾的是,《民法總則》仍然采用了無行為能力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的劃分,規定無行為能力人的法律行為一律無效,限制行為能力的人的法律行為效力等待法定代理人來決定。⑩《民法總則》第23、24、144、145條。這直接承繼了上世紀的《民法通則》,無視本人的自我意思決定及殘余的意思能力,與《公約》相悖離。這表面上是為了保護本人,實際上依然是為了保護交易安全與家產維護,?劉德寬:《德國成年監護制度之改革》,載《法學叢刊》1998年第1期。其結果是不合理地剝奪個人的自由和地位,全面犧牲了本人的行為能力和自治機會。
關于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法律行為效力,《民法通則》規定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須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同意。這表明,對于一般法律行為,本人有權獨立實施,例外時,對于某些特殊法律行為,本人須由監護人代為意思表示。而《民法總則》卻規定限制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實施法律行為須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同意、追認,但是可以獨立實施純獲利益的法律行為或者與其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法律行為,采取的是一般法定代理、例外獨立實施的表述,幾乎與限制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一致。?《民法通則》第13條,《民法總則》第19、22條。對限制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因其年齡決定了智力發育程度未足,采取一般法定代理、例外獨立實施的立場是妥當的;但對限制行為能力成年人,因其年齡已達成年,應采取一般允許獨立實施、例外須法定代理的立場。因此,《民法總則》在這方面可謂不進反退。
無行為能力制度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對成年監護人財產處分權利的不加限制。《民法總則》僅在第35條規定監護人除為維護本人利益外不得處分本人財產,而未有更具體的規定。但是,如何理解為本人利益,是采主觀標準還是客觀標準?如果采主觀標準,那么只需監護人認為是為本人利益即可;如果采客觀標準,那么監護財產處分情形紛繁復雜,以立法的形式列舉規定幾無可能。實際上,對本人財產的保護,重在財產報告與監督制度,這是《民法總則》所欠缺的。
(二)基本原則之間的沖突
成年監護和未成年監護,兩者遵循不同的規則規律。?李霞:《監護制度比較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7頁。后者遵循最佳利益,前者強調尊重本人意愿,即使是“愚蠢行為”也應尊重。?Mental Health Act 2005,1(4).例如抽煙有害健康,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的吸煙根據最佳利益原則予以制止;而對成年本人則須尊重其意愿。《民法總則》將尊重意愿與最佳利益原則等同適用于成年監護和未成年監護,由此將引發兩者沖突。
這種沖突首先表現在監護人確定糾紛中。《民法總則》第31條第2款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民政部門或者人民法院應當尊重本人的真實意愿,按照最有利于本人的原則在依法具有監護資格的人中指定監護人。問題在于,如果本人的意愿與法定的最有利的選擇發生沖突時,該如何選擇呢?兩種原則的沖突還表現在監護職責上。《民法總則》一方面規定最有利原則是履職的一般性原則;另一方面在第35條規定未成年人監護人須尊重本人真實意愿,成年人監護人須最大程度尊重本人真實意愿。最佳利益與尊重意愿不可能并列,既然最佳利益原則為一般原則,則尊重意愿只能是次要原則,而不應在條文中將兩者羅列不分主次;其次,法律規范應注意操作性與可實現性,成年監護在尊重監護人真實意愿時,如何才能稱為最大程度,是否能夠優先于一般性的最佳利益原則?而且,從未成年監護與成年監護表述對比容易產生這樣的印象,即未成年監護不是最大程度地尊重意愿,這顯然不合理。
此外,在監護撤銷與恢復上,同樣存在原則沖突的問題。《民法總則》在監護撤銷上規定的是最佳利益原則,在監護恢復上規定的是尊重意愿原則,兩者都有偏頗。實際上,《民法總則》的監護撤銷與恢復均脫胎于《侵害未成年人意見》,在一審稿說明中全國人大表示這兩個條文的立法目的在于“針對實踐中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等本人合法權益時有發生的情況”。?《民法總則》第36、38條,《侵害未成年人意見》第35、38、39、40條,《民法總則(草案)》(一審稿)第34、35條。張維煒、王博勛:《讓民法典成為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的立法表達——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李適時》,載《中國人大》2016年第13期。因此,這兩個條文出現在民法總則部分并且不區分成年與未成年監護,是早已注定的局面。更可惜的是,多次審議修改都沒有彌補不足,甚至還越改越亂。在一審稿中,監護恢復并沒有“尊重被監護人真實意愿”的表述,但是《民法總則》后來卻增加了這個內容,導致監護的撤銷與恢復遵循的是兩種可能矛盾的邏輯,制度割裂更加嚴重。
(三)措施單一,難以滿足自我決定
根據本人殘留意思能力的多少和對保護需求的不同程度,劃定本人意思自治的類型范圍,通過輔助、保佐等方式為本人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決定措施,這是《公約》所倡導的標準。
《民法總則》在這方面有一定的努力,初步建立了意定監護,即在第33條規定完全行為能力人可與近親屬、其他個人或者組織事先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在本人喪失或者部分喪失行為能力時履行監護職責。但是,一方面《民法總則》僅規定了意定監護,卻沒有規定應如何處理意定監護與法定監護的關系;另一方面,多元化監護措施不僅要求在法定監護之外創設意定監護,還要求在法定監護之內建立多元化的措施,例如輔助和保佐等。《民法總則》在法定監護方面基本沿襲了《民法通則》的一元化措施立場,違背了多元監護措施的要求。雖然其在第22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成年人可以獨立實施與智力、精神狀況相適用的法律行為,但如上文所述,采取的是一般法定代理、例外獨立實施的表述,而且僅憑該條無法抽象出類型化、制度化的因應本人殘留意思能力的多元化措施。第三,由于個體差異甚大,即使設置了輔助、保佐等類型化決定支援措施,仍可能無法精準滿足本人需要,因此需要賦予法官相應的自由裁量權,為不同個案中的本人自治范圍和監護人代理范圍劃定界限。由此可見,《民法總則》仍缺乏對本人自我決定的保障,違背了《公約》的要求。
(四)無從保障的程序權利
《公約》要求各締約國保障殘疾人本人有效參與監護開始、撤銷、恢復、終止等訴訟程序。但是,《民法總則》沒有關注本人的程序權利。
第一,監護的發生與終止并不以訴訟程序為要件。從語義看,《民法總則》第22至24條規定的利害關系人或有關組織“可以”向法院申請認定成年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沒有必然性的措辭;從體系上看,無行為能力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的定義在申請認定行為能力之前,監護關系終止條件是本人取得或恢復行為能力。由于法律概念的行為能力在我國被偷換為醫學概念,醫學機構的醫院僭越法院成為判斷行為能力的主體,因此監護實際上取決于行為能力評估報告而非法院審查,?李霞:《精神衛生法律制度研究》,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頁。即監護這一雙刃劍完全可以脫離法律程序自行發生與終止,從而導致現實中普通人只要“被精神病”后,就有人擔任自己的監護人從而所有民事權利都無法親自實施,只能由監護替代做決定。可見,申請認定程序只是針對行為能力,而不是監護的發生與終止的必經程序,并且認定程序的宣告制度是行為能力受剝奪或限制的公示要件而非監護的生效要件,導致監護的發生與終止脫離了訴訟審判可以徑行發生,本人參與、申辯的程序權利更是無從談起。
第二,在監護發生、終止以及監護人選任的司法程序中,本人被剝奪了作為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一方面,《民法總則》規定,本人的利害關系人或有關組織可以申請認定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但既沒有規定本人的訴訟權利,也沒有規定法院在訴訟中應依職權支援本人行使訴訟權利。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89條規定,在認定行為能力程序中由近親屬擔任本人的代理人,但申請人除外;本人健康情況許可的應當詢問本人意見。也就是說,我國民事訴訟法對未經裁判認定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的人在監護啟動程序中實施強制代理制度。然而,這并不能保障本人的訴訟權利。首先,民事訴訟是否委托代理人,應由訴訟當事人自行決定。在法院裁判之前,應當推定本人擁有訴訟能力和行為能力,而不應對未經裁判的人實行強制代理。其次,盡管禁止認定行為能力的申請人擔任本人的代理人(即禁止雙方代理),但仍存在明顯的道德風險。由于申請人與代理人大部分都在近親屬中產生,不問本人行為能力多少而強制代理,易引發惡意串通損害本人利益的行為;即使代理人能夠依法履行職責,在申請人與本人共同居住甚至控制本人飲食起居的情況下,代理人無法有效搜集證明本人行為能力的證據,法院也可能因為申請人不配合或欺詐、脅迫本人而難以查明本人真實意愿或行為能力真實情況,代理人幾乎沒有實施有效抗辯的可能。究其根本,在于本人的意愿在訴訟中僅在健康許可下定位為“詢問”,而非決定性作用。再次,《民法總則》雖然設立了臨時監護,但其范圍過窄,并不包括訴訟中的臨時監護人。
另一方面,本人完全沒有辦法影響監護人的選任。《民法總則》規定,無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人,由有監護資格的人按照順序選定監護人,不論殘留意思能力多少,本人都無法決定監護人的選任。
四、我國與其他《公約》締約國成年監護法的距離
在比較法中,《公約》的要求已經在眾多先進國家的成年監護中轉化為現實。
(一)廢除無行為能力制度
與我國不同,各國紛紛廢棄無行為能力制度,僅劃分完全行為能力與限制行為能力,與此相適應,限制行為能力所從事的法律行為也僅分為有效與可撤銷,而非“無效”。例如日本民法第15條到18條的規定,成年本人的法律行為可以撤銷,但購買日用品等其他有關日常生活的行為不在此限。韓國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場,規定成年本人的法律行為是可撤銷而非無效,并且還進一步規定,法院可以劃定成年本人在哪些范圍內的法律行為是有效,即限縮可撤銷的適用。?《日本民法典》第9條,《韓國民法典》第10條第1、2款。本文所引日本民法參見《日本民法典》,王愛群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韓國民法以2016年施行的《韓國民法典》為準。德國民法參見《德國民法典(第4版)》,陳衛佐譯,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瑞士民法參見《瑞士民法典》,戴永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意大利民法參見《意大利民法典》,費安玲、丁玫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是否采取無行為能力制度關鍵在于法律行為的效力,凡規定法律行為無效的即為無行為能力制度,凡規定可撤銷的,雖然名為無行為能力,實際上已拋棄傳統禁治產的立場。例如意大利民法雖然規定了禁治產人與準禁治產人,但由于這兩類人的法律行為效力是可撤銷而非無效,并且還規定了保佐等替代監護措施,因此意大利實際上也拋棄了無行為能力制度。?《意大利民法典》第427條第1、2款。反觀我國《民法總則》規定無行為能力人的法律行為一律無效,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效力待定,即須經監護人追認才有效,是對本人法律行為效力的一般性否定。尤其是《民法總則》采取了一般法定代理,例外獨立實施的表述,不僅與我國締結的《公約》相違背,也與國際潮流相反。這種理念下的法律施行,必然導致本人被隔離在社會生活之外,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基本上被剝奪,其實質是以保護財產和交易安全為中心,漠視對本人人身自由和醫療保健事務的保護。因此,第一,應盡快取消無行為能力人,自然人僅劃分為完全行為能力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第二,廢棄無行為能力人法律行為無效、限制行為能力人法律行為效力待定的規定,確認凡限制行為能力人法律效力有效,僅在經司法認定的范圍內可撤銷。
各國和地區還非常重視保障本人財產。例如臺灣地區規定,在作出監護宣告時,應指定會同監護人開具財產清冊的人;日本、韓國均規定,法院認為有必要的,應為本人指定監護監督人,其職責是代表本人利益監督監護人行為,包括監護人處分財產的行為;在德國,監護人必須將本人在監護宣告時及之后歸屬于本人財產編制目錄交法院備案,有監護監督人的,由監督人附加正確性和完備性的保證;瑞士民法典也有類似規定。?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111條,《日本民法典》第849、851條,《韓國民法典》第940條之4、940條之6,《德國民法典》第1802條,《瑞士民法典》第408、410條。
(二)尊重自我決定的首要原則
各國都同意,未成年監護應遵循最佳利益原則而成年監護遵循尊重意愿原則,但在立法技術上有兩種不同的實現進路。一種進路是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隱略最佳利益而彰顯尊重意愿的模式,即將最佳利益原則視為不言而喻的原則,因為維護本人最佳利益不僅是監護制度的主要目標,也是代理制度的應有之義。而尊重意愿原則是成年監護的特點,并且需明確與最佳利益沖突時誰優先,因此只在成年監護中強調。例如韓國未成年監護人的選任并沒有強調最佳利益或尊重意愿,而在成年監護人的選任中則強調應當尊重成年本人的意思。又如日本并沒有一般性的監護人履職原則,但是特別強調,監護人在對成年本人生活、療養看護及財產管理事務時,應當尊重成年本人的意思。?《韓國民法典》第932、936條,《日本民法典》第858條。
另一種進路是以德國為代表的,將最佳利益和尊重意愿分而述之的模式,即在未成年監護中強調最佳利益,在成年監護中強調尊重意愿。例如德國民法規定,未成年監護以最佳利益為一般原則,父母必須以自己的責任并彼此一致地為子女最佳利益進行父母照顧;當子女最佳利益受到危害而父母無意或不能避開危險時,法院應依職權采取措施保護子女,包括撤銷父母監護資格。由于德國采取了類型化的監護措施,在成年本人有殘留意思能力的情況下,監護人選任不得違反本人意志。例如,照管人選任不得違反被照管人的意愿。德國對尊重意愿的強調與日、韓略有不同,主要體現在成年監護中,尊重意愿被作為判斷是否符合本人最佳利益的主要標準之一。它還明確規定,照管人必須滿足本人的愿望,但以不與本人最佳利益抵觸且對照管人可合理期待為限。[21]《德國民法典》第1697a、1627、1666、1896之(1a)、1901之(2)和(3)條。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德國,還是日本、韓國,均將監護主要內容放在親屬編中,而鮮有國家將監護具體內容放在總則部分。關于監護體例編排的各國做法及我國《民法總則》的不合理之處,參見金可可:《〈民法總則(草案)〉若干問題研究對草案體系等若干重大問題的修改意見》,載《東方法學》2016年第5期。
在監護撤銷和恢復的問題上,各國都沒有將監護的具體內容放在總則部分,而是放在分編中詳細規定,因此未成年監護的撤銷,在親權關系中可以恢復;而成年監護在類型化之后,有殘留意思能力的,不存在恢復問題;沒有殘留意思能力的,曾被撤銷監護資格的人也被禁止擔任監護人,因此成年監護并不需要對恢復問題作出具體規定,只需對擔任成年監護人作出資格準入規定即可。由此可見,只要條例編排得當,監護撤銷與恢復遵循不同原則這種矛盾是可以避免的。[22]《意大利民法典》第334、335條,《德國民法典》第1908b條。
德國分而述之的模式促使其立法在成年監護中對最佳利益進一步作擴張解釋,其后果是模糊了最佳利益與尊重意愿的界限,尤其是當兩者沖突時何者優先并沒有明確的立場。相比之下,日本、韓國模式更為簡單易明,在處理諸如成年本人吸煙等問題上更能給監護人和法院以明確指引。
(三)支援自我決定的多元措施
國際上普遍采用多元化措施來支援本人的自我決定,盡管因為法律傳統和翻譯的原因,各國多元監護措施名稱各不相同,但其具體制度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例如日本和韓國均為三元化的國家,其中日本民法規定的是監護、保佐和輔助,韓國規定的是監護、限定監護、特定監護。[23]《日本民法典》第876-1、876-2、876-4、876-6、876-7、876-9條,《韓國民法典》第959之2、959之3、959之4、959之8、959之9、959之11條。這些制度的共同特點是盡量縮減過去陳舊的替代本人做決定的全面監護,而盡量擴大本人自我決定的范圍,不同的監護替代措施,其實質是對本人自我決定干預程度的強弱變化。
另外,即使這些國家已經對監護措施進行多元化和類型化,但絕不意味著每種類型的監護替代措施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本人的需求是參差百態的,各國普遍賦予法院自由裁量權,在決定替代監護類型以后,法官依然有權調整本人自我決定與監護人代理的邊界和范圍。例如韓國規定,法院可以劃定監護人對成年本人的法定代理權以及人身決定權的范圍,本人、近親屬、監護人等可以申請變更該范圍。[24]《韓國民法典》第938條。德國法院的裁量權更大,照管開始后并不當然發生限制本人能力的效果,只是在個案需要的時候才由監護法院以賦予照管人同意權的方式,要求本人的意思表示應當經照管人同意才生效。這種方式由于對司法人員素質和司法資源要求極高,因此采用的國家并不多。[25]同注①。
(四)以司法審查保護本人權利
監護制度是一把雙刃劍,其特點是替代本人做決定,以對本人基本權利的干預為前提的,因此先進國家對監護的發生與終止普遍采取司法審查主義,即未經司法程序認定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的,不得為其設立監護,他人不得僅因本人在事實上可能存在的精神、智力障礙而徑行擔任監護人,成為其法定代理人。司法審查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監護啟動模式,典型代表是日本民法,它規定監護從監護裁定開始,即規定監護開始的時間以司法裁判為準。[26]《日本民法典》第838條。第二種是監護限定模式,典型代表是德國,雖然其沒有規定照管從照管裁判時啟動,但是由于其立法上的成年人能力推定原則,照管人的職責范圍需經司法審查并遵循最少限制原則,只要不經司法裁判,本人行為能力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德國成年監護實際上是納入訴訟程序之內。[27]《德國民法典》第1896條(2)、(4)項。德國法上監護特指親權喪失后的未成年人監護,而照管指的是成年監護。第三種是混合模式,例如韓國,一方面在監護上它并沒有規定成年監護從監護裁定開始,但是它立法精神也是成年人能力推定原則,采取的是德國的監護限定模式,賦予法院劃定監護人職責范圍的權力;另一方面對限定監護和特定限護,它又明確規定發生與終止均以裁判為準,采取的是日本的監護啟動模式。
盡管司法審查主義的實現模式不同,但是上述國家有兩個方面的共性:一是區分未成年監護與成年監護,因為父母對未成年人的監護是自然發生而不可能、不必要納入司法程序的。因此,要么采日本模式,區分親權與監護,將成年監護與親權外的未成年監護納入司法程序;要么采德國模式,限制成年人的行為能力范圍需經司法程序,當然也可以考慮像韓國一樣采取混合模式。
二是這些國家的被監護人法律行為是“可撤銷”而非無效,要以本人為限制行為能力為由而撤銷其法律行為,必須訴諸法院,因此其法律行為制度本身就蘊含著未經司法裁判不得認定成年人法律行為無效的準則。
在監護相關的訴訟程序中,本人也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在監護人的選任上,又有兩種不同的做法。一種是本人獨占申請,例如德國,成年監護只能由本人提出申請,并依本人意愿選擇監護人,即使本人是無行為能力人;唯一例外是本人無法表明其意思。另一種是他人兼可申請,例如韓國民法規定,本人以及親屬、利害關系人、檢察官、自治地方首長都有權向法院提出申請選任監護人,但法院選任時應尊重本人意見。[28]《德國民法典》第1896條(1)項,《韓國民法典》第936條第2、4款。兩種做法略有不同,但在以下兩點完全相同:一是承認本人在監護人選任程序中的主體地位,本人獨占申請自不待言,韓國采兼可申請后,特別規定法院選任監護人時應尊重本人意見。二是允許法院依職權選任監護人,體現了國家照料的立法精神。
既然本人可獨立申請選任監護人,也就不存在強制代理及其帶來的問題,但仍需重視本人實質、有效參與監護訴訟的程序保障,即為其指定訴訟的臨時監護人。例如意大利的監護宣告判決可以上訴,因此其民法規定法官在駁回監護宣告申請后,在裁判生效前,可為本人指定臨時監護人,直到終審判決作出為止。[29]《意大利民法典》第422條。
五、我國新成年監護制度的法律解釋與婚姻家庭編立法
(一)《民法總則》第22條的體系解釋
眾多國家將被監護人的法律行為普遍規定為有效,只有在裁判劃定范圍內才可撤銷。為解決這個問題,從解釋論的立場看,重點是《民法總則》第22條的解釋。從民法體系出發,該條中關于限制行為能力人法律行為須經法定代理人代理、同意、追認的表述,只能解釋為效力待定而無法解釋為可撤銷,但是,仍然有兩種解釋方法可作為當下的權宜之計。
第一種是對第22條與第145條的關系作擴大解釋和舉證責任分配。第22條規定在自然人章,旨在劃分不同能力層次的自然人;第145條在法律行為章,專為法律行為效力而設,因此,關于法律行為的效力,第145條應優先于第22條適用。由于第145條的表述是限制行為能力人在心智范圍內法律行為有效在前,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認在后,因此應認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法律行為效力是一般獨立實施、例外法定代理的規則:被監護人法律行為除涉及重大財產人身關系的,有效,不需經法定代理人追認;對本人或其監護人主張該法律行為超出本人心智能力而無效的,除非該法律行為涉及重大財產、人身關系,否則需舉證證明該法律行為超出行為當時的本人心智理解范圍;相對人主張催告權和撤銷權的,負證明行為超出本人心智范圍的舉證責任,無法證明的不享有催告權和撤銷權。
第二種方法則是對《民法總則》第22條和第35條第3款的關系作出解釋。第35條在監護章,其第3款關于“對(成年)被監護人有能力獨立處理的事務,監護人不得干涉”的規定,屬于監護章對成年本人與監護人關系的調整性規范,根據規范主旨和特別法優先于一般法的規定,也可以從監護人不得在本人心智范圍內行使法定代理權的角度得出與第一種解釋相近的效果。
同時,應增加關于監護人財產報告制度以及監護監督制度的立法內容。《民法總則》只有關于監護人除為維護本人利益外不得處分本人財產的規定,無異于將本人財產的安危交由監護人道德水平決定,顯然不合理。既然《民法總則》為監護設了專節17個條文,為何花費大量筆墨在監護人職責的抽象性規定(共2條6款)、監護的撤銷與恢復(共2條4款)上,卻沒有提及更為重要的監護監督制度?如果說《民法總則》偏重原則和框架,那為什么一直到了《婚姻家庭編》二審稿草案都沒有一個成年監護的條文?相比之下,《民法總則》對宣告失蹤人的財產作出了相當篇幅的規定(共4條10款),更讓人產生被監護人地位甚至不如失蹤人的錯覺,也再次印證關于《民法總則》編排不當的批評。因此,在《婚姻家庭編》中增加監護人財產報告以及監護監督的條文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符合制定《民法總則》時立法者關于監護制度在總則作原則性規定、在婚姻家庭編細化展開的設計路線。[30]李適時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釋義》,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頁。
(二)《民法總則》第24條確立司法審查主義的限縮解釋
承認被監護人有行為能力的必然邏輯,就是監護人不得僅因監護而成為本人所有事務的法定代理人。先進國家都規定監護人的法定代理范圍須經司法審查,未經審查的仍由本人自我決定。但是根據《民法總則》,本人法律行為由監護人代理,他在事關本人重大切身利益的監護程序中被強制代理,不具有當事人的主體地位;同時在監護人履職、監護撤銷、監護人選任等方面又規定了最佳利益原則,體現的是一種從立法家父主義出發而形成的對成年本人的全面監護模式。這名為保護被監護人,實際上過度剝奪了本人的自由,成為“剝奪公民權利最徹底的民事懲罰制度,本人的法律地位與死人相差無幾”,[31]Lawrence O.Gostin & Anna Garsia,Governing for Health as the World Grows Older: Healthy Lifespans in Aging Societies,The Elder Law Journal,Vol.22,p.115.當然不符合《公約》的要求。因此,應及時變革這種全面監護模式,改采部分監護模式,即僅在本人實際需要的限度內設立的保護或援助措施,在限度以外的則由本人自我決定。
第一,應明確成年監護強調尊重意愿原則,監護人應努力同時滿足尊重意愿與最佳利益原則的要求,但當兩者沖突時,不危及生命下應優先適用尊重意愿原則。[32]危及生命時,例如安樂死、大麻合法化等,是否還需要尊重個人意愿的問題,并非成年監護獨有,完全能力人也會遇到,因此不是本文討論重點。比較法中有以日、韓為代表的隱略最佳利益而彰顯尊重意愿模式,與以德國為代表的將兩個原則分而述之的模式。但是,日、韓模式簡單易用,發生原則沖突時更能突出尊重意愿在成年監護中的優先適用地位,而且在我國家長主義傳統濃厚的背景下,最佳利益原則不需要過多強調,而尊重意愿才更需要反復強調。但是由于《民法總則》監護一節將兩個原則多次混用,解釋論已無適用余地,只能通過婚姻家庭編確立成年監護的尊重意愿原則,監護撤銷與恢復等問題也只能留給分編解決,[33]李霞、陳迪:《〈民法總則(草案)〉第34、35條評析——監護執行人的撤銷與恢復》,載《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再次印證婚姻家庭編增加成年監護內容的必要性。
第二,將成年監護納入司法審查。最根本的是將不完全行為能力人法律行為效力規定為可撤銷而非無效,這將確保成年監護的啟動進入司法程序,解決方案前文已述。其次,考慮到《民法總則》采取了司法宣告的規定以及長久以來我國司法實踐中的“被精神病”問題,我國將監護納入司法審查應采取混合模式。具體而言,一方面應像日本一樣規定監護從監護宣告裁判開始,另一方面借鑒德國經驗,規定監護人的法定代理權范圍在監護裁判中劃定,在能力推定原則下,裁判未認定或認定不明的,仍由本人自我決定而監護人不得行使法定代理權。在新法修訂之前,則應對《民法總則》第24條第1款作限縮性的反向推論解釋,即非經法院認定能力受限,都是完全行為能力人,以盡快消除實踐中脫離司法程序而“體外循環”地剝奪本人行為能力的荒唐現象。
第三,承認本人在監護程序中的主體地位。既然向法院申請認定本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那么本人在法院裁判之前就是完全行為能力人,否則就是未審先判。因此,應從解釋論立場出發,將《民事訴訟法》關于認定行為能力程序中由近親屬擔任本人代理人的規定,視為因與《民法總則》第24條的規定存在內在沖突而無效,避免在認定行為能力程序中對本人實施強制代理。該類案件在立案后、審判前,法院應先征求本人意愿,本人需要輔助參加訴訟的,或確難表達個人意愿的,為保護本人權益,法院可準用《民法總則》第31條第3款規定為本人指定訴訟中的臨時監護人,輔助或者代表本人參加訴訟。
第四,明確成年監護人應依選任確定,而且本人是選任的主體。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采德國的本人獨占申請主義短時間內難以實現,因此可采韓國的他人兼可申請主義,即除本人外的其他近親屬、利害關系人均可申請為本人選任監護人,但須明確本人申請為主,他人代為申請為輔。
(三)《民法總則》第35條第3款意定監護優先的擴大解釋
為符合《公約》第12條“適應本人情況”的要求,滿足被監護人層次不同、內容不同的支援自我決定要求,多元化的決定支援措施在比較法中已蔚為大觀。我國《民法總則》法定監護仍只有一種類型,不僅無法滿足《公約》要求,在邏輯上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將不完全能力人劃分為“限制”與“無”兩種,為何法定監護措施卻只有一種呢?因此,構建多元化的監護措施體系是必然選擇。
一方面,意定監護與法定監護應并舉。從立法技術上看,《民法總則》沒有規定意定監護的具體內容可以理解,但是沒有規定意定監護與法定監護的關系則屬遺漏。既然兩者同時出現在總則中,則邏輯上就要求在總則中也規定解決兩者關系的一般規則。缺少這個規則,即使規定了意定監護也難以在實踐中有效實施。在分編立法完成之前,應采取解釋論立場解決該問題,即對于《民法總則》第35條第3款中關于“被監護人有能力獨立處理的事務”采擴大解釋,凡本人已通過意定監護委托意定監護人處理的事務,視為本人已憑自己能力獨立處理,監護人不得干涉,從而確立意定監護優于法定監護的地位。
另一方面,多元措施與法院裁量要并用。縱觀各先進國家,無論二元、三元或四元,均在豐富法定監護類型的同時賦予法院自由裁量權,唯恐類型化還不夠細致,還不能滿足被監護人參差百態的實際需要。在經驗借鑒時應看到,多元措施與法院裁量權之間某種程度上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一般來說類型越是豐富,法院裁量權余地與必要性也越少,反之亦然。德國是多元化類型少而裁量權大的典型代表,但這對司法要求極高,尤其是我國此前并沒有類型化的多元化支援決定措施,期望法官在短時間內從一刀切的單一全面監護迅速轉變為完全滿足個體需要的高度自由裁量是不現實的。英美國家多元化類型最為豐富,但四元化措施可能規則過于繁瑣,沒有判例法支撐的情況下應用難度也不小。[34]同注⑤,第181~182頁。相比之下,日本、韓國等國家將三元化措施與法院自由裁量相結合,既能夠為本人提供足夠的支援措施類型,又允許法官根據個案情況適度調整,較好地在兩者之間實現平衡,值得我國借鑒。盡管《民法總則》只有監護而沒有諸如保佐、輔助等規定,但可依據第35條第3款、第128條,在婚姻家庭編中規定多元化的決定支援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