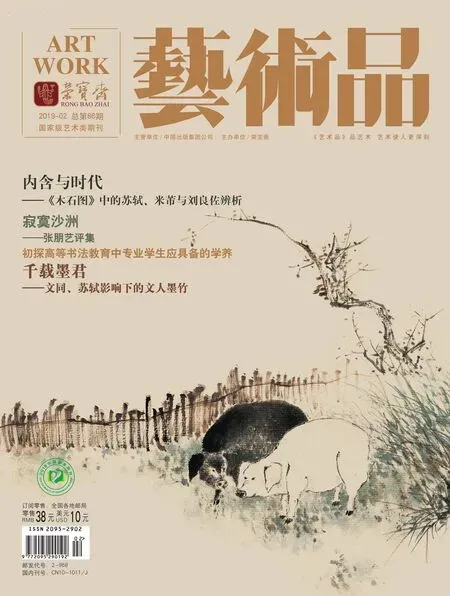藏雜雜說(shuō)(十四)
文/韓天衡



清趙之謙楷書對(duì)聯(lián)
對(duì)聯(lián)作為書法的一種形式,要早于立軸。據(jù)記載,宋代的陳摶就書寫過(guò)“開(kāi)張?zhí)彀恶R,奇逸人中龍”的對(duì)聯(lián),這算得上是開(kāi)山鼻祖了。但是紙本對(duì)聯(lián)的隆興,當(dāng)在明中期。這與紙張生產(chǎn)的大幅化,及明式房屋的廳堂設(shè)計(jì)和陳式有關(guān)。廳堂主座的背壁上,務(wù)必要張掛大畫軸,左右兩側(cè)則張掛對(duì)聯(lián)的上下聯(lián),甚至有分掛二三副者。字畫的主題及珍貴程度,往往要與主人地位身份相稱,而且是時(shí)常要更換的,這可是主人的門臉。客人來(lái)了,先瞻觀書畫,有文化,也有了話題。所以到民國(guó)營(yíng)造的中式房屋里,還保留了這種格局。以往的對(duì)聯(lián),存世量多多,而現(xiàn)今則近式微,藝術(shù)的裝幀形式,都還是跟實(shí)用相關(guān)。
這是清代詩(shī)書畫印皆擅的大師趙之謙的佳作,去些嬈佻,多些澀重,魏碑里能讀到顏真卿法書的風(fēng)骨。記得是1999年由拍場(chǎng)競(jìng)得,當(dāng)時(shí),炒作之風(fēng)未熾,三萬(wàn)二拍得,加百分之十傭金,總計(jì)三萬(wàn)五千二百元。如今的傭金也漲了許多,水漲船更高了,一哂。
晉唐云銘磚硯
漢晉磚為筑墻砌墓之用。但到了清中葉,金石學(xué)的盛興,文人,尤其是清高嗜古的文人,視堅(jiān)硬的古磚有拙樸之趣,往往還多按有圖畫和吉語(yǔ),即取來(lái)開(kāi)塘注蠟,作硯之用。且也蔚成一時(shí)風(fēng)氣。
這是藥翁唐云先生舊藏的晉磚,早已制成硯。一次他令我刻對(duì)章,呈上,頗滿意,說(shuō):“你畫兒蠻多了,這次送方磚硯給你。”老輩的思維真周到,如古話所說(shuō):投桃報(bào)李。我說(shuō):“太謝謝了。”但一看,除了晉代的年款,別無(wú)所有。我開(kāi)玩笑地說(shuō):“唐先生,送硯不落款,人家會(huì)以為是從大石齋里撈來(lái)的。”就這樣,他老人家在硯背寫了三行字,搬回家里,興致勃勃地一口氣刻成,又在硯的天頭,自書了“貞石壽”,時(shí)在1980年。
藥翁對(duì)我等后輩多獎(jiǎng)掖,但很實(shí)在,一般不當(dāng)面說(shuō)令你輕飄而虛夸的表?yè)P(yáng)話。他仙逝后,一次讀到他學(xué)生寫的一本回憶錄,里面居然記錄了先生對(duì)我的許多褒獎(jiǎng)。先生正氣一身,跟許多今人的作派恰恰相左,古風(fēng)可頌啊。

清于碩刻象牙紅木座硯屏
此為象牙紅木座的硯屏。硯屏之盛行當(dāng)在宋代,擱置于硯之上風(fēng),書寫者多右手執(zhí)筆,防風(fēng)亦免硯中墨汁之速干,既利于靜心書寫,且也是文人設(shè)置之精致雅具。誠(chéng)然,寒酸文士是配置不了的。至明中后期,盛行書寫巨幅大字,此物多為案頭擺設(shè),雖無(wú)實(shí)用,而對(duì)達(dá)官顯貴似又不可或缺。近于聾子的耳朵。
此硯屏之微刻書畫,為晚清于碩(字嘯軒)所作,此公書畫兼擅,更擅于微刻。讀此畫則清麗可人,淵源有自:讀其字則宗師東坡,樸茂醇正。尤其不可思議者,在指甲般大的范圍里竟刻寫了約六百字的吳梅邨西田詩(shī),簡(jiǎn)直神乎其神,不可思議。
故我謂,書畫入微雕不易,更不易者不在其微,而在兼具書畫之精妙,若于碩者,堪稱古來(lái)微刻之翹楚。嗟前無(wú)古人,嘆后無(wú)來(lái)者。

清揚(yáng)璣刻壽山石印
揚(yáng)璣字玉璇,是康熙時(shí)最享盛名的壽山石雕家。當(dāng)時(shí)藝人膽子小,也把名利看得淡,大都不在雕件上署名。道理也簡(jiǎn)單:好則留芳百世,孬則遺恨一生。有自知之明,所以前清三代署名者寥寥。
此件真品雕一甪端神獸氣格雄渾,小中見(jiàn)大,神采奕奕,且署款也屬的真。
時(shí)在1995年,接待外賓后自錦江飯店出,有一蘭馨古玩店,素知此店有幾位掌眼的老法師,而此件標(biāo)價(jià)僅一千五百元,可謂是鐵鞋磨穿無(wú)覓處,得來(lái)全不費(fèi)功夫。遂購(gòu)歸。
多年來(lái)示以業(yè)內(nèi)專家,把玩之際,皆贊佩無(wú)已,有國(guó)手級(jí)雕家嘗摹刻先后兩鈕,均自嘆古賢之不可及。我也每嬉言,這可是從老虎嘴里拔來(lái)的寶牙,一笑。

清胡開(kāi)文制張果老禮墨
文房四器,硯之外,筆、紙、墨多是消耗品,即使宮廷內(nèi)府中物,也都屬使用的,作純裝飾用者極少。然而,此三物中,尤其是墨,著意附加藝術(shù)的元素,不計(jì)工本地飾以金銀,點(diǎn)以珍珠,著朱衍翠,極盡華貴,從而演化為實(shí)用外足可遞藏觀賞的文玩。以我有限的見(jiàn)識(shí),觀玩且貽于友朋非僅實(shí)用的禮墨,濫觴于乾隆,之后則蔚然成風(fēng),這也是嘉慶、道光后一道特別的風(fēng)景。禮墨有外觀奇美而質(zhì)佳者,也有金玉其外,敗絮其里者,前者可實(shí)用,后者則傷硯、傷筆、傷神。此八仙中人物張果老,墨高23厘米,巨品。滿身泥以真金,又點(diǎn)綴石青、石綠,工藝精妙,造型別致,光彩奪目,一派富美氣象,乃晚清不可多見(jiàn),且傳世極少之品。惜墨之保存,干不得、濕不得,碰不得、嬌氣十足,不遜賈府林妹妹,故美術(shù)館開(kāi)幕時(shí)陳列不多日,即回庫(kù)房靜養(yǎng)矣。

明鐵犁木騎象羅漢
這尊明代騎象羅漢,經(jīng)歷過(guò)一場(chǎng)被毀容的慘痛經(jīng)歷。記得是在1993年,經(jīng)過(guò)新閘路,新開(kāi)了一家古玩店,看得上眼的東西不多,東西不多的店鋪,叫價(jià)特狠,時(shí)去走動(dòng),也先后買了幾件伊秉綬、齊白石的書畫和名家的舊章。漸漸地熟了,又常回答他一些古玩知識(shí),價(jià)格也松動(dòng)了。
一日偶過(guò),見(jiàn)被正面砍去臉部的這尊羅漢。細(xì)睇,乃木中最堅(jiān)硬的鐵犁木,這木材硬到一般的刀槍不入,被砍成這付殘相,要有多大的“仇恨”,詢問(wèn),說(shuō)是從“文革”前的大戶人家收購(gòu)古玩時(shí),這件劫后余身的木器,是順帶送他的。我詢價(jià),說(shuō):“儂韓先生要,給四十塊,收個(gè)坐義頭(出租車)銅鈿。”
請(qǐng)了尊有病的羅漢,一直想為其“整容”,兩年后請(qǐng)滬上高手楊留海修復(fù),遂得如今尊容。毀物只需一旦,而修復(fù)之難,多有“玉碎難復(fù)”者,此物算是大幸。看來(lái)在“文革”那荒唐詭詐的時(shí)段,菩薩還得人保佑。

元剔犀心形紋毛筆
漆是中國(guó)人的發(fā)明,這漆是指生漆,也叫大漆,我國(guó)的使用可上溯到七千多年前,出現(xiàn)時(shí)間太久了,生活里用得太廣泛、太普及了,泛泛加之普通,人們則不以為然、不以為奇了,頗有點(diǎn)“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shí)廬山真面目”的況味。戰(zhàn)國(guó)乃至漢墓里,出土過(guò)諸多精妙絕倫的漆器和漆繪,內(nèi)里的胚骨早已朽蝕,得以整體的保存至今,全賴大漆不朽的功勞。
漆器的雕刻工藝在宋代已勃興,在木胚、金屬胚的器物表面髹漆,一層稍干,又復(fù)一層,往往要髹幾十層,超百層,這層次里也還有色彩的區(qū)分,疊加到一定的厚度,則有高明的雕刻匠在其上施藝,或人物、或山水、或花鳥(niǎo)、或龍?、或幾何紋飾,題材廣泛,多寓吉祥意。一般純黑漆的,或面漆黑色,下層多有其他色彩相參的稱剔犀。純紅色者稱剔紅。做一件漆器經(jīng)年而成則是常態(tài)。
此為元代所制剔犀心形紋毛筆。筆長(zhǎng)21厘米以黑漆為面,間以紅漆兩道,色感穩(wěn)重深幽,由筆套至筆桿貫穿心形紋,線感起伏,流暢自如,大匠用刀之圓勁婉潤(rùn)令人嘆服。心形紋在元代以后即未見(jiàn)衍用,此也鑒別時(shí)代的機(jī)竅之一。
此件元筆,國(guó)內(nèi)博物館皆未曾見(jiàn)。十四年前,在東京以重值得之,今在我們美術(shù)館長(zhǎng)期展示。

清壽山白芙蓉石太平洗象圖
說(shuō)到壽山石的雕件,清初的福州名家堪稱一枝獨(dú)秀,講得霸氣點(diǎn),是獨(dú)步天下。雖說(shuō)彼時(shí)青田、昌化都產(chǎn)美石,但缺失的是人文環(huán)境。壽山屬八閩首邑,一時(shí)人文薈萃,如謝在杭、毛奇齡、高固齋輩,好石賞石,工匠運(yùn)斤,文氣熏陶,學(xué)藝相輔,故工匠之作,多洗剔俗骨、文心勃發(fā),盡得風(fēng)流。其時(shí)最著名者有周尚均、楊玉璇,以及魏汝奮、魏開(kāi)通等。
此以將軍洞白芙蓉雕刻之太平洗象圖,一仆踞地洗刷,一童捧瓶騎象背,彼此呼應(yīng),披毯染丹,淺刻繁花,填以真金,牽索賦彩,嵌以紅寶綠翠,高技大藝外,顯現(xiàn)出別致的富美氣象,大匠手筆,名不虛傳。作者周尚均,有“識(shí)”(古之通例,款字陰刻曰款,陽(yáng)刻稱識(shí))于象之內(nèi)腹,不予錄出,恐好事者仿真牟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