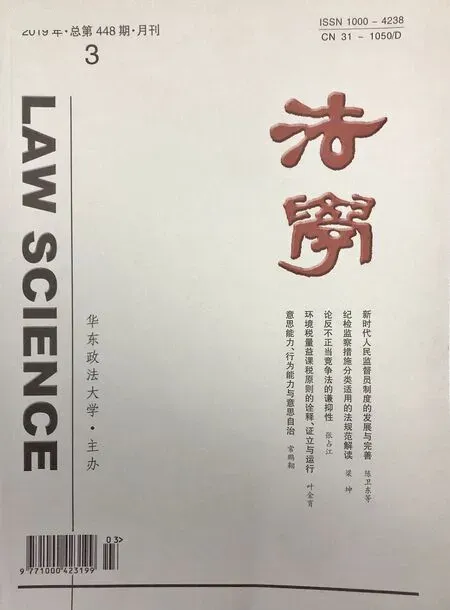“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法律適用
●胡東海
自上世紀80年代起,證明責任問題便受到我國理論和實務持續而廣泛的關注。有關證明責任的國外先進理論,尤其是羅森貝克的“規范說”,在我國學界獲得普遍接受,并直接影響了司法解釋相關條文的制定。這類司法解釋主要包括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訴法解釋》)。其中,《證據規定》第2條、第4~7條、第73條以及《民訴法解釋》第90~91條、第108條,與1991年《民事訴訟法》及其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修正案的第64條第1款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等,共同構建起我國的證明責任規范體系。在前述立法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國學界無須專注于相關比較法學說的引介以及立法論上的批判性討論,而應在解釋論上展開對各項證明責任規范的教義學研究,實現“規范說”的本土化。鑒于此,本文擬探討此種本土化的重要一環,即在司法解釋參與構建的證明責任規范體系中“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法律適用問題。
一、證明責任規范的類型和法律屬性
現代證明責任理論認為,任何要件事實在訴訟中均可能出現被證明、被駁回和真偽不明三種情形;客觀證明責任是指要件事實真偽不明時的不利后果或法律風險;證明責任規范以分配該法律風險為規范內容。證明責任規范與標的物的風險負擔規則(《合同法》第142條)具有類似性,前者在當事人之間分配要件事實真偽不明的風險,后者分配標的物意外毀損、滅失的風險。羅森貝克和普維庭均認為,證明責任規范的法律屬性取決于特定要件事實的法律屬性。〔1〕參見[德]萊奧·羅森貝克:《證明責任論》,莊敬華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頁;[德]漢斯·普維庭:《現代證明責任問題》,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頁。由此,若特定要件事實(如代理權的授予)是民事法律事實,其證明責任規范(《證據規定》第5條第3款〔2〕《證據規定》第5條第3款規定:“對代理權發生爭議的,由主張有代理權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具有民法規范的屬性;若特定要件事實(如管轄協議的訂立)是民事訴訟法律事實,其證明責任規范具有民事訴訟法規范的屬性;〔3〕關于民事訴訟法中的證明責任規范,參見前注〔1〕,萊奧·羅森貝克書,第401頁以下;李浩:《民事訴訟法適用中的證明責任》,《中國法學》2018年第1期。若特定要件事實(如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是行政法上的法律事實,其證明責任規范(《行政訴訟法》第34條第1款〔4〕《行政訴訟法》第34條第1款規定:“被告對作出的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關于行政訴訟法中的證明責任規范,參見劉善春:《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規則論綱》,《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朱新力:《行政訴訟客觀證明責任的分配研究》,《中國法學》2005年第2期。)具有行政法規范的屬性。
我國實在法規定了兩類民事證明責任規范。其一,證明責任基本規則,即“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它是對《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的概括。此外,《民訴法解釋》第91條也被認為具有證明責任基本規則的特性。〔5〕參見沈德詠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16頁;袁中華:《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及其適用——〈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91條之述評》,《法律適用》2015年第8期;胡學軍:《我國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理論重述》,《法學》2016年第5期。其二,證明責任特殊規則,它在民事法律中隨處可見。如《合同法》第152條關于買受人證明標的物權利瑕疵的規定、第374條關于保管人證明自己無重大過失的規定;《侵權責任法》被認為是證明責任特殊規則規定得最多的民事單行法,〔6〕參見李浩:《〈民事訴訟法〉修訂中的舉證責任問題》,《清華法學》2011年第3期;胡學軍:《證明責任“規范說”重述》,《法學家》2017年第1期。如第58條(醫療損害責任)和第81條(動物園動物損害責任)有關過錯推定的規則。此外,司法解釋中也存在大量證明責任特殊規則,如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3條規定,合同相對人主張構成表見代理的,應證明其善意;〔7〕關于該項證明責任規范的評論,參見胡東海:《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實質性原則》,《中國法學》2016年第4期。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物權法解釋(一)》)第15條第2款規定,原所有權人主張不構成善意取得的,應證明受讓人的惡意。
由此可知,在民事證明責任規范的立法上我國采二元體例:證明責任基本規則被納入民事訴訟法,而證明責任特殊規則主要被規定在民事單行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中。域外采此例者,如希臘、比利時、瑞典、芬蘭、巴西和我國臺灣地區等。與之不同,法國、瑞士、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等采一元體例,證明責任基本規則和特殊規則均被規定在民法典中。然而,由于在兩種體例中證明責任基本規則和特殊規則在本質上均為民法規范,〔8〕證明責任基本規則不僅適用于私法領域,而且在除刑法之外的公法領域同樣有效。參見前注〔1〕,漢斯·普維庭書,第380~383頁。所以,若證明責任基本規則適用于私法領域,它是私法領域的基本規則,具有私法規范的屬性;若適用于公法領域,它是公法領域的基本規則,具有公法規范的屬性。兩種體例僅具有形式上的差別。作為證明責任基本規則,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具有民法規范的屬性。
適用法律就意味著解釋法律。〔9〕參見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頁。同樣地,“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法律適用必然伴隨著對該規則的解釋,即闡明其規范內容。然而,筆者認為,基于“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特殊性,為實現該規則的法律適用,不僅應闡明其規范內容,還須探求該規則在特定民法制度中的具體適用形式。這兩項解釋作業在理論和實踐中極易引起爭論,如我國學說對于“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以及該規則在善意取得和動物損害責任等制度中的具體適用形式等方面所發生的嚴重分歧。〔10〕關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證明責任分配的爭論,可參見徐滌宇、胡東海:《證明責任視野下善意取得之善意要件的制度設計》,《比較法研究》2009年第4期;吳澤勇:《論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證明》,《中國法學》2012年第4期。關于動物損害責任中證明責任分配的爭論,可參見袁中華:《規范說之本質缺陷及其克服》,《法學研究》2014年第6期;吳澤勇:《規范說與侵權責任法第79條的適用》,《法學研究》2016年第5期。此種分歧不可避免地會影響該規則的正確適用,為此下文將集中討論這兩項解釋作業。
二、“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
(一)“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主觀解釋
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第1款確立了“誰主張誰舉證”規則,該規則在1991年《民事訴訟法》及其三次修正案中均獲得沿用。為實現“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法律適用,第一項解釋作業是闡明其規范內容。根據解釋目標的不同,法律解釋分為主觀解釋和客觀解釋,前者旨在探知法律規則中的立法者意思,后者旨在探知法律規則獨立于立法者的法律內在意思。〔11〕參見[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97頁;同前注〔9〕,黃茂榮書,第65頁以下。所以,“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依主觀解釋系指該規則中的立法者意思,依客觀解釋系指該規則獨立于立法者的法律內在意義。關于該問題,我國學界主要依主觀解釋認為,立法者在“誰主張誰舉證”規則中所表達的意思存在如下兩方面的重大缺陷。
首先,依主觀解釋,“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僅指主觀證明責任,而不涉及客觀證明責任。〔1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民事訴訟證據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頁;李浩:《民事證明責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頁;同前注〔5〕,沈德詠主編書,第311頁。主觀證明責任與客觀證明責任的區分是現代證明責任理論的基石。其中,主觀證明責任,也稱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它從當事人角度要求負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應就特定要件事實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客觀證明責任,也稱結果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它從法官角度要求在要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應判決負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受不利后果。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為減輕法院查明事實的負擔,提高當事人舉證的積極性,必然要強調主觀證明責任的重要性。持主觀解釋的論者認為,雖然自上世紀80年代我國學界開始討論民事證明責任問題,〔13〕參見顧培東:《淺析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法學季刊》1982年第2期;李浩:《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含義新探》,《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986年第3期;羅華俊:《略論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88年第4期。但民事訴訟法的立法者對客觀證明責任尚無清晰認識。而且,“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文義即為提出主張者負責舉證,僅符合主觀證明責任的表達,而與客觀證明責任無關。
為回應學說對“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忽略客觀證明責任的批評,2001年《證據規定》第2條第2款明文規定了客觀證明責任,〔14〕《民訴法解釋》第90條第2款直接來源于《證據規定》第2條第2款,前者被認為系客觀證明責任的規定。參見任重:《論中國“現代”證明責任問題——兼評德國理論新進展》,《當代法學》2017年第5期。不同觀點認為,兩項規定指向的均是主觀證明責任,參見李浩:《證明責任的概念——實務與理論的背離》,《當代法學》2017年第5期。即“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該條款經過簡單修改后為2015年《民訴法解釋》第90條第2款所沿用。我國法律實務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漠視客觀證明責任,導致法官在要件事實真偽不明時無限延長舉證期限或者恣意裁判。〔15〕同前注〔1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書,第22頁。憑借客觀證明責任的規定可有效解決此類問題,即法官在真偽不明時必須依客觀證明責任作出不利于負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的判決。所以,通過司法解釋明文規定客觀證明責任,在我國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其次,依主觀解釋,由于當事人主張的含義模糊,導致“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不明。〔16〕參見李浩:《民事舉證責任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頁。例如,在民間借貸糾紛中,原告“主張”借款合同成立,被告“主張”借款合同不成立。如果認為雙方當事人均提出“主張”,將出現雙方對同一要件事實(合同成立或不成立)均承擔證明責任的錯誤結果。那么,問題是到底哪一方當事人提出了“主張”。主觀解釋的論者認為,由于從立法者意思中無法獲知主張的準確含義,根據“誰主張誰舉證”規則不能回答該問題。由此可知,闡明“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其關鍵在于界定主張的含義。
為界定當事人主張的含義,我國學界曾借鑒國外理論,提出區分“權利主張”與“事實主張”、“否認”與“抗辯”等解釋方案。〔17〕參見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頁以下;陳剛:《抗辯與否認在證明責任法學領域中的意義》,《政法論壇》2001年第3期;李秀芬:《反思“誰主張,誰舉證”》,《法學》2004年第4期。其中,關于否認與抗辯的區分,如果被告的陳述只是否定了原告的主張,該陳述成立否認。由于否認不構成被告的主張,被告不負證明責任。例如,針對原告的借款合同成立的主張,被告的陳述“合同不成立”只是否定了原告主張,該陳述成立否認,被告不負證明責任。如果被告在承認原告主張的基礎上為陳述,該陳述可成立抗辯。由于抗辯構成被告的主張,被告應負證明責任。同樣針對原告的借款合同成立的主張,被告陳述已償還借款,該陳述在承認原告主張的基礎上,提出了清償(抗辯)的主張,被告應對其抗辯承擔證明責任。
(二)“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客觀解釋
依主觀解釋,“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存在缺陷,即使通過司法解釋和學說發展可補救該缺陷,但在解釋論上無法永久消除該缺陷本身。由于主觀解釋發現了“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缺陷,卻無法消除該缺陷,此種解釋的價值十分有限。與此不同,現代民法解釋學偏重客觀解釋,強調法律應當因應社會變化而發展。〔18〕參見王澤鑒:《民法思維: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頁;梁慧星:《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頁。雖然本文強調客觀解釋,但不反對應在兼顧立法者意思的前提下,依客觀目的發展法律。關于折中說,參見前注〔9〕,黃茂榮書,第271~272頁。依客觀解釋,應根據“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客觀目的,探知其在現今法律秩序中所具有的規范意義。
首先,依客觀解釋,“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同時包含主觀證明責任和客觀證明責任的概念。與“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境遇相同,我國臺灣地區所謂“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句〔19〕我國臺灣地區所謂“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句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于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規定的證明責任基本規則,同樣也曾被學界批評為僅指主觀證明責任。但時移世易,我國臺灣地區學界早已承認雙重含義的證明責任,便依客觀解釋,將該條解釋為既指主觀證明責任,也指客觀證明責任。〔20〕參見姜世明:《舉證責任與真實義務》,臺灣新學林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6 年版,第16頁;姜世明:《民事程序法實例研習(二)》,臺灣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10頁。在我國大陸地區,不僅學界早已對雙重含義的證明責任達成共識,〔21〕在此種共識的背景下,司法解釋的起草者卻走向了另一條歧途,錯誤地認為主觀證明責任的外延同時包括主觀抽象證明責任和具體證明責任。參見前注〔1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書,第16~17頁;同前注〔5〕,沈德詠主編書,第310頁。另外,關于雙重含義證明責任概念的術語選擇,學說上存在不同觀點。參見霍海紅:《證明責任的法理與技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頁以下。而且2001年《證據規定》和2015年《民訴法解釋》均規定了雙重含義的證明責任。在這種背景下,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民事訴訟法》三次修正案的立法者應早已熟知客觀證明責任。對于三次修正案均保留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即便依主觀解釋,也應當解釋為該規則同時包含雙重含義的證明責任概念。
此外,雖然客觀證明責任概念是現代證明責任理論的重要成果,但鮮有立法例如《證據規定》第2條第2款和《民訴法解釋》第90條第2款那樣,明文規定客觀證明責任。在法律適用時,客觀證明責任概念指向的是法官在真偽不明時的法律推理,要求法官在真偽不明時作出不利于負擔證明責任一方當事人的判決,涉及的完全是法律方法問題。對于法律方法問題,法律一般不作規定。即使加以規定,該規定也不具有法律規范的特征。〔22〕同前注〔1〕,漢斯·普維庭書,第234頁。鑒于此,在理論上承認客觀證明責任概念之后,立法例卻不對其加以規定,而只是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那樣,僅從舉證行為或主觀證明責任的角度規定證明責任基本規則;〔23〕同前注〔14〕,李浩文。而此種基本規則在學說上被認為包含客觀證明責任概念,乃無須爭辯之理。
同理,在我國實在法中,司法解釋對客觀證明責任的明文規定并不意味著其他相關規定(如民事訴訟法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指向的只能是主觀證明責任,而不能蘊含客觀證明責任。一方面,起草者在《民訴法解釋》第91條中采用全新的術語“舉證證明責任”,并認為該術語與“舉證責任”“證明責任”均是同義語,它同時包括主觀證明責任和客觀證明責任。〔24〕同前注〔5〕,沈德詠主編書,第309~312頁。另一方面,《民訴法解釋》第91條也被認為具有證明責任基本規則的屬性,那么可推知同屬基本規則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也應包括雙重含義的證明責任。綜上,在我國學說和實務普遍接受證明責任雙重含義的背景下,從客觀解釋的角度,“證明責任”“舉證責任”“舉證證明責任”均為同義語,“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同時包含主觀證明責任和客觀證明責任的概念。
其次,依客觀解釋,可界定當事人主張的含義,闡明“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如前所述,為界定“主張”的含義,我國學界曾提出區分“否認”和“抗辯”的解釋方案。該解釋方案與立法者意思并無關聯,屬于對“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客觀解釋。至少現今看來,該解釋方案并無實在法基礎。在現行有效的證明責任規范體系下,應結合《民訴法解釋》第91條解釋“誰主張誰舉證”規則。一般認為,除《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外,證明責任基本規則也包括《民訴法解釋》第91條。然而,由于在同一法律體系中證明責任基本規則應具有唯一性,所以在解釋上應認為,雖然兩項規定均被認為是證明責任基本規則,但它們在實質上具有同一性,指向的是同一證明責任基本規則。
一是根據《民訴法解釋》第91條第1項,“主張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產生該法律關系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其中,“法律關系存在”和“法律關系產生”之間的關系是,“法律關系存在”不僅要求“法律關系產生”,還要求“法律關系未消滅”,但后者屬于該條第2項的規范內容。在訴訟中有所請求的當事人,既然依該條第1項僅須舉證“法律關系產生”,那么也就不必主張“法律關系存在”,而只須主張“法律關系產生”。所以該項的內容在于,主張法律關系產生的當事人應當舉證法律關系產生的要件事實。〔25〕司法解釋的起草者認為,該條規定的“基本事實”與“要件事實”同義,參見前注〔5〕,沈德詠主編書,第317頁。
二是根據《民訴法解釋》第91條第2項,“主張法律關系變更、消滅或者權利受到妨害的當事人,應當對該法律關系變更、消滅或者權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其中,由于“法律關系的變更”可被納入法律關系消滅的范疇,因為法律關系變更意味著雖然承認法律關系已經產生,但該法律關系由于變更而不復存在。所以該項的內容在于,主張法律關系消滅或受到妨礙的當事人應當舉證法律關系消滅或受到妨礙的要件事實。
基于此,《民訴法解釋》第91條與《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的同一性體現為前者澄清了后者的規范內容。申言之,《民訴法解釋》第91條從法律關系的視角界定當事人主張的含義,闡明“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從法律關系的視角,“主張”是指“法律關系產生的主張”與“法律關系變動(消滅或妨礙)的主張”。在此基礎上,“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可被解釋為誰主張“法律關系產生”,誰舉證“法律關系產生的要件事實”;誰主張“法律關系的變動”,誰舉證“法律關系變動的要件事實”。
借助《民訴法解釋》第91條闡明已歷經數十年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這顯然是對該規則的客觀解釋。經過客觀解釋,“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對曾經的立法者可能完全陌生。但如果固守主觀解釋,不僅只能獲得存在重大缺陷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而且還將導致該規則在規范內容上與《民訴法解釋》第91條不一致,引起兩項規定之間的適用沖突。惟有依據客觀解釋,才能在法秩序內闡明“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擺正該規則與《民訴法解釋》第91條之間的體系關系,化解二者在法律適用中的潛在沖突。
(三)“誰主張誰舉證”規則與“規范說”之等同關系
根據《民訴法解釋》第91條,可從法律關系的視角闡明“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此種法律關系的視角具有兩種轉換形式,所以“誰主張誰舉證”規則還存在另外兩種解釋方案。〔26〕參見胡東海:《“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歷史變遷與現代運用》,《法學研究》2017年第3期。其一,由于法律關系的內容要素主要是權利,《民訴法解釋》第91條的法律關系視角可轉換為主觀權利視角。從主觀權利的視角,“主張”是指“權利產生的主張”和“權利變動的主張”。“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可被解釋為誰主張“權利產生”,誰舉證“權利產生的要件事實”;誰主張“權利變動”,誰舉證“權利變動的要件事實”。其二,由于客觀法與主觀權利相對應,主觀權利視角可被轉換為法律規范視角。從法律規范的視角,“主張”是指“適用權利產生規范的主張”與“適用權利變動規范的主張”。“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可被解釋為誰主張“權利產生規范”,誰舉證“權利產生規范的要件事實”;誰主張“權利變動規范”,誰舉證“權利變動規范的要件事實”。
從法律規范的視角,“誰主張誰舉證”規則與羅森貝克的“規范說”完全一致,二者均表現為一種民法規范的類型劃分理論。根據“規范說”,每一方當事人均應證明對自己有利的法規范的適用條件或構成要件,主張權利者應證明權利產生規范的要件事實,反對權利者應證明權利阻礙和消滅規范的要件事實。〔27〕同前注〔1〕,萊奧·羅森貝克書,第104頁;同前注〔1〕,漢斯·普維庭書,第362~363頁。正是由于羅森貝克從法律規范視角而非法律關系視角或主觀權利視角分配證明責任,其學說被稱為“規范說”。因此,民法規范在民法教義學中具有實體屬性,而在證明責任理論中具有證明責任屬性,“誰主張誰舉證”規則或“規范說”旨在依據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將其劃分為權利產生規范和權利變動規范,以此得到證明責任分配的結果。
綜上,為闡明“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不能滿足于依主觀解釋指出其缺陷,而應在與其他證明責任規范和通行證明責任理論不相沖突的前提下,依客觀解釋揭示其規范內容。一方面,從實在法條文之間體系關聯的角度,《民訴法解釋》第91條闡明了《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的規范內容,即借助法律關系的解釋視角,二者具有等同的規范內容。另一方面,從實在法與“規范說”之間理論關聯的角度,借助法律規范的解釋視角,“誰主張誰舉證”規則與證明責任理論的通說“規范說”之間得以建立等同關系。
三、“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具體適用形式
(一)“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具體化:尋找權利產生規范和權利變動規范
由于任一要件事實均可能出現真偽不明的情形,每項民法制度都涉及證明責任分配問題。如果特定民法制度的法律規整中不存在證明責任特殊規則,那么其舉證問題便適用證明責任基本規則,即“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由于規范內容極為抽象,“誰主張誰舉證”規則表現為一種框架性規則,它僅一般性地要求主張權利產生規范者與主張權利變動規范者,分別承擔證明責任。此種框架性規則在適用于特定民法制度時,必須獲得其具體適用形式,即從該民法制度相關的民法規范中尋找其權利產生規范和權利變動規范。
關于“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具體化,我們以無權處分制度為例說明。首先,在無權處分時,受讓人提起所有權確認之訴(《物權法》第33條)。其一,作為原告的受讓人,應證明權利產生規范構成要件的滿足。根據《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后半句,受讓人惟有依善意取得才能從無處分權人處取得所有權,這項規定是受讓人(所有權的)權利產生規范。其二,作為被告的原所有權人,應證明權利阻礙規范構成要件的滿足。〔28〕根據《物權法解釋(一)》第21條,若轉讓合同因特定事由無效或被撤銷,則排除善意取得的構成;該條也屬于權利阻礙規范。另外,此時也存在權利消滅規范,如根據《物權法》第113條,受讓人在依善意取得獲得物的所有權后,遺失該物且6個月內未認領,該物歸國家所有。根據《物權法解釋(一)》第15條第2款,若“受讓人惡意”,將排除善意取得的構成,該條是權利阻礙規范。
其次,在無權處分時,原所有權人提起原物返還之訴。其一,作為原告的原所有權人,應證明權利產生規范的適用條件。根據《物權法》第34條和《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前半句,權利人可以請求無權占有人返還原物。這兩項規定均是權利產生規范,原所有權人應證明自己是所有權人以及被告是物的占有人。〔29〕參見王澤鑒:《民法物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頁;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其二,作為被告的受讓人,應證明權利消滅規范的適用條件。〔30〕此時也存在權利阻礙規范,被告若為有權占有,將阻礙原所有權人追回權的行使,故關于有權占有的相關規定是權利阻礙規范。被告若依善意取得獲得物的所有權,將消滅原所有權人的權利,故《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后半句是權利消滅規范。〔31〕不同觀點認為,有關善意取得的規定是權利阻礙規范,參見吳澤勇:《論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證明》,《中國法學》2012年第4期;徐滌宇:《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解釋基準》,《法學研究》2016年第3期。但權利阻礙規范與權利消滅規范的區別在于,前者阻礙權利的產生,后者使已經產生的權利歸于消滅。若受讓人構成善意取得,將導致原所有權人已產生的所有權及其追回權歸于消滅。所以,關于善意取得的規定是權利消滅規范。其三,作為原告的原所有權人應證明權利消滅規范的阻礙規范之適用條件。依《物權法解釋(一)》第15條第2款,“受讓人惡意”排除善意取得的構成,該條款是權利消滅規范的阻礙規范。
因此,為實現“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法律適用,第一項解釋作業旨在闡明“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規范內容,其解釋對象就是該規則本身。與此不同,第二項解釋作業旨在探求該規則的具體適用形式,即以“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為標準,尋找特定民法制度的權利產生規范和權利變動規范。此項解釋作業的解釋對象實際上是特定民法規范,解釋的任務在于通過法律解釋識別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將其定性為權利產生規范或權利變動規范。〔32〕對于《民訴法解釋》第91條的具體適用,起草者同樣認為,法官應根據該條識別權利產生規范、權利阻礙規范和權利消滅規范,以此確定證明責任的分配。參見前注〔5〕,沈德詠主編書,第317頁。須注意的是,學理上將該項解釋作業稱作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解釋。例如,在無權處分時,學說上均在民事證明責任分配解釋的標題下,〔33〕同前注〔31〕,吳澤勇文;同前注〔31〕,徐滌宇文。討論基本規則的具體適用形式問題。
(二)與請求權基礎理論的關聯脈絡:尋找請求權基礎和抗辯基礎
雖然“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具有民法規范的屬性,但該規則在規范內容和具體適用形式,以及術語表達和理論脈絡等方面,顯然與其他民法規范存在較大差異。此種差異構成了從民法教義學角度理解“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障礙。但另一方面,“誰主張誰舉證”規則與傳統民法學中的請求權基礎理論實際上具有諸多關聯脈絡,若從請求權基礎理論的角度重新審視“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可以徹底克服從民法教義學角度對該規則的理解障礙。
首先,請求權基礎理論對民法規范的類型劃分,與“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類型劃分完全相同。根據請求權基礎理論,民法規范被劃分為請求權基礎和抗辯基礎兩大類。其中,請求權基礎,是指支持當事人權利請求的法律規范。在字面含義上,請求權基礎理論只符合給付之訴,而與確認之訴和形成之訴無關。不過,在法律實務中,提起確認之訴和形成之訴的最終目的仍在于請求特定給付,以請求權或給付之訴為中心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34〕參見田士永:《民法學案例研習的教學實踐與思考》,《中國法學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但即便如此,仍有必要擴大請求權基礎理論的適用范圍。為此,不妨將“請求權”擴張解釋為支持原告請求的權利,將“請求權基礎”擴張解釋為支持原告請求的法律基礎,以此涵括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兩種訴訟。
與此相對,抗辯基礎,又稱抗辯性規范、反對性規范,是指支持當事人抗辯的法律規范,它可分為“權利消滅的抗辯基礎”“權利阻礙的抗辯基礎”和“抗辯權基礎”。〔35〕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請求權基礎》,陳衛佐等譯,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頁;同前注〔18〕,王澤鑒書,第41頁。其中,權利消滅的抗辯基礎,是指已產生的權利因特定事由歸于消滅的法律規范;權利阻礙的抗辯基礎,是指權利因特定事由受到阻礙而未能產生的法律規范;抗辯權基礎,顧名思義以民法上的抗辯權為內容,是指已產生的權利因特定事由被排除行使的法律規范。須注意的是,在“誰主張誰舉證”規則或“規范說”之下,抗辯權基礎被稱為權利受制規范,只不過理論上一般將權利受制規范歸入權利阻礙規范中。〔36〕另有部分權利受制規范因其內容在于消滅已產生的權利,故而被歸入權利消滅規范之中,參見前注〔1〕,萊奧·羅森貝克書,第106~107頁。因此,根據采用術語的不同,在請求權基礎理論中,民法規范被劃分為“請求權基礎”和“抗辯基礎”;在“誰主張誰舉證”規則中,民法規范被劃分為“權利產生規范”和“權利變動規范”。兩種民法規范的類型劃分相互對應,請求權基礎對應權利產生規范,抗辯基礎對應權利變動規范。
其次,請求權基礎理論在具體化上與“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具有一致性。就如“誰主張誰舉證”規則是一種框架性規則,請求權基礎理論也表現為一種框架性理論。該理論在用于實例分析時,必須獲得其具體適用形式,即從該實例涉及的民法規范中尋找特定的請求權基礎和抗辯基礎。例如,對于原告依買賣合同請求被告支付價金的實例,依請求權基礎理論應遵循如下三個步驟尋找其請求權基礎和抗辯基礎。〔37〕參見葛云松等:《法治訪談錄:請求權基礎的案例教學法》,《法律適用》2017年第14期;朱曉喆:《請求權基礎實例研習教學方法論》,《法治研究》2018年第1期。其一,請求權是否產生?從積極要件的角度,判斷案件事實是否符合請求權基礎(《合同法》第159條第1句)的要件,如合同成立等;從消極要件的角度,判斷案件事實是否符合權利阻礙抗辯基礎的要件,如合同當事人無行為能力(《民法總則》第144條)。其二,請求權是否消滅?判斷案件事實是否符合權利消滅抗辯基礎的要件,如合同清償、抵銷、提存等(《合同法》第91條)。其三,請求權可否行使?判斷案件事實是否符合抗辯權基礎的要件,如時效經過的抗辯權(《民法總則》第192條第1款)。
因此,在規范內容上,“誰主張誰舉證”規則與請求權基礎理論均立足于民法規范的類型劃分,將民法規范劃分為權利產生規范(請求權基礎)和權利變動規范(抗辯基礎)。在規范內容的具體化上,由于二者表現為框架性規則或框架性理論,故而在法律適用中須予以具體化,此種具體化就是尋找權利產生規范(請求權基礎)和權利變動規范(抗辯基礎)的過程。
(三)與請求權基礎理論的不同側重點:權利產生規范與權利變動規范的區分意義
雖然在民法規范的類型劃分和規范內容的具體化上,請求權基礎理論與“誰主張誰舉證”規則高度契合,但二者各有其側重點。首先,在實例分析中,請求權基礎理論側重判斷案件事實是否具有法律基礎,至于將法律基礎劃分為請求權基礎與抗辯基礎,僅具有理論上的認識意義。例如,王澤鑒先生強調請求權與抗辯的對立性思維,以及請求權基礎與抗辯基礎的對立性思維,并指出此種對立性思維“不僅有助于辯證的思考方法,實務上亦甚重要”,但他實際上并未道明其實踐意義。〔38〕同前注〔18〕,王澤鑒書,第137~147頁。事實上,在請求權基礎理論的具體化上,民法規范的類型劃分對實例分析的結論并無實質影響。
在無權處分時,對于受讓人提起所有權確認之訴的實例,依請求權基礎理論,第一步驟須判斷請求權(原告的所有權)是否產生。從積極要件的角度,判斷案件事實是否符合請求權基礎(《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后半句)的三項構成要件,即“受讓人善意”“合理交易價格”和“物權公示”;從消極要件的角度,判斷案件事實是否符合權利阻礙抗辯基礎(《物權法解釋(一)》第15條第2款)的構成要件,若滿足“受讓人惡意”要件,將排除善意取得的構成。如果第一步驟的結論為原告的所有權已產生,既可承認“受讓人善意”是請求權基礎的積極要件,也不妨將“受讓人惡意”當作權利阻礙抗辯基礎的消極要件。但問題是,即使在實例分析中未能指明《物權法解釋(一)》第15條第2款屬于權利阻礙的抗辯基礎,以及“受讓人惡意”是權利阻礙抗辯基礎的構成要件,甚至將該條款與請求權基礎混作一談,均不會改變實例分析的結論。
其次,在實例分析中,“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側重判斷各項法律基礎的證明責任屬性,將法律基礎劃分為權利產生規范和權利變動規范,具有分配證明責任的實踐意義。在上例中,依“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后半句是權利產生規范,由作為原告的受讓人證明其要件事實;《物權法解釋(一)》第15條第2款是權利阻礙規范,由作為被告的原所有權人證明其要件事實。比較而言,在實例分析時,依請求權基礎理論,關鍵在獲得實例分析的結論,即當事人的權利請求是否具有法律基礎的支持;依“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側重在獲得實例分析結論的過程中識別法律基礎的證明責任屬性,并由此分配證明責任。所以,民法規范的類型劃分對“誰主張誰舉證”規則至關重要,將決定證明責任的分配,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然而,在探求“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具體適用形式時,學說和實務經常就特定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發生爭議。同樣地,在受讓人提起所有權確認之訴中,《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后半句是受讓人的權利產生規范,其三項構成要件包括“受讓人善意”要件。有觀點據此認為,“受讓人善意”是權利產生規范的構成要件,應由“主張權利產生規范的受讓人”舉證,即受讓人證明自己的善意。〔39〕參見鄭金玉:《善意取得證明責任分配規則研究》,《現代法學》2009年第6期;同前注〔31〕,吳澤勇文。不同觀點認為,不應將“受讓人善意”解釋為權利產生規范的構成要件,而應將“受讓人惡意”解釋為權利阻礙規范的構成要件;此時存在一項獨立的權利阻礙規范“若受讓人惡意,則排除善意取得”,由原所有權人舉證“受讓人的惡意”。〔40〕同前注〔10〕,徐滌宇、胡東海文。《物權法解釋(一)》第15條第2款為平息學說爭議,統一裁判規則,〔41〕參見李浩:《規范說視野下法律要件分類研究》,《法律適用》2017年第15期。贊同第二種觀點,規定“真實權利人主張受讓人不構成善意的,應當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縱然對于善意取得善意要件的證明責任分配,司法解釋通過明文規定平息了學說和理論的爭議,但有理由預期的是,在具體適用“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其他諸多情形,同樣會遭遇識別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之難題。為解決此類難題,顯然不能等待或依賴司法解釋逐一規定。因此,在探求“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具體適用形式時,根本的問題在于如何通過法律解釋科學合理地識別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
四、“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具體化的解釋方法
為獲得“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法律適用,第一項解釋作業旨在闡明其規范內容,解釋對象是該規則本身,該項作業被稱作“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解釋;第二項解釋作業旨在探求其具體適用形式,解釋對象是各項民法規范,該項作業被稱作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解釋。其中,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解釋,可借助民法解釋學的諸種解釋方法,以識別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為解釋目標,將不同民法規范分別定性為權利產生規范和權利變動規范,最終獲得“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具體適用形式,實現該規則的具體化。
(一)文義解釋:民法規范的實體屬性決定其證明責任屬性
在法律解釋中,解釋者應綜合考慮文義因素、歷史因素、體系因素和目的因素。針對不同因素展開的法律解釋,即為文義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首先,法律規范為獲得民眾的普遍理解經常使用日常用語,為精確陳述和避免重復也廣泛使用法學術語。但不論如何,法律語言不可能達到符號語言的精確度,總需要對法律規范的字面含義加以解釋。〔42〕同前注〔11〕,卡爾·拉倫茨書,第200~201頁。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文義解釋,是指根據語言規則理解民法規范的字面含義,識別其證明責任屬性。
1.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與實體屬性的關聯性
民法規范依其證明責任屬性,可以是權利產生規范、權利消滅規范和權利阻礙規范。在絕大部分情形,尤其是在民法規范依其證明責任屬性為權利產生規范或權利消滅規范的情形,由于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與實體屬性之間具有關聯性,民法規范的文義不僅體現其實體屬性,也指出其證明責任屬性。因此,依文義解釋可簡單有效地識別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
首先,針對當事人的權利請求,依文義解釋可確定其權利產生規范。根據法條理論,法條區分為完全法條與不完全法條,前者是具備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法條。〔43〕同前注〔9〕,黃茂榮書,第127頁。完全法條在請求權基礎理論中屬于請求權基礎,〔44〕同前注〔18〕,王澤鑒書,第46頁。在證明責任理論中屬于權利產生規范。例如,針對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返還借款的權利請求,《合同法》第206條第1句是請求權基礎或權利產生規范。
其次,針對當事人的權利請求,依文義解釋可確定其權利消滅規范。其一,民事法律章節標題的措辭表明該章節下的法律規范均是權利消滅規范。如《合同法》第六章的標題為“合同權利義務的終止”,表明該章有關履行、解除、抵銷、提存、免除、混同的法律規范均是(合同權利的)權利消滅規范。其二,法律條文的措辭表明其是權利消滅規范。如《合同法》第55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銷權消滅”,它是(撤銷權的)權利消滅規范。其三,法律條文的措辭雖未言明,但其含義表明它是權利消滅規范。如《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后半句關于善意取得的規定是(原所有權的)權利消滅規范。
2.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與實體屬性的無關性
在民法規范依其證明責任屬性為權利阻礙規范的情形,可否依文義解釋識別民法規范的權利阻礙屬性,不能一概而論。首先,在部分情形,由于民法教義學對抗辯事由或抗辯權的廣泛承認,針對當事人的權利請求,仍可依文義解釋確定其權利阻礙規范。其一,民事法律章節標題的措辭表明該章節下的法律規范在實體屬性上均系抗辯事由的規定,故而在證明責任屬性上均屬權利阻礙規范。例如,《侵權責任法》第三章“不承擔責任和減輕責任的情形”中有關不可抗力、正當防衛等抗辯事由的法律規范,均是(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權利阻礙規范。其二,法律條文的措辭表明其在實體屬性上系抗辯權的規定,故而在證明責任屬性上屬于權利阻礙規范。例如,《民法總則》第192條第1款系時效抗辯權的規定,屬于權利阻礙規范。
其次,在部分情形,雖然證明責任理論認為民法規范的文義與其證明責任屬性有關,但民法教義學認為,該文義與其實體屬性無關。這表明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與實體屬性之間全無聯系。所以,依文義解釋識別民法規范的權利阻礙屬性存在較多疑問。在證明責任理論上,有觀點認為,法律條文中的但書條款屬于權利阻礙規范。〔45〕同前注〔1〕,萊奧·羅森貝克書,第132頁;同前注〔1〕,漢斯·普維庭書,第390頁。例如,《德國民法典》第932條第1款第1句前半句是權利產生規范,即在無權處分時,若就所有權移轉達成合意且已交付,受讓人取得物的所有權;后半句的但書條款是權利阻礙規范,但受讓人惡意不在此限(即排除善意取得的構成)。
此種觀點的問題在于,其一,在證明責任理論上,如果立法者將條文改為不包括但書條款的表述方式,將改變該條文的證明責任屬性。例如,與《德國民法典》第932條第1款第1句的表述不同,我國《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第2句(善意取得規范)不包含但書條款,不涉及權利阻礙規范,該條文在整體上屬于權利產生規范。所以,依此種觀點的文義解釋不具有十足的確定性。其二,在民法教義學上,法律條文中的但書條款通常與其實體屬性無關。如果依善意取得支持受讓人的權利請求,那么法律條文中是否包含但書條款,均不影響善意取得規范的實體屬性,即對于《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第2句和《德國民法典》第932條第1款第1句,善意取得以受讓人善意為構成前提。因此,在此種情形,民法規范的實體屬性與證明責任屬性毫無關聯,依文義解釋不能有效識別其證明責任屬性。
綜上,在絕大部分情形,基于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與實體屬性的關聯性,依文義解釋可有效識別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獲得“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具體適用形式。文義解釋的有效性表明,依“誰主張誰舉證”規則所劃分的規范類型,具有堅實的民法教義學基礎,它必然與請求權基礎理論的規范類型具有一致性。僅在例外情形,基于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與實體屬性的無關性,依文義解釋不能有效識別民法規范的權利阻礙屬性。
(二)歷史解釋:民法規范被立法者賦予證明責任屬性的必要性
立法者制定法律規范借以表達其規范意圖和價值目標,探知立法者意思有助于民法規范的理解。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歷史解釋,是指借助立法文獻,探知民法規范被立法者賦予的證明責任屬性。
根據學說上廣泛認同的觀點,《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對每項民法規范均賦予了相關的證明責任屬性。〔46〕如有觀點認為,《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絕大部分法條中均考慮了證明責任分配問題,參見前注〔10〕,袁中華文。立法者甚至經常有意識地制定但書條款(如第932條第1款第1句),并賦予其權利阻礙的證明責任屬性。〔47〕參見[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頁;同前注〔1〕,萊奧·羅森貝克書,第133頁以下。另一方面,該觀點認為,絕大部分國家的立法者并未自覺地賦予民法規范以相應的證明責任屬性。如日本學界承認民法典的立法者忽視了證明責任分配;〔48〕參見[日]高橋宏志:《民事訴訟法: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林劍鋒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頁;陳榮宗:《舉證責任分配與民事程序法》第2冊,臺灣三民書局1979年版,第39頁。我國學界也認為,民事法律的制定多未考慮證明責任分配。〔49〕同前注〔17〕,陳剛書,第275~276頁。基于此種觀點,在探求“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具體適用形式時,僅可在德國法中進行歷史解釋。
但此種觀點并不妥當。一方面,此種觀點夸大了《德國民法典》立法者的工作,立法者并無必要對每項民法規范賦予證明責任屬性。依文義解釋便已知在絕大部分情形,民法規范的實體屬性決定了其證明責任屬性。如提存的實體屬性(債的消滅原因)直接決定了其證明責任屬性(權利消滅規范)。所以,在絕大部分情形,立法者僅須關注民法規范的實體屬性。〔50〕關于該問題的類似觀點,可參見吳澤勇:《規范說與侵權責任法第79條的適用》,《法學研究》2016年第5期;同前注〔6〕,胡學軍文。另一方面,此種觀點貶低了我國民事法律立法者的工作。同理,在絕大部分情形,基于民法規范的實體屬性和證明責任屬性的關聯性,立法者在依實體屬性制定民法規范后,無須多此一舉再賦予其證明責任屬性。
因此,在絕大部分情形,由于立法者無須關注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不論在德國法還是在我國法中,歷史解釋的適用范圍均十分有限。此項結論的原因還在于,既然在不存在證明責任特殊規則的所有情形,均適用“誰主張誰舉證”規則,那么立法者不必在這些情形下考慮證明責任分配問題。但最后仍須承認的是,在例外情形,立法者仍自覺地賦予民法規范相應的證明責任屬性。
(三)體系解釋:民法規范在法律的意義脈絡中的證明責任屬性
法律規范均處于特定的意義脈絡之中,其內涵應在此意義脈絡中被理解。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體系解釋,是指根據民法規范在意義脈絡中的位置和作用,以及與其他民法規范之間的相互關系,識別其證明責任屬性。實際上,“規范說”正是基于民法規范之間的相互關系而發現證明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它常因此被有失偏頗地稱作“規范構造說”。〔51〕同前注〔1〕,漢斯·普維庭書,第387~388頁;同上注,吳澤勇文。但這也表明規范之間的相互關系對于證明責任分配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體系解釋識別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同樣應區分不同情形分析。首先,在絕大部分情形,基于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與實體屬性的關聯性,不僅單個民法規范的實體屬性決定其證明責任屬性,而且多個民法規范依各自實體屬性所形成的相互關系,決定其依證明責任屬性將形成的相互關系。例如,《合同法》第159條第1句(出賣人的價金請求權)與《合同法》第91條第1項(清償導致合同權利消滅),前者是權利產生規范,后者是權利消滅規范。其次,在例外情形,基于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與實體屬性的無關性,多個民法規范依證明責任屬性所形成的相互關系,與其依實體屬性所形成的相互關系毫無聯系。例如,在證明責任屬性上,《德國民法典》第932條第1款第1句前半句是權利產生規范,后半句的但書條款是權利阻礙規范。但兩者之間的權利產生與阻礙的關系對民法教義學毫無意義。這是因為在實體屬性上,前半句和后半句共同組成有關善意取得的法律規范。
另需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意義脈絡中,同一民法規范具有不同的證明責任屬性。例如,在無權處分時,若受讓人提起所有權確認之訴,由于受讓人依善意取得才可獲得所有權,善意取得規范(《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后半句)是其權利產生規范;若原所有權人提起原物返還之訴,由于受讓人所主張的善意取得,將消滅原所有權人的原物返還請求權,善意取得規范是權利消滅規范。由此可知,善意取得規范在不同的意義脈絡中具有兩種不同的證明責任屬性。但即便如此,在兩種意義脈絡中,證明責任分配不發生變化,〔52〕從證明責任分配的視角,不同意義脈絡的形成取決于受讓人起訴還是原所有權人起訴。但偶然的訴訟當事人地位(原告或被告)不改變證明責任的分配。參見前注〔1〕,萊奧·羅森貝克書,第97頁。總是由受讓人對善意取得規范的要件事實承擔證明責任。
因此,在民法教義學上,各項民法規范依其實體屬性構建的規范體系,在學理上被稱為民法的外部體系。與此相對,在證明責任理論上,各項民法規范依其證明責任屬性,在彼此之間形成獨立的意義脈絡,構建起由權利產生、阻礙、消滅規范組成的規范體系。同樣地,在絕大部分情形,基于民法規范的實體屬性和證明責任屬性的關聯性,兩種規范體系的意義脈絡只是硬幣之兩面而已,具有相互對照的關系;在例外情形,基于民法規范的實體屬性和證明責任屬性的無關性,兩種規范體系的意義脈絡之間不具有對照性。
(四)目的解釋:民法規范的立法目的決定其證明責任屬性
法律規范皆有其立法目的,其解釋應秉持和貫徹該項目的。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目的解釋,是指以民法規范的立法目的為導向,識別其證明責任屬性。如前所述,在例外情形,基于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和實體屬性的無關性,借助文義解釋、歷史解釋和體系解釋識別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均存在疑義。對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疑義可借助目的解釋解決。〔53〕同前注〔1〕,漢斯·普維庭書,第458頁。對此仍以前例說明,對于善意取得中善意要件的證明責任分配,學說和實務曾長期存在疑義。第一種觀點認為,善意要件是權利產生規范的要件事實,由受讓人舉證。該觀點符合文義解釋、歷史解釋和體系解釋。第二種觀點認為,惡意要件是權利阻礙規范的要件事實,由原所有權人舉證。該觀點獲得《物權法解釋(一)》第15條第2款的贊同。在該條款制定生效之前,對于兩種觀點的分歧及其證明責任分配的疑義,惟有借助目的解釋才能判斷其優劣。
首先,善意取得規范的立法目的是保護交易安全。若無處分權人轉讓財產,要么受讓人支付價金而未能獲得物的所有權,要么原所有權人喪失物的所有權。為平衡二者之間的利益沖突,物權法規定若滿足特定條件,受讓人可依善意取得獲得物的所有權;否則,原所有權人可行使原物返還請求權。所以,善意取得規范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護動態的交易安全;〔54〕同前注〔29〕,王澤鑒書,第471頁、第475~476頁;同前注〔29〕,謝在全書,第272~273頁。原物返還請求權規范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護靜態的財產歸屬秩序。有觀點認為,善意取得規范的立法目的在于調和信賴保護與所有權保護。〔55〕同前注〔39〕,鄭金玉文;同前注〔31〕,吳澤勇文。該觀點應被理解為通過技術構成的設計,善意取得僅在技術構成范圍內保護受讓人的信賴;〔56〕同前注〔29〕,謝在全書,第274頁。在技術構成范圍之外,由于不成立善意取得,應保護原所有權人的權利。此處的所有權保護只是善意取得技術構成的反射效果。如善意取得僅適用于占有委托物,其反射效果是,由于占有脫離物不適用善意取得,〔57〕根據《物權法》第107條、第114條,占有脫離物原則上不適用善意取得。但有觀點認為,在例外情況,占有脫離物可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如果原所有權人自知道或應當知道受讓人有償受讓占有脫離物時起逾兩年未請求返還,受讓人有權拒絕返還。對此在理論上可解釋為此時發生了善意取得的效果。參見崔建遠:《物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頁。故而應保護所有權人的利益。
其次,善意取得規范的立法目的決定其證明責任屬性。〔58〕關于民法規范的立法目的與證明責任分配之間的關系,參見前注〔7〕,胡東海文。關于該問題的不同觀點認為,由善意取得制度的證明責任分配可推導出該制度的規范目的,參見前注〔31〕,吳澤勇文。但這被認為是一種“倒果為因”的觀點,參見前注〔31〕,徐滌宇文。其一,基于善意取得規范的立法目的,可借助目的解釋評價兩種觀點的優劣。由于第一種觀點要求“受讓人證明自己的善意”,而第二種觀點要求“原所有權人證明受讓人的惡意”,比較而言,第一種觀點加重受讓人的舉證負擔,而第二種觀點減輕受讓人舉證負擔,更符合善意取得規范的立法目的,有利于保護交易安全。其二,依善意取得規范的立法目的,可識別其證明責任屬性。第一種觀點將“受讓人善意”作為權利產生規范的構成要件,卻不符合善意取得規范的立法目的。第二種觀點將“受讓人惡意”作為一項獨立的權利阻礙規范構成要件,符合善意取得規范的立法目的。
因此,依目的解釋,《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后半句被區分為具有不同證明責任屬性的兩項法律規范:該條款的第1項是權利阻礙規范,其內容在于若受讓人惡意,則排除適用善意取得;該條款的其余部分是權利產生規范,其內容在于若符合第2項、第3項要件,則支持受讓人的權利請求。此項解釋結論中關于權利阻礙規范的部分與《物權法解釋(一)》第15條第2款完全一致。由此可知,在善意取得的證明責任分配問題上,司法解釋主動擔負起探求“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具體適用形式的重任。〔59〕此種情形還體現為《證據規定》第4條、第5條、第6條關于侵權案件、合同案件、勞動合同案件中證明責任規則的規定。最后需指出的是,由于權利阻礙規范不具有實體法上的意義,而僅在目的論上具有證明責任分配的意義,所以此項解釋結論不影響《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后半句在教義學上的實體屬性。
綜上,在探求“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具體適用形式時,可借助各種解釋方法識別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在絕大部分情形,基于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和實體屬性的關聯性,根據文義解釋、歷史解釋和體系解釋,可有效識別民法規范的證明責任屬性。這表明“誰主張誰舉證”規則與民法教義學之間并無實質的理論隔閡,僅存的差別只是二者選擇的理論術語不同。在例外情形,由于權利阻礙規范在民法教義學中不存在理論根基,導致民法規范的實體屬性和證明責任屬性之間欠缺關聯性,此時應借助目的解釋解決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疑義。由于民法規范的立法目的決定其證明責任屬性,所以在例外情形,“誰主張誰舉證”規則仍與民法教義學存在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