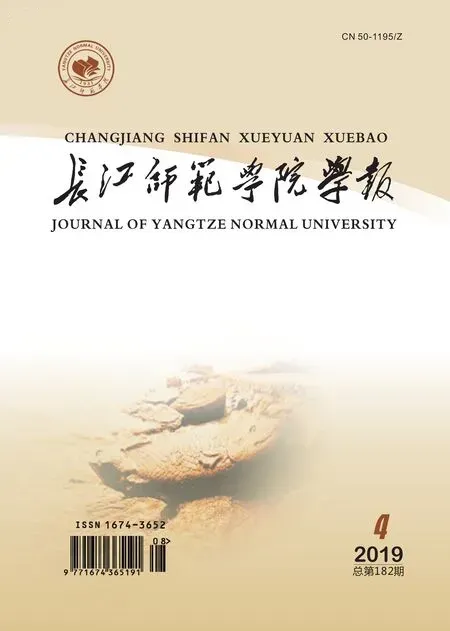試論汪曾祺的上海書寫及其情感轉(zhuǎn)變
孫 榮
(華東師范大學(xué) 中文系,上海 200241)
一、引言
《矮紙集》(1996)是汪曾祺眾多小說(shuō)選集中比較獨(dú)特的一部,因?yàn)樗峭粼饕宰髌匪鶎懙降牡胤綖楸尘皝?lái)進(jìn)行編排的創(chuàng)作集。在汪曾祺一生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中,寫高郵、北京和昆明的居多,而上海,據(jù)他個(gè)人所說(shuō),“住過(guò)兩年,只留下一篇《星期天》”[1]195。對(duì)于汪曾祺這篇小說(shuō),及其在上海兩年的經(jīng)歷(1946年7月—1948年2月),目前只有郜元寶作了較為詳細(xì)的討論,其他的研究則相對(duì)簡(jiǎn)略和零散。2017年,郜元寶發(fā)表了一系列關(guān)于汪曾祺與上海的研究文章,他從手法(“間離效果”)、結(jié)構(gòu)、人物描寫(白描、留白)、語(yǔ)言(滬語(yǔ))四個(gè)方面,對(duì)《星期天》進(jìn)行了全面分析[2];又將“汪曾祺文學(xué)生涯和上海的關(guān)系始末”(從20世紀(jì)40年代末到90年代)作了極為細(xì)致的爬梳[3];進(jìn)而他又探討了汪曾祺故里小說(shuō)中的上海敘事,并從中發(fā)現(xiàn)在汪曾祺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高郵與上海兩地存在著一種鮮明的雙向互動(dòng)關(guān)系[4]。可以說(shuō),郜元寶的這些研究成果為汪曾祺研究打開了一種新思路。本文以汪曾祺20世紀(jì)40年代和80年代的上海書寫為研究對(duì)象,通過(guò)分析其截然不同的情感狀態(tài)與創(chuàng)作風(fēng)格,探究其中的緣由,以期從一個(gè)新的視角來(lái)觀照汪曾祺與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某種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
二、1980年代回憶中的上海
1994年6月,由《鐘山》雜志社和德國(guó)歌德學(xué)院北京分院聯(lián)合舉辦的“94中國(guó)城市文學(xué)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在南京召開,汪曾祺受邀參會(huì)。在這次研討會(huì)上,汪曾祺闡發(fā)了他對(duì)城市文學(xué)的幾點(diǎn)見解:“第一,他認(rèn)為中國(guó)的城市文學(xué)仍處于萌芽狀態(tài)……茅盾的《子夜》不能代表城市文學(xué)。而是穆時(shí)英的《上海狐步舞》,以及一些狎邪小說(shuō)、妓院文學(xué),是城市的產(chǎn)物。第二,城市文學(xué)必然是新潮文學(xué),城市文學(xué)與先鋒派文學(xué)緊緊相連,二者不可分開。第三,城市文學(xué)還必然帶來(lái)文體上的變化。”[5]在提到城市文學(xué)的文體變化時(shí),他還特意以小說(shuō)《星期天》的最后一句來(lái)加以說(shuō)明,“失眠的霓虹燈明滅在上海的夜空”只能出現(xiàn)在城市的語(yǔ)匯之中。總而言之,城市產(chǎn)物、先鋒派文學(xué)、文體變化等構(gòu)成了汪曾祺對(duì)于城市文學(xué)的總體理解。那么汪曾祺在創(chuàng)作中又是如何落實(shí)其城市文學(xué)的理念呢?這就需要從他所舉例的《星期天》開始談起。
《星期天》寫于1983年7月,刊載于《上海文學(xué)》1983年第10期,是汪曾祺20世紀(jì)80年代唯一一篇全篇幅記敘上海的小說(shuō)。通篇雖然是上海的城市書寫,但卻延續(xù)了其20世紀(jì)80年代寫高郵、昆明等地的創(chuàng)作筆調(diào),即從環(huán)境到人物的白描,再到故事的簡(jiǎn)短敘述,是典型的以20世紀(jì)80年代的筆法去寫20世紀(jì)40年代往事的表現(xiàn)手法。
首先,汪曾祺在書寫上海時(shí)所選取的時(shí)空角度是獨(dú)特的。一方面,他聚焦于“致遠(yuǎn)中學(xué)”這樣一個(gè)相對(duì)封閉的里弄世界,從“校舍”“教學(xué)樓”到所謂“聽水齋”的木板棚,雖然簡(jiǎn)單而狹小,但卻成為各色人等相聚的重要活動(dòng)空間。另一方面,他將“星期天”別出心裁地貫穿于小說(shuō)始末,除了舞會(huì)故事的那個(gè)星期天之外,在占全文三分之二的人物白描中,汪曾祺多次提及“星期天”,透過(guò)不同星期天人物的活動(dòng)軌跡,看到的是各種鮮明的人物性格:校長(zhǎng)趙宗浚的星期天,體現(xiàn)的就是他為人漂亮、大方,他會(huì)“把幾個(gè)他鄉(xiāng)作客或有家不歸的單身教員拉到外面去玩玩。逛逛兆豐公園、法國(guó)公園,或到老城隍廟去走步九曲橋,坐坐茶館,吃兩塊油汆魷魚,喝一碗雞鴨血湯。凡有這種活動(dòng),多半是由他花錢請(qǐng)客”[6]99;體育教員謝霈,在生活上是個(gè)節(jié)儉的人,但因是個(gè)棋迷,格外舍得花錢請(qǐng)人下棋:“一到星期天,他就請(qǐng)兩個(gè)人來(lái)下棋,他看。有時(shí)能把上海的兩位圍棋國(guó)手請(qǐng)來(lái)……不僅預(yù)備了好茶好煙,還一定在不遠(yuǎn)一家廣東館訂幾個(gè)菜,等一局下完,請(qǐng)他們?nèi)バ∽谩ㄆ疱X不覺得肉痛”[6]104;再如寄住在學(xué)校里的李維廉,他的星期天“有時(shí)到叔叔家去,有時(shí)不去,躲在屋里溫習(xí)功課,寫信”[6]105,體現(xiàn)出他性格上的靦腆特質(zhì)。
其次,汪曾祺通過(guò)塑造一些神秘而又傳奇的小人物,所展現(xiàn)出來(lái)的是一個(gè)許多事都“蠻難講”的大上海。比如一個(gè)大字不識(shí)、只會(huì)傻笑的流浪漢,竟被培養(yǎng)成上海灘票友中數(shù)一數(shù)二的月琴高手;又如賣小黃魚的沈福根和首飾店學(xué)徒出身的史先生,竟成了致遠(yuǎn)中學(xué)的英文教員和史地教員;再如那個(gè)“有點(diǎn)神秘”的郝連都,“雖然住在一間暗無(wú)天日的房子里,睡在一張破舊的小鐵床上,出門時(shí)卻總是西裝筆挺,容光煥發(fā),像個(gè)大明星”[6]107,從早忙到晚,與白俄結(jié)交,喜聊政治,加之熱血爽朗的性格,因而在痛打美國(guó)兵之后被懷疑是共產(chǎn)黨。總而言之,這些神秘而又頗富傳奇色彩的小人物,不僅構(gòu)成了小說(shuō)中一道道亮麗的風(fēng)景線,更是給上海這座城市本身增添了幾分神秘而又傳奇的意味。大上海,這個(gè)風(fēng)云詭譎、變化多端之地,即使是看似平常的小人物,也有著令人驚訝的非凡經(jīng)歷!
再次,汪曾祺透過(guò)描述這些人物的生活方式,所塑造出來(lái)的是一個(gè)“中西合璧”的上海。這些生活方式既有現(xiàn)代的一面,比如逛公園(兆豐公園、法國(guó)公園)、看電影、泡咖啡館(DDS、卡夫卡司)、軋馬路、追讀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去健身房練拳擊、到馬場(chǎng)騎馬;也有傳統(tǒng)的一面,比如聽?wèi)颉⑾聡濉⒗佟R蚨凇缎瞧谔臁分校瑹o(wú)論是傳統(tǒng)還是現(xiàn)代的生活方式,它們顯然并不是對(duì)立沖突、不可調(diào)和的,而是可以交融在星期天的那幢“俱樂(lè)部”之中的。甚至在那個(gè)星期天的舞會(huì)中,人們可以品嘗著“中西并蓄”的雞尾酒(可樂(lè)兌白酒),也可以和著“雅俗雜陳”的音樂(lè)(古典、爵士、倫巴、地方流行曲),而正是這樣別具魅力的城市生活氣息,才使汪曾祺即使過(guò)了三十多年仍然記憶猶新。
最后,從城市文學(xué)書寫的實(shí)踐上來(lái)講,汪曾祺的滬語(yǔ)使用是一大特色,通篇都滿溢著上海話的濃重味道。比如“辰光”“銅鈿”“交關(guān)舒服”“嘸不啥”,這些滬語(yǔ)方言正如汪曾祺本人所說(shuō),是不能被代替的、是有勁的、是過(guò)癮的,正因如此才更能彰顯上海城市生活氣息的。而結(jié)尾那句“失眠的霓虹燈明滅在上海的夜空,這里那里,靜靜地燃燒著”[6]112-113,更是一種具有先鋒技巧的象征手法,是全文的點(diǎn)睛之筆。《星期天》所描寫的小人物,神秘而又頗負(fù)傳奇色彩,其中敘述的故事,生動(dòng)而又鮮活,他們是汪曾祺上海回憶中的那一抹抹亮點(diǎn),宛如上海夜空下的霓虹燈。總而言之,汪曾祺在1983年所創(chuàng)作的《星期天》中給我們呈現(xiàn)的,是一個(gè)凡事都“蠻難講”的上海,是一個(gè)“中西合璧”的上海,是一個(gè)充滿市民生活氣息的上海,更確切地說(shuō),停留在汪曾祺20世紀(jì)80年代回憶中的,是一個(gè)分外和諧的上海。
除《星期天》之外,在《讀廉價(jià)書·舊書攤》(1986)和《尋常茶話》(1989)中也都有一些汪曾祺對(duì)20世紀(jì)40年代上海生活的記敘。比如在《尋常茶話》中,他就寫道:“一九四六年冬,開明書店在綠楊村請(qǐng)客。飯后,我們到巴金先生家去喝功夫茶。幾個(gè)人圍著淺黃色的老式圓桌,看陳蘊(yùn)珍(蕭珊)‘表演’濯器、熾炭、注水、淋壺、篩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7]汪曾祺曾說(shuō):“小說(shuō)是回憶。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樣,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經(jīng)過(guò)反復(fù)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這樣才能形成小說(shuō)。”[8]透過(guò)這些回憶性文字,可以看出,汪曾祺所書寫的上海,是經(jīng)過(guò)反復(fù)沉淀才最終形成的。但是就是這樣一個(gè)和諧的、宛如在水晶球中的上海,卻總是讓人感覺缺點(diǎn)兒什么,也許需要重返20世紀(jì)40年代汪曾祺的生活及其創(chuàng)作中去尋找答案。
三、上海1947:嘈雜聲中的矛盾感覺
有人曾說(shuō),汪曾祺在早期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中,有一種“特別敏銳的感覺能力和很強(qiáng)的一種感覺意識(shí)……比較喜歡品味自己的感覺或琢磨別人的感覺,有時(shí)候干脆就沉浸在對(duì)世界的感覺之中”[9]。那么,20世紀(jì)40年代的汪曾祺對(duì)上海的感覺又是怎樣的呢?
我教書,教國(guó)文,我有時(shí)極為痛苦……一種攻不破的冷淡,絕對(duì)的不關(guān)心,我看到的是些為生活銷蝕模糊的老臉,不是十來(lái)歲的孩子!我從他們臉上看到了整個(gè)社會(huì)。我的腳下的地突然陷下去了!我無(wú)所攀泊,無(wú)所依據(jù),我的腦子成了灰蒙蒙的一片,我的聲音失了調(diào)節(jié),嗓子眼干燥,臉上發(fā)熱。我立這里,像一棵拙劣的匠人畫出來(lái)的樹。用力捏碎一只粉筆,我憤怒!
但是,我自己都奇怪,一邊批判著一邊恨恨的叫著,忽然傷狗似的大吼一聲,用力抓揪自己的頭發(fā),把手里紅筆用力摔去,平常決不會(huì)有的粗野態(tài)度這時(shí)都來(lái)了;這樣也有不少年了;(我的青春!)我仍然有耐心把一本本“作文”改了。有時(shí)候要大喜若狂,不能自禁了,當(dāng)垃圾堆中忽然發(fā)現(xiàn)了一點(diǎn)火星;即便只是一小段,三句,兩句;我趕緊附近它,我吹它,扇它,使它旺起來(lái),燒起來(lái)……自然,有時(shí)我是騙了自己,閃了一下的不是火,是一種甚么別的東西。這是一種嘲笑,使我的孤獨(dú)愈益深厚。[10]
1946年9月,經(jīng)李健吾介紹,汪曾祺得以在上海致遠(yuǎn)中學(xué)教書。這是一所私立中學(xué),在當(dāng)時(shí)的福煦路(Avenue Foch),校長(zhǎng)高宗靖(《星期天》中校長(zhǎng)趙宗浚的原型)曾是李健吾的學(xué)生。在這所學(xué)校里,汪曾祺負(fù)責(zé)教三個(gè)班的國(guó)文。但是從上面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感到,汪曾祺在致遠(yuǎn)中學(xué)的教書工作并不如意,當(dāng)他陷入一群無(wú)知的幼童當(dāng)中,他內(nèi)心的失落、苦悶以及孤獨(dú)感,只能借由內(nèi)心獨(dú)白的方式來(lái)表達(dá)!
黃梅天,總是那么悶。下雨。除了直接看到雨絲,你無(wú)法從別的東西上感覺到雨。聲音是也有的,但那實(shí)在不能算是“雨聲”。空氣中極潮濕,香煙都變得軟軟的,抽到嘴里也沒有味,但這與“雨意”這兩個(gè)字的意味差得可多么遠(yuǎn)。天空淡淡漠漠,毫無(wú)感情可言。雨下到地上,就變成了水。哪里是下什么雨,“下水”而已。[11]114-115
天倒是晴了。早晴,今天一定熱得很。——隔壁那個(gè)老頭子咳了整整一夜。——不得了,汽車都出來(lái)了,這個(gè)世界上充滿了汽車!還有,那時(shí)無(wú)線電的流行歌曲,已經(jīng)唱起來(lái)也!我想起那位乖戾的哲人叔本華的那一篇荒謬絕倫的文章:論嘈雜。[11]134
下雨天,雨點(diǎn)落在鐵皮頂上。乒乒乓乓,很好聽。聽著雨聲,我往往會(huì)想起一些很遙遠(yuǎn)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現(xiàn)在在上海。雨已經(jīng)停了,分明聽到一聲:“白糖蓮心粥——!”[6]105
工作并不如意的汪曾祺,生活也是苦悶的。《綠貓》這篇所謂的“怪”小說(shuō),正寫出了汪曾祺當(dāng)年茫然而又苦悶的情緒,其中透露出他對(duì)上海城市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又與20世紀(jì)80年代所創(chuàng)作的《星期天》大相徑庭。意識(shí)流或獨(dú)白等現(xiàn)代手法的運(yùn)用在筆者看來(lái)是十分巧妙的。一方面,它與人物對(duì)話能夠形成鮮明對(duì)比,從而突出人物的處境之窘迫,小說(shuō)中有這樣一句,“我還是敲門。剝啄一聲,我心歡喜。心里一陣子暖,我這才知道我為什要來(lái),我該來(lái)。門里至少有我一個(gè)朋友,在茫茫人海之中可以跟我談話”[11]115,偌大的上海,“我”的心事卻很難找人訴說(shuō),因而只能通過(guò)意識(shí)流或獨(dú)白的方式才能得以表達(dá)。另一方面,也正是通過(guò)意識(shí)流和獨(dú)白,我們才得以了解20世紀(jì)40年代的汪曾祺對(duì)于上海的城市感覺:“嘈雜”是他對(duì)上海的總體印象,從早到晚的汽車聲、咳嗽了整整一夜的隔壁老頭兒、叫賣聲、關(guān)窗聲,等等,這些聲音屬于現(xiàn)代都市,都讓他覺得厭惡,甚至成為打斷其意識(shí)、干擾其創(chuàng)作靈感的因素。更不用說(shuō)那《星期天》中被稱贊為“很好聽”的梅雨了,在汪曾祺筆下,從觸覺到聽覺,都是絲毫沒有“雨意”的,簡(jiǎn)直就是“毫無(wú)感情”的“下水”罷了。就是這樣充滿嘈雜聲的上海,哪里還是《星期天》中那個(gè)和諧的上海?!
我想起柏文章中提到的小院子,那時(shí)我們住在一起。想起那棵大白蘭花樹,現(xiàn)在正是開花的時(shí)候了。只有在云南那樣的氣候,白蘭花才能長(zhǎng)得那么大,罩滿了整個(gè)一天井。開花時(shí),在巷子里即聞到香氣,如招如喚。我們常搬了一張竹椅,在花樹下看書,聽老姑娘念經(jīng)敲磬。偶然一抬頭,綠葉縫隙間一朵白云正施施流過(guò),閑靜無(wú)比……這時(shí)候!我們多半已經(jīng)到了呈貢,騎馬下鄉(xiāng)了。道路都在栗樹園中穿過(guò),馬奔駛于闊大的綠葉之下,草頭全是露,風(fēng)真輕快。我們大聲呼喝,震動(dòng)群山。村邊或有個(gè)早起老人,或穿鮮紅顏色女孩子,聞聲回首,目送我們過(guò)去。此樂(lè)至不可忘。——一說(shuō),也十年了,好快!——而這里,就是汽車!汽車又一輛一輛地開出來(lái)了。[11]131
鄉(xiāng)村生活的景觀化描寫,有時(shí)只不過(guò)是大都市體驗(yàn)的投射性產(chǎn)物。嘈雜的上海使得汪曾祺對(duì)昆明的往昔生活充滿了眷戀之情,眷戀那個(gè)“平凡之地”的“平凡生活”。實(shí)際上,汪曾祺在昆明的生活并不比在上海好過(guò),他先后居住在民強(qiáng)巷和若園巷兩處,尤其是“在民強(qiáng)巷的生活,真是落拓到了極點(diǎn)”:房租是經(jīng)常拖欠;睡在一尺多寬的條幾上,因鄰窗,隔壁鴨子的叫聲吵得無(wú)法入睡;四季“都是擁絮而眠”;沒錢吃飯時(shí),或不起床,或把字典賣掉[12]。但辛酸的昆明生活在汪曾祺處于上海之時(shí),竟變得格外恬靜而又美好;而到了20世紀(jì)90年代,當(dāng)汪曾祺再次踏上作為第二故土的昆明之時(shí),在曾經(jīng)的居住之地近在跟前之時(shí),他竟不知道為什么不怎么想去了。因而,在汪曾祺20世紀(jì)40年代筆下的昆明,并非那個(gè)現(xiàn)實(shí)中的昆明,它常常成為其上海都市體驗(yàn)后的一種近似于烏托邦式的投射,這種投射只有放在作家上海城市體驗(yàn)的背景中,才能夠顯現(xiàn)出某種特別的意味,這是一種對(duì)城市絕望后燃起的把鄉(xiāng)村景觀化的希望!
融不進(jìn)的城市、回不去的鄉(xiāng)村,是當(dāng)時(shí)知識(shí)分子共有的矛盾感覺,汪曾祺也不例外。他在《牙疼》(1947)中這樣寫道:“上海既不是我的家鄉(xiāng),而且與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來(lái)干什么呢?你問(wèn)我,我問(wèn)誰(shuí)去!找得出的理由是來(lái)醫(yī)牙齒了。”[13]通過(guò)這樣一種“冷嘲”的方式,汪曾祺表達(dá)出了上海生活的無(wú)意義,上海這座充滿可能的大都市顯然沒有讓他展現(xiàn)出自身的價(jià)值,既然汪曾祺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是如此地不盡如人意,那么他為什么還要留在那里呢?或許我們可以從下面的這段文字中看出些眉目:
他(黃永玉——筆者注)說(shuō)他在上海遠(yuǎn)不比以前可以專心刻制。他想回鳳凰,不聲不響地刻幾年。我直覺地不贊成他回去。一個(gè)人回到鄉(xiāng)土,不知為什么就會(huì)霉下來(lái),窄小,可笑,固執(zhí)而自滿,而且死一樣的悲觀起來(lái)。回去短時(shí)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我自己也正跟那一點(diǎn)不大熱切的回鄉(xiāng)念頭商量,我也有點(diǎn)疲倦了,但我總要自己還有勇氣,在狗一樣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樣的事。[14]4
在去上海之前,汪曾祺的家人曾給他在家鄉(xiāng)找了一份銀行的工作,但是被他拒絕了。城市與鄉(xiāng)村,對(duì)于從事文學(xué)寫作的汪曾祺來(lái)說(shuō)區(qū)別甚大,即使在大都市中是“狗一樣的生活”,也絕不會(huì)妥協(xié)回鄉(xiāng)村發(fā)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汪曾祺的內(nèi)心深處,在城鄉(xiāng)生活的抉擇問(wèn)題上充滿了矛盾,而且肯定經(jīng)過(guò)一番痛苦的掙扎,遠(yuǎn)非信中所表現(xiàn)的那樣瀟灑。不管怎樣,正是抱著這份夢(mèng)想與堅(jiān)持,形單影只的汪曾祺最終還是選擇了繼續(xù)留在上海。
四、現(xiàn)代體驗(yàn)與當(dāng)代重塑:文學(xué)史視野下的跨年代書寫
直到此時(shí),我們才能清晰地看出,汪曾祺對(duì)上海的城市書寫,出現(xiàn)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狀態(tài)與創(chuàng)作風(fēng)格:一種是在20世紀(jì)40年代寫當(dāng)時(shí)的際遇,他對(duì)上海這座大都市,流露出一種雖厭惡但不得不留下的情緒,因而在其創(chuàng)作中,一方面是將昆明作了景觀化的描寫,另一方面是對(duì)城市生活的冷嘲;另一種則是20世紀(jì)80年代寫20世紀(jì)40年代,時(shí)隔三十多年,上海這座大都市,經(jīng)過(guò)沉淀,在其回憶式書寫中,變換成了分外和諧的模樣。究竟是什么緣由導(dǎo)致汪曾祺的上海書寫會(huì)如此迥然不同呢?如何從文學(xué)史的脈絡(luò)中去理解汪曾祺的這種轉(zhuǎn)變呢?這是值得我們進(jìn)一步思考與探討的問(wèn)題。
(一)“冷嘲”與無(wú)法規(guī)避的現(xiàn)代性體驗(yàn)
汪曾祺在《兩棲雜述》中曾寫道:
我追隨沈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兩句話。一句是:“要貼到人物來(lái)寫”……另外一句話是:“千萬(wàn)不要冷嘲”。這是對(duì)于生活的態(tài)度,也是寫作的態(tài)度。我在舊社會(huì),因?yàn)樯畹母F困和卑屈,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不滿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讀了一些西方的現(xiàn)代派的作品,對(duì)于生活形成一種帶有悲觀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沈先生發(fā)覺了這點(diǎn)……(他要求我)要對(duì)生活充滿熱情,即使在嚴(yán)酷的現(xiàn)實(shí)面前,也不能覺得“世事一無(wú)可取,也一無(wú)可為”。一個(gè)人總應(yīng)該用自己的工作,使這個(gè)世界更美好一些,給這個(gè)世界增加一點(diǎn)好東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喪失對(duì)于生活帶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喪失對(duì)于生活的愛……沈先生的這句話對(duì)我的影響很深。[15]
眾所周知,沈從文對(duì)汪曾祺的影響是巨大的,是一種從文格到人格的全面影響。汪曾祺曾在《沈從文的寂寞》《一個(gè)鄉(xiāng)下人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的抗議》等多篇文章中一再?gòu)?qiáng)調(diào),沈從文不是一個(gè)悲觀主義者,對(duì)于絕望、對(duì)于憤世嫉俗、對(duì)于玩世不恭,他最為反對(duì),“千萬(wàn)不要冷嘲”便成為了沈從文對(duì)汪曾祺的囑咐。然而,即便是沈從文自己,當(dāng)其身處于上海之時(shí)(1928—1931),也和汪曾祺一樣是二十多歲,“千萬(wàn)不要冷嘲”也是很難做到的。在那個(gè)階段他與程朱溪、王際真等人的通信中,沈從文認(rèn)為“上海住下來(lái)不好,離開了也覺得不好”[16],多次表達(dá)自己的性格在這里變得乖張、愛生氣,他認(rèn)為自己身處在一個(gè)無(wú)聊的社會(huì)與人生之中,甚至動(dòng)不動(dòng)就會(huì)有一番“冷嘲”。由此可以發(fā)現(xiàn),20世紀(jì)20年代的沈從文同樣是個(gè)尚未做到“千萬(wàn)不要冷嘲”的年輕人,而這種通過(guò)“冷嘲”的方式所表達(dá)出的矛盾感覺,簡(jiǎn)直與20世紀(jì)40年代的汪曾祺如出一轍!
相比沈從文,汪曾祺40年代在上海的際遇則更為凄苦。他連作為“文化工人”的“職業(yè)作家”都不是,更不用說(shuō)什么“天才作家”“多產(chǎn)作家”了。加之當(dāng)時(shí)上海時(shí)局的動(dòng)蕩、生活的顛簸,以及那個(gè)“烏煙瘴氣”“胡鬧”[14]2的上海文藝界對(duì)他的排斥與輕視,使汪曾祺在上海的兩年,無(wú)論生活還是創(chuàng)作,其實(shí)并不舒展自在。生活上的落魄與創(chuàng)作上的不順利,使得他對(duì)上海、對(duì)文壇,甚至對(duì)一切,都感到格格不入,但又不得不有一種依戀性的牽連,因疏離與依戀而產(chǎn)生的這種愛恨交織的矛盾感覺,同樣在汪曾祺這個(gè)青年人身上。
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這種對(duì)上海的矛盾感覺,這種在創(chuàng)作中所采用的“冷嘲”方式,是包含著特別意味的,這是一種無(wú)法規(guī)避的現(xiàn)代性體驗(yàn)的產(chǎn)物。在馬歇爾·伯曼看來(lái):“現(xiàn)代生活就是過(guò)一種充滿悖論和矛盾的生活……完全現(xiàn)代的生活是反現(xiàn)代的……最深刻的現(xiàn)代性必須通過(guò)嘲弄來(lái)表達(dá)自己。”[17]13“事實(shí)上,這種愛恨交織的自相矛盾的嘲諷,結(jié)果是人們對(duì)待現(xiàn)代城市的主要態(tài)度之一……說(shuō)話者愈是強(qiáng)烈地譴責(zé)這座城市,他就愈是生動(dòng)逼真地讓它再現(xiàn)出來(lái),使得它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愈是讓自己脫離它,他就愈深地與它融合在一起,他離開它就不能生活這一點(diǎn)就愈是清楚。”[17]262因而,只有在這個(gè)層面上去理解汪曾祺20世紀(jì)40年代上海書寫中的矛盾感覺與“冷嘲”手法,才不至于片面地否定其中的感傷情緒與悲觀色彩。我們也應(yīng)該更深刻地理解到,汪曾祺在上海這座現(xiàn)代大都市中所產(chǎn)生的矛盾感覺,是其最為即時(shí)地、也是最為真實(shí)地面對(duì)現(xiàn)代生活所產(chǎn)生的情緒反應(yīng)。這些作品放置在汪曾祺一生的創(chuàng)作中,也是難以復(fù)制的存在,這種具有現(xiàn)代特質(zhì)的矛盾感覺被剔除干凈,卻是汪曾祺20世紀(jì)80年代回憶式書寫的一種遺憾。
(二)當(dāng)代城市意識(shí)與“和諧”的美學(xué)情感
即便如此,汪曾祺20世紀(jì)80年代的上海書寫也并非是虛假的,它同樣顯露著逼真。在這逼真之中,汪曾祺注入了兩種呈現(xiàn)其個(gè)人風(fēng)格的元素,一是當(dāng)代意識(shí),一是美學(xué)觀念。在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理念中,小說(shuō)從根本上說(shuō)就是回憶式的。汪曾祺在這種回憶式書寫中,有意識(shí)地添加“當(dāng)代意識(shí)”元素,使過(guò)去的往事帶有當(dāng)下的精神內(nèi)核。1983年所創(chuàng)作的《星期天》也是如此,雖然寫的是20世紀(jì)40年代的上海,但從其創(chuàng)作背景上來(lái)看,卻極富當(dāng)代意味。
汪曾祺創(chuàng)作《星期天》的時(shí)段,正值全國(guó)開展城市化建設(shè)之際,文學(xué)當(dāng)然也是緊跟著時(shí)代的腳步。1983年8月21日至30日,由天津、北京、河北三省(市)文聯(lián)文藝?yán)碚撗芯渴遥ú浚┌l(fā)起的首屆城市文學(xué)理論筆會(huì)在北戴河召開。在這次會(huì)議上,與會(huì)人員“就城市文學(xué)的命題、歷史發(fā)展、基本特征、存在問(wèn)題及未來(lái)展望,進(jìn)行了初步的討論,并就某些問(wèn)題展開了爭(zhēng)鳴”[18],最為重要的是,城市文學(xué)的內(nèi)涵在此次會(huì)議上被首次提出來(lái),即“凡以城市人、城市生活為主,傳出城市風(fēng)味、城市之意識(shí)的作品,都可稱為城市文學(xué)”。此次筆會(huì)是有著轟動(dòng)效應(yīng)和導(dǎo)向意義的文學(xué)事件:一方面,它標(biāo)志著新時(shí)期城市文學(xué)開始興起,自覺的城市文學(xué)研究由此形成;另一方面,它對(duì)城市文學(xué)的發(fā)展遠(yuǎn)景及其與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相互作用,有著極高的期待與要求。在20世紀(jì)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多數(shù)作家仍以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意識(shí)來(lái)觀察城市,而以城市意識(shí)來(lái)藝術(shù)地表現(xiàn)城市的創(chuàng)作則十分匱乏。事實(shí)上,城市文學(xué)的產(chǎn)生順應(yīng)了時(shí)代的要求,也成為文學(xué)發(fā)展貼合現(xiàn)實(shí)的必然選擇。只有從城市文學(xué)的意義上來(lái)觀照汪曾祺的《星期天》,才能發(fā)現(xiàn)其產(chǎn)生并不突兀。雖然講述的是20世紀(jì)40年代的舊上海,但這是一篇屬于20世紀(jì)80年代的小說(shuō)。在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中,舊貌常因這種當(dāng)代意識(shí)煥發(fā)出新顏。
除此之外,汪曾祺曾指出,和諧是其創(chuàng)作上的追求,這正是一種“美學(xué)感情的需要”[19]:在他看來(lái),和諧的美學(xué)感情,并非是要原生態(tài)地呈現(xiàn)過(guò)去,而是需要將過(guò)去的一切健康化、美化、詩(shī)意化。晚年的汪曾祺,逐漸形成了比較成熟而又明凈的世界觀,看待事物的方式自然也發(fā)生了變化,對(duì)于那些感傷的過(guò)去,希望除凈其中或矛盾、或冷嘲的底色,轉(zhuǎn)變?yōu)楹椭C之美。汪曾祺在后期創(chuàng)作中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和諧美,實(shí)際上對(duì)于“京派”、對(duì)于他自身而言,都是一種超越:這是“從‘有意為之’轉(zhuǎn)入‘自然流露’的境界……是徹頭徹尾的和諧,是由內(nèi)及外的和諧,是人文一致的和諧”[20]。因而從美學(xué)感情的意義上來(lái)看,汪曾祺在《星期天》中的上海書寫,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不再僅僅是為了追尋那個(gè)20世紀(jì)40年代的舊上海,而是如同其在這一階段寫高郵、昆明等地一樣,都是通過(guò)和諧化的美學(xué)改造,來(lái)表達(dá)他作為“通俗抒情詩(shī)人”所獨(dú)有的個(gè)人氣質(zhì)和文化意識(shí)。在這里,我們不再去追究汪曾祺20世紀(jì)80年代的上海書寫是否符合過(guò)去的真實(shí),而是要在當(dāng)代意識(shí)與美學(xué)需要兩個(gè)層面上,來(lái)理解他是如何通過(guò)構(gòu)建過(guò)去來(lái)抵達(dá)和諧的境界。
(三)“回到民族現(xiàn)實(shí)主義”:多重資源的嫻熟融合
20世紀(jì)80年代末,黃子平曾撰文指出,汪曾祺20世紀(jì)80年代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具有“中介”的文學(xué)史意義:一方面他承接了由魯迅、廢名等人在二十世紀(jì)二三十年代所開創(chuàng)的“現(xiàn)代抒情小說(shuō)”傳統(tǒng),另一方面他將40年代的新文學(xué)、現(xiàn)代派文學(xué)傳統(tǒng)“帶到‘新時(shí)期文學(xué)’的面前。”[21]羅崗則在此基礎(chǔ)上撰文強(qiáng)調(diào),汪曾祺從20世紀(jì)40年代到80年代的這三十年并非是毫無(wú)意義的空白,他通過(guò)闡釋汪曾祺從“現(xiàn)代主義”到“民間文藝”的轉(zhuǎn)向,來(lái)說(shuō)明20世紀(jì)50到60年代的思想文化(甚至包括延安文藝)同樣是沉潛于其20世紀(jì)80年代創(chuàng)作中的內(nèi)在動(dòng)力,從而打通了汪曾祺從20世紀(jì)40年代到80年代創(chuàng)作上的斷裂[22]。同樣是討論汪曾祺20世紀(jì)80年代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前者發(fā)現(xiàn)了其對(duì)于20世紀(jì)40年代新文學(xué)、現(xiàn)代派文學(xué)傳統(tǒng)的承接,后者則是強(qiáng)調(diào)不應(yīng)忽略20世紀(jì)50到60年代民間文藝傳統(tǒng)對(duì)其深遠(yuǎn)影響,可以說(shuō)兩者都是從傳統(tǒng)文學(xué)資源的吸收與繼承上去談及這一創(chuàng)作階段的文學(xué)史淵源。
但是問(wèn)題也緊接而至,縱觀汪曾祺20世紀(jì)80到90年代的創(chuàng)作及觀念,似乎與任何一個(gè)文學(xué)傳統(tǒng)脈絡(luò),無(wú)論是現(xiàn)代派也好,還是民間文藝也好,都無(wú)法做到完完全全的匹配:有人認(rèn)為汪曾祺這一階段屬于現(xiàn)代派的脈絡(luò),他卻一再?gòu)?qiáng)調(diào)民間文化的重要性;有人認(rèn)為他這一階段屬于民間文藝的脈絡(luò),但他在1994年提出的城市文學(xué)理念卻是如此的現(xiàn)代。問(wèn)題的關(guān)鍵點(diǎn)就在于,為何汪曾祺對(duì)于城市文學(xué)的內(nèi)容和形式在其強(qiáng)調(diào)民間文化重要性的時(shí)段,又加入現(xiàn)代派的角度。
這一問(wèn)題自然還是要返回新時(shí)期城市文學(xué)的發(fā)展脈絡(luò)上來(lái)談。自1983年開始興起的城市文學(xué),到20世紀(jì)90年代初,一直是從題材角度去理解的,反映和針對(duì)的始終是“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而到了20世紀(jì)90年代之后,城市文學(xué)(有些批評(píng)家開始改稱為“都市文學(xué)”)則漸漸受到西方現(xiàn)代性理論的強(qiáng)烈滲透,轉(zhuǎn)向有意識(shí)地展現(xiàn)“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之間的撕裂與對(duì)立,強(qiáng)調(diào)城市是現(xiàn)代文明的產(chǎn)物,城市文學(xué)要以現(xiàn)代意識(shí)為內(nèi)核,并且應(yīng)具有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形式。此時(shí)的城市文學(xué)的概念,早已迥異于20世紀(jì)80年代的標(biāo)準(zhǔn),其討論的焦點(diǎn)是要剔除與傳統(tǒng)觀念緊密聯(lián)系的“市井小說(shuō)”,并將城市文學(xué)逐漸納入到文學(xué)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軌道之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4年對(duì)于城市文學(xué)來(lái)說(shuō)是熱鬧非凡的一年,當(dāng)代文學(xué)迎來(lái)“新”字號(hào)的高潮,各個(gè)刊物都鮮明地豎起了“新”的旗幟,展現(xiàn)出它們“新”的理想與追求,以適應(yīng)時(shí)代和文學(xué)發(fā)展的需要。比如《上海文學(xué)》的“新市民小說(shuō)”、《當(dāng)代文壇》的“新都市小說(shuō)”、《鐘山》的“新狀態(tài)小說(shuō)”等,而這一切的“新”都是圍繞著城市文學(xué)緊密開展的。對(duì)于這番當(dāng)代文壇的“新”景象,汪曾祺則認(rèn)為,“關(guān)于方法,我覺得有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主義、一個(gè)浪漫主義,頂多再有一個(gè)現(xiàn)代主義,就夠了。有人提出‘新寫實(shí)’、‘新狀態(tài)’、‘后現(xiàn)代’,花樣翻新,使人眼花繚亂。我覺得寫小說(shuō)首先得把文章寫通。文字不通,疙里疙瘩,總是使人不舒服。搞這個(gè)主義,那個(gè)主義,讓人覺得是在那里蒙事,或者如北京人所說(shuō)‘耍花活’,不足取。”[1]196由此觀之,汪曾祺雖不贊成各式各樣的“新”,但傾向于以現(xiàn)代主義來(lái)概括城市文學(xué),究其緣由,一方面在于他個(gè)人對(duì)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法的理解,另一方面則在于城市文學(xué)發(fā)展現(xiàn)狀對(duì)其創(chuàng)作理念的深刻影響。
20世紀(jì)80到90年代的汪曾祺在創(chuàng)作上“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現(xiàn)實(shí)主義、回到民族傳統(tǒng)……這種現(xiàn)實(shí)主義是容納各種流派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這種民族傳統(tǒng)是對(duì)外來(lái)文化的精華兼收并蓄的民族傳統(tǒng)。路子應(yīng)當(dāng)更寬一些”[23]。無(wú)論是現(xiàn)代主義,還是民間文藝,在汪曾祺這里,并非如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路徑一樣,只是一種簡(jiǎn)單的壓抑與被壓抑的關(guān)系,或者是斷裂與承接的關(guān)系,而是體現(xiàn)出一種非常復(fù)雜的內(nèi)化與融合,尤其是他對(duì)于多種文學(xué)因素的交互運(yùn)用,已并非是簡(jiǎn)單的現(xiàn)代主義轉(zhuǎn)向所能概括。總而言之,此時(shí)的汪曾祺已經(jīng)能夠在“民族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旗幟下,將不同的文學(xué)傳統(tǒng)以及迥異的創(chuàng)作手法嫻熟地運(yùn)用與融合,能夠與其個(gè)人氣質(zhì)和文化意識(shí)融為一體而未見絲毫的生硬與突兀。
五、結(jié)語(yǔ)
顯而易見,汪曾祺的上海書寫在不同年代出現(xiàn)了截然不同的情感狀態(tài)與創(chuàng)作風(fēng)格,探究其緣由,則發(fā)現(xiàn)個(gè)中意味:一方面,20世紀(jì)40年代通過(guò)“冷嘲”的方式所呈現(xiàn)的處于矛盾感覺之中的上海,屬于無(wú)法規(guī)避的現(xiàn)代性體驗(yàn)的產(chǎn)物,是其最為及時(shí)、也是最為真實(shí)的情感反映與書寫方式;另一方面,20世紀(jì)80年代通過(guò)“回憶”的方式所呈現(xiàn)的和諧的上海,則是其有意識(shí)地融合“當(dāng)代意識(shí)”和“美學(xué)感情”,將過(guò)去進(jìn)行重塑的結(jié)果,是最能夠顯示其后期個(gè)人氣質(zhì)和文化意識(shí)的書寫方式。更為重要的是,汪曾祺的上海書寫,尤其是其后期的上海書寫,只有被放置在其對(duì)于傳統(tǒng)文學(xué)資源的吸收與繼承上,放置在文學(xué)史的脈絡(luò)中,才能彰顯其意義,作為一個(gè)能夠?qū)⒏鞣N傳統(tǒng)文學(xué)資源嫻熟融合的創(chuàng)作大家,汪曾祺無(wú)疑具有了典范意義,從而也能夠?yàn)楦鄬W(xué)者關(guān)于跨越現(xiàn)當(dāng)代作家的轉(zhuǎn)向軌跡研究提供參考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