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一顆心
【英】斯蒂芬·韋斯塔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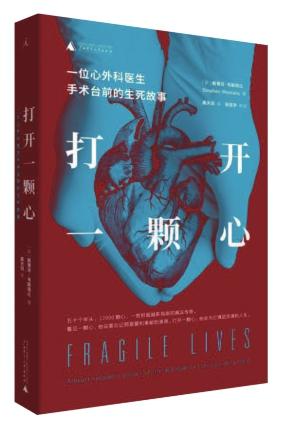
【內容簡介】
“我經手過12000顆心臟。”
工薪家庭的窮小子,幼年時被醫學紀錄片鼓舞,也被親人的離世刺痛,終于將自己歷練成一名杰出的心外科醫生。在展現心胸外科手術的神乎其技之余,作者也在書中借病癥、病患和自己的業務游歷,揭示了人世百態,展現了一名外科醫生眼中所見的悲傷與愛,以及對醫療制度、倫理和醫學教育的反思。
①
那是在1987年的沙特阿拉伯王國。我當時年輕無畏,自認為英勇無敵,自信得膨脹。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一家富有聲望的沙特心臟中心,服務整個阿拉伯地區的病人。他們的主刀醫生請了三個月的病假,想找個臨時代理,要求能同時做先天性和成人心臟病手術——這種人屬于極端珍稀品種。我當時并不在意,但第二天就來了興趣。三天之后我跳上了飛機。
當時正值主馬達·阿色尼月,是中東的“第二個干燥月”。我從來沒有體驗過這樣的炎熱,猛烈的熱氣從不停歇,名為“夏馬”的熱風卷著沙子吹進城里。不過那家心臟中心還是很好的。我的醫生同事匯集了各路人才,有的是在海外受訓過的沙特男人,有的是為獲得經驗從大醫學中心輪轉過來的美國人,還有的是從歐洲和大洋洲組團來掙大錢的醫生。
護理就很不同了。沙特婦女不做護士,因為沙特人對這門職業懷疑而不敬,沙特文化也禁止婦女從事護理,因為干這行需要與異性混在一起。因此這里的女護士都是外國人,她們大多只簽一兩年的合同,在這里享受免費食宿,不用繳稅,等存夠家鄉的房貸就會離開。她們不能開車,乘公車時只能坐在后排,在公共場合要把身體完全遮起來。
這個新的工作環境讓我很感興趣:宣禮塔上反復傳來禮拜的號召,醫院里總有一股檀木、焚香和琥珀混合的誘人氣味,阿拉伯咖啡烘烤在平底鍋上,或是和豆蔻一起煮沸。這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我告誡自己絕不要越過界限——這是他們的文化,他們的規矩,違反者會受到嚴厲懲罰。
這也給了我獨一無二的機會,可以接觸任何你能想到的先天性心臟異常病例。大量的年輕病人因為風濕性心臟病從遙遠的鄉鎮轉到這里治療,他們大多接觸不到西方習以為常的抗凝療法或藥物。
這里的農村醫療還停留在中世紀水平,我們在治療中不得不有所創新和發揮,修補他們的心臟瓣膜,而不是用人工材料替換。我現在還記得當時的想法:每一個心臟外科醫生都應該去那里歷練歷練。
一天早晨,一位年輕聰明的小兒心內科醫生來手術室找我,他來自梅奧診所,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座世界聞名的醫學中心。他的開場白是:“我有個有趣的病例,你想看看嗎?你以前肯定沒見過這樣。”緊接著又說:“可惜呀,你恐怕也做不了什么。”還沒等看過病例,我就決心證明他想錯了,因為對外科醫生來說,罕見的病例永遠是挑戰。
他把X光片貼上燈箱。這是一張普通的胸腔X光片,上面的心臟呈現為灰色的陰影,但在受過專門教育的人看來,它仍能透露關鍵信息。很明顯,這是一個幼童,他的心臟擴大,而且長到了胸腔錯誤的一邊。這是一種罕見的異常,稱為“右位心”——正常心臟都位于胸腔左側,他的卻相反。另外,肺部也有積液。不過單單右位心并不會造成心力衰竭。他肯定還有別的毛病。
②
這個熱情的梅奧心內科醫生是在考驗我。他給這個十八個月大的男孩做過心導管檢查,已經知道病因了。我提了一個富有洞見的猜想,賣弄說:“以這個地區來說,可能是魯登巴赫綜合征。”也就是說,這顆右位心的左右心房之間有一個大孔,二尖瓣也因為風濕熱而變得狹窄,這是一個罕見的組合,使大量血液灌入肺部,身體的其他部分卻處于缺血狀態。我贏得了梅奧男的敬意,但我的猜測還差了一點。
他又提出帶我去心導管室看血管造影片(在血流中注入顯視劑,再用X光片動畫揭示解剖結構)。這時我已經煩透了他的測試,但還是跟著去了。在病人的左心室里,主動脈瓣的下方有一個巨大的團塊,位置十分兇險,幾乎截斷了通向全身的血流。我看出這是一個腫瘤,不管它是良性還是惡性,這個嬰兒都活不了多長時間。我能摘掉它嗎?
我從來沒見過有人在右位心上動手術。做過這類手術的年輕外科醫生很少,多數永遠不會做。不過我很了解兒童心臟腫瘤。我甚至就這個課題在美國發表過論文,這位小兒心內科醫生也讀過。在這個領域,我算是沙特境內的專家。
嬰兒身上最常見的腫瘤是反常的心肌和纖維組織構成的良性團塊,稱為“橫紋肌瘤”。這往往會導致腦部異常,引發癲癇。沒有人知道這可憐的孩子是否發作過癲癇,但是我們都知道這顆梗阻的心臟正在要他的命。我問了男孩的年齡,還有他的父母知不知道他的病情有多嚴重。接著,他的悲慘故事展開了。
男孩和他年輕的母親是紅十字會在阿曼和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交界處發現的。在炙熱的沙漠中,母子倆瘦骨嶙峋,渾身脫水,已經快不行了。看樣子是母親背著兒子穿越了也門的沙漠和群山,瘋狂地尋找醫學救助。紅十字會用直升機將他們送到阿曼首都馬斯喀特的一家軍隊醫院,在那里,他們發現她仍在設法為孩子哺乳。她的奶水已經干了,她也沒有別的東西喂養兒子。男孩通過靜脈輸液補充了水分后,開始呼吸困難,診斷結果是心力衰竭。他母親也因為盆腔感染而嚴重腹痛,高燒。
她來自一個法外之地。她在那里受過強暴、虐待和殘害。而且她是黑人,不是阿拉伯人。紅十字會懷疑她是在索馬里遭人綁架,然后被帶到亞丁灣對岸賣作奴隸。但是由于一個不尋常的原因,他們也沒法確定她的經歷:這個女人從不說話,一個字也不說。她也沒有顯出什么情緒,即使在疼痛中也沒有。
阿曼的醫生看了男孩的胸腔X光片,診斷出右位心和心力衰竭,然后就把他轉到了我所在的醫院。梅奧男想看看我能不能施展魔法把他醫好。我知道梅奧診所有一位優秀的小兒心臟外科醫生,于是我試探性地問這位同事丹尼爾森大夫會怎么做。
“應該會做手術吧。”他說,“已經談不上有什么手術風險了,不做的話只會越來越嚴重。”我料到他會這么說。
“好吧,我盡量試試看。”我說,“至少要弄清楚這是什么類型的腫瘤。”
關于這個孩子,我還需要知道些什么?他不僅心臟長在胸腔里錯誤的一邊,就連腹腔器官也全部調了個兒。這種情況我們稱為“內臟反位”。他的肝臟位于腹腔的左上部分,胃和脾臟則位于右邊。更棘手的是,他的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間有一個大孔,因此從身體和肺靜脈回流的血液大量混合。這意味著通過動脈流向他身體的血液含氧量低于正常水平。要不是因為皮膚黝黑,他或許已經獲診為藍嬰綜合征,也就是動脈中混入了靜脈血。真是復雜的病情,就連醫生都覺得頭疼。
③
在這里錢不是問題。我們有最先進的超聲心動圖儀,這在當時還是激動人心的新技術。設備使用的是偵測潛艇的那種超聲波,一名熟練的操作員能用它繪出心臟內部的清晰圖像,并測出梗阻區域的壓力梯度。我在他那小小的左心室里看見了一幅清晰的腫瘤圖像,它的樣子光滑圓潤,就像一枚矮腳雞的蛋,我敢肯定它是良性的,只要摘除,就不會再長出來。
我的計劃是消除梗阻,關閉心臟上的孔,從而恢復它的正常生理機能。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理論上簡單直接,但是對一顆前后顛倒、長在胸腔錯誤一側的心臟來說卻相當費力。我不想中間出什么岔子,于是做了每次境況艱難時都會做的事——我開始繪制詳細的解剖圖。
這臺手術做得成嗎?我不知道,但我們非試不可。就算不能把腫瘤完全切除,對他也依然有幫助;但如果開胸后發現那是一顆罕見的惡性腫瘤,那他的前景就很不妙了。不過我和梅奧男都確信這是一顆良性的橫紋肌瘤。
該和男孩還有他母親見面了。梅奧男帶我去了兒科加護病房,男孩還插著鼻飼管,他很不喜歡。他母親就在兒子小床邊的一只墊子上盤腿坐著,她日夜守護在兒子身邊,始終不離。
看到我們走近,她站了起來。她的樣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美得令我震驚,像極了大衛·鮑伊的遺孀,那個叫伊曼的模特。她有一頭烏黑的長直發,消瘦的手臂環抱在胸前。紅十字會已經證實了她來自索馬里,是一名基督徒,所以她的頭發并沒有包起來。她手指纖長,握緊包裹兒子的襁褓。這塊珍貴的破布卷替男孩遮擋熾熱的陽光,在沙漠的寒夜里給他保暖。一根臍帶似的輸液管從襁褓中伸出,連到輸液架和一只吊瓶上,吊瓶里盛著乳白色的溶液,里面注滿葡萄糖、氨基酸、維生素和礦物質,好讓他細小的骨骼上重新長出肉來。
她的目光轉向了我這個陌生人,這個她聽人說起過的心臟外科醫生。她的腦袋微微后仰,想要保持鎮靜,但頸底還是沁出一粒汗珠,蜿蜒地流到胸骨上窩。她焦慮起來,腎上腺素正在涌動。
我試著用阿拉伯語和她溝通:“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她沒說話,只是望著地板。帶著賣弄的心情,我繼續問道:“你懂阿拉伯語嗎?”接著是:“你是哪里人?”她還是不作聲。我走投無路了,終于問道:“你會說英語嗎?我從英國來。”

這時她抬起頭來,大睜著眼睛,我知道她聽懂了。她張開嘴唇,但還是說不出話,原來她是個啞巴。邊上的梅奧男也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他沒想到我還有這項語言技能;他不知道的是,我幾乎只會說這幾句阿拉伯語。這位母親似乎很感謝我的努力,她的肩膀放了下來,心里松開了。我想對她表達善意,想抓起她的手安慰她,但是在這個環境里,我做不到。
我示意要檢查一下男孩,她同意了,只要孩子還抱在她手里就行。當她掀開亞麻的襁褓,我不由吃了一驚。這孩子瘦得皮包骨頭,肋骨一根根地凸在外面。他身上幾乎沒有一點脂肪,在胸壁下方,我能看見那顆古怪的心臟在搏動。他呼吸很快,好克服肺部的僵硬;突起的腹部注滿了液體,擴大的肝臟赫然顯現在與常人不同的一邊。他的膚色與母親不同,我猜想他父親是個阿拉伯人。他那深橄欖色的皮膚上蓋了一層奇怪的皮疹,我似乎在他眼中看見了恐懼。
男孩母親愛惜地將亞麻布蓋回他臉上。她在這世上已經一無所有,除了這個男孩和幾片破布、幾枚戒指。我心中不由升起了對母子倆的一股憐憫。我的身份是外科醫生,但此時的我卻被吸入了絕望的漩渦,客觀和冷靜都消失了。
(張迪摘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打開一顆心》)
鏈接:
【作者簡介】斯蒂芬·韋斯塔比(1948— ),英國牛津約翰·拉德克利夫醫院主任醫生,世界一流的心外科手術專家和人工心臟專家。參與過1萬多臺心外科手術,其中有很多極為精彩、驚險甚至開創性的手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