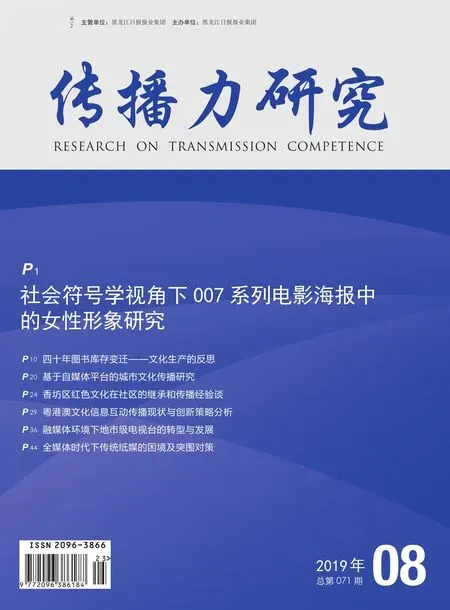建構、認同與消費:亞文化節目的符號學解讀
——以《這!就是街舞》為例
余琪 田思夢 華僑大學
近年來,視頻網站積極探索自制內容,一系列的網絡綜藝節目得以誕生發展。2018年伊始,眾多視頻網站又紛紛瞄準青年亞文化這一領域,制作出一系列諸如《中國有嘻哈》《奇葩說》《中國新說唱》《這!就是街舞》等優秀亞文化綜藝節目。而在眾多節目中,《這!就是街舞》無疑是最成功的節目之一。該節目截至目前兩季節目已有超25 億的點擊量,成為了毫無爭議的現象級爆款網綜。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我國的消費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正如鮑德里亞[1]所指出:“現代社會的消費實際上已變成了符號化的物品、符號化的服務中所蘊含的‘意義’的消費。”由此,我們當今的社會已經變成了一個被符號消費所包裹的社會。而在當下,除了經濟的發展,消費主義的發展也與大眾傳媒存在著緊密的聯系,作為大眾傳媒的重要類型,很大程度上來說,新媒體已經逐漸成為了消費主義最重要的建構者與推行者。[2]
根據筆者進行文獻綜述發現,已有的對亞文化網絡綜藝節目的研究較多集中于對其節目制作和宣傳營銷角度進行探討,而較少從觀眾的角度探討怎樣影響觀眾并引發后續的符號消費行為的。在當今傳播語境下,引入符號學及觀眾的角度是極其必要的。因此,本文嘗試引入“自我認同”及“符號消費”理論,從符號學的角度對亞文化網絡綜藝進行解讀。
一、符號系統的建構
對于商品的自我認同以及符號消費要以商品的符號生產和建構為前提,商品的符號意義世界構成了身份認同的語境[3]。網絡綜藝節目作為一種重要的媒介文化商品也是如此,綜藝節目的編碼構成了觀眾自我認同的語境。本文結合《這!就是街舞》節目文本,試圖從節目模式編碼、內容編碼、影像編碼、人物編碼這四個方面對節目的符號元素進行解讀。
(一)模式編碼:街舞規則的媒介建構
伯明翰學派是研究亞文化的重要學派,其強調亞文化的關鍵就在于“風格”,風格“是亞文化群體的‘第二肌膚’和‘圖騰’”,也是我們了解亞文化形成的重要解讀路徑之一。[4]作為一種青年亞文化,街舞也有其鮮明的風格,街舞作為一種以青年為主體的大眾文化范式,從產生之初就帶有鮮明的反抗烙印,其精神實質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自由。而為了表達自由,街舞形成了眾多特有的比賽規則。
回到節目本身,我們會發現《這!就是街舞》節目對街舞的特有規則和儀式進行了幾乎原始的復現。首先,在賽制設計上,眾多街舞規則被完整地移植到節目中。街舞比賽分為個人、齊舞、battle 三個環節,在三個環節中又穿插著callout(不服挑戰)、cypher(圍圈跳舞)、freestyle(即興表演)三種挑戰形式。而在《這!就是街舞》中,海選時,規則為每位舞者的個人秀;在100 強進49 強時,舞者根據舞種進行組隊pk,也就是齊舞秀;在個人秀與齊舞秀中待定的舞者可對已晉級的舞者發起上述三種挑戰形式。其次,在進行出戰選擇和投票時,節目組分別采用了“轉酒瓶子”以及“扔毛巾”的方式。這兩種方式均來源于美國街舞文化,都體現了街舞的“自由、公平”精神。
(二)影像編碼:媒體奇觀的視覺建構
“媒體奇觀”這個概念是由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所提出,媒體奇觀是指“能體現當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生活方式,并將當代社會中的沖突和其解決方式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5]。在我們當今社會中,影像作為一種極其重要的傳播介質,用其生動逼真的音視頻形式,在節目中構建出眾多媒體奇觀,而這些奇觀又構建出一個精彩的街舞亞文化世界,讓專業舞者及普通觀眾都能產生認同感。
作為一檔亞文化網絡自制綜藝,《這!就是街舞》在節目中的一開始就展現出了處處有著亞文化元素的舞臺設計。在《這!就是街舞》當中,舞臺不再是聚焦的傳統競技臺,而是轉換為具有街舞特色的四條街道。這四條街道分別為充滿復古風格的上海石窟門街、鐵門林立的廣州騎樓街、紅墻大燈的老北京街、賽博朋克風的極限未來街。這四條街道成放射狀展開,中心聚集點為節目主舞臺,主舞臺也獨具特色,為未來都市風與傳統中國風的嫁接。這為舞者們表演加分的同時,更讓觀眾感受到了街舞亞文化的風格符號。
(三)內容編碼:專業知識的符號建構
“亞文化”,是相對于社會主流文化的邊緣文化,其受眾規模相對較小。街舞作為一種亞文化,對于普通大眾來說不甚了解,所以在觀眾觀看的過程中極易出現理解困難的問題。而要想讓節目與觀眾之間產生“共同的意義空間”就必然要把專業的街舞知識進行普及。在《這!就是街舞》中,大量的街舞專業知識則變成了一系列具象化的符號,節目組用觀眾能快速易懂的符號指代專業的街舞知識,使得街舞文化易于被理解和接受,節目也顯得更加具有趣味性。
節目中對專業的街舞表演闡釋則是運用字幕這一方式,但這種字幕提示并不是簡單的街舞知識的傳達,而是在節目組對該動作進行重新編碼才得以傳達。如街舞中一個經典動作Scooba(地機),在選手進行舞蹈展示時,節目組將這一專業舞蹈動作進行重新編碼,用花字幕的形式呈現出“咖啡研磨機”的注解。Scooba(地機)的動作為一個腳往旁邊踢半圈以后另一個腳也畫半圈,這一動作與“咖啡研磨機”的形狀和工作狀態相似,于是節目組就用通俗易懂的符號指代了專業的舞蹈動作。類似的還有海豚下潛(Bankhead bounce)、彈簧扭轉(Tidal wave)等。
除此之外,節目還增設了“街舞課堂”板塊。這一板塊主要是舞種科普,節目對舞種進行科普時也是將其符號化,用具體的舞者和舞者裝扮來代指某一種舞蹈。如節目組直接將典型的locking 選手葉音來指代這一舞種,讓觀眾易于理解且具有記憶點。
(四)人物編碼:參賽選手的形象建構
麥尚文曾談到:“人物價值表達及信仰維系的實現,取決于公眾‘認同’所能達到的程度。任何‘認同’都是以特定社會中的個人或群體為參照而展開。”[6]從中可見,若想獲得觀眾對節目的認同,人物的編碼顯得尤為重要。
在《這!就是街舞》中,為了獲得觀眾的認同,節目組對人物的建構主要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選手的專業化。在《這!就是街舞》兩季節目中,選手由街舞圈的眾多“重量級”專業舞者構成。如第一季中的胡浩亮,是中國街舞委員會常務理事;選手楊文昊為全美街舞大賽popping battle冠軍,類似的還有選手韓宇、謝文珂。這些人物都是讓“圈內人”高度認同的人物,而這些人物的精彩表現也給廣大的觀眾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是選手的個性化。《這!就是街舞》節目對舞者們各自的性格、舞種和人生經歷進行總結,并概括出每個人的人物標簽。如在“街舞復活榜”上擁有超高人氣的陳杰,他的標簽是“公主阿K”,原因就是其臺上臺下判若兩人,臺下是小公主,臺上舞蹈爆發力如同“猛獸”。這樣的標簽引得眾多網友討論,接地氣的同時更突顯出舞者性格的差異化、獨特化。除此之外,“團寵小可愛”“瘋狂大魔王”“靈活騷胖子”等選手標簽也比賽中被反復提及、強化。建構這樣個性化的選手則與街舞文化的“自由”“個性解放”等訴求符合,從而更能獲得觀眾的認同。
二、互動:自我認同與符號消費
(一)觀眾對節目的自我認同
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最早由心理學家Erikson 提出,指個體在職業、政治、宗教、價值觀等方面的自我評價和自我定位。[7]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則進一步發展,他認為自我認同是對共同身份的建構,是依據個人經歷所反思和理解到的自我。[8]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自我認同與以往的個人經歷緊密相關。
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指出,“以大眾的解讀方式而言,文本的價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而非它的本質或美學價值,大眾的辨識力旨在識別和篩選文本與日常生活之間相關的切入點”。[9]“相關性”則概括出了節目觀眾在觀看活動中意義實現的原動力,對于節目來說,實現“相關性”的重要途徑就是將節目與觀眾以往的個人經歷進行連接,而這樣的連接則能進一步實現觀眾對節目的自我認同。
網絡綜藝節目作為一種媒體形態,在觀眾與互聯網視頻平臺之間搭起一個互動與認同的橋梁。在觀眾具有決定權的情況下,認同的順利完成,需要生產平臺以觀眾為導向進行“相關性”的符號建構。
回到我們此次的研究對象《這!就是街舞》,該節目作為亞文化網絡綜藝節目的成功典型,其熱度長期居高不下正說明了生產平臺對街舞文化的建構成功實現了觀眾的自我認同。根據前文分析,《這!就是街舞》這檔節目分別在節目的模式、影像、內容、人物上進行建構,節目的亞文化風格在影像中不斷凸顯,形成了鮮明的視覺符號,從而在網絡中的節目建構了與現實中高度一致的街舞文化。因此,《這!就是街舞》網絡綜藝節目無論是對專業舞者還是廣大的街舞愛好者來說都具有與現實中的街舞文化帶給自己高度一致的“相關性”,由此,觀眾的自我認同得以實現。
(二)觀眾對節目的符號消費
符號消費是當今消費社會的重要景觀,在觀眾對于《這!就是街舞》節目的認同基礎之上,該亞文化網絡綜藝就不再單純的是傳遞信息的網絡消費產品,而是包含著更多豐富的意義,這滿足了觀眾的社會需要和心理需求,因此,觀眾追隨著節目的符號價值,并作為消費者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符號消費行為。
此外,除了對節目這一網絡產品本身進行消費外,對于該節目延伸出的符號消費也表現明顯。如選手韓宇在參加節目后,開啟了他的個人舞蹈專場,演出的票價從最低200 元漲到了最低800 元。在參加節目后,選手楊文昊的淘寶店‘THE V BRAND’月銷量達到一萬件左右,月銷售額超過百萬[10]。
在對《這!就是街舞》節目的觀看過程中,觀眾與符號完成了一次互動,節目通過編碼完成嘻哈亞文化符號體系的構建。由于其具有的相關性,誘導了觀眾的自我認同,而觀眾也發揮著主觀能動性,并進而發生后續的符號消費行為。可以說,《這!就是街舞》的傳播過程是節目尋求認同與觀眾找到認同的雙向互動過程,它實現了觀眾的心理參與,也促進了觀眾的符號消費。
三、結語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節目之所以能夠成功在于其從模式編碼、影像編碼、內容編碼、人物編碼四方面都對街舞亞文化進行了高度的借鑒,具有了與觀眾的“相關性”,進而得到觀眾的自我認同,而觀眾這種自我認同也發揮著主觀能動性,從而反作用于觀眾進行符號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