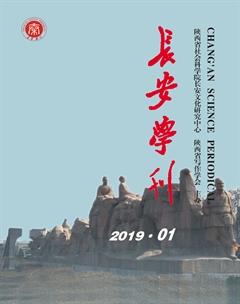淺談頻陽子小說的鄉(xiāng)土敘事
申麗平
摘要:鄉(xiāng)土題材是現(xiàn)代以來中國文學重要的題材之一,它關注時代巨變下中國鄉(xiāng)民的命運浮沉,在歷史中訴說現(xiàn)實的鄉(xiāng)村,在無盡的鄉(xiāng)愁中流露鄉(xiāng)民的幸福或苦難,作品構成十分獨特的中國鄉(xiāng)土藝術世界,頻陽子的系列鄉(xiāng)土小說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而其文學才華與人生體悟又賦予了作品獨特的敘事風格。。
關鍵詞:城鄉(xiāng)融合;日常生活;人物群像;語言
文章編號:978 -7 - 80736 - 771 -0(2019) 01 -151 - 02
“歷史敘事”、“鄉(xiāng)土文學”、“自我想象”是21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鍵詞,盡管作家的創(chuàng)作風格還帶有較為強烈的社會意識與時代精神,但其主體意識與傳統(tǒng)鄉(xiāng)土文化的發(fā)展脈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lián)性,在民族本土的自我想象的語境下,鄉(xiāng)土文學融入了更多的個人情感與語言形式上的新變,頻陽子的系列鄉(xiāng)土小說就是如此。
一、城鄉(xiāng)融合的民間敘事
新世紀以來的鄉(xiāng)土文學一直存在著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一城鄉(xiāng)對立化敘事,即現(xiàn)代城市的發(fā)展對中國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社會構成了毀滅性的摧殘,農(nóng)民成為了時代變革的犧牲品。這種看似成熟的書寫范式似乎已經(jīng)成為很多鄉(xiāng)土小說作家默認并且屢試不爽的創(chuàng)作“習慣”,他們把鄉(xiāng)村置于被侵害的弱的位置上,城市成為蠶食鄉(xiāng)村的惡魔。這就將一個復雜的問題簡化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而這種模式下的文學也變得索然無味。
而頻陽子的系列鄉(xiāng)土小說則摒棄了新世紀以來鄉(xiāng)土文學創(chuàng)作的“拒城懷鄉(xiāng)”的書寫范式,其小說中的確再次呈現(xiàn)了了一個回望而回不去的鄉(xiāng)村,但不同于以往只醉心于對傳統(tǒng)鄉(xiāng)村風俗、日常生活、地方色彩等的描述鄉(xiāng)土文學,頻陽子的小說中有了對鄉(xiāng)土現(xiàn)在和未來的建構。比如《老六和它的狗友們》中最終的鄉(xiāng)村生活的漸漸消亡;《天風》中以四勝為代表的來自農(nóng)村的地層小人物在城市中立足;《烙餅兄弟》中趙小山一家通過烙餅這個生意逐漸在城市中立足:最典型的代表是中篇小說《東辛莊》,小說描述了一個遭遇了拆遷、安置向城市化靠攏的東辛莊,以及在此居住的農(nóng)民如何在改革變遷的社會潮流下生活狀態(tài)和身心的變化,重建了有別于都市文明的現(xiàn)代鄉(xiāng)村。這些小說普遍的采取了第三人稱的上帝視角,客觀冷靜地進行敘事,聚焦于這一農(nóng)民群體的生老病死、柴米油鹽、飲食起居,呈現(xiàn)出最真實的瑣碎俗世。
不可否認,鄉(xiāng)村是一切落后因素呈現(xiàn)最為集中的地方,但在現(xiàn)代化之路上,沒有人可以置身于世外桃源,也沒有能夠反對農(nóng)村現(xiàn)代化的理由,正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已經(jīng)日漸習慣了手機支付,這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今天農(nóng)民心理是多層次的,歷史的、文化的東西也必然沉淀到他們的心理中去,傳統(tǒng)農(nóng)民要轉變成現(xiàn)代農(nóng)民,要經(jīng)過艱難漫長的路程。農(nóng)村正以遲緩、漸變、多樣的形式出現(xiàn)。然而,歷史每前進一步都是疼痛的,文學作品所書寫的鄉(xiāng)村漸行漸遠,甚至已經(jīng)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從而使得這類作品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帶有悵惘的虛無感,即使是在充滿浩蕩之氣的《老六和它的狗友們》中,行文至后三章,文風突轉,由悲壯轉為凄涼,字里行間中也可體味到作者的些許失落:老六子一死,他的狗友們群龍無首,關于野獵和波斯獵犬的話題,就漸漸被人們遺忘了。
二、日常生活中的鄉(xiāng)土人物群像構建
作為中國社會最顯性、最廣泛的存在,鄉(xiāng)村總是在時代變革中充當著歷史前進的犧牲品或是被時代所遺忘。頻陽子善于農(nóng)民群體的日常生活去涉筆,書寫或城市或鄉(xiāng)村的的百姓生活樣態(tài),從而為我們呈現(xiàn)了眾多鮮活生動、平凡而又充滿傳奇色彩的鄉(xiāng)土人物形象。
《老六子和他的狗友們》書寫了渭北高原上一群關中漢子的野獵傳奇與日常生活,塑造了老六子、老段、新娃、桿子、亂堂、聾子媳婦這主要的六個人物。他們都是平凡普通的莊稼人,老六子死了老婆,人到中年卻浪蕩無依;新娃小小年紀就開始繼承莊稼人的生活方式;桿子孑然一人,家里零碎也不妨礙四處助人;亂堂家道中落,頹敗度日;聾子媳婦美麗善良,無奈命運捉弄;老段境遇略好,有個體面的工作,但他卻一心都在波斯獵犬上。他們有著愚昧、無知,也有憨厚和善良,堅韌不撥、樂觀豁達;他們散發(fā)著人性的光輝,但也充斥著欲望。每個人物的出現(xiàn)都和“狗”有關,因為“狗”而聚焦到一起,“狗”是小說中的敘述重點,也是一個及其重要的意象。不管是關中土狗,還是波斯獵狗,亦或是二者雜交的后代,“狗”都代表著野性、代表著自然、代表著最原始的欲望。同時和主題形成了巧妙的互文:老六子和他的狗友們。頻陽子用野獵把人與狗巧妙的結合在一起,兩次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野獵場面將這群普通的莊稼人內心中的昂揚的生命狀態(tài)盡情的釋放,他們原始,健康,充滿了生命力。
《東辛莊》則圍繞鄉(xiāng)村拆遷,重點關注村民變?yōu)槭忻襁@一身份轉變中的生存狀態(tài)。小說主要聚焦于辛王兩家,對兩戶人家的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有細致的刻畫。但這種刻畫更多的是生命狀態(tài)的刻畫,比如小說中這樣描寫辛來:
辛來沒上過學,自他懂事時候起,只知道打豬草、牽上老山羊去荒野里放牧。日日看著太陽緩慢東升,他伸著懶腰走出家門,悠閑地踢著便道上的瓦礫、土疙瘩,他衣衫襤褸,四周的草長花落,傍晚日落西山了,暮色漸漸籠罩開來,他吹著口哨,踽踽獨行在田埂水畔。父母只給了他生命,沒有教給他做人的道理,把他當做小貓小狗似的養(yǎng)著。他四處浪蕩,和不三不四的野孩子們混在一起。為了一張饞嘴,經(jīng)常在村子周邊,干些偷雞摸狗的事情。他是在村人的鄙視中長大的。嚴酷的生存狀態(tài),過早地銷蝕了他的童心,人性的溫暖與和善,未能融入靈魂,更缺乏切膚的體驗。他只在意得到和實惠,不知道人生還有許多更重要的東西。他昏昏迷迷地打發(fā)著所有的日子。
不同于很多作家采取新奇陌生的敘事策略來表現(xiàn)生活的異化和荒誕。頻陽子的小說中有著一以貫之的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度,他擅長在柴米油鹽、飲食起居的瑣碎俗世中表現(xiàn)現(xiàn)實的本真和深奧的生存哲學。
《東辛莊》中的順天老漢是一個傳統(tǒng)中國的典型農(nóng)民形象,儒家思想的痕跡無處不在。他沒有文化卻知綱常禮教,和兒女談話的言辭之間都是一家之長的模樣:他沉默寡言,卻又喜歡聽村人熱鬧的聲音;他勤勞節(jié)儉,但對生活艱難的拾荒者一樣抱以同情和善良:他固執(zhí)卻又淡然,在物欲面前始終秉守自己的原則和底線。而小說中的其他人,不管蠻橫粗獷的胖女黑妞母女,還是生意成功,財大氣粗的老板辛坤,亦或是漂泊異鄉(xiāng),低聲下氣開飯館的的四川小夫妻,頻陽子筆下的每個人物都有著個體的獨異性,每個人都是鄉(xiāng)土中國命運的真實寫照。他們?yōu)樯娑嗫嗟貟暝汃さ泥l(xiāng)村激發(fā)了他們負重前行的生命活力,面對歷史巨變,他們只能盲目地隨波逐流,并與故鄉(xiāng)一起走向消亡。
三、閑雅自然的語言特色
頻陽子筆下的鄉(xiāng)土世界是以家鄉(xiāng)渭南為原型進行再創(chuàng)造的名為“東辛莊”“劉家堡”“高家堡”的農(nóng)村小鎮(zhèn),如同魯迅筆下的“未莊”、“魯鎮(zhèn)”,頻陽子用白描式的文字,把這些極富濃厚的鄉(xiāng)土氣息的鄉(xiāng)土世界勾勒得簡潔而詩意,再加上親切從容的敘述,使讀者在安祥靜謐之中聽聞這些平凡人物的傳奇故事,比如在《老六子和他的狗友們》中第二部分寫新娃:
他騎在騾馬背上,一個人能走出去一二里地。牲口們幾乎和他形成了某種默契,任憑他如何折騰,不急不躁,十分溫順。他也學了老爹,做了一只鞭子,牛皮筋的,他把鞭子舉過頭頂,輕輕一揚,牲口們好像就明白了他的旨意,馴服地聽從他的指揮。他喔喔喔吆喝幾聲,牲口們隨聲而動,加力,或拐彎,四蹄生風。新娃閑了也拔了馬尾,牛尾,做了套桿,去順陽河灘套知了,抓蟈蟈。姐姐們給他做的貓娃鞋,豬娃鞋,虎頭鞋,新娃一年穿爛五六雙。他就是閑不住,四處亂跑,水里泥里,風里雨里,沙礫堆,石頭灘,莊稼地里,想去哪就去哪兒,誰也管不住。他是劉家堡有名的野孩子。
高度口語化的文字在頻陽子的小說中隨處可見,使得小說讀來簡潔易懂、自然流暢;同時,長短不一、錯落有序的句子賦予了小說散文詩一樣的旋律感和節(jié)奏感。這些鄉(xiāng)土故事在閑雅的文風中娓娓道來,從而帶給讀者一種清新恬淡、新鮮生動的感受,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小說的品格和風貌,而作者由此所建構起的充滿濃郁畫境畫趣的藝術世界也更加個性鮮明,耐人尋味。
四、結語
賈平凹曾這樣說到自己的家鄉(xiāng):“我恨這個地方,我愛這個地方。”這是現(xiàn)在很多人對自己故鄉(xiāng)的最真實的感受,他們身在城市,又惦念故鄉(xiāng);而回到家鄉(xiāng),卻總是失望離去,甚至是盡快逃離,故鄉(xiāng)成了一個只可回望而永遠回不去的地方。在頻陽子創(chuàng)作的系列鄉(xiāng)土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家對過去農(nóng)民生活的珍視,也可以看到中國農(nóng)村過去常態(tài)的生活,甚至可以看到中國鄉(xiāng)土社會的文化基因在農(nóng)民身上的縮影,其建構的鄉(xiāng)土世界展現(xiàn)了當代鄉(xiāng)土小說深厚寬廣的多層面人文關懷,值得深入地挖掘和探討。
參考文獻:
[1]頻陽子:《烙餅兄弟》,《滿族文學》2017年第二期.
[2]頻陽子:《故鄉(xiāng)事》之《哥倆好》.
[3]頻陽子:《故鄉(xiāng)事》之《東辛莊》.
[4]頻陽子:《老六和他的狗友們》.
[5]周明全:《中國小說的審美》,《小說評論》2018年第4期.
[6]趙園:回歸與漂泊——一關于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的鄉(xiāng)土意識[J].文藝研究,1989(4).
[7][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
[8]程金城:《當鄉(xiāng)土小說研究的新范式》,《飛天》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