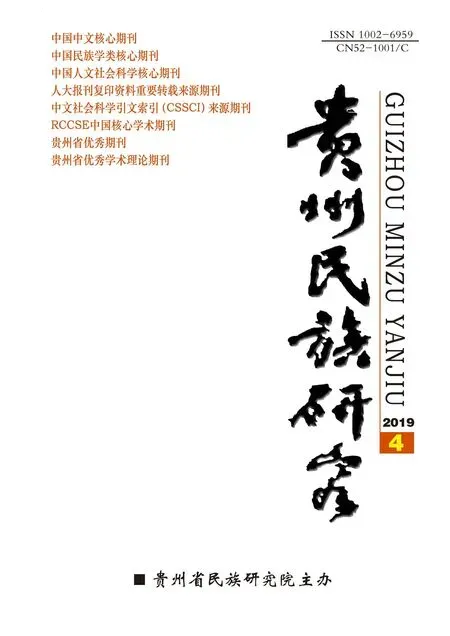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哲學(xué)化考量
張景先
(內(nèi)蒙古民族大學(xué) 經(jīng)濟(jì)管理學(xué)院,內(nèi)蒙古·通遼 028043)
“精準(zhǔn)扶貧”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在治國領(lǐng)域的新華章[1]。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開展既要以習(xí)近平總書記新時代指導(dǎo)思想為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出發(fā)點,以哲學(xué)的辯證法思維布局精準(zhǔn)扶貧工作,使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在哲學(xué)的思維向度中洗禮,在哲學(xué)思維的方法論中付諸于實踐;又要挖掘民族哲學(xué)在扶貧工程中的有機銜接,在民族多元文化習(xí)俗中開辟扶貧新紀(jì)元,從而在克服當(dāng)前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困境的同時聚焦民族社會保障,力挖民族哲學(xué)中的扶貧思維與樸素哲學(xué)韻味,并構(gòu)筑民族文化扶貧的新起點,以期在哲學(xué)化的精準(zhǔn)扶貧工作推進(jìn)中實現(xiàn)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攻堅克難。
一、民族地區(qū)扶貧是雙向哲學(xué)基線的基礎(chǔ)性建構(gòu)
(一)扶貧是民族哲學(xué)辯證思維的源泉與踐行
民族地區(qū)扶貧思想的演進(jìn)與政策性變遷在跨時空的思想軌跡中始終秉承哲學(xué)的辯證思維[2]。在民族扶貧的思想構(gòu)建中民族地區(qū)幫扶精準(zhǔn)扶貧是創(chuàng)新性的歷史延續(xù),是對民族地區(qū)扶貧工作高度哲學(xué)化的概括與統(tǒng)籌,是民族扶貧政策質(zhì)變性的產(chǎn)物。一方面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針對民族地區(qū)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現(xiàn)狀的客觀實際,在優(yōu)惠性、幫扶性政策的被動求變中不斷升華,逐漸形成以貧困群體為主體,主動謀發(fā)展的創(chuàng)新格局。另一方面民族地區(qū)扶貧始終以辯證思維為導(dǎo)向,以不斷斷層的歷史痕跡與鄉(xiāng)約民俗為參照,量體裁衣,對口扶持與指導(dǎo)。比如西南佤族地區(qū)生產(chǎn)力欠發(fā)達(dá),在土司制度確立中技術(shù)扶貧、政策性扶貧源源不斷,但是在原始公社制的庇佑下,佤族扶貧依托同根共榮的辯證思維,提倡以家族宗室為單位的幫扶,同時注重幫扶的點、線、面的全方位推進(jìn),既注重族群內(nèi)部富人“珠米”的選擇性幫扶,又注重老人的子女習(xí)俗性強制幫扶[3]。換言之,民族扶貧始終在樸素哲學(xué)的辯證思維中探索前行,特別是民族扶貧政策中的辯證思維的反映,是哲學(xué)辯證思維的源泉與實踐。是當(dāng)前推進(jìn)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發(fā)展的重要參照。
(二)扶貧共濟(jì)是民族哲學(xué)思維的基礎(chǔ)性取向
民族地區(qū)推進(jìn)精準(zhǔn)扶貧工作需遵循黨的智慧布局外,理應(yīng)挖掘民族哲學(xué)史的基本價值取向。一方面民族哲學(xué)在潛移默化的歲月嬗變中成為少數(shù)民族群眾習(xí)以為常的價值取向與人文關(guān)懷。比如藏族群眾在早期宗教哲學(xué)的枷鎖中推崇“同生共死”“萬物一理”的價值取向,在天祝藏區(qū)“扶貧共濟(jì)”是天意,是個體順應(yīng)天意的應(yīng)然之舉。當(dāng)然,藏族“同生共死”“萬物一理”的哲學(xué)思辨始終停滯在唯心主義的悲觀主義人生觀當(dāng)中,而水族樸素的“同耕互助”則將民族哲學(xué)的人文關(guān)懷折射得淋漓盡致,進(jìn)而以地域輻射為基本,以文化跨民族接納為軸心的“扶貧共濟(jì)”成為民族哲學(xué)基本的思想探尋。另一方面少數(shù)民族樸素哲學(xué)思維的傳承,是開展民族工作,提高政府行為公信力的關(guān)鍵,以扶貧為基準(zhǔn)的民族工作是勾勒少數(shù)民族群體國家認(rèn)同的重要依據(jù),尊重民族習(xí)俗的優(yōu)惠性幫扶與扶持是黨在民族地區(qū)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手段。毋庸置疑,人文關(guān)懷是民族哲學(xu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共同追尋的價值取向,“扶貧共濟(jì)”思維是民族哲學(xué)的基礎(chǔ)性價值構(gòu)建,是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哲學(xué)化考量的動力源泉和文化壁壘。
首先,民族哲學(xué)思維中同根同源的群體認(rèn)同是幫扶共濟(jì)的基礎(chǔ)。少數(shù)民族群眾在群體本源的追尋中或以神話傳說為切入點,洞悉同根同源的族群認(rèn)同。比如水族神話《人龍雷虎爭天下》中提倡人獸同源,使同耕互助等不同形式的幫扶共濟(jì)在同根同源的群體認(rèn)同中成為民族哲學(xué)思維的基本人文關(guān)懷。或以宗教鬼神觀為依托,闡述群體同根同源的族群認(rèn)同,比如《梯瑪歌·開天辟地》《鴻均老祖歌》在宗教的禮贊中折射著同根同源的哲學(xué)思維,而生產(chǎn)生活領(lǐng)域的幫扶共濟(jì)則在哲學(xué)思維的神話色彩中賦予權(quán)威性。當(dāng)然,在土家族哲學(xué)思維中同根同源間的幫扶共濟(jì)是和諧理念的基本體現(xiàn)。
其次,原始宗室婚姻血緣和鄉(xiāng)土觀念是扶貧共濟(jì)哲學(xué)思維發(fā)展的人文紐帶。一方面民族地區(qū)原始婚姻習(xí)俗決定了潛在血緣關(guān)系的廣度,特別是在走婚制等特殊婚姻關(guān)系中,幫扶既是家族宗室內(nèi)部的必然涉及又是血緣關(guān)系的本能釋放。比如赫哲族群眾在狩獵中注重幫扶性分獵,對于家族內(nèi)部老人長輩優(yōu)先割取外相對貧困的家族成員也有救濟(jì)習(xí)俗。另一方面以婚姻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鄉(xiāng)土觀念也是扶貧共濟(jì)思維的重要保障。比如納西族、彝族等民族群眾在早期的原始生活中都尤為注重以村寨為單位、以元老幫扶為主體的扶貧共濟(jì),在幫扶及傳授手工藝技術(shù)過程中給予特定角色獲取相關(guān)報酬。
再者,私有化在原始社會的漸進(jìn)式分離是扶貧共濟(jì)人文關(guān)懷的哲學(xué)社會性濃縮。民族地區(qū)同根共生的民族認(rèn)同在私有化逐漸擴散的過程中群體之間幫扶從哲學(xué)思維中的天意轉(zhuǎn)變?yōu)樯鐣U闲缘膸头鯷4]。或者說,私有化的擴散實現(xiàn)了民族扶貧共濟(jì)人文關(guān)懷的社會化轉(zhuǎn)變,扶貧成為民族哲學(xué)思維社會性的基本衡量標(biāo)尺。
總之,扶貧共濟(jì)在民族同根同源的思辨中成為哲學(xué)社會性的基本航標(biāo),是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哲學(xué)化考量的基本價值取向。推進(jìn)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進(jìn)一步開展,要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xué)韜略中滲透民族哲學(xué)扶貧共濟(jì)的價值取向和文化鑲嵌,這是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深入推進(jìn)的主體性選擇。
(三)民族扶貧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牽引機
扶貧共濟(jì)不單是民族哲學(xué)思維的線性框架,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牽引機,民族問題儼然是馬克思主義重點詮釋的價值位階。民族地區(qū)扶貧作為歷代共產(chǎn)黨人不斷踐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切入點,是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哲學(xué)化思維構(gòu)建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共力聚推的結(jié)果。
一是在黨的民族政策時間維度的洞悉中,民族扶貧逐漸成為馬克思主義民族觀踐行的主要陣地[5]。在民主革命時期,民族扶貧基本以上層建筑為基礎(chǔ),黨在民族地區(qū)的扶貧碎片化地推進(jìn),蘇維埃精神在民族地區(qū)的扎根成為民族地區(qū)幫扶共濟(jì)的時代號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民族地區(qū)的實踐中不斷生根發(fā)芽。在實事求是的價值導(dǎo)向中,民族區(qū)域自治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民族扶貧從根本性的制度構(gòu)建著手,開辟了民族扶貧的新紀(jì)元,與以往階級壓迫性扶貧截然不同,民族群體成為扶貧的主導(dǎo)力量,進(jìn)而充分發(fā)揮了民族群眾的主體性。馬克思主義民族觀中國化切實地轉(zhuǎn)變?yōu)槊褡鍏^(qū)域自治。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確立中,國家立足法制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在民族地區(qū)不斷協(xié)作扶貧,全面推動民族地區(qū)小康社會的建設(shè)。精準(zhǔn)扶貧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離不開民族地區(qū)發(fā)展困境的推動[6]。
二是民族地區(qū)扶貧的歷史廣度在辯證實踐的探索中迫切需要精準(zhǔn)扶貧的布局與開展。不論是早期的政治幫扶還是經(jīng)濟(jì)扶貧,民族地區(qū)扶貧工作的持續(xù)性推進(jìn)都需要協(xié)調(diào)并進(jìn)、全方位多層次開展,這是彰顯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協(xié)同精神、實踐精神,助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趨勢。首先,從制度扶貧、經(jīng)濟(jì)扶貧、技術(shù)扶貧的現(xiàn)實困境的轉(zhuǎn)變中,不斷驅(qū)動著馬克思主義實踐精神、協(xié)同精神的創(chuàng)新運用,而精準(zhǔn)扶貧的時代創(chuàng)舉,從金融扶貧到就業(yè)扶貧,從健康扶貧到生態(tài)扶貧,是對馬克思主義協(xié)同精神、實踐精神的高度概括。其次,不同時期的民族扶貧實踐都是精準(zhǔn)扶貧在民族地區(qū)運行的高度概括與參照。換言之,不同時期的民族扶貧實踐是精準(zhǔn)扶貧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實踐保障。再者,在民族地區(qū)扶貧開展過程中,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運用,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轉(zhuǎn)化啟迪了動力源泉,使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開展始終以哲學(xué)思維為向?qū)А?/p>
總之,在歷史的軌道中探索,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的開展需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為基準(zhǔn),以民族哲學(xué)的幫扶共濟(jì)為接入點,深化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是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哲學(xué)化考量的內(nèi)在動力。
二、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需要吸納民族哲學(xué)
(一)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需要本土化的辯證思維
少數(shù)民族樸素辯證法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重要源泉,在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開展中巧用本土化的辯證思維,有助于扶貧工作策略民族化與科學(xué)化的統(tǒng)一,從而避免在精準(zhǔn)扶貧開展中脫離主體性而效率不高[7]。比如阿昌族群眾將佛教教義同社會熱點問題相結(jié)合,通過群體習(xí)以為常的辯證法思維開展扶貧工作,特別是在社會保障領(lǐng)域,在充分發(fā)揮祖先崇拜的同時將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社保扶貧統(tǒng)籌一體,使精準(zhǔn)扶貧呈多層次齊驅(qū)共進(jìn)的發(fā)展態(tài)勢,極大地緩解了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單項性開展。
要促進(jìn)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本土化辯證思維的運用,首先,要不斷從民族哲學(xué)文化中挖掘婦孺皆知的、扎根生活的辯證法思維,使之成為開展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的本土化、民族化的橋梁。通過民族禁忌的辯證思維,引導(dǎo)廣大干部群體在民族扶貧道路上不斷民族化推進(jìn)[8]。比如鄂溫克族忌諱捕撈幼苗,注重發(fā)展觀在生產(chǎn)生活中的運用,在精準(zhǔn)扶貧工作開展要不斷將忌諱捕撈幼苗的辯證思維運用到具體問題當(dāng)中。其次,要將少數(shù)民族群體喜聞樂見哲學(xué)辯證觀念移植到精準(zhǔn)扶貧工作當(dāng)中,以哲學(xué)思維實現(xiàn)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攻堅克難,特別是毛南族等少數(shù)民族群眾注重事物的聯(lián)系,要發(fā)揮傳統(tǒng)民族哲學(xué)思維中的辯證觀念,實現(xiàn)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從機制扶貧到具體扶貧的轉(zhuǎn)變,實現(xiàn)民族扶貧從產(chǎn)業(yè)扶貧到教育扶貧、健康扶貧、就業(yè)扶貧等領(lǐng)域的多元化發(fā)展。再者,要將民族哲學(xué)思維不斷納入到精準(zhǔn)扶貧的框架布局中,成為推動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發(fā)展的不二法門[9]。民族地區(qū)生態(tài)扶貧、教育扶貧困境重重,在民族地區(qū)開展精準(zhǔn)扶貧工作要充分挖掘民族哲學(xué)中的神態(tài)思想和教育觀念,不斷植入到民族地區(qū)的精準(zhǔn)扶貧工作當(dāng)中,成為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開展的亮點和內(nèi)在驅(qū)動力。
(二)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必然要將哲學(xué)文化納入
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必然要將哲學(xué)文化納入,需要將民族哲學(xué)的歷史與未來并軌銜接,從而使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在本土化、民族化的哲學(xué)建構(gòu)中攻堅克難[10]。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納入哲學(xué)文化,要以民族傳統(tǒng)文化為整體,充分發(fā)揮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哲學(xué)化維度,積極發(fā)揮雙向哲學(xué)的文化統(tǒng)籌。具體而言,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推進(jìn),要不斷聚焦民族文化,以文化精準(zhǔn)扶貧為中心,牽動其他領(lǐng)域協(xié)作扶貧的統(tǒng)籌發(fā)展。一方面民族地區(qū)以哲學(xué)文化為依托的文化典范是最具民族化、本土化的元素,統(tǒng)籌文化能有效地突出民族扶貧的亮點和動力所在。比如鄂爾多斯蒙古族貧困區(qū),在精準(zhǔn)扶貧戶信息采集、數(shù)據(jù)對照、建檔立卡過程中充分發(fā)揮傳統(tǒng)哲學(xué)文化的魅力外,還要以草原游牧文化為切入點,大力挖掘文化扶貧的動力通過文化扶貧促進(jìn)全面扶貧,從而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扶貧效益[11]。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在精準(zhǔn)扶貧工作中的納入,有助于發(fā)揮民族文化的協(xié)作效能。使文化扶貧同就業(yè)扶貧、教育扶貧、社保扶貧等有機銜接。比如肅南裕固族依托民族刺繡文化,助力文化扶貧,通過富達(dá)民族服飾公司等民族文化企業(yè),舉辦系列文化扶貧暨裕固族非遺技能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培訓(xùn)班,以文化扶貧促就業(yè)扶貧和產(chǎn)業(yè)扶貧。
毋庸置疑,民族地區(qū)開展“精準(zhǔn)扶貧”工作是新時期黨和國家治國理政重要創(chuàng)舉,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民族地區(qū)創(chuàng)造性的實踐與沉淀。洞悉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哲學(xué)化考量,是推進(jìn)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攻堅克難”的必要法寶。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法論是深入開展工作的基本保障,是民族地區(qū)開展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重要工作法則;另一方面立足民族哲學(xué)思維,為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開展注入民族化價值觀,是提高精準(zhǔn)扶貧工作效率不可忽視的因素[12]。總之,探究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哲學(xué)化考量是剖析當(dāng)前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困境、構(gòu)筑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文化命脈、高效推進(jìn)民族地區(qū)精準(zhǔn)扶貧工作共同的價值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