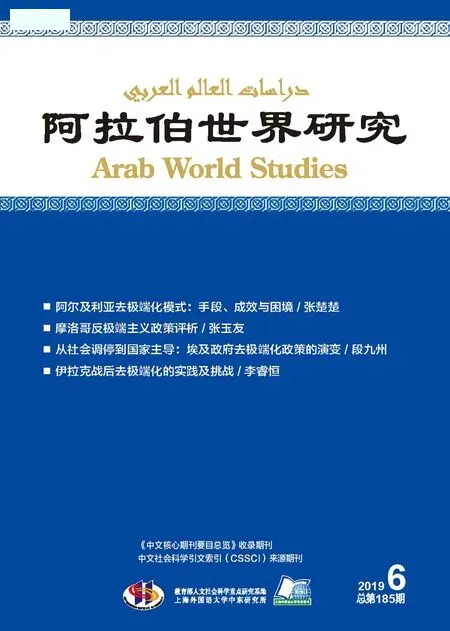從社會調停到國家主導:埃及政府去極端化政策的演變*
段九州
一、 埃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及其成因
自1952年法魯克王朝被推翻以來,埃及的共和國時代歷經多次政治劇變。從納賽爾領導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時期、薩達特領導的“經濟開放”和解除黨禁時期,到穆巴拉克領導的有限多黨體制時期,再到“阿拉伯之春”后短暫的多黨民主競爭時期,不同時期埃及的政治格局和政府形態結構各異,國內的極端主義也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態勢。作為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社會運動,伊斯蘭極端主義武裝長期以來一直是埃及政府最主要的國內安全威脅。(1)Omar Ashour, “Collusion to Crackdown: Islamist-Military Relations in Egypt,” Brookings Doha Center Analysis Paper, No. 14, March 2015, p. 4.
(一) 埃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
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是埃及最具影響力的伊斯蘭主義組織。盡管該組織在官方聲明中一直強調使用和平手段,但其長期與政治暴力甚至暴力“圣戰”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臭名昭著的極端分子也曾聲稱受到過穆兄會思想的啟發和影響。穆兄會的內部分歧往往導致該組織分裂出持不同話語和策略的暴力分支。從理論淵源來看,20世紀后期以來,穆兄會極端主義和暴力行動的理論來自于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庫特布在其代表作《路標》中指出,西方的影響和“蒙昧主義”是制約伊斯蘭社會實現進步的主要障礙(2)Sayyid Qutb, Milestones, Indianapolis: American Trust Publications, 1990, p. 8.,這些障礙必須通過“圣戰”手段加以清除,“圣戰”分為廣義的個人奮斗和狹義的“武裝斗爭”。(3)Barbara Zolln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Hasan al-Hudaybi and Ide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58-63.穆兄會在不同歷史時期采用過武裝“圣戰”和政治暴力的策略,在1981年薩達特遇刺后,穆兄會的暴力活動曾達到頂峰。在庫特布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穆兄會年輕成員對埃及政府的打壓持不滿態度,這直接導致他們與該組織的其他成員產生矛盾,甚至轉而出走穆兄會,加入更加激進的武裝組織。(4)Ana B. Soage,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gypt,” in Barry Rubin, 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New York: Palgrave, 2010, pp. 40-55.
伊斯蘭極端組織是指在意識形態上反對現行國家體制,試圖以暴力手段實現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的伊斯蘭主義組織。穆兄會在納賽爾時期長期受到打壓,主要成員在被釋放后轉變了武裝斗爭的激進策略,而是以和平手段開展政治活動。(5)Anne Alexander, “Brothers-in-Arms? The Egyptian Military, the Ikhwan and the Revolutions of 1952 and 2011,”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4, 2011, pp. 533-554.20世紀70年代,一批伊斯蘭主義者發起成立了數個極端化的武裝組織,其中以“伊斯蘭團”(Islamic Group)和“伊斯蘭圣戰”(Islamic Jihad)最具代表性。在90年代埃及的官方語境中,伊斯蘭極端組織被定義為從事武裝叛亂和暗殺行動的暴力極端組織,但其分支組織也可能從事社會服務和宣教活動等非暴力行為。1981年,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在紀念十月戰爭的閱兵式上被“伊斯蘭圣戰”組織成員伊斯坦布利刺殺,埃及各地隨后爆發了不同規模的極端組織武裝叛亂。穆巴拉克上臺后通過各種手段暫時平息了地方叛亂,但未遏制住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蔓延勢頭。20世紀90年代,極端主義在埃及出現激化態勢。1992年至1997年間,大量政府官員、游客、學者和基督徒受到伊斯蘭極端組織的襲擊,約1,300人因此而喪生。(6)Fawaz A. Gerges, “The End of the Islamist Insurgency in Egypt?: Costs and Prospect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4, No. 4, 2000, pp. 592-612.
自2013年7月埃及穆爾西政權被推翻以來,埃及經歷了自1952年獨立以來最嚴重的極端主義浪潮。2013年7月3日至2014年1月31日間,埃及國內有281人因極端組織的暴恐襲擊而身亡,其中包括224名官兵和57名平民。至2014年2月28日,埃及境內共發生了180起極端主義事件,極端分子的死亡人數也因埃及軍方的反恐行動而上升,僅2014年2月西奈半島就有56名極端主義分子被軍方擊斃。(7)Michele Dunne and Scott Williamson, “Egypt’s Unprecedented Instability by the Number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4, 201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3/24/egypt-s-unprecedented-instability-by-numbers-pub-55078, 登錄時間:2019年7月9日。總的來看,20世紀90年代和2011年“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國內經歷了兩波極端主義高潮,埃及政府在這兩個時期的去極端化政策頗具代表性。
(二) 埃及極端主義興起的因素
理解極端化的成因,是打擊和預防極端主義的關鍵。美國國際援助署將極端主義興起的成因分為“推動”因素和“拉動”因素。其中,“推動”因素是指使整個環境有利于極端主義滋生,包括教育缺失、低就業率、貧困、邊緣化人群的存在和低效治理等結構性因素;“拉動”因素主要指促使個人傾向于暴力極端主義的外部誘因。(8)“The Development Response to Violent Extremism and Insurgency,” USAID Policy Paper, September 2011.在埃及的語境中,“推動”因素主要表現為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因素,“拉動”因素則表現為跨國極端主義思想和組織的宣傳與引導。
1. 埃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推動”因素——社會經濟困境
社會經濟論的解釋普遍認為,極端主義的興起與物質貧困和缺乏社會正義有關。(9)Terry Boswell and William Dixon, “Dependence and Rebell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5, No. 4, 1990, pp. 540-559.作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埃及各地區之間發展極不平衡,很多地區缺乏清潔水源、教育和健康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服務。發展失衡導致不滿社會貧富分化的民眾數量增加,而居住在城市的社會邊緣群體最容易被動員起來。(10)Edward Muller and Mitchell Seligson, “Inequality and Insurgen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2, 1987, pp. 425-451.英國學者多曼(W.J. Dorman)認為,埃及政府長期疏于關注首都開羅的貧民窟現象,其在經濟社會上的無序狀況為奉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武裝分子提供了建立“國中之國”的完美土壤。(11)W.J. Dorman, “Informal Cairo: Between Islamist Insurgency & the Neglectful State?,” Security Dialogue, Vol. 40, No. 4-5, 2009, pp. 419-441.法國學者吉爾·凱佩爾(Gilles Kepel)指出,在1981年薩達特遇刺后被捕的武裝分子大部分都居住在開羅城市邊緣的定居點。(12)參見Gilles Kepel, Muslim Extremism in Egypt: The Prophet and the Pharao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在開羅的貧民區中,伊斯蘭極端分子嘗試建立自成一體的小社會。“伊斯蘭團”的社會工作委員會向居民提供社會服務,“巡夜人”負責保護街道安全,“調解委員會”負責仲裁鄰里爭端。極端分子以貧民區為試驗田,試圖對埃及社會進行所謂的“道德化”改造。他們不僅在當地禁止酒精和光碟,還強制要求婦女佩戴面紗。(13)[埃及]希夏姆·穆巴拉克:《恐怖分子來了! 穆斯林兄弟會和“圣戰”組織對暴力問題的立場比較研究(1928年至1994年)》(阿拉伯文版),開羅:馬赫魯薩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113頁。1992年“伊斯蘭團”公開宣布在西穆尼拉區成立“伊姆巴巴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mbaba),同年12月,1.8萬名埃及準軍事警察包圍西穆尼拉區的“伊斯蘭團”武裝分子,由此開啟了20世紀90年代伊斯蘭極端分子在埃及全境的大規模武裝叛亂活動。(14)Diane Singerma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litical Spectacle: The Siege of Imbaba and Egypt’s Internal ‘Other’,”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series on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Logics of Action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Distributive and Normative Processes in the Arab Countries of the Mediterrane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airo University, 2009.
埃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與特定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落后有關,上埃及(Sa’id)和西奈半島分別是20世紀90年代和“阿拉伯之春”后埃及極端勢力最猖獗的地區。從開羅以南到阿斯旺的上埃及通常被埃及民眾和學者視為“鄉土氣息更重、教育水平低、健康狀況差和更貧窮”的地區。(15)Nicholas Hopkins and Reem Saad, “The Region of Upper Egypt: Identity and Change,” in Nicholas Hopkins and Reem Saad, eds., Upper Egypt: Identity and Change,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4, pp. 1-23.埃及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時常表現出獨特的“上埃及”特征,如所有參與刺殺薩達特的嫌犯都來自上埃及地區。20世紀90年代的極端分子較70年代的極端分子更年輕、更缺乏教育、更貧窮且更多地住在農村和城市邊緣地區。(16)Cassandra, “The Impending Crisis in Egypt,”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49, No. 1, 1995, pp. 9-27.廣義上,埃及的伊斯蘭極端分子都具有“上埃及”特征,他們希望通過特定的伊斯蘭價值觀來改造埃及社會,如提倡上埃及人的誠實和勤勞,這與位于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的埃及政府和富裕家庭的腐敗和懶惰形成鮮明對比。(17)James Toth, “Islamism in southern Egypt: A Case Study of a Radical Religious Mo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5, No. 4, 2003, pp. 547-572.上埃及和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水平的差異,使得上埃及人擁有強烈的本土化身份認同,如重視榮譽、尊重長者、部落親緣關系等。(18)Catherine Miller, “Between Myth and Re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a Sa’idi Identity in Cairo,” in Nicholas Hopkins and Reem Saad, eds., Upper Egypt: Identity and Change, pp. 25-54.上埃及地區爆發的宗教暴力“更多體現了當地追求‘血親復仇’的部落傳統,而非對政府鎮壓的反應”(19)James Toth, “Islamism in southern Egypt: A Case Study of a Radical Religious Movement,” pp. 547-572.。
2. 埃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拉動”因素——國際安全形勢
除國內社會經濟因素外,20世紀90年代埃及所處的國際環境助長了國內極端主義的泛濫。埃及政府曾指控外國機構參與煽動、資助、訓練和武裝埃及境內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叛亂。1992年,埃及政府多次指責伊朗和蘇丹向埃及境內的極端分子走私武器,指控2,000多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在蘇丹境內協助訓練武裝分子。(20)P.B. Sinha, “Threat of Islamic Terrorism in Egypt,” Strategic Analysis, Vol. 22, No. 8, 1998, pp. 1193-1213.20世紀90年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安全形勢的惡化間接助長了埃及境內極端主義的興起。在阿巴邊境活動的武裝分子訓練營并未在蘇聯撤軍后解散,在營中接受培訓的“圣戰”青年很多來自埃及等阿拉伯國家,他們中的不少人在阿富汗戰爭后返回原籍國追求“伊斯蘭的事業”。埃及安全部門認為,本·拉登是位于阿富汗庫納爾的“圣戰”分子訓練營的主要資助者,埃及的“伊斯蘭團”和“伊斯蘭圣戰”成員都在那里接受訓練。(21)Scott Macleod, “The Paladin of Jihad,” Time, May 6, 1996, p. 16.
與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況類似,2011年后埃及極端主義再度興起的重要原因是境外“圣戰”分子的回流。2011年敘利亞戰爭爆發后,至少3,000名埃及人前往安全形勢惡化的敘利亞參加“圣戰”,參戰人數在穆爾西執政時期達到頂峰。(22)Aaron Y. Zelin, Evan F. Kohlmann and Laith al-Khouri, Convoy of Martyrs in the Levant: A Joint Study Charting the Evolving Role of Sunni Foreign Fighters in the Armed Uprising Against the Assad Regime in Syria,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une 2013,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uploads/Documents/opeds/Zelin20130601-FlashpointReport.pdf,登錄時間:2019年9月2日。部分埃及籍極端分子受“基地”組織或“伊斯蘭國”高層中的埃及人指使返回埃及,企圖在埃及本土發動“圣戰”。穆兄會的部分激進成員和“耶路撒冷支持者”(AnsarBeital-Maqdis)等極端勢力也試圖與西亞地區的極端組織建立聯系,派遣人員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接受武裝訓練。2014年12月,“耶路撒冷支持者”宣布效忠“伊斯蘭國”組織頭目并成為該組織的西奈分支。
二、 穆巴拉克政府的去極端化政策: 社會調停
在穆巴拉克時期,埃及政府奉行以社會調停為主的去極端化政策。自1997年至2007年間,埃及境內兩大伊斯蘭極端武裝——“伊斯蘭團”和“伊斯蘭圣戰”在意識形態和行為層面完成溫和化轉向,成為阿拉伯世界去極端化的典型案例。有學者認為,“迄今為止,其他任何宗教恐怖組織都不曾像埃及的極端組織那樣,向世人提供過如此規模的對宗教的重新詮釋”(23)Lisa Blaydes and Lawrence Rubin, “Ideological Reorienta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Confronting Militant Islam in Egypt,”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0, No. 4, 2008, pp. 461-479.。英國學者歐麥爾·阿舒爾(Omar Ashour)曾提出行為、意識形態和組織三個維度的去極端化。行為維度的去極端化指在事實上放棄暴力活動;意識形態維度的去極端化指宣布暴力的非法性;組織維度的去極端化指組織領導層和結構的改變,包括取消武裝分支。“伊斯蘭團”在上述三個維度成功實現了去極端化;“伊斯蘭圣戰”未完成組織維度的去極端化,其海外分支和埃及境內的部分分支拒絕解除武裝。上述兩個極端組織都是“基地”組織的盟友,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它們制造的暴力襲擊活動導致1,000多人死亡。(24)Lisa Blaydes and Lawrence Rubin, “Ideological Reorienta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Confronting Militant Islam in Egypt,” p. 462.兩者均參與了1981年對總統薩達特的刺殺及其他多起暴力活動。“伊斯蘭團”曾刺殺了埃及前議長和多名知識分子,試圖在亞的斯亞貝巴刺殺時任總統穆巴拉克,并在埃及境內實施針對外國游客、科普特人和軍警的暴力襲擊。從去極端化的成效來看,“伊斯蘭團”在1997年后未再從事任何暴力活動,且強烈譴責埃及境內其他小型武裝組織的暴力行徑。阿舒爾將類似“伊斯蘭團”的集體去極端化定義為“發生在伊斯蘭極端主義運動內部的相對變化的過程,它重塑了意識形態,并譴責使用暴力手段實現政治目標,逐漸接受了多元社會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變化”(25)Omar Ashour, The De-Radicalisation of Jihadis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6.。
針對“伊斯蘭團”和“伊斯蘭圣戰”的去極端化實踐,集中體現了穆巴拉克時期埃及政府重視發揮社會力量在去極端化過程中的作用。在政府武力優勢和選擇性激勵的前提下,社會力量調停和極端組織領導倡議成為埃及政府開展去極端化的關鍵手段。政府武力優勢是指政府的武力鎮壓足以使武裝組織頭目否定以武裝斗爭實現政治目標的可行性。社會調停是指武裝組織與溫和派宗教人士以及成功實現去極端化的組織進行對話與互動。政府選擇性激勵是指政府以釋放囚犯、改善民生、納入政治體系作為與武裝組織進行談判的條件。組織領導倡議是指具有廣泛宗教影響力、斗爭歷史以及高層職務的組織領導層發起意識形態重塑的倡議,借助出版書籍、開展監獄巡回演講等形式,最終實現組織的徹底去極端化和回歸社會。
在策略上,穆巴拉克政府通過發揮武裝組織領導和社會力量的規勸作用來實現武裝組織集體去極端化。“伊斯蘭團”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埃及大學校園。1974年至1989年是該組織在埃及境內的迅速擴張期,1989年至1997年是該組織與埃及政府開展暴力對抗的階段。“伊斯蘭團”曾強烈譴責穆兄會的政治實用主義和放棄暴力斗爭路線,它宣揚以暴力手段實現社會和政治變革,并輔以在清真寺、大學和街頭開展宣教活動。1981年該組織參與刺殺薩達特總統后,其許多成員都在穆巴拉克上任初期的“嚴打運動”中被捕入獄,這導致該組織回到上埃及地區發展。其間,納吉赫·易卜拉欣和卡邁勒·哈比比等組織領導人撰寫了大量宣揚暴力對抗政府的意識形態和教義學出版物。(26)Fua’ad Tal’at Qasim, “What Does the Gama’a Islamiyya Want?,” in Joel Beinin and Joe Stork, eds., Political Islam: Essays from Middle East Repo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vember 1996.1988年,“伊斯蘭團”中大量未被關押的成員前往阿富汗參加抗蘇“圣戰”,在當地接受軍事和游擊戰訓練。戰爭結束后,這些成員返回埃及,同政府開展對抗。1989年至1997年間,該組織在埃及境內實施多起刺殺、爆炸行動,埃及政府遂在上埃及實施宵禁,逮捕了3萬名極端主義“同情者”。雙方對峙的長期化使得“伊斯蘭團”和政府安全部隊都對武力對抗心生厭倦,導致“伊斯蘭團”在1997年開始了去極端化進程。
首先,埃及政府成功勸說擁有強大的宗教影響力、斗爭歷史以及高層職務的武裝組織領導人發起去極端化倡議。為實現這一目標,穆巴拉克政府首先推動“伊斯蘭團”高層領導宣布去極端化的意圖,使領導層達成政策共識。政府的武力優勢是迫使該組織老一輩領導人改變行為和轉變意識形態的原因之一。政府的壓制迫使這些領導人對形勢進行了重新評估,其結論是沖突的代價超過收益,因此主張該組織應該終止“圣戰”。(27)[埃及]哈姆迪·阿卜杜·拉赫曼、[埃及]納吉赫·易卜拉欣、[埃及]阿里·沙里夫:《闡明“圣戰”中的錯誤》(阿拉伯文),開羅:伊斯蘭遺產書局2002年版,第66頁。政府的壓制還導致“伊斯蘭團”部分領導人改變了世界觀,如該組織領導人之一馬哈茂德·優素夫曾表示:“我們在監獄中受盡折磨,家人在外也飽受經濟困難和社會歧視之苦。如果安拉真的站在我們一邊,為何這些事情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他認為,對抗政府的策略在教義學解釋上是經不起考驗的。(28)Omar Ashour, “Lion Tamed?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De-Radicalization of Armed Islamist Movements: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 Islamic Group,”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1, No. 4, 2007, pp. 596-625.1997年7月,“伊斯蘭團”另一位領導人穆罕默德·艾敏·阿卜杜·阿利姆在庭審中宣讀了由6名該組織領導人共同簽署的聲明,宣布在埃及境內外永久停止使用暴力。在宣布停火后,“伊斯蘭團”領導人陸續完成了意識形態和組織的去極端化。1999年3月,該組織在埃及境內外的領導人達成共識,宣布支持“停火倡議”。(29)“停火倡議”一開始并不被所有組織成員所接受,這些被關押的領導人并不能完全掌控在獄外的武裝分支,后者仍于1997年9月制造了盧克索慘案,近60名游客遇難。直到1999年,被關押在美國的該組織精神領袖“盲人謝赫”阿米爾·阿卜杜·拉赫曼宣布支持該倡議,“伊斯蘭組織”在海外的舒拉會議才接受了倡議。從此,該組織領導層開始作為一個整體與外界互動。參見Lisa Blaydes and Makram Mohammed Ahmed, “Wadi al-Natroun Penitentairy: The Rank and File Has a Discussion with Their Leadership in the Courtyard of the Penitentiary,” June 28, 2002, 轉引自Lisa Blaydes and Lawrence Rubin, “Ideological Reorienta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Confronting Militant Islam in Egypt”。
“伊斯蘭團”老一輩領導人積極推動“停火倡議”也歸功于穆巴拉克政府推行的選擇性激勵措施。自1998年起,埃及政府與“伊斯蘭團” 頻繁互動,降低了對后者的壓制力度。政府停止了對各大監獄中該組織成員的暴力壓制,同時改善監獄食宿環境。1999年至2000年間,此前被禁止的監獄探訪逐漸恢復。至2001年,埃及政府和“伊斯蘭團”領導層進入協調階段。“9·11”事件的發生使得埃及政府轉向支持停火協議和極端組織的轉型,允許組織領導人在監獄巡回宣講和在電視臺發表言論,甚至資助出版“伊斯蘭團”領導人的新書。(30)Rohan Gunaratna and Mohamed Bin Ali, “De-Radicalization Initiatives in Egypt: A Preliminary Insigh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2, No. 4, 2009, pp. 277-291.2002年底以來,埃及政府開始向該組織提供選擇性激勵,包括老一輩領導人在內的大批“伊斯蘭團”成員被釋放出獄;(31)Mohammed Salah, “Al-Qahira Tuqir bi-Itlaq A’da al-Jama’a al-Islamiyya ‘Ala Duf’at,” Al-Hayat, April 13, 2006, p. 6.政府支持“伊斯蘭團”在社會宣介著作和建立官方網站;該組織領導層宣布解散武裝分支,其成員可享受源自組織募款和政府資助的經濟補貼。(32)Makram Ahmad, “Al-Qawa’id Tunaqish Qiyadatiha fi Liman Wadi al-Natrun,” Al-Mussawar, June 28, 2002, p. 16.
1997年“全面停火”前,“伊斯蘭團”和埃及政府之間至少嘗試過14次停火,(33)1988年至1994年間,愛資哈爾學者嘗試勸說“伊斯蘭團”放棄暴力。1993年,由愛資哈爾學者和溫和伊斯蘭主義者組成的“協調委員會”嘗試調解該組織和政府的矛盾;同年,埃及內政部監獄部門負責人阿卜杜·拉烏夫·薩利赫將軍建議該組織停止攻擊游客,但后者提出的六項條件遭政府拒絕。1996年,該組織的阿斯旺分支前“埃米爾”哈利德·易卜拉欣·庫希呼吁停止暴力活動,但因缺乏前領導層的支持而失敗。參見Omar Ashour, “Lion Tamed?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De-Radicalization of Armed Islamist Movements: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 Islamic Group,” pp. 596-625。但都以失敗而告終。1997年前“伊斯蘭團”領導層尚未對完全停火達成共識,而這些嘗試都缺乏老一輩領導層從意識形態層面對使用暴力的批判和反思。在“伊斯蘭團”的追隨者看來,只有老一輩領導人才具有號召集體放棄暴力手段的“宗教合法性”,而愛資哈爾學者等人士都是政府的“同路人”。2002年6月,納特侖谷地(Wadial-Natrun)監獄的1,000多名“伊斯蘭團”成員召開會議,親吻老一輩領導人的手和胡須,展現出對后者的極大尊重。(34)Makram Ahmad, “Al-Qawa’id Tunaqish Qiyadatiha fi Liman Wadi al-Natrun,” p. 12.但老一輩領導人只能有限地掌控追隨者的思想,他們在宣布改變意識形態后,還需對中層領導、基層成員和秘密成員等開展細致的說服工作。1997年停火倡議實施伊始,“伊斯蘭團”內部反應不一。此后至2002年12月,這些領導人在各大監獄開展巡回宣教和答疑,成功說服了被關押的1.5萬名組織成員。(35)Makram Ahmad, “Ahmad Yuhawir Qiyadat al-Jama’a al-Islamiyya Kharij al-Sujun,” Al-Mussawar, July 5, 2002, p. 7.關于“伊斯蘭團”勸說秘密成員的公開資料較少,該組織領導人卡拉姆·祖赫迪曾提到其不斷勸說秘密成員向安全部隊投降,使這些成員最終接受了停火倡議。1997年盧克索事件(36)盧克索事件是指1997年11月17日“伊斯蘭團”在埃及觀光勝地盧克索無差別襲擊外國游客的恐怖事件,事件導致61名外國游客和2名埃及警察共計63人死亡、85人受傷。發生后,“伊斯蘭團”成員未再從事暴力活動,其中部分人甚至成為停火倡議和新意識形態的宣傳者。(37)Makram Ahmad, “Ahmad Yuhawir Qiyadat al-Jama’a al-Islamiyya Kharij al-Sujun,” p. 18.
其次,穆巴拉克政府通過鼓勵兩類社會調停,推動“伊斯蘭團”在行為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去極端化。一種是外部互動,即“伊斯蘭團”與社會政治組織以及個人進行互動,包括與其他伊斯蘭主義運動之間的互動,這在事實上推動了“伊斯蘭團” 老一輩領導人的觀念轉變。老一輩領導人在去極端化著作和宣講中提到,他們之所以在1997年提出停火倡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擔心出現類似阿爾及利亞的情況,即在暴力持續升級時領導人失去了對追隨者的控制并最終導致組織的分裂。(38)Nagih Ibrahim, Hatmiyyat al-Muwajaha wa Fiqh al-Nata’ij, Cairo: Al-Abikan, 2005, pp. 59-60.此外,定叛(判定穆斯林叛教)主義者和世俗自由派之間的互動也推動了組織成員的思想轉變。自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由于監獄囚犯數量過多,埃及政府只能將不同意識形態的囚犯關押在同一座監獄。在與同監獄的定叛主義分子交流后,“伊斯蘭團”領導層擔心自己的追隨者可能會被更加極端的定叛思想所吸引。而在與同一監獄中的世俗自由主義人士交流后,“伊斯蘭團”領導層吸取了部分現代主義和多元主義的觀點,包括強調文化歷史的多元維度而非固化的本本主義、選擇文化對話而非文明沖突、承認更新宗教話語的必要性等。(39)Omar Ashour, “Lion Tamed?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De-Radicalization of Armed Islamist Movements: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 Islamic Group,” pp. 596-625.
另一種是內部互動,即“伊斯蘭團”組織內部成員通過互動來轉變思想觀念。該組織老一輩領導人向中層指揮官闡釋停火倡議的原則和新的意識形態,通過召集全體大會介紹自己的新著,來回應組織成員的關切和批評。1999年以來,在埃及獄中的“伊斯蘭團”領導人積極批判《伊斯蘭行動憲章》、《為伊斯蘭教法與暴力正名》等反映其早期意識形態的作品,主張放棄暴力行為。(40)Paul Kamolnick, “The Egyptian Islamic Group’s Critique of Al-Qaeda’s Interpretation of Jihad,”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7, No. 5, 2013, pp. 93-110.“9·11”事件后,“伊斯蘭團”領導層坦言應部分為該事件負責,開始更加認真地對待去極端化。2002年,“伊斯蘭團”成員出版“概念糾正”系列著作,為“譴責暴力和放棄武力推翻政府”提供教義學解釋。(41)Amr Hamzawy and Sarah Grebowski, From Violence to Moderation: Al-Jama’a al-Islamiya and al-Jihad, Carnegie Papers, No. 2, April 201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violence_moderation.pdf, 登錄時間:2019年1月2日 。老一輩領導人通過開展監獄巡回演講,勸說武裝人員放棄暴力。“伊斯蘭團”曾多次發布教令譴責“基地”組織的暴力行徑,部分領導人甚至致信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勸說他們抵制暴力。(42)Khalil Al-Anani, “Jihadi Revisionism: Will It Save the World?,” Middle East Brief, No. 35, April 2009.“伊斯蘭團”還面向埃及大眾、伊斯蘭世界和國際社會,創立官方網站,發布新的關于去極端化的作品,接受埃及國家媒體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媒體的采訪,主動宣介去極端化的理念。(43)Rohan Gunaratna and Mohamed Bin Ali, “De-Radicalization Initiatives in Egypt: A Preliminary Insight,” pp. 277-291.
三、 塞西政府的去極端化政策: 國家主導
2011年以來,中東地區和埃及國內的安全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在地區層面,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等國的動蕩局勢,導致埃及周邊安全環境持續惡化。在國內層面,2011年和2013年的兩場“革命”為極端主義在埃及社會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由此引發了此后持續數年的埃及境內極端主義的抬頭。塞西自2014年上臺以來積極呼吁進行宗教改革,領導埃及政府推動教法判令機構、宗教基金部和愛資哈爾三大國家宗教機構的改革。2015年,埃及議會通過法律,允許來自愛資哈爾的高級學者委員會、教法判令機構和宗教基金部的學者在埃及境內發布宗教教令(法特瓦)。該法律還規定,未通過合法媒體途經發布教令的宗教人士將受到處罰。(44)M. Gamil, “Fighting Odd Fataws: Egypt to Rule out Unlicensed Preachers,” Egypt Today, March 14, 2018.2015年7月,埃及內閣通過新反恐法。該法律以寬泛的概念來定義恐怖主義行為,對恐怖主義行為判處死刑和對強迫個人加入恐怖組織的行為判處終身監禁。(45)S. Farid, “Egypt’s New Anti-Terror Law: An In-Depth Reading,” Atlantic Council, July 10, 201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menasource/egypt-s-new-anti-terror-law-an-in-depth-reading/, 登錄時間:2019年3月8日.新《反恐法》還賦予警察未經批準便可逮捕恐怖主義嫌犯的權力,而在口頭和文字上公開支持恐怖主義的行為將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46)Egypt Source, “Egypt’s Anti-Terror Law: A Translation,” Atlantic Council, September 3, 201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menasource/egypt-s-anti-terror-law-a-translation/, 登錄時間:2019年3月8日。
2017年以來,埃及政府的關注重點逐漸轉向“反暴力極端主義”的政策。盡管這些政策已在埃及社會中產生了積極效果,但在執行層面仍處于探索階段。塞西政府的去極端化政策是其反恐戰略的組成部分,旨在預防社會中潛在的恐怖分子,其重點在于修正滋生宗教極端主義的話語和宣教行為。埃及總統塞西不止一次提到修正宗教話語的必要性,指出宗教機構在這方面肩負重任。負責執行去極端化政策的埃及官方宗教機構包括愛資哈爾、教法判令機構、宗教基金部和2017年7月26日成立的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作為埃及最重要和最具影響力的宗教機構,愛資哈爾長期以來是政府指導埃及社會伊斯蘭事務的主要機構。對于埃及社會而言,愛資哈爾既是宗教機構,又是教育機構,其頒布的教令具有很高的威望,這些因素使愛資哈爾在去極端化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推行埃及政府的去極端化政策,愛資哈爾成立了“愛資哈爾對話中心”(Al-Azhar Dialogue Center)、“愛資哈爾打擊極端主義觀察站”(Al-Azhar Observatory for Combating Extremism)和“世界愛資哈爾畢業生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for Al-Azhar Graduates)等多個相關機構或網站。
2015年1月1日,埃及總統塞西發表新年全國講話,提到“埃及當前的恐怖主義是由于對宗教話語的錯誤理解”所致,要求“愛資哈爾盡快達成與當前轉型相適應且符合伊斯蘭溫和精神的宗教新話語。”同年2月,“愛資哈爾對話中心”成立,旨在促進多元化和跨宗教對話。(47)“The Grand Imam: For Eight Years, Al-Azhar Led the Battle to Spread Enlightenment and Combat Takfirism,” Al Ahram Online, March 3, 2018, http://gate.ahram.org.eg/News/1840932.aspx, 登錄時間:2019年10月9日。2015年6月,愛資哈爾大教長艾哈邁德·塔伊布發起成立“愛資哈爾打擊極端主義觀察站”網站。該網站受到阿聯酋方面的資助,通過8種語言監控世界各地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發展。該網站的建立使得愛資哈爾不再被動回應極端分子的話語攻擊,而是通過創建平臺主動收集極端分子和組織的言論并予以批駁。不僅如此,它還引發了埃及國內關于信仰問題的大討論,愛資哈爾通過該網站在埃及全境組織各類宗教知識普及運動。(48)E. De Lavarene, C. Williot and N. Bletry, “Top Muslim Body Al-Azhar Faces Criticism in Fight Against Extremism,” France 24, June 7, 2017,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70607-focus-egypt-al-azhar-mosque-university-online-observatory-islam-salafism-extremism, 登錄時間:2019年10月8日。“世界愛資哈爾畢業生組織”是2007年成立的非政府組織,本不屬于愛資哈爾的行政體系。該組織在埃及境內設有13個分支,在索馬里、乍得、馬里、肯尼亞和利比亞等國設有15個海外分支。該組織最重要的倡議是和埃及政府青年部合作在埃及各大城市開展去極端化工作。2017年,該組織發起對埃及邊境城市青年的培訓項目,旨在打擊極端主義思想的蔓延。邊境城市通常在埃及處于邊緣化地位,其經濟發展水平低,失業率高,極易受到極端主義的影響。邊境城市青年培訓項目主要針對來自北西奈、新河谷、馬特魯、紅海、哈萊伊卜和盧克索等邊境省市的青年。2017年該組織和埃及青年部共培訓了1萬名青年男女,專門邀請軍事學院的專家為邊境省市的青年解讀國家安全戰略。作為非政府組織與青年部的合作成果,這項針對邊境省份青年這一“脆弱群體”的項目突破了埃及傳統去極端化的模式,其培訓課程包括公民教育、國家安全和宗教宣導,體現了埃及政府去極端化的新思路。
愛資哈爾并不是埃及政府內部唯一負責去極端化的機構。2017年6月和7月,埃及北西奈、伊斯梅利亞和吉薩省先后遭遇恐怖襲擊。7月26日,塞西總統頒布2017年第355號總統令,宣布成立“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國家委員會”。2018年3月,埃及政府起草關于該委員會權責的法律,并提交議會審核,委員會自此更名為“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高級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的初衷是整合國家機構在去極端化問題上的努力,實現政策效果的最大化。根據上述草案,該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每五年設計一項反恐怖主義和反極端主義的國家戰略;為國家相關機構設計具體的反恐和去極端化政策、計劃、項目和倡議;提高民眾意識,為最易遭受極端主義影響的地區創造就業機會等。
埃及宗教基金部主要在兩條戰線上開展去極端化工作,既主導和監督每周五聚禮的演講內容,也監管全國清真寺的活動。上述兩項任務使得宗教基金部得以實現對宗教場所的結構性控制。2016年11月,宗教基金部決定建立監督全國清真寺的行政機構后,其監督范圍拓展至經堂教育、捐獻分配、清真寺的銀行賬戶等。該部還禁止極端宗教人士繼續宣教。至2015年,宗教基金部取消了5.5萬名埃及宣教人員的官方執照。(49)M.S El Din, “Dar Al-Ifta Aims to Control Fatwas Worldwide,” Mada Masr, August 19, 2015, https://madamasr.com/en/2015/08/19/feature/politics/dar-al-ifta-aims-to-control-fatwas-worldwide/, 登錄時間:2019年10月9日。與此同時,埃及境內的小清真寺(zawya)也被關閉或在宗教基金部核準資格后置于該部的直接監管下。(50)“A Court Supports the Decision to Entrust Mosques and Zawyas to the Authority and Superv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Endowments,” Aswat Masriya, February 2, 2016, http://www.aswatmasriya.com/news/details/59283, 登錄時間:2019年10月9日。這些遍布埃及尤其是農村地區和貧困社區的小清真寺,曾是20世紀80年代埃及伊斯蘭極端主義滋生的溫床。通過統一周五聚禮的演講內容,埃及宗教基金部有效修正了基層社區的宗教話語。(51)R. Ahmad, “The Unification of Friday’s Prayers in Egypt Ignites Debates in Its First Day of Application,” Al Hayet, July 16, 2016, http://alturl.com/jg7zg, 登錄時間:2019年10月9日。
埃及的教法判令機構主要負責發布教令,使伊斯蘭宗教教育更加靈活、包容和與時俱進。為推進去極端化工作,教法判令機構擴大了其在埃及宗教領域的存在。社交媒體是該機構傳播溫和宗教話語的重要工具,其通過“臉書”和推特官方賬戶與埃及社會頻繁互動。教法判令機構還成立了全球教法判令機構總秘書處,培訓來自全球各地的宗教人士,旨在使埃及成為伊斯蘭話語的中心,削弱極端宗教人士發布教令的影響力。(52)M.S El Din, “Dar Al-Ifta Aims to Control Fatwas Worldwide”.教法判令機構還向易受極端思想影響的社區派遣宗教學者,對已出獄的前極端分子實施康復計劃。(53)U.S. Department of Stat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2016, p. 35.對于政治參與度低的埃及穆斯林而言,教法判令機構是他們獲得宗教觀點最重要的來源。因此,教法判令機構與埃及社會的互動對提升去極端化效果具有積極意義。
四、 穆巴拉克和塞西政府的去極端化政策效果評估
“伊斯蘭團”的去極端化實踐表明,穆巴拉克時期埃及政府的去極端化政策通常依賴極端組織領導人和社會力量的調停,極端組織領導人個人放棄暴力的行為以及對組織成員的勸說會進一步推動武裝組織的集體去極端化。迄今為止,“伊斯蘭團”在同類組織中的去極端化最成功、成效最明顯,先后有1.5萬名“伊斯蘭團”武裝分子通過去極端化進程脫離了“基地”組織。(54)Omar Ashour, The De-Radicalisation of Jihadists, p. 2.盡管近年來西奈半島的恐怖襲擊仍處于高發狀態,但同“伊斯蘭團”并無關聯,如今90%的埃及人居住的尼羅河河谷地區的恐怖襲擊頻度較20世紀90年代已大為降低。2004年10月西奈塔巴地區和2005年4月愛資哈爾附近的恐怖襲擊發生后,“伊斯蘭團”曾予以公開譴責。由于以扎瓦希里為代表的“伊斯蘭圣戰”海外陣營和在埃及獄中的兩個分支不支持去極端化倡議,“伊斯蘭圣戰”的去極端化進程相對較晚。然而,該組織獄中成員被釋放后未再從事過恐怖活動。2011年“阿拉伯之春”發生后,“伊斯蘭團”成立“建設與發展黨”(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Party),“伊斯蘭圣戰”成立“伊斯蘭黨”(Islamic Party),兩者被正式納入埃及官方政黨政治的進程。
塞西時期埃及政府去極端化政策的特點是國家主導去極端化進程,弱化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塞西政府之所以強化國家在去極端化進程中的角色,原因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塞西政府需要在政治上與穆兄會爭奪宗教話語權,并得到阿聯酋和沙特兩大地區盟友的支持。2013年以來,埃及社會的極端化現象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許多伊斯蘭主義者為向軍方復仇而加入極端組織。可以說,塞西政府主導的去極端化政策呈現出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的特征,有時甚至將去極端化政策同反恐政策綁定。其次,“阿拉伯之春”后,伊斯蘭主義力量再度激進化和極端化,埃及政府意識到穆巴拉克時期通過社會調停達成的武裝組織集體去極端化成效的局限性。因此,塞西政府去極端化政策的目標轉變為通過修正宗教意識形態,徹底根除極端主義的思想土壤,而此類社會改革更需要國家機構的介入。與穆巴拉克時期相比,塞西時期埃及政府更加積極主動地開展與極端主義受害者的互動。對于潛在的極端主義受害者,埃及政府有針對性地派遣溫和的宗教人士進行宣教和引導。
盡管穆巴拉克和塞西時期埃及政府的去極端化措施都取得了積極效果,但對康復和補償環節的重視相對較低。去極端化不應止于監獄,大量放棄暴力的囚犯需要重新融入社會,埃及政府在這方面并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集體去極端化使得數千名前極端分子走出監獄后,面臨更加艱難的社會環境,尤其是工作和生活的壓力使得有人甚至要求重回條件更好的監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仍處在安全部門的監控之下,有時警官會幫助他們找工作或者提供少量援助,但埃及政府仍缺乏系統的康復計劃。埃及內政部前發言人拉烏夫·米納維曾呼吁政府協助被釋放的前極端分子就業,并提供心理和經濟援助。(55)Jane Harrigan and Hamed El-Said, “Group Deradicalization in Egypt: The Unfinished Agenda,” in Hamed El-Said and Jane Harrigan, eds., Deradicalising Violent Extremists: Counter-Radicalisation and Deradicalisation Programmes and Their Impact in Muslim Majority St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56.但是,經濟實力有限的埃及政府尚難以在高失業率的社會環境中為3萬名刑滿釋放的前極端分子提供就業機會。在伊斯蘭世界的去極端化項目中,埃及是少數未在極端分子意識形態去極端化后提供改善生活條件配套措施的國家。雖然這證明埃及的極端分子并非因物質獎勵而暫時放棄極端意識形態,但從長遠來看,缺乏康復計劃仍可能對埃及去極端化政策的持續性和有效性構成障礙。
五、 結 語
本文探討了穆巴拉克時期和塞西時期埃及政府的去極端化政策。穆巴拉克時期的去極端化政策強調極端組織領導人和社會力量的勸說作用,輔之以政府的武力鎮壓和選擇性激勵措施。極端組織領導層與去極端化進程的合法性密切相關,這些領導人有效推動了政府建立與極端組織基層成員的對話機制。同時,旨在影響組織領導人和基層成員的社會調停也是關鍵因素,并成為意識形態領域去極端化的重要推手。塞西時期,埃及政府的去極端化政策旨在配合軍警對極端組織的武力打擊,它更加強調由官方宗教機構推動意識形態改革,同時也增強了官方機構的宗教話語權。雖然埃及政府從武力和意識形態上削弱了伊斯蘭極端組織在埃及社會的影響力,但從長遠來看,去極端化政策的效果還取決于埃及政府是否能夠有效解決社會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