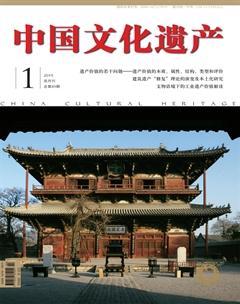遺產價值的若干問題
孫華


摘要:遺產價值問題是遺產保護學的重要內容,但目前遺產保護界在遺產價值的基本概念、本質屬性、要素結構和評價作用等方面,都還存在著認識的分歧,需要進行研討。遺產價值與價值哲學的價值一樣,是人這個主體與遺產這個客體發生聯系后產生的,屬于關系范疇而非實體范疇。人對遺產價值的認知具有主觀性,因而遺產價值也具有多樣性和變異性。遺產價值有內在存在價值和外在使用價值兩大類,前者包括年代價值,這是一切遺產外在價值的源泉;后者包括了歷史、藝術、科學等價值,兩者之間主要依靠精神情感進行關聯。遺產的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應該是遺產對現世科學技術和藝術審美的作用,藝術史價值和科技史價值都應歸屬歷史價值。遺產價值評估的意義,主要體現在遺產重要性的分級,以及遺產保護行動先后次序的安排上。
關鍵詞:文化遺產;自然遺產;遺產價值;遺產保護學
遺產的價值,尤其是文化遺產的價值,是遺產保護學的重要問題。遺產保護學家近年特別注重價值,除了申報文物保護單位、申報世界遺產需要提煉文物或遺產的價值外,編制各類文物保護規劃,或者編寫具體的保護方案,也要羅列文物/遺產的價值。實際上,文化遺產的價值是相當復雜的歷史問題和哲學問題,它既需要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對具體的遺產進行價值的發現、分析和解釋,也需要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對遺產價值的基本問題進行定義和闡釋,還需要遺產保護學、文化學和博物館學領域的學者來做遺產的價值保全、價值提煉和二次詮釋。由于目前遺產保護學界(包括文化遺產學和文物保護科學)對遺產價值的基本問題研究不足,在一些涉及遺產價值的基本問題上往往將復雜多樣的價值問題簡單化,不少習以為常的文物或遺產的價值評估,在不少方面都并不恰當。由于遺產的價值問題源于價值哲學,涉及面廣,有些關于存在價值和普遍價值的問題,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簡要討論。本文僅就遺產價值的屬性、關系、要素、體系、部分要素的含義以及文化遺產的價值評估方面存在的問題,談點筆者個人的思考。
一、遺產價值的基本屬性
“價值”(value)一詞據說來源于拉丁文valus(堤)、valallo(用堤護住,加固,保護),該詞本身就具有“可珍貴”和“值得重視且加以保護”的意思。按照通行的解釋,價值學(axiology)是人類生活中的價值及其意識規律和實踐方式的科學,是由哲學和各門具體科學關于價值的研究所構成的一門綜合學科。作為一門具體學科的遺產保護學,主要是由遺產類型學、遺產價值學、遺產保護學和遺產管理學四個方面所構成,其中的遺產價值既是遺產保護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也是構成價值哲學的多學科價值學的組成部分。
說到遺產的價值,離不開遺產的定義。我們給遺產的定義是:遺產是地球自然進化和人類發展過程中歷史積淀的精華,經由后人根據主流的價值觀有目的、有選擇地予以繼承或傳承的東西。在這個定義中,遺產之所以會被作為區域、國家(民族)或全人類的遺產,是與遺產這種事物被創造后人們的認識緊密相關。無論是自然演進的遺產,還是人類創造的遺產,它被“人”這種主體選擇后,本身就是作為人這個主體相對的客體而存在的。人們根據對自然或人類遺留的這個客體的認識,來決定它們是否是遺產、遺產的重要性以及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對待遺產。因此,人類對自然和文化遺留的認知和判斷,是遺產價值得以形成的關鍵。
遺產價值既然是人的一種認知,一種判斷,它就是人及其所認知對象“遺產”之間所存在的一種關系。這與哲學關于“價值”屬性的解釋完全一致,因為哲學范疇的價值正是一種社會關系而不是某種實體,價值是關系范疇而非實體范疇。為什么說遺產價值是一種關系范疇呢?除了哲學的價值定義外,我們從遺產價值的生成過程,也可以得到這個答案。
價值離不開主體即人和人的需求。在人產生以前,在人有需求之前,自然之物只有其內在的存在價值,還無外在的對人有用的價值。這些內在的價值離不開價值的承擔者,也就是相對于人的客體及其自然屬性,自然之物這個客體對人這個主體的作用是價值關系得以建立的客觀基礎。事實上,正是由于自然之物自身有能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屬性,因而它才能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東西。今天被人們認為是自然遺產的東西,如地質結構、自然地貌、古生物化石、動物和植物,幾乎在人類出現之前就早已存在了,它們本身作為地球自然演進的產物,與人尚未發生關聯,本身并無有用無用、重要不重要、稀少常見之類的分別。人類產生以后,隨著人類心智的發展和知識的積累,這些自然存在的東西被逐漸認為是有用之物而被人們獲取和消耗,人們會首先認識到這些自然之物的使用價值。自然之物的數量本來就有多有少,其分布還有地理上的不均衡,因而就會因珍稀而產生貴重的價值觀念,還會出現此地尋常而彼地珍稀的社會現象。隨著自然之物因為人們無限制地獲取或索取,有些原本很豐富的自然之物逐漸變得稀少甚至滅絕,這些自然之物的價值也就隨之提高,具有了稀缺的價值。而隨著人類科學的發展和認識的提高,人類會認識到這些自然之物對于認識我們賴以棲身的地球及其演變,乃至于認識人類自身,都具有意義,這些自然之物又具有了科學的價值。由于不愿意這些具有多種價值的自然之物消失,就會產生保存和保護這些自然之物的意識。人類從大量獵殺野生動物,逐漸發展為保護野生動物,就反映了這種從單純向自然索取轉變為保護自然的演變過程。
自然遺產如此,與人類誕生和發展同步的文化遺產更是如此。人類自制作工具開始,有了自己最初的創造物,這些創造物當然具有其滿足當時人們某種需求的使用價值。在人類尋找石料制作石器的過程中,一些如水晶、玉石等具有鮮艷色澤的稀少石料被發現并用作工具組件后,人們就會珍視這些器物,不會輕易丟棄;即便原有的使用者已經去世,人們也會將這樣的器具保留下來,遺傳下去,從而產生不同于對待一般器具的價值觀念和收藏觀念。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思維和社會的復雜化,人類開始創作沒有多少實際用途卻有某種抽象功能的作品,如人體上佩戴的裝飾、武器上的飾件、崖壁上的巖畫等,1990年代發現的法國肖維巖洞壁畫就是這樣的例子。再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在制作具有實際和抽象用途作品的同時,也開始創作“有意為之”的紀念物,創作“純粹的”藝術品。這些紀念物或藝術品缺乏實際的使用功能,其價值來自于創造它們的人們的賦予,而且它們的價值狀況恰恰與有具體用途的物品相反。那些為了某一具體用途而制作的物品,由于制作材料的老化,使用過程中發生的損壞,以及人們創造了更好的同類物品對原物品的取代,其使用功能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不斷減少;只是由于時間的流逝,這些物品逐漸具有了研究歷史的價值,并且隨著這些物品存世數量的逐漸稀少,可能還會產生“物以稀為貴”的稀缺價值。而那些只對特定人群有抽象的紀念意義而沒有具體用途的藝術品,其創作當初往往被賦予很高的“藝術價值”和“紀念性價值”。隨著人類社會的變化,人們對這些藝術品的價值認知也會發生變化。法國大革命時期及大革命后的一段時間,曾經發生有意破壞舊法蘭西王朝具有象征意義的建筑物和雕塑作品的現象;另外我國“文革”時期,在當時社會思潮下發生的對歷史文物大規模刻意破壞的事件,都是典型的例子。
上面我們主要對自然遺產和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產生過程進行了闡述,實際上,人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認識也是如此。有鑒于隨著人類社會快速發展和全球化浪潮,能夠體現地域性、族群性和傳統性的民間文化迅速消減,世界文化的多樣性逐漸喪失,世界有識之士紛紛行動起來,倡言民間文化、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過去被視為尋常事項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納入了人們保護的視野。
因此,無論是哪種類型的遺產(自然/文化、可移動/不可移動、紀念性/非紀念性、有意/無意等),其價值都與人這個主體有著密切的關聯,遺產價值是人這個主體對具有遺產屬性之物的一種意義的判斷。我們有些遺產價值的研究者將人、遺產和價值并列起來,將遺產價值分析為一種實體范疇,是不恰當的。正確的人與遺產和價值的關系應該如圖1所示。
二、遺產價值的生成原因
遺產價值是人這個主體與已經具有遺產資格的這些客體發生聯系后的產物,是人們判斷身外之物有用還是有害、重要還是一般的一種判斷。這種屬于主體與客體關系范疇的價值判斷適用于人們以外的一切事物,不僅限于遺產。那么,遺產價值與其他事物的價值有什么不一樣呢?人們判斷遺產的價值又與判斷其他非遺產事物的價值有何不同呢?我們繼續來分析這些問題。
當我們的面前放著兩件器物,一件是古代遺留下來的文物,一件是現代工匠仿模仿前者制作的工藝品。后者采用了與原作完全相同的材料,外部造型與原作一模一樣,裝飾和色澤與原作也幾乎沒有差別,就連歲月的痕跡也與原作惟妙惟肖(當代的作偽者甚至使用與仿制對象年代相應的木材來偽造漆木器,采用科技手段使得現代燒制的瓷器具有古代瓷器的測定數據)。然而,前者卻具有很高的價值,以至于無法用市場價格來衡量,因而被所有者精心保存和保護,希望能留傳后世;而后者卻只有很低的市場價格,因而被所有者隨意處置,不為他們所重視。這是什么原因呢?簡單的回答是,這是真假之間的價值判斷,文物因其真,故價值高;贗品因其假,故價值低,甚至幾乎沒有價值。誠然,真實與虛假,這是決定遺產價值的首要判斷標準。也正由于這個標準,在某項文化遺產申報世界遺產時,申報文本中就需要有真實性的聲明。不過,如果我們再繼續設問,為什么真的古物價值就高,假的仿品價值就低?這就涉及到了奧地利藝術史家李格爾(Alois Riegl,1858-1905)所倡言的文物的“新物價值(newness-value)”和“年代價值(age-value)”。李格爾將紀念性文物的價值區分為多個要素,其中“年代價值”是他最為關注的價值要素,他認為文物保護的一切矛盾都與如何對待文物的“年代價值”有關,這無疑是相當重要且恰當的。我們這里借用李格爾的兩個概念,對這兩個概念重新定義,以分析文物價值生成的邏輯過程。
我們先看“新物價值”。李格爾認為,新物價值體現在一件作品的完整性及其呈現的藝術風格的純粹性。他將這種新物價值的概念,既用以描述今人基于“現世價值”鑒賞古物時產生的“藝術價值”,也用以描述在維修建筑遺產(尤其是宗教建筑遺產)時,某些宗教人士所持的那種以新換舊的價值觀念。不過,在筆者看來,新物價值是人們創造制作新事物時具有的價值,這種價值普遍適用于一切事物的“價值一般”。新物價值不僅存在于事物被剛剛創造和制作之時,也存在于事物的使用過程中(當然在這個新物逐漸變為舊物的過程中,新物價值也在逐漸降低),當然還存在于舊物或古物在維護或修繕過程中的“修舊如新”的行為中。新物價值的產生主要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物所使用的材料是否貴重珍稀,例如商周青銅器,鑄造之初這些象征著身份、地位和財富的新銅器就受到十分珍視,因而在銅器銘文中要有“子子孫孫永保用”之類的文字。二是新物所包含材料和勞動的多少,有些新物因人們付出了巨大的勞動和財物,如集建筑、雕塑和裝飾于一身“紀念碑”,新建時就具有“紀念碑性”的價值。三是新物的實際使用功能所具有的價值,也就是當時制作這些物品就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某種需求。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技術和審美藝術的變化,多數物品的使用功能會逐漸減弱甚至消失。仿照文物制作的贗品,在仿制當時屬于新物,當然也具有新物價值;但由于仿制品已經脫離了所仿文物的社會和技術環境,已經失去了其實際使用功能和原先的審美功能,其新物價值反而低于被仿文物當初設計制作時期的新物價值了。
接著我們來看“年代價值”。李格爾這樣解釋文物的年代價值:“年代價值要求對大眾具有吸引力,它不完整,殘缺不全,它的形狀與色彩已分化,這些確立了年代價值和現代新的人造物的特性之間的對立”“完全不考慮各種因素,而是作為一個準則、單一的現象,僅僅是珍視主觀的感受。”由于年代價值與其他價值要素相比,有著超越受教育程度的、從修養和藝術理解的優點,即使“頭腦最簡單的農民也能區分一座古老的鐘樓與一座新建的鐘樓”價值的不同,因而至關重要。由于年代價值是歲月的流逝形成的,帶上了往昔歲月的痕跡,歲月是時間的代名詞,時間將“財產”造就為“遺產”,也賦予遺產年代的價值。經歷了時間洗禮的事物,它們逐漸減少或失去新物的價值,卻不斷增加年代的價值,使得這些事物從一般“新物”轉變為“文物”甚至“古物”。真實的文物或古物是距離現在已經有了相當時間計量的物品,其內在價值主要包含了年代的價值,因而受到人們的珍視,只要這些文物不徹底損壞,其年代價值就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或消失。相反,那些現代假冒的文物仿品,其內在價值中沒有包含古物價值中的年代價值這個關鍵的價值要素,新物價值中又缺乏了實際的功用價值,所以人們在進行價值判斷的時候才會將其看得很低。當然,一件本來缺乏年代價值的仿制古物,如果它又經歷了歲月的洗禮,它也就具有了年代價值,從只具有少許外在使用價值的新物演變為具有年代價值的古物。北宋張擇端創作的《清明上河圖》是一件具有很高古物價值的繪畫作品,后來有不少人臨摹甚至作偽,但如果一件明清時期臨摹或偽作的《清明上河圖》留傳至今,它們也就具有了年代價值,成為了價值較高的文物;如果這幅明清時期臨摹的《清明上河圖》是當時的著名畫家所作(如明仇英摹《清明上河圖》等),那么它在臨摹的當時就因系大師之作而具有了“經典價值”,留傳至今更兼具經典價值和年代價值,所以會被各大博物館視為珍品收藏。
遺產所蘊含的年代價值造就了遺產,確定了遺產不同于新物的價值,同時也帶給遺產了其他一些重要的關聯價值要素。下面繼續以文物為對象分析這些關聯價值。
文物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距離后,由于自然和人為因素的侵襲,其材質有可能會逐漸老化,形態有可能變得不完整,色澤可能也變得斑駁,給人以飽經歲月滄桑的感覺。隨著時光的流逝,尤其是經歷了戰火等人為的毀壞,有些文物被徹底摧毀,有的文物部分毀壞,還有些文物保存得相對完整。在同類文物中,那些損壞程度較小的文物,自然就受到人們更多的關注,認為它們的價值高于那些損壞嚴重的文物,這就產生了文物的“完整性價值”。這種完整性價值,小的方面可以體現在藝術品市場上的古董交易,體量、形態、裝飾相同的兩件同類古物,完整的那件估價較高,殘缺的那件估價較低;大的方面就體現在不可移動文物上,《實施<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就對申遺項目有完整性闡述的要求。完整性與真實性一樣,是遺產價值的要素之一。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文物歷經的時間越長,遇到的人為和自然變故就越多,保留下來的數量也就越少。有些當初或早些時候的尋常之物,久之也會變得稀罕,這就會產生文物的“稀缺性價值”。例如山西五臺山的南禪寺大殿,在晚唐時期不過是五臺山偏僻的南臺一座小廟中的三開問小殿,只由于它躲過了歷史上的水火之災和后人的重建,成為保留至今最早的木構建筑。古老的年代所帶來的稀缺性價值,使得這座小小的木構建筑成為我國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隨著五臺山申遺的成功而成為五臺山世界遺產的組成部分。文物經歷這種歲月所發生的變化,還會使其具有不同于新物的特殊風貌。由于人類與生俱來的懷舊情感,這種顯示過去時光特征的往昔之物,足以勾起人們對往昔的追憶和懷念,使得這些文物產生所謂“歷史紀念性”。某些非紀念碑性的文物,當初創造或制作這些物品時,人們并沒有賦予它們“紀念性“,屬于李格爾所說的“無意為之”的物品,這種因時間產生的懷舊情感所帶來的紀念性,可以視為因年代價值衍生的歷史紀念價值。關于紀念性價值,涉及的問題比較復雜,已有許多學者討論,這里不再贅言。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遺產之所以具有不同于一般事物的獨特價值,主要是在于其內在的年代價值,正是這種價值要素造就了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稀缺性和無意為之的歷史紀念性等價值要素。可以說“年代價值”是遺產一切往昔價值和現世價值的源泉。
三、遺產價值的多樣性
遺產的價值,無論是自然遺產的價值還是文化遺產的價值,既然是與人發生關系后才出現的觀念,是人們關于這些客觀存在的事物對自己有用性的判斷。那么,不同的個人,不同的社群,不同的族群,乃至于不同的國家,他們對于同樣事物的價值判斷可能就會不同。李格爾早已注意到,同樣是教堂的修繕,有教養的城市牧師和居民注重保存文物,“他們對年代價值最為敏感”;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鄉村牧師和居民,他們是“新物價值最頑固的提倡者”。這是人們對遺產價值認知差異性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人或人們都具有社會性,這種社會性隨著時代前行還會發生改變,人們對遺產的看法當然也會發生變化。因此,遺產的價值不會是凝固的和一成不變的,人們對遺產價值的認知會隨著認知水平的發展、所處社會環境狀況的變化、以及對某項具體遺產研究的深入而有所不同。這兩方面的差異性,就會導致遺產價值的多樣性和可變性。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對遺產價值的不同認知,就要有一種包容的態度,不能因為我們強調遺產的一些主要價值,就否認遺產還具有其他價值。
遺產作為一種地球演變和人類發展的客觀存在,它首先具有其“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也就是非使用價值。按照哲學家的定義,所謂內在價值是事物本身內在固有的、不因外在的其他相關人或事物而改變的、以存在價值(Existence value)為主體的價值。就遺產來說,也就是包括其存在時間和空間在內的遺產的存在價值,我們前面重點討論的遺產的“年代價值”,實際上應該就是遺產內在價值的時間價值。這種由于時間形成的遺產價值,不因為面對遺產的主體“人”及其所在社會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受其他環境和關系的影響而增減,它是一種客觀存在。李格爾對遺產價值分析的最大失誤,就是將時間所致年代價值當成了人對遺產認知的主觀價值,卻將具有主觀性的歷史價值當成了客觀價值。李格爾這樣解釋年代價值與歷史價值的區別:“歷史價值是以客觀的方式識別不同的事件,而年代價值不區分地方性特色,不考慮紀念物的客觀特性,也就是說,年代價值僅僅把紀念物的特殊性整合到普遍性當中,因此主觀效應替代了其客觀特征。”李格爾認為年代價值具有主觀性,這又源自于他關于年代價值的另一個失誤,那就是他將年代本身與年代賦予遺產(包括紀念物在內)的歲月痕跡和懷舊情感混在了一起。遺產的歲月痕跡會使得人們產生懷舊的情感,而這種懷舊情感,與人和遺產的關系、人們的文化背景、乃至于個人的經歷與體驗等,都是分不開的,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因此,認識李格爾關于年代價值解釋的誤區,分清客觀的年代價值本身與年代所衍生的其他主觀價值,是我們閱讀李格爾首先應當注意的問題。
遺產的內在價值既然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價值,那么,它就會與遺產的“普遍價值”聯系起來。遺產保護學界(尤其是從事世界遺產申報的工作者)都耳熟能詳的遺產“突出普遍價值”(OUV),究竟是遺產的什么價值,恐怕許多遺產研究者都沒有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實際上,“突出”的價值,是世界遺產要求的不同于一般遺產的特殊價值,這種價值是一種主觀價值,因而需要遺產地的人們對提名的遺產進行價值研究、發掘和歸納,提煉出其中能夠反映其重要性和獨特性的價值;而“普遍價值”則是存在于所有遺產的以年代價值為核心的價值,是一種獨立于主體之外,不受個人、社群、文化、國家影響的普適價值,是一種客觀存在,因而也是不受遺產評估專家左右的為所有人都認可的價值。UNESCO倡導世界遺產概念的專家將“突出”的獨特價值與“普遍”的共有價值這兩個概念捏合起來,形成了“突出普遍價值”這樣一個具有矛盾統一的概念,其用心良苦,可以理解。不過,使人不能理解的是,我們不少人將以西方為主流的特殊價值當作了普遍價值,回避或批評普遍價值,這顯然是將應該評判的對象搞反了。遺產的普遍價值是一種客觀存在,無須也難以進行評判,遺產保護領域對遺產進行評價,評價的對象都只能是具有主觀性的特殊價值或獨特價值。
遺產的價值評判,是人這個主體與遺產這個客體發生關系后,人們對遺產的有用性或重要性的一種判斷。可以這樣說,我們所說的遺產價值,除了遺產內在客觀存在的年代價值等要素外,幾乎都是主觀價值。人們對遺產的這種價值,基于自己的愛好和需求有不同的取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包括藝術史家)和歷史愛好者關注遺產所傳遞的歷史信息,自然就偏重于倡言遺產的“歷史價值”;藝術家和藝術品愛好者關注遺產的各種美感元素,自然也就大力弘揚遺產的“藝術價值”;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關注遺產所記錄的與今天科技相關的某類信息,以便為他們的科學研究和工程技術提供長時段的數據。除了這些被遺產保護學界視為遺產的“基本的”或“重要的”價值外,傳播學家、旅游專家和遺產地政府及公眾希望有更多的人們知道并來參觀遺產,他們關心的則是遺產的“經濟價值”和“品牌價值”。遺產還會給當地居民某種權屬的感覺,使他們因某種形式的“擁有”而產生自豪感,從而賦予遺產以“象征價值”;遺產也會給參觀游覽的外地客人產生賞心悅目的愉悅感,或從中獲得知識的滿足感,從而使遺產又有了“娛樂價值”和“教育價值”。總之,遺產外在的主觀價值是多種多樣的,絕不會因為遺產保護學界不喜歡這些價值而不存在。有的學者強調文化遺產只有歷史、藝術、科學“三大價值”,而否認其他方面的價值,這是沒有必要的。這些否認往往是出于對文化遺產受到其他因素干擾而招致損害的擔憂,2015版《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中的“社會價值”也的確給人內涵和外延不清的感覺,但從遺產主體與客體關系來看,從遺產本身的多樣性和認知主體構成的多樣性來看,文化遺產的價值無疑是多樣的,不會僅限于歷史、審美(藝術)、科學“三大價值”。
當然,我們認同遺產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包括時下一些地方政府或遺產地管理者所說的利用價值(如發展旅游等),并不等于說我們贊同將這些價值要素作為遺產保護需要首先考慮的因素。人們之所以要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更多是為了滿足精神和文化需求,包括歷史的認知,科學的借鑒,藝術的體驗,心靈的陶冶等。杜曉帆指出,“過去的遺存之所以被視為文化遺產,從客觀上來講,就是它和原生社會文化環境產生了分離,進而來到了當下的語境,成為了一項有待保護和繼承的文化資源。”“如果我們再往前追溯到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也會發現,人們在對古希臘羅馬文化遺產的追尋過程中,本質上體現的是一種人文關懷,滿足了人們重新認識自我的精神需求。從一開始,過去的遺存作為文化遺產進入到人們的視野當中時,首先滿足的是人類的精神需求。”遺產的價值是由許多方面的要素組成的,要保護好包括文化遺產在內的人類共有的遺產,關鍵是在遺產價值評估時,要將哪些價值要素排在前面,而將哪些價值要素排在后面的排序問題。正確的遺產價值要素的排序,是遺產價值評估與遺產保護行動之間的重要關聯環節。
四、遺產價值的要素結構
遺產價值既然是多種多樣的,具有不同的價值要素或價值類型,那么就涉及到了遺產價值要素的層級階元,遺產價值要素問的相互關系,以及全部遺產要素組合而成的遺產價值結構體系。關于這個問題,遺產價值學的先驅李格爾早就有過分析,當今的遺產研究者也作了很多探討,但距離構建一個完善、邏輯關系清晰的遺產價值體系仍然存在距離,還需要繼續研究。
李格爾提出了一系列與遺產價值要素相關的重要概念,他提出這些概念是為了論述“紀念物的現代崇拜”這一主題,探討這些價值因素與保護之間的關系,并非為了構擬全部遺產的價值系統。因此,有多位遺產的研究者根據李格爾遺產價值的論述,對李格爾的價值要素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梳理,試圖更加條理化地理解李格爾心目中的遺產價值體系。按照這些梳理結果,李格爾的紀念性遺產的價值要素首先被按照時間軸線先劃分為“往昔價值/“紀念性價值”(past values)和“現世價值(Present-day Values)”,其中往昔價值又分為“歷史價值(historic value)”和“歲月價值(age-value)”,現世價值又分為“使用價值”(use-value)和“藝術價值”(art-value)”,此外藝術價值還可繼續細化為“新物價值”等。李格爾關于遺產價值的論述并不全面,他所針對的只是具有紀念性的(他又將這種紀念性區分為“有意為之”和“無意為之”兩種)的“紀念物”,因此他對自己提出的價值要素的概念、概念的定義、以及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的闡釋也還存在誤區,所構擬的遺產價值體系還不夠完善。
在李格爾以后,遺產保護學界對于遺產的價值要素和分類又有多種闡述,除了平行羅列多種價值類型的不那么嚴密的表述外,其他具有分類層級和結構的遺產價值分類不外乎兩種:一是基于遺產價值的使用功能的分類,二是基于遺產價值的空間結構分類。這些遺產價值研究的學者,如同李格爾一樣,多將遺產價值的類型要素及其關系與遺產保護和管理結合起來,體現了遺產類型學、遺產價值學與遺產保護學和管理學的關系。在分析遺產價值要素,構建遺產價值體系時,的確需要首先樹立將遺產保護作為這種研究目的的思想;不過在具體分析過程中,還需要緊扣哲學價值論的基本原理,才能構擬出合理的遺產價值體系。
當今世界,遺產保護學界也越來越關注遺產的使用價值,尤其關注遺產的經濟價值。蘭德爾·梅森(Randall Mason)在《文化遺產的價值評估》一書中將文化遺產的價值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社會文化價值”,另一類就是“經濟價值”。前者包括了歷史價值、文化/象征價值、社會價值、精神/宗教價值;后者則包括了使用(市場)價值、非使用(市場)價值、存在價值、選擇的價值、贈與的價值。尤嘎·尤基萊托(Jukka Jokilehto)在《價值與遺產保護》之中,也將文化遺產劃分為“文化價值”和“現代社會——經濟價值”兩大類,文化價值包括了身份、相關的藝術/技術價值、稀缺價值,現代社會——經濟價值則包括了經濟價值、實用價值、教育價值、政治價值、社會價值。將經濟價值從遺產使用價值的一個要素擴展到遺產價值的兩個大類之一,將使用價值、非使用價值、存在價值納入經濟價值(或將實用價值納入經濟價值),都不大符合價值哲學。在這方面,我國一些學者關于遺產價值要素和價值體系的闡述,顯然更加合理一些。
從遺產的功能形態分析或闡述遺產價值的學者,如王秉洛從價值功能的角度將世界遺產的價值概括為:直接實物產出價值、直接服務價值、間接生態價值和存在價值四個方面;梁學成則從旅游資源系統的角度出發,將世界遺產價值分為有形(顯性)價值和無形(隱形)價值兩個大類,旅游價值、科考價值、文化價值和環境價值4個亞類。但較成體系的還是余佳以可否定量為標準所對遺產價值要素的分類,以及陳耀華等以本底還是衍生為標準所構擬的遺產價值體系之樹。我們這里著重對這兩種遺產的價值體系進行分析。
余佳將文化遺產劃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是“由文化遺產區別于一般物品的特性而產生”的不可定量的“存在價值”,第二大類是在文化遺產開發利用中產生的可以定量的“使用價值”。前者又可以劃分為“歷史價值…文化審美價值”“科學教育價值”和“情感價值”四類;后者則可劃分為“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兩類。余佳所說遺產的“存在價值”,系指遺產獨特性和不可再生性所決定的一般物品所不具備的價值,實際上主要就是年代價值,因為往昔的遺產對于現世的人們來說,盡管可以再造完全相同的形式,卻不能賦予它已經過去的時間,這種遺產獨有的存在價值是可以成立的。不過,作為遺產存在價值的時間或年代,這恰好是可以定量的,并且將遺產的歷史、文化(審美)、科學、教育價值納入遺產內在的存在價值,這也顯然欠妥。因為這些價值要素都是外在于遺產的,應該歸屬于遺產使用價值的范疇。遺產的使用價值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不能定量的價值,歷史、藝術、科學等都屬于這一類;另一部分使用價值是可以定量的,如遺產的“經濟價值”等。如果將遺產的不可定量的使用價值從存在價值改移到使用價值中,就與價值哲學的基本原理相吻合了。
陳耀華和劉強基于系統論的理論,認為中國自然文化遺產價值體系是由“本底價值”“直接應用價值”和“間接衍生價值”兩個層面、三個大類的價值所構成,其中本底價值包括了“歷史價值”“美學價值”“科學價值”等,直接應用價值包括了“科學研究”“教育啟智”“山水審美”“旅游休閑”等,間接衍生價值包括了“社會促進”“產業發展”等價值。陳耀華等構擬的價值體系具有明顯的層次性,其中本底價值是所有價值存在的基礎,這決定了遺產資源必須在保護的前提下才能合理利用;該體系也有空間性,三種價值主要分別存在于遺產地范圍以內、遺產地及相鄰區域、遺產地范圍以外的更大的區域(圖2)。陳耀華等構擬的遺產價值體系,可以視為對整個遺產價值體系的一種空間架構。在這個構架中,本底價值決定了應用和衍生價值,二者是從屬的關系,這自然有助于強調遺產“三大價值”的重要性;然而,從遺產主體與客體、內在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基本關系來看,歷史、美學、科學這遺產價值要素與其他價值要素一樣,仍然都屬于使用價值的范疇,它們應該是并列關系而非領屬關系。如果要說遺產的“本底價值”的話,遺產內在的以年代為核心的普遍價值,倒是可以視為遺產的本底價值,它才是遺產其他使用價值產生的基礎。
筆者認為,遺產的價值如同所有事物的價值一樣,都應該劃分為內在的存在價值和外在的使用價值兩大類。存在價值的構成要素包括時間價值、空間價值和其他最基本的遺產生成的要素,其中最核心的要素則應該是時間所構成的年代價值。使用價值則包括了不可定量的相對抽象的情感價值、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和藝術價值,以及可以定量的經濟價值等。在遺產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之間,內在價值的年代價值與外在價值的情感價值最為緊要,年代產生了懷舊等情感,正是這種情感使得人們有了探尋歷史的興趣,有了與往昔藝術品之間的共鳴,產生了收藏這些文物或參觀這些遺產的想法和行為。因此,遺產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乃至于教育價值和經濟價值等價值要素之所以能夠成立,都與遺產的情感價值分不開,情感價值是遺產內在的存在價值與外在的使用價值問聯系的主要紐帶。
五、遺產三大價值的含義
在遺產的價值構成中,最經典的價值要素或類型莫過于“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這三大價值,幾乎所有對文化遺產的價值認知都要設法提煉這些價值。然而,遺產保護學界對于遺產“三大價值”的理解卻存在偏差,絕大多數遺產保護學家都將歷史價值以外的“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當作了與現世價值無關的往昔價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現在文物價值評估所歸納的所謂藝術和科學價值,實際上都屬于歷史價值的范疇,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當另有所指。
(一)遺產的歷史價值
“歷史”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歷史是指客觀世界發展的過程,既包括了自然世界的發展演變,也包括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1964年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形成的《關于古跡遺址保護與修復的國際憲章(威尼斯憲章)》開篇中說,“世世代代人民的歷史古跡,飽含著過去歲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為人們古老的活的見證”,說的就是文化遺產的狹義的歷史價值。如果按照狹義歷史的定義,歷史價值就只是人類創造和遺留的文化遺產的一個價值要素。
文化遺產的歷史價值與遺產的年代價值密切相關,但二者并不等同。年代價值是遺產價值的內核,它是其他遺產價值得以產生或成立的基礎。由于年代是由時間構成的,它與空間一樣是中性即客觀性的概念。歷史則不是這樣,盡管將歷史作為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過程,這種已經發生的人、事和場所都是往昔的客觀存在,但這種存在已經隨著時間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今天的人們去探索和研究過去的歷史,包括使用過去遺留下來的物證去追尋歷史,都帶上了我們當下認識的主觀色彩。關于歷史的主觀性,意大利的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有“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英國的歷史學家科林伍德(R.C.Collingwood)也有“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論斷。就如同人們對待歷史一樣,我們對遺產的認識也必將打下我們個人、時代、地域、文化的烙印。
歷史既然不全然是客觀的,我們通過研究文化遺產所抽繹出來的歷史價值自然也不會是完全客觀的,這與遺產的年代價值有所不同。與歷史研究一樣,由于歷史和歷史價值具有強烈的主觀性,不同的個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和教育背景的研究者,他們對歷史或遺產歷史價值的認知肯定有所不同。正是由于這種不同,才使得包括遺產歷史價值研究在內的歷史研究,有了吸引研究者的無窮魅力。
遺產的“歷史價值”這個概念,當下遺產保護學界對其的定義和在具體遺產歷史價值闡釋中的運用,是基本得當的。蔡靖泉這樣解釋歷史價值:“文化遺產是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活動中創造的財富遺存,因而其基本的特征就是歷史性,其首要的價值也是反映歷史、補正歷史和傳承歷史的價值”。我們知道,在歷史研究中,通過充分的史料以獲取歷史的事實,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史料主要由三大部分組成,一是歷史上留傳下來的典籍文獻,二是包括考古材料在內的物質文化遺存,三是包括民族志在內的非物質文化事項,所有這些,都屬于文化遺產的范疇。保護了這些文化遺產,也就保存了歷史的史料,今人乃至于后人就可以據以考證往昔的歷史事實,研究這些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和發生背景,品評歷史上人物和事件的功過得失,乃至于歸納總結出供今人借鑒的經驗教訓。
由于關于遺產的歷史價值,目前遺產保護學界認識的歧義最小,這里不再多言。
(二)遺產的藝術價值
關于遺產的藝術價值,目前中外研究者都存在一些不正確的認識。例如,奧地利學者B·弗拉德列認為,建筑遺產的藝術價值包括最初形態的概念、最初形態的復原等“藝術歷史的價值”,也就是,“藝術質量價值”,以及包括古跡自身建筑形態的直接作用與古跡相關的藝術作品的間接作用在內的“藝術作品本身的價值”三個方面。弗拉德列所列舉的藝術價值的三個要素,有些價值顯然應該歸屬于歷史價值而非藝術價值,如“藝術歷史的價值”;有些價值如“藝術品本身的價值”究竟屬于什么類型的價值,弗拉德列也交代得不夠清楚。顯然,這種對遺產藝術價值的闡述不可能令人滿意。秦紅嶺認為,“建筑遺產保護中所指的藝術價值,主要是指遺產本身的品質特性是否呈現一種明顯的、重要的藝術特征,即能夠充分利用一定時期的藝術規律,較為典型反映一定時期的建筑藝術風格,并且在藝術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審美感染力。”秦紅嶺所列舉的這些遺產藝術價值要素,既包含了遺產的藝術史價值,也包含了遺產的“審美感染力”的美學價值,顯得有點混雜。
那么,什么是遺產的藝術價值呢?一般認為,藝術價值是指藝術品或藝術形式對于藝術的有效性,反映了遺產本身對人類藝術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因此,遺產的藝術價值必然是與當下審美和藝術創作相關的價值取向,屬于當下的現世價值而非往昔的藝術史價值。正如李格爾所說,藝術價值必須是當下的,不存在超驗的或者是永恒的狀態。遺產的藝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反映了不同社群和文明所具有的獨特的傳統審美取向,說明其審美水平和藝術表現力得到了古今不同時代,甚至現今不同地域人們的認可和傳承。例如我國古代的書法作品,至今仍然被我們所欣賞,有的人天天都還在臨摹古人的書法杰作,古代法帖的印刷品仍然是銷售最為廣泛的書刊之一。
二是反映了人類追求藝術本源,返璞歸真的心理訴求,可以糾正經歷了多次藝術變革后的異化的藝術形式,從而使藝術的發展既豐富多彩又不失本真。例如14~16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通過對中世紀以前的希臘和羅馬的文學藝術的“復古”,表達新興社會力量對當下的不滿和變革的訴求,糾正并改變了中世紀以來僵化的思想和藝術,促進了思想的解放和藝術的繁榮。
三是可為當代藝術家激發創作靈感,提升藝術創作力,為藝術的變革和發展帶來重要的啟示。例如陜西興平霍去病墓前的西漢石雕,我記得在1980年代的雜志上曾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雕塑家在參觀陜西興平縣的霍去病墓后的觀感,他認為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正是現代雕塑家藝術的追求。1980年以后,我國雕塑創作趨于多樣化,這盡管是改革開放的大勢所趨,但我國古代藝術對當代中國藝術的繁榮,無疑也起到了啟迪作用。
從上述遺產藝術價值的體現方面來看,我們對遺產藝術價值的評價一定要與當今審美、鑒賞和藝術創作結合起來,要反映遺產對現實藝術的作用,否則就會與遺產的歷史價值發生混淆。
(三)遺產的科學價值
遺產的科學價值,全面地說,應該是遺產的科學技術價值。科學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技術泛指根據生產實踐經驗和自然科學原理發展而成的各種工藝操作方法與技能。遺產的科學價值是指遺產本身的信息有助于當代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運用的遺產價值和意義的構成要素。2015版《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將科學價值定義為文物古跡作為人類創造性和科學技術成果本身或創造過程的實物見證的價值。王巍和吳蔥已經指出,“上述定義都將科學價值視為一種實物見證,如見證人的創造性、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革新,或促進其他學科發展的卓越成果等。如果科學價值只是一種實物見證,那么應該被歸為科學技術史上的價值,即從屬于歷史價值,而不是和歷史價值并列存在,所以這種角度的定義值得商榷”。王巍等的批評意見是中肯的。
秦紅嶺以建筑遺產為對象來闡述遺產的科學價值。她先給科學價值下了一個定義,“所謂科學價值,主要指建筑遺產中所蘊含的科學技術信息”。這當然是正確的。但她又解釋說:“不同時代的建筑遺產一定程度上代表并體現著當時那個時代的技術理念、建造方式、結構技術、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藝,進而反映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成為人們了解與認識建筑科學與技術史的物質見證,對科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秦紅嶺解釋的科學價值又回到了建筑技術史的價值上,實際上說的仍然是歷史價值,正如她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說:“從更廣的視角看,建筑遺產所蘊含的科學技術信息,不過是建筑遺產所攜帶的歷史信息的一部分”。建筑遺產當然有歷史價值,但如果進而認為“科學價值實質上是歷史價值的一種具體表現”,卻又有以偏概全之嫌。
綜上所述,“科學技術價值就是指事物所具有的探求客觀真理的、揭示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用途,是指根據生產實踐經驗和自然科學原理發展成的能夠指導人們改造世界的各種工藝操作方法與技能所具有的積極作用。”遺產的科學價值也是如此。正如王巍等指出的那樣,應該“將科學價值定義為一種現今的價值,即服務當今社會的價值,與歷史價值區分開來”。遺產的科學價值也主要分為三類:
一是如某些自然遺產,本身可以作為當代科學研究的對象或材料,具有科研資料的價值。如自然遺產中動物棲息地的支撐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某些地質現象可作為研究地球演變的資料,史前動物化石和人類化石是研究動物和人類進化的主要對象等;這些作為地球、地質、地貌、植物、動物和人類自身科學研究的重要資料,當然具有科學價值。
二是如某些地質遺產、天文遺產、水文遺產、災害遺產等,它們是需要長時段積累觀測數據的科學研究門類的重要資料,具有科學數據的價值。重慶涪陵區的白鶴梁題刻中的古水文題刻,是古人長期觀察枯水水位的記錄,其枯水水文數據對當今認識長江千年以來的最低水位、長江水位的變化規律、以及北半球氣候的變化等都有意義,因此具有科學價值。
三是如某些礦山遺產、水利遺產和工程遺產,可以為當代工程的基礎,或作為當代科學技術的借鑒和參照,并在當代仍然可以繼續沿用。始建于戰國時期的四川都江堰水利樞紐工程,自從建成以后就一直發揮著作用,使得四川成都平原成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的天府之國。都江堰的分水調節、灌溉系統和管理模式至今還運行正常,并還在繼續擴展和完善。這也是遺產科學價值的一種體現。
按照上述遺產科學價值的定義,我們可以知道,在文化遺產中,只有較少的一部分具有科學價值。在當下的文化遺產價值評估中,最容易將歷史價值與科學價值和藝術價值混淆的遺產類型是古代建筑。古代建筑盡管是歷史上一定時期人們建筑技術和藝術的結晶,但這些都是從事建筑科學技術史或建筑藝術史學者所要研究的內容,是這些古代建筑的歷史價值,不是科學價值和藝術價值。不恰當的建筑遺產的價值評估,應當予以修止。
六、遺產價值評估的作用
遺產價值學是分析自然和文化遺產的存在價值、價值要素、價值構成、價值闡釋以及如何保持其價值的學問,它是遺產保護學的基礎。遺產價值學在遺產保護中的重要意義,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對于遺產價值在遺產保護中的具體作用,遺產保護學界的認識卻似乎也存在偏差。在不少研究遺產價值的論著中,都把遺產價值與遺產保護的方法和技術關聯起來,認為對文化遺產價值的認知會影響和制約遺產保護方法和技術的采用。這種認識是不盡準確的。遺產保護的方法和技術的使用,主要是基于不同類型遺產所具有的特點,針對不同類型和不同個例遺產所出現的危害因素,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的保護方法、技術和管理措施,與遺產重要性的價值評估沒有必然的關聯。在已經認識到了某一遺產重要的情況下,編制其保護規劃、制定保護方案、以及實施保護工程時,重復進行遺產價值的評估已經沒有多大必要,除非保護者對于需要保護遺產的價值有新的認識,以及該規劃或方案涉及到遺產價值要素的先后排序等問題的時候。
我們這樣說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慮。
首先,無論是地區一級的、國家一級的、還是世界的文化遺產,只要同一類型的遺產,其基本的保護方法與技術都是差不多的。而不同類型的遺產,不同遺產的價值取向,以及不同的病害情況,才會影響到我們的保護方法和技術。例如,文化景觀類型的遺產,是兼具物質和非物質文化的“活態”遺產,保護文化景觀不是為了保護其現有狀態,而是要保持其文化的延續性。那么,歷史城鎮、傳統村落、神山圣地等類型的遺產,其價值之一就是延續性價值,需要采取不同于遺址、建筑、石刻這樣的方法和技術來維持這種價值。
其次,由于價值研究是很復雜的科研課題,就文化遺產來說,往往需要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建筑史學家、藝術史家、技術史家等對遺產進行研究分析,不斷發現和提煉遺產的價值。文物保護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們針對遺產本體劃定保護范圍并提出保護規定和措施,或者針對遺產具體危害因素采取相應的保護對策,難以承擔這些基礎研究工作,也沒有必要重復或轉述既有的價值認知的描述。目前多數的遺產保護規劃和保護方案,其中關于遺產價值的評價多沒有經過仔細的研究,當然也沒有多大意義。
其三,在文物保護工程中,對遺產價值的評價需要具體對待,要對遺產的要素、關系、系統進行全面的分析,對保護行動前后遺產的價值的可能變化進行對比,從而判定遺產保護項目對遺產的價值維系是否起到了作用。尤其是那些出于特別的原因,需要搬離原址進行異地遷建保護的遺產,更需要對搬遷前后遺產的關聯信息和全部價值是否有所損失進行預先評估。例如,重慶云陽張飛廟的搬遷,搬遷前確定遷建方案時,就應該有搬遷前后的價值評估研究,從而使得異地遷建對遺產價值的影響降至最低。張飛廟搬遷后出現的環境景觀大不如前,多數古樹已經死亡,作為一處中國傳統的優秀山水建筑(而不僅僅是祠廟建筑本身),張飛廟搬遷后的價值已經大大降低。
筆者認為,在遺產的保護和管理中,遺產價值的重要性,也就是價值評估的作用,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當保護者面對大量的遺產,無論是人力、物力還是財力,都沒有辦法同時均衡地兼顧所有遺產保護的時候,通過對遺產資源的調查,以及對所知遺產的價值研究,在認識這些遺產價值狀況的前提條件下,可以對這些遺產的重要性進行排序,以便能夠調集相關資源優先保護最重要的遺產。我國不可移動文物管理對三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劃分,以及可移動文物的一級、二級、三級的定級,主要就是基于這種考慮。
2.當遺產保護者在對一處大型的不可移動文物——尤其是遺產要素多樣的大型遺址、歷史城市、傳統村落等——制定保護規劃的時候,需要對其中不同遺產要素的重要性進行評估,以便在規劃的保護規定中,分別針對不同遺產要素作出相應的保護規定;并在規劃的分期中,按照重要性的先后次第采取保護措施。即便收藏在博物館中的可移動文物(包括圖書檔案),也需要進行價值評估,認識每件文物的重要性,以便在保護管理規劃中對保存環境、保管制度和應急響應等作出安排。
3.一項遺產申報世界遺產時,申遺文本需要對遺產的價值進行評估,對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進行說明,并與已登錄遺產進行對比分析。不過,現在回頭看來,不少已經登錄《世界遺產名錄》的遺產,申遺文本對于遺產價值的闡述也未必準確和全面。預先對有申遺訴求的遺產開展細致的基礎研究,包括價值評價,很有必要。即便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以后,也有繼續研究其價值的必要,以便將新的研究成果運用到保護、管理、展示和公眾教育中去。
遺產的價值研究是相當復雜和仔細的學術研究,需要研究者的知識積累,也需要研究者具有開闊的學術視野。西方漢學家魯唯一(Michael Loewe)和夏含一(Edward L.Shaughnessy)在《劍橋古代史》的序言中也指出,“一個不注意考古證據的歷史學家很快就會感到他無法順應當代的學術潮流;同樣,一位不熟悉傳統文獻的考古學家會難以把握相當一部分的中國文化之精髓。”要理解一個、一類、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遺產的價值,自然也需要掌握相關知識,并在一定觀念和方法的指導下,通過分析這些知識,來揭示隱含在遺產表面形態之下的價值。
在結束本文之前,再舉一個例子,以說明對一處遺產持續深入研究其價值的重要性,并以此作為本文的結語。已經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的山西應縣木塔,自從1933年梁思成等進行考察、測繪和研究以來,其研究成果不能不說是相當豐富,對該木塔的價值也從建筑歷史的角度進行過細致全面的分析。不過,過去的研究者都將塔的建筑與塔內塑像和佛藏分離開來,認為塔是遼代所建,塑像是金代后塑,因而在進行價值評估時就建筑談建筑,未能從遺產整體上去闡述其價值。根據羅熠的研究,應縣木塔的塔與塑像都是遼代的遺存,過去認為該塔塑像晚于木塔的認識應當修正。羅先生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并且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確的。如果木塔與塑像都是遼代所造,是一個整體,那么,應縣木塔的價值就要重新認識。至少在價值評估時要增加“應縣佛官寺釋迦塔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遼代以塔為主體的傳統佛教寺廟類型,建筑、塑像、壁畫、經藏諸要素均備,為認識唐遼顯密兼修佛寺的宗教崇拜體系提供了最好的樣本”這類的價值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