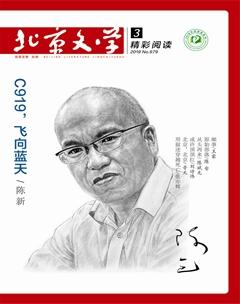《水滸傳》讀札三則
座次和廳堂政治
老驥有篇《大哥是怎樣做成的》,里面講到梁山好漢的幫派問題,說梁山上幫派眾多,讓人眼花繚亂。頭一個就是黃泥崗派,吳用劉唐阮氏三雄等人;接下來就是青州派,花榮秦明王英等人;然后是江州派,戴宗李逵張順等人。這三派,是梁山的主體隊伍。然后還有登州派,孫立解珍解寶等人;三山(二龍山、白虎山、桃花山)派,武松魯智深楊志等人;軍官派,關勝林沖徐寧等人;獨立派,如楊雄石秀時遷等人。這些派別中,只有黃泥崗派,是晁蓋的嫡系,卻還都欠著宋江的救命之恩;其他的派別,多多少少,都和宋江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尤其是青州派和江州派,都是宋江的嫡系,可以合稱宋江派。這個觀點,自2010年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以來,多次被研究水滸的專家們引用,頗以為然,老驥因此也頗有得色。
青州派和江州派,雖然是宋江的嫡系,但不是一起上的梁山。梁山大業,肇始于王倫;但是到了天王晁蓋帶領黃泥崗派上山,才走上自覺自信的顯赫道路來,所以說“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茍且”。此后上山的第二撥頭領,正是青州派。因為鬧了清風寨,殺了知寨劉高,又打了青州城池,在清風山小地方待不住,所以決議在宋江帶領下上梁山。只不過上山路上,宋江得到老父身亡的假信,撇下眾好漢,一個人奔喪去了。此時青州派進退兩難,面臨就地解散的危險(“事在途中,進退兩難,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正是花榮臨危受命,實際上代替了宋江臨時頭領的地位,帶著隊伍走完了剩下的路程。青州派這支隊伍,實在了不得。首先,燕順、王英、鄭天壽,這仨人有管理山寨的經驗;其次,他們在路上經歷了波折考驗,實際上鍛煉了隊伍的核心凝聚力。這支隊伍剛上梁山,就蓋過了黃泥崗派的威風。先是花榮射雁贏得聲名,使山上頭領“無一個不欽敬”;然后排座位,更是后來居上。關于排座次,書上寫道:
眾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座次。本是秦明才及花榮,因為花榮是秦明大舅,眾人推讓花榮在林沖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坐第六位,劉唐坐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
各位,花榮、秦明,雖然是新上山的頭領,卻不顧“強龍不壓地頭蛇”的古訓,直接越過劉唐和阮氏三雄,排在元老林沖肩下,分別坐了第五和第六把交椅。而黃信僅僅是個地煞星,居然也排到阮氏三雄這三位天罡星前面去了。從中一則可見青州派的威風,二則也可看出官本位意識之盛,因為花榮、秦明、黃信,以前都是武官。如果再算上林沖,這個現象更加明顯:此時梁山前八名,除了晁蓋吳用公孫勝所謂“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再往下五個人,只有劉唐一個出身流民,其余都是體制內做過官的,不過官位低微而已。官員反目加入起義軍隊伍,一般都會擔任高級頭目,這個自古皆然,大概也是因為他們的領導能力和管理水平有過人之處罷。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青州派上山時,晁蓋已經議定了座次。那么好,到群雄鬧江州劫法場之后,宋江帶領江州派上山,卻又把座次打亂了,這是什么道理?讀來百般不思其解。
江州派上山,是在青州派之后。從實力上講,江州派這支隊伍更加厲害。第一,江州派人數更多,多達十六人。第二,江州派有水軍頭領,而且多達五人。提請各位注意,八百里梁山水泊,水軍是一支重要力量。而宋江的青州派里面,沒有一個會水的,所以他們上山,風頭雖然蓋過黃泥崗派,但是水軍大權,仍然掌握在黃泥崗派的阮氏三雄手里。但是如今江州派上山,這個情況就大為改觀。江州派里面,有混江龍李俊、船火兒張橫、浪里白條張順、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這幾個人,聽外號就知道都是在水里不好惹的。反過來再看黃泥崗派阮氏三雄的外號,一個叫立地太歲,一個叫短命二郎,一個叫活閻羅,好像跟水也不沾邊。這也難怪,三阮生活在北方,也就在石碣湖里逞英雄。石碣湖該有多大?書上說連十五六斤的大魚都養不住。而江州派李俊這五個人,可都是萬里長江中的弄潮兒,特別是張順,水底下能伏三五夜,這個本領了不得。
所以江州派上山,排座次更應該有得好看。果然,宋江帶領江州派上山,自己坐了第二把交椅后,就先聲奪人,說,不爭功勞高下,先上山的居左,后上山的居右。看書上寫道:
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勞高下,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眾人道:“哥哥言之極當。”左邊一帶,是林沖、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右邊一帶,論年甲次序,互相推讓,花榮、秦明、黃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盛、蕭讓、王矮虎、薛永、金大堅、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威、童猛、馬麟、石勇、侯健、鄭天壽、陶宗旺。共是四十位頭領坐下。
宋江這個提議,表面上看,是不想和晁蓋等老人爭權奪利,顯示出大度隱忍。但是,卻要把已經排好座次、并且已經初步融入黃泥崗派的青州派,給生生地劃出來。老驥說青州派已經初步融入黃泥崗派,并非胡說八道。諸位看鬧江州兵分四路,黃泥崗派和青州派齊心協力,配合得還算默契。結果宋江提議把青州派割裂出來,這么一搞,左邊一帶,黃泥崗派為主體,只有九位;右邊一帶,青州派和江州派為主體,多達二十七位。前面說過,黃泥崗派是晁蓋嫡系,青州派和江州派是宋江嫡系,一邊九位,一邊二十七位,晁宋分野,高下立判矣!說一句誅心之論,這個可算是宋江對晁蓋的一次示威。白龍廟小聚義,只是個臨時示威,所謂投石問路者也;聚義廳示威,那才是長期的,才是站穩腳跟的基石。那么宋江搞這個示威有什么用呢?第一,可以強化青州派、江州派的派別意識。第二,可以促進兩派精誠合作。第三,還可以讓對面的黃泥崗派相形見絀,感到有壓力。
兩派分庭抗禮,為什么黃泥崗派會感到壓力呢?如前所述,相比于晁蓋領導的黃泥崗派,青州派和江州派各有兩大優勢。青州派的兩大優勢,第一,體制內武官多,花榮、秦明、黃信,比較起來,黃泥崗派純草根。第二,那些不是武官出身的人,卻有管理山寨的經驗,燕順、鄭天壽、王英,原本就在清風山經營多年。江州派的兩大優勢,第一,人多,有十六位。第二,水軍多,多達五人,而且本領高強。這兩派強強聯合,黃泥崗派就只剩下“元老”的資歷,此外基本上沒得混了。
當然,這個相形見絀的壓力,別人未必很快能感受出來。然而軍師吳用、半仙公孫勝,可是馬上就明白了。作為知識分子和半仙,他倆的智力和敏感,的確比那些武夫強得多。
先說吳用。吳用看了廳堂示威,立刻判斷事態發展趨勢,雖說和晁蓋“自幼相交甚厚”,到此也顧不得了,他迅速調整站位——不久后宋江還道村授天書,九天玄女叮囑宋江“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這個言語,立刻就讓吳用心領神會,此后兩人沒事兒就關起門來研究所謂“天書”,搞得神神道道,摒晁蓋于圈子之外了。
再看公孫勝,他大約還是念著晁蓋的情義,不忍看修正主義路線的大行其是,所以很快辭職,下山回鄉。直到宋江兩次派江州派重要人物戴宗去請——特別是高唐州吃了虧、派戴宗和李逵兩人誠心去請,讓公孫勝掙足了面子和地位,于是重回梁山,一戰成功,殺了高廉,救了柴進。有意思的是,公孫勝回梁山之前,他的師父羅真人,還借機把李逵狠狠地捉弄一番,整治得服服帖帖,坐實了公孫勝神仙地位,讓江州派夢里也不敢跟公孫勝作對。從此他在宋江心中站穩了地位,也就不再提回鄉探母的話頭矣。
游走于邊緣和更加邊緣間
浪子燕青,是梁山里面一個比較悲情的人物。書上說燕青“雖是三十六星之末,卻機巧心靈,多見廣識,了身達命,都強似那三十五個”,這是相當高的評價。然而他的出身,卻和其他好漢們不同。其他好漢,特別是三十六天罡,大多是各級軍官、地主富戶、江湖俠士,只有他出身奴仆,身份卑微。燕青原是盧俊義收養的孤兒,和盧俊義的關系,介于父兄之間。所以即使上了梁山,他依然言必稱“主人”,盧俊義也不見外,動輒就說“我那小乙”——雙方這種稱呼,即使受了招安、進入體制,也不改口。征方臘結束返回東京的路上,兩人有一次談話(這是兩人最后一席談話),盧俊義還在說“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可見情同一家。
正因為這樣的關系,燕青死心塌地效忠于盧俊義,幾次舍身相救。特別是盧俊義遭了官司,要被發配到沙門島,半路上被燕青射死解差救了。盧俊義杖瘡發作、腳皮破損,不能走路,燕青只好背著他走。書上明明寫著,盧俊義身高九尺,大概合現在兩米多;而燕青身高“六尺以上”,合現在一米五。一米五的小個子,背著兩米高的大塊頭,這個場景比較尷尬。所以走了“不到十數里”,就走不動了,又被公人們發現抓走。行文到此,很覺得燕青的身高和他的魅力不匹配。武大郎“身不滿五尺”,不到一米二;燕青其實比他高不了多少。一米五的個頭,居然人見人愛:泰岳爭交,知州見了就喜歡;后來和李師師接觸——李師師她可是皇上的情人,又是東京著名的“行首”,什么風流倜儻的男人沒見過,居然也愛上了他,實在讓人大跌眼鏡。當然,也許知州和李師師,愛的不是“一米五”,愛的是他的刺身花繡,比較性感。
盧俊義雖然武功蓋世,坐了梁山第二把交椅,卻只有燕青一個心腹。這和宋江完全不同。宋江嫡系眾多,尤其是以花榮、秦明為首的青州派和以張順、李俊、李逵為首的江州派,更是宋江心腹中的心腹。所以盧俊義在勢力上,根本沒法兒和宋江爭競。盧俊義聰明,也從不想和宋江爭競(老驥有一篇《大哥是怎樣做成的》,專論梁山領袖之爭)。每分派盧俊義任務,盧俊義總是說“哥哥差遣,安敢不從”,“先鋒差遣,無有不從”。在宋江面前,放低身段,自我定位為小頭目。特別是南征方臘前夕,二人在東京街上有一段見聞,寫得尤其明白:
出得城來,只見街市上一個漢子,手里拿著一件東西,兩條巧棒,中穿小索,以手牽動,那物便響。宋江見了,卻不識的,使軍士喚那漢子問道:此是何物?那漢子答道:“此是胡敲也。用手牽動,自然有聲。”宋江乃作詩一首:“一聲低來一聲高,嘹亮聲音透碧霄。空有許多雄力氣,無人提挈漫徒勞。”宋江在馬上與盧俊義笑道:“這胡敲正比著我和你,空有沖天的本事,無人提挈,何能震響。” 盧俊義道:“兄長何故發此言?據我等胸中學識,不在古今名將之下;如無本事,枉自有人提挈,亦作何用?”宋江道:“賢弟差矣!我等若非宿太尉一力保奏,如何能勾天子重用,為人不可忘本!”盧俊義自覺失言,不敢回話。
“自覺失言,不敢回話”,可見盧俊義相比于宋江,根本不能算是二把手。領袖只有一個,盧俊義很明白。
盧俊義明白,燕青比盧俊義更明白。他深知要在梁山立足,光有一個主人是不行的。無論是為了盧俊義還是為了他自己,他都必須融入宋江派。前面說過,宋江派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青州派,一個是江州派。青州派的花榮秦明黃信,出身軍官,貴不可攀;燕順王英鄭天壽,地位又無足輕重。而江州派的李逵則不然,人傻好接觸,而地位尤為顯要。李逵和宋江的關系,簡直就是同性戀、好基友(老驥有一篇《梁山泊里的同性戀》,專門講這個問題)。所以在梁山泊里,燕青李逵,倆人走得最近,無論是鬧東京,還是喬捉鬼、雙獻頭,還是岳廟爭跤,都是他兩人的主角。除努力融入宋江派,燕青還為宋江招安大業及其征討四方立下汗馬功勞。從東京看燈開始,燕青就表現出情報工作和外交工作的非凡能力。后來兩次去見李師師,一次去見宿元景,再后來獻地圖破田虎(百二十回本),以及隨同柴進深入虎穴破方臘,都是燕青的功勞。
然而,盡管燕青如此努力,又有如此大功,宋江好像都沒有看到,根本就沒把他當兄弟。燕青主動要求去東京打通李師師這條招安渠道,宋江就說:“賢弟此去,須擔干系。”這句話,表面上看是為燕青的安全擔心,實際上是對燕青不放心、有懷疑。這時,宋江的嫡系、江州派重要人物戴宗站起來,表示要和燕青一起去。宋江這才同意。事實證明,戴宗同行,啥用也沒有,只是一個監工督辦。比如有一回戴宗就當面懷疑燕青道:“只恐兄弟心猿意馬,拴縛不定。”逼得燕青對天發誓說:“若為酒色而忘其本,此與禽獸何異?燕青但有此心,死于萬箭之下!”戴宗也覺得自己疑心過重,笑著打哈哈說,咱倆都是好漢,發誓干啥!燕青也沒給戴宗留面子,當時揭露其真實面目,直言說道:“如何不說誓,兄長必然生疑。”
除了不放心、有懷疑,宋江對燕青似乎也沒啥好臉色。破遼回來路過雙林渡(百二十回本寫作“秋林渡”,放在了征王慶之后),燕青學箭射雁,箭箭不空,諸將驚訝不已,這是多露臉的事兒!郭靖彎弓射大雕,鐵木真就高興,以為有此神箭將軍護佑,可以在疆場上立功。但是宋江卻不這么想,把燕青叫來,一頓潑冷水:
“為軍的人,學射弓箭,是本等的事。射的親是你能處。我想賓鴻避暑寒,離了天山,銜蘆渡關,趁江南地暖,求食稻粱,初春方回。此賓鴻仁義之禽,或數十,或三五十只,遞相謙讓,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次序而飛,不越群伴,遇晚宿歇,亦有當更之報。且雄失其雌,雌失其雄,至死不配,不失其意。此禽仁、義、禮、智、信五常俱備:空中遙見死雁,盡有哀鳴之意,失伴孤雁,并無侵犯,此為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為義也;依次而飛,不越前后,此為禮也;預避鷹雕,銜蘆過關,此為智也;秋南冬北,不越而來,此為信也。此禽五常足備之物,豈忍害之!天上一群鴻雁,相呼而過,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卻射了那數只,比俺弟兄中失了幾個,眾人心內如何?兄弟今后不可害此禮義之禽。”
同樣是射大雁,花榮就沒事兒,燕青就挨批。這也是沒辦法,誰讓你不是人家的嫡系!燕青當時默默無語,悔罪不及。論理說這事兒也不大,磨磨唧唧教訓一頓也就算了。但是宋江不依不饒,還在馬上口占一首詩道:“山嶺崎嶇水渺茫,橫空雁陣兩三行。忽然失卻雙飛伴,月冷風清也斷腸。”當晚屯兵于雙林渡口,還不肯罷休,又作詞一首:“楚天空闊,雁離群萬里,恍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草枯沙凈,水平天遠。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暮日空濠,曉煙古塹,訴不盡許多哀怨!揀盡蘆花無處宿,嘆何時玉關重見!嘹嚦憂愁嗚咽,恨江渚難留戀。請觀他春晝歸來,畫梁雙燕。”分明在拿一件小事做文章。一把手念念不忘你的錯誤,翻來覆去覆去翻來地說,你心里怎么想?千百年后,我們也能分明地感受到燕青當時心里的壓力。每次讀書,讀到這里,都不免懷疑宋江的本意。他是否有借機敲打燕青的意思?不要以為我給你臉讓你當一個天罡星,不要以為你屢立功勞,就能融入我的法眼,就可以處處嶄露頭角。年輕人,你要學習李逵,要學習其他眾位兄弟,不要耍小聰明。
后來破了方臘,衣錦還鄉。回京路上,燕青決意脫離體制隱遁江湖。他只跟盧俊義當面辭行,對宋江,僅僅寫了一份辭職信,根本不肯再見面,這大概與宋江的自始至終的猜忌和敲打不無關系。在這封辭職信里,燕青留了四句口號,說什么“雁序分飛自可驚,納還官誥不求榮。身邊自有君王赦,灑脫風塵過此生”,顯然對雙林渡射雁之事并沒有全然忘記。宋江看了燕青的書并四句口號,心中郁悒不樂。臨了還被奚落一通,又無處發泄,他當然不樂。
放眼梁山,盧俊義只有燕青這一個心腹,按說他應該珍惜。但是盧俊義并不珍惜。上梁山之前,他不過是將燕青當作心腹家人,呼來喝去,未必有好臉色,有時候發怒還動手。燕青向他報告賈夫人和李固的奸情時,他就沖口而出道:“你這廝休來放屁!”然后“一腳踢倒燕青”。到后來燕青箭射董超薛霸,救了盧俊義的性命,盧俊義還抱怨說:“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卻射死這兩個公人,這罪越添得重了。”到上了梁山,受了招安,盧俊義也并沒有把燕青放在心上加以體恤。征王慶到伊闕山,盧俊義輕率進兵不顧后路,根本不聽燕青的勸阻。燕青請分兵五百伐木造橋以斷后,盧俊義就不屑一顧,說“看你做出甚事來”,分明看不起燕青。燕青領兵自去,盧俊義還在那里“冷笑不止”。這個冷笑不止,真是笑冷了弟兄們的心。這大概也是燕青辭盧俊義、中途隱遁的原因之一。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我待君、如初見,君虐我、千百遍。思來想去,大爺不伺候了!
對比而言,宋江的心腹,則寧愿殉葬。李逵自不必說,甘愿“生時服侍哥哥,死了也愿做哥哥帳下一個小鬼”。便是吳用、花榮,聽說了宋江的死訊,也拋家舍業,千里迢迢跑來,在宋江墳前自縊而死。這樣的兄弟情義,豈不讓盧俊義羞愧!為啥有這樣不同的結果?豈非是盧俊義太薄情、燕青太聰明歟!
飯局中的學問
神行太保戴宗,原是江州牢城營兩院押牢節級,位在管營、差撥之上,本身又是江州蔡九知府的眼前紅人(蔡九知府送家書,就是差戴宗前往。個中原因當然是戴宗走得快,但也說明蔡九知府對戴宗的信任)。有這個背景,即使他級別低,手中也有相當大的權力,所以就要公然詐取犯人銀錢,犯人不給,他就大棍打將來。
之所以說他“公然”詐取錢財,是因為他看見宋江第一句話,就明明白白地要錢:“你這黑矮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各位,我們往前看看,林沖刺配滄州,滄州的差撥也想問林沖要錢,但是他就不敢明說,只是對著林沖一通臭罵,罵了半晌,絲毫不提錢的事兒。武松刺配孟州,孟州的差撥也想問武松要錢,他也不敢明說,只是罵武松“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也沒有明確提錢的事情。從這個方面說,戴宗在江州的勢力,遠非旁人可比。
然而,宋江和旁的犯人不同,首先,他名揚四海,江湖敬服;其次,他手里掌握著吳用的書信,知道戴宗身為官員卻私通梁山好漢的證據。所以當宋江點破戴宗吳用這層關系后,戴宗大吃一驚,哪里還敢打著要錢?反而約宋江出去吃飯。各位請注意,戴宗約宋江吃飯,他就是主人,論理說他就該買單;然而,牢頭約犯人吃飯,情況自然不同。宋江再有名的好漢,到此也是個犯人,所以宋江臨出門,卻“慌忙到房里”,“自帶了銀兩出來”,表現得十分懂事。這席酒,書上雖然沒說,顯然是宋江買單。
正是在這頓飯間,李逵出場。李逵雖然是傻人、粗人,也知道宋江是遠來的客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完了,他就應該做東,請宋江吃飯。但是他是個赤貧之人,身上沒錢,所以他心里懊惱,想“卻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他沒別的辦法弄錢,就接著去賭,希望贏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可見粗魯的人,未必不懂禮節。他太想贏錢請客,所以不惜大鬧賭場傷人。可見在花錢請朋友吃飯這個問題上,李逵頗懂規矩、好面子。
后來,宋江戴宗李逵,又去江邊琵琶亭上繼續飲酒。因為宋江要吃鮮魚,引出黑旋風斗浪里白條,認識了張順,宋江又約張順一起吃飯。張順是宋江約來的,而且他加入潯陽樓飯局的時候,這個飯局基本上已經快結束了(書上說酒保“連篩了五七遍酒”,而且大家又都吃了魚湯,李逵還多吃了二斤羊肉),這個時候來的人,一般不會買單。但是,記著,張順是個魚伢主人,是個生意人,生意人和人吃飯,無論去得多晚,都要買單,除非同席者有另外的生意人。此番琵琶亭飯局,參加者是什么人呢?一位是遠來的客人宋江,一位是官員戴宗,一位是個監獄協警李逵而且還是赤貧之人,最后一位是生意人張順。你說誰買單?當然是張順。所以飯畢,張順提出“這席酒錢,我自還他”。然而宋江覺得臉上掛不住,因為畢竟張順過來,是他約的。所以宋江就說:“兄弟,我勸二位來吃酒,倒要你還錢?”然而張順“苦死要還”,說“權表薄意,非足為禮”。宋江不好意思,戴宗卻好意思,他看宋江張順搶著買單,他自己不掏錢,卻來勸宋江別爭了,說既然張順一片相敬之心,“仁兄曲允”,你就讓他買吧!宋江說這個“卻不好看”,但是拗不過,只好約改天他再回請。
四個人,兩頓飯,反映了一個人情道理:一,戴宗作為頗有權力的官員,吃拿卡要慣了,自己絕不買單,別人請他,他覺得很自然,不會覺得難為情。二,李逵作為協警,則不大一樣,因為級別低沒權力,估計平時請他吃飯的人少,所以他還沒有形成白吃的習慣,且知道要面子,知道有客人遠來,自己要做東請吃飯、臉上才好看。三,張順是生意人,天生買單的命,要么別去吃飯,去就得拿錢。四,宋江家里有錢,一直以來都是仗義疏財,出去吃飯,買單成了習慣。可是,他雖然如此天下好漢、四海聞名,一聽說戴宗約他出去吃飯,他卻要“慌忙回房里拿錢”,這個“慌忙”,也可見他身在矮檐下、不敢不低頭的凄楚。
世態人情,《水滸》這一段書都寫盡了。
責任編輯 師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