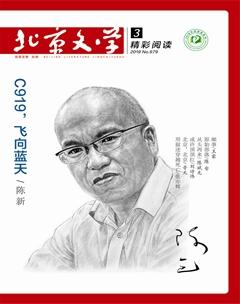陳倉如何走出大廟村
王干
陳倉最早的小說《父親進城》發在《花城》上,據說是作為散文投稿的,后來編輯一看,可以作為小說發啊,就成了中篇小說。我在審稿時,看到這篇小說情真意切,生活氣息土得掉渣,里面父親的形象太有典型意義了,就在《小說選刊》當頭條發了。之后《新華文摘》也緊跟著轉載,陳倉一時頗受關注。
陳倉的小說之路由此開啟,這幾年創作勢頭極為喜人。他長期堅持詩歌創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他的小說之路顯得有些幸運,他自己也有些欣喜和意外。陳倉小說的成功在于,抓住了當下生活的一個痛點:城市與鄉村的糾結。改革開放40年,對于更多的人來說,最大的變化就是城鄉生活變化帶來的沖擊——欣喜與焦慮。陳倉的進城系列,寫農民進城之后的不適應和焦慮,老邁的父親和年輕的妹妹在大都市里,迷失了自己,失去了魂似的。回到了塔兒坪或者大廟村之后,他們能找回自己,少了很多的焦慮。
自1979年高曉聲發表《陳奐生上城》之后,當代作家描寫農民進城的故事一直延續不斷。這一新的小說板塊的出現,打破原先鄉土小說一統天下的格局。另一方面鄉土小說在近年來也出現“再書寫”的轉機。“再書寫”一個特征體現在對農民精神家園失落的描寫,寫回不去的無歸宿的苦楚。進入新世紀之后,農村城鎮化的推進,加深了鄉村文明的變遷和動蕩。鄉村文明的挽歌,在作家的筆下緩緩地流了出來。“再書寫”的另一個特征就是對家園的告別之后的回望,回望之后的回不去的喟嘆。莫言小說中的“戀鄉”和“怨鄉”,曾打動無數讀者。近些年來,大量的小說以“故鄉”“還鄉”作為書寫的主題,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那場“進城”(打工潮)遙遠地呼應著。陳倉的小說屬于鄉土小說再書寫潮流中的佼佼者。
雖然依然是城與鄉的焦慮,不同的是人物從進城改成了返鄉。《原始部落》這一篇,是這個系列的一篇,女主人公白小靜與“我”在原始部落大廟村發生的故事,述說的是城市對人的精神的掏空。白小靜,作為一個進城者,和之前那些小說里描寫過的外來工一樣,顯然受到過侮辱和欺凌,她來到大廟村與其說是尋求逃避,不如說是一場自我埋藏。埋藏那些苦難,埋藏那些記憶。當然在大廟村里,必然有一個守望者,這是陳倉小說的魂所在。在《摩擦取火》里是那個瘋女人,在這篇小說里的“我”就是那個守望者,大廟村全村唯一留守的人,當然這個留守的人似乎帶有更多的人文情懷,是作者理想中的“村民”。一男一女在荒蕪的大廟村說的是關于生存、信仰和家園的問題,但背后隱藏著城市這座魔鬼如何戕害鄉村的深刻主題。
陳倉在小說里善于捕獲表達人物性格和小說內核的道具,這道具成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也成為人物命運的象征,甚至暗示小說的主題。在《原始部落》里關于長槍的反復描述,就是很有意味的:“有一天晚上,我擦著修長的槍管,忽然有點喜出望外。那個謎語的關鍵,就是槍比自己高,自己比槍矮,用槍瞄準自己的腦袋或者胸口的時候,自己就夠不著扳機了。如果是一桿短槍,或者是一把手槍,那開槍打死自己不就輕而易舉了嗎?于是,我和槍說話了。我說,你看這樣行不行,我把你給鋸一截下來吧?槍用黑洞洞的槍口嘲笑似的說,誰讓你長得那么矮呀,你不能自己努力努力長高一點嗎?你整天吃那么多飯喝那么多水,再長兩三尺能有那么難嗎?我說,你這個傻瓜,你雖然沒有吃什么糧食,但是你也吃過幾次黑火藥,我們幾輩人把你傳下來,你長高了嗎?而且我已經三四十歲了,早過了生長發育的年齡了。”這樣的對話讓道具人格化,也讓小說在更大的范圍里凝聚讀者的想象力。
比起《父親進城》單線條的敘述,《原始部落》在藝術上有了變化 開始嘗試復調敘述,“我”作為鄉村的守望者是一條線索,白小靜作為都市的漂泊者是一條線索。他們在大廟村相遇,歷史和現實,記憶與苦難,家園與困境,交織在一起。陳倉小說的詩性,在《原始部落》里得到充分的體現。
陳倉開始走出了大廟村的步伐,大廟村或塔兒坪是陳倉小說的發祥地,是陳倉小說的根,他離不開這個根據地,但拓展和變化正是他最新的追求和夢想。
責任編輯 張頤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