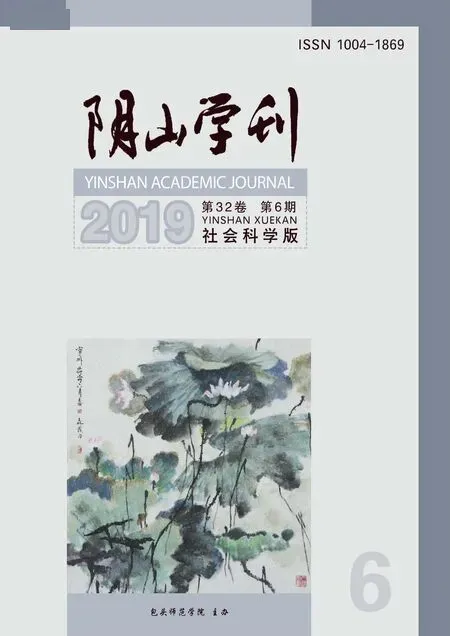評析Bickerton的語言進化突變論及其語言觀的哲學特征*
周 文 美
(北京外國語大學 中國外語與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作為現代語言進化論的領軍人物,Bickerton對傳統進化論大膽提出挑戰,在其1995年的著作《語言與人類行為》中闡述了他的語言哲學觀,從進化論的角度探討了語言起源、本質、語言與意識的關系等方面的問題。[1]Bickerton認為,“語言不是人類大腦高度進化后的產物。人類只是偶然進入了語言的領地”[2]56,而語言的出現與發展的直接結果就是人類的意識、思維與智力也得到了發展。該論述的出現立即引發了眾多學者們的關注。他的語言進化論究其本質是一種語言中心論。本文將分析其語言進化論的核心內容,試圖從理性主義和存在主義的西方哲學認識論視角分析其語言觀的哲學特征,并指出其語言觀存在的合理性及一些相關問題,來探討其對加深語言進化問題和人本質問題認識的意義。
一、Bickerton的語言進化突變論
Bickerton的語言中心論認為,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在于語言。語言的出現賦予人類行為最獨特的認知能力和意識活動。語言的核心特征在于句法。Bickerton認為,人類語言的發展不是緩慢平穩進化的,而是經歷了兩個階段,其兩段論(two-stage account)揭示了語言之于人類產生和存在的關鍵意義。
(一)原始語言階段
原始語言(proto-language)階段呈現出的語言特征是詞匯很少,詞與詞之間沒有結構關系,就像一顆顆由語義連接的珠子組成的珠串,沒有“合并”(merge)和語言“遞歸性”(recursiveness)的存在[3],表達手段極為有限,不流暢、有停頓和猶豫,幾乎所有的語言單位都能在自然界中找到所指。這與兩歲以下的孩子、早期的夏威夷洋涇浜語,以及經過訓練后的類人猿所呈現的語言很相似。Chomsky的語言進化突現觀對Bickerton語言進化觀點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其理論立論過程中使用很多喬氏術語。Chomsky認為原始語言應該會有符號的“合并”,并不贊同原始語言的存在。Bickerton不認可Chomsky的思想,認為“合并”存在于句子層面,原始語言中沒有句法。[3]
(二)句法語言階段
Bickerton認為句法產生于他所假設的“神奇的一刻”(magic moment)。在那一次災難性的事件中,大腦的內部結構產生了質的變化,人類語言完成了從原始語言到自然語言(human natural language)的飛躍[1]69-70。句法是大腦自然而然的產物,是人類頭腦中一種抽象的內在邏輯機制,能把凌亂、獨立的詞匯連接起來,組成具有無限生成能力、極其流暢和具有可解釋性的語言。Bickerton認為原始語言與現代人類語言不僅有句法之分,更存在二者在詞匯方面的本質差異。人類語言的詞匯與自然事物分離,以意義關系和結構分層次儲存在意識場里,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突顯了人類語言的“位移性”(displacement),這種結構特征使得人類語言明顯區別于動物交際系統,也正是這種特性才使抽象的句法成為可能。[2]58
二、Bickerton語言觀的哲學特征
理性主義(rationalism)是西方哲學的一種認識論理論,該理論認為理性是知識的主要來源,是運用抽象推理就可以認識事物及其結構,不需要通過經驗驗證而獲得關于事物真理的一種天賦知識。近代西方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Descartes強調理性思維的作用,否認真理性認識的感性來源和感性認識的可靠性。作為西方現代哲學流派之一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從揭示人的本真存在出發來揭示一切存在物的存在結構和意義,以及人與自然界、社會的關系。其主要代表人物Heidegger認為,語言的本質是存在的本真居所,而非表達功能和工具性質。語言經驗反映存在的本質和內在結構,哲學家只有通過語言才能把握存在的本質和內在結構。Bickerton語言觀中關于語言起源、語言本質、語言和意識關系的三個方面具有西方哲學的理性主義或存在主義特征。[4]14-15
(一)語言起源突變論的理性主義特征
從古希臘Plato對語言起源的研究開始至今,該問題仍然懸而未決。20世紀Aitchison的語言嵌合式進化說單純用延續性(continuity)與非延續性(discontinuity)來解釋語言的進化,主張語言是“靠某些已有的東西應急生成”[5]259,語言和人類行為一樣屬于嵌合式進化(mosaic evolution),即語言的某些方面具有很強的延續性,其它方面有一定或者沒有什么延續性[6]。Pinker則認為語言是生物本能(language instinct)。他認為語言不是文化的產物,不是學會表達時間或政府管理方式之類的知識,而是一種使用起來絲毫不知其內在邏輯的本能。語言的復雜屬性不是父母或教師能教會的內容,而是生物稟賦[7]。新達爾文主義的漸變論(neo-Darwinian gradualism)認為,“現代人類語言是由原始語言過渡發展而來的。先有原始語言的詞匯,繼而產生了現代人類語言的句法”[2]57-58。21世紀Chomsky的天賦思想認為,基因變化誘發了語言,語言是人類物種的先天稟賦,不是逐漸學得的后天產物,介于中間的語言存在是難以想象的。這與Bickerton語言突變論關于突變天賦能力的觀點如出一轍。
Bickerton繼承發揚了Heidegger的存在主義,通過對原始語言研究分析進一步論證了原始語言與人類自然語言之間沒有過渡階段存在的可能性。他認為完全意義上語言的出現是突變的結果,以句法為核心。Bickerton找到了支撐突變論最充分的理由。首先,現有證據證明人類認知是突變而成的。兩百多萬年前,在人科動物進化過程中沒有留下行為和技術方面逐漸發展的痕跡。十二萬年前南部非洲出現的認知飛躍和語言突現論表現出理論上的一致性。其次,尚未找到原始語言和人類語言之間有同期出現的各種中介語言和某些穩定階段,至少從大量失語癥、言語困難癥、一語和二語習得的發展階段以及語言官能的反常現象中沒有找到相應證據。句法的自毀無法恢復性證明沒有語言發展中間階段出現的可能性。[5]259Bickerton語言起源突變論合理的方面在于從多學科視角為深入研究語言起源問題提供了新的范式和思路。其哲學基礎屬于理性主義,具有典型的西方哲學的理性主義特征。
(二)語言生物性本質觀的存在主義特征
什么是語言?Bickerton在分析人們對語言概念兩個誤解的基礎上闡明語言生物性的本質觀。第一個是語言工具性的誤解。第二個誤解是語言交際功能的唯一性。傳統的語言哲學把語言的交際功能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認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是語言的交際功能。Bickerton認為這種觀點是大錯特錯的,因為動物也會使用符號來交際。很顯然,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于語言的表征功能,人類用語言儲存信息、進行思維活動、表達思維和意識,語言是不受時空限制的開放系統。相比之下,動物的“語言”僅僅局限于表達情緒與需要,其單一孤立的交流單位不能組合傳達新的意義,最終導致其交流方式的封閉性。從這個意義上講,Bickerton認為人類行為的基礎是語言,研究人類的行為就必須研究人類的語言。只有語言才使能使人類感知、體驗和再現所處的世界。
Bickerton主張語言本質上是人類這一物種經進化而來的生物性特征,并非可創造的文化性特征,來源于人的本真存在,是隨著人本真存在的發展進化來的,是不能被創造的。Bickerton關于語言本質觀的合理性在于從人本真存在出發來解釋語言的存在結構和意義,通過研究語言的生物性本質來研究語言結構的生物特性即大腦神經網絡結構這一人本真存在的重要內容之一。它從人類自身的生物特性解釋語言的本質特征,強調語言結構的生物特性和人本真存在對語言生物特性決定作用同時,也強調語言對人本真存在的影響,其哲學基礎屬于存在主義,具有典型的西方哲學的存在主義特征。[4]16
(三)語言與意識關系的存在主義特征
句法的出現是人類基因突變的結果,這種突變促使大腦結構復雜化,更重要的是促使人類思維和意識產生。Bickerton把意識界定為人類大腦達到高度發達程度后而出現的創造性特征,他區分了三種意識形式。第一意識(consciousness l, Cl)是所有生物(動物和人類)具有的一種線上意識,既包括對外部環境的客觀感應,也包括內部主觀產生的體驗。人類不但具有Cl,還可意識到自己的意識,這種意識的意識就是第二意識(consciousness 2,C2)。第三意識(consciousness 3,C3)是指用語言表達思想感情的能力。例如,我感到癢(C1),知道自己癢(C2),能說出“我癢”(C3)。Bickerton強調,C2和C3只為人類所有,因為只有人腦才可回顧和反思意識內容。他認為人類只有一個意識C2,語言使得C2產生的三個結果整體出現。[2]59-60作為擁有語言物種的人類必然會意識到自身的意識,并對其進行表達和分析。人類的自主能力和主動性引出了語言在其意識形成過程中的決定作用。
Bickerton三種意識形式的區分讓我們從存在主義視角更清晰地看到了語言的生理基礎。意識為語言的出現和運作提供了生理基礎和必要條件;神經系統的本真存在為語言提供初級的生理基礎;語言突變促使人類大腦質變,為意識的產生提供了本真存在的生物基礎。Bickerton關于語言和意識關系的觀點的合理性在于從人的本真存在出發來揭示意識發展的必要條件(語言的存在結構),從二者共同的生理基礎——人的本真存在(人腦神經網絡)出發,揭示意識的內在結構是語言的生理基礎,語言的存在結構是意識發展的必要條件,二者聯系密切不可分割,是人類思維認知過程中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哲學基礎是存在主義,具有西方哲學典型的存在主義特征。[4]17Bickerton思想激進偏頗,觀點大膽創新,但他過分強調語言生物性的本質以及語言和意識關系的生物性特征,忽視了語言社會性的交際功能和社會文化屬性特征,很難徹底全面揭示語言的本質以及語言和意識關系的本質。
三、對Bickerton的語言進化突變論的簡評
Bickerton的語言哲學觀認為,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在于語言,突出了句法的核心作用。Bickerton的語言中心論是一種語言決定論。該理論在語言認知觀和研究方法這兩個方面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和局限性。
(一)強硬的模塊說、偏頗的突變論和溫和的認知觀
長期以來,以Chomsky為代表的許多認知學家推崇大腦本質的“模塊說”,即大腦是由一系列各司其職、高度專門化且相對獨立的模塊所組成。語言是大腦的一個獨立模塊之一。Pinker更是堅持一種強硬的語言交際觀,認為思維可以獨立于語言之外,不依賴語言存在,語言的功能只是傳達思維。Bickerton的突變論旗幟鮮明,不做任何溫和的修飾,突出語言的中心作用,把語言幾乎等同于整個中央認知系統。在他看來,句法是人類語言的核心,句法和命題推理構成了人類認知的基礎。抽象的語言的出現帶來抽象的思維。Bickerton過于偏頗的突變論缺乏有力的經驗證據的支撐,欠缺進化心理學的證據——大腦的中央認知系統完成復雜的認知功能是由語言模塊和各感覺模塊巧妙結合的結果,因此難免會導致其語言認知觀的前后矛盾。
Carruthers接受喬氏的模塊說,其溫和的語言認知觀(a weak form of cognitive conception of language)認為,雖然語言是大腦的一個獨立邊緣模塊,但它的基本功能是思維的載體,與思維有著密切的關系,在認知活動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Carruthers指出Bickerton觀點中的不足,認為Bickerton既否認了大腦的模塊本質,又割裂了原始語言與句法語言之間的聯系,語言進化的兩段論過于簡單,不符合進化事實。Carruthers認為,雖然原始語言抽象程度低,但創造性思維的開始是思維既能以直觀想象的方式利用視覺模塊,又能利用內部言語(inner speech)來使用語言模塊以支持其自身功能。語言就像一個國際通用語言,作用于不同的模塊之間,它是命題思維和概念思維的載體,在人類的創造性思維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8]
(二)研究方法的邏輯推理
Bickerton反駁新達爾文主義的漸變論,對傳統進化論提出了顛覆性的挑戰。他認為,語言進化過程中,具有意義的“神奇一刻”是句法的出現。該觀點主要是基于抽象推理而形成,具有典型的理性主義特征。但缺乏直接的考古記錄和經驗證據進行推測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許多學者質疑Bickerton研究中的因果推理太模糊[9],觀察對象有限,觀察時間過短,是否屬實還有待證明[5]259,只能作為一個有待驗證的假設。由此可見,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要遵循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人類語言發展是人類進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原始語言是人類語言進化若干階段中的第一階段,語言進化要從原始語言逐漸地發生量變,最后實現質變過渡到人類自然語言階段,這樣的語言進化觀才是較為合理和全面的。
四、結 語
雖然Bickerton的語言中心論存在一些缺陷,但他試圖從眾多領域研究人類語言起源,闡述語言起源的認知,為深入研究語言起源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他對語言起源研究的重大貢獻是對克里奧爾語的發展研究成果,為他的推理立論提供了比較強硬的推理依據。他將語言學與人類起源和進化研究緊密結合,將語言視為人類起源和進化的唯一先決因素,剖析語言本質的同時,看到了語言對于人類存在的關鍵意義,更是對人之為人、語言與思維、語言與意識關系等這些有關人本質問題的執著追求。因此,“任何解釋人類行為的企圖都必須建立在語言理論基礎之上”,因為“只有明白了語言,我們才有可能明白自己”[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