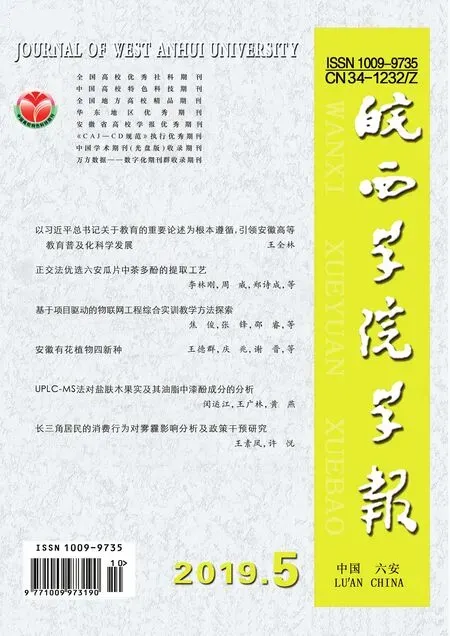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藝術初探
王方好,閻方正
(1.安徽大學 藝術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2.華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安徽民間關于地方戲曲有“徽黃廬泗花”的說法,其中的“花”便是指皖南花鼓戲。皖南花鼓戲作為安徽省的第五大劇種,有著深厚的民間土壤。皖南花鼓戲形成于清末,“百年前湖北民間花鼓調和河南燈曲子隨移民進入皖南,與皖南地區的民間歌舞合流演唱,后又吸收了徽劇、京劇等兄弟劇種的藝術的有益成分,逐漸發展演化而成長的”[1](P55)。直到今天,皖南花鼓戲依然在我省宣城、廣德、郎溪、寧國一帶廣為流行,深受民眾喜愛。
皖南花鼓戲傳統劇目的題材多樣,具有十分濃郁的地域性特征。“皖南花鼓戲的藝術積累比較豐富,有大戲四十一本;小戲八十七個;另有殘本二十個左右。”[2](P158)1959年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印的《安徽省傳統劇目匯編·皖南花鼓戲卷》(1—9集)收錄了皖南花鼓戲傳統劇目87個。這87個劇目名稱具體如下:雙合鏡、蘭衫記、繡像記、小清官、珍珠塔、雞籠山、告經承、天仙配、柳蔭記、余老四、鬧公堂、送香茶、大清官、烏金記、白扇記、賣花記、湘子渡妻、站花墻、西樓會、倒栽麻、天平山、云樓會、血汗衫、蕎麥記、雙插柳、雷公報、糍粑案、沉香救母、陰陽錯、曬羅裙、藍絲帶、打紅梅、荒年記、平頂山、店家會、藍橋會、下揚州、酒醉花魁、思凡、思兒望郎、郭華買胭脂、何義保扯狀、南沖耕種、攔馬、張老三下南京、胡氏下書、小姑賢、花亭會、秦雪梅觀畫、湯老二試妻、瞧干娘、釣雞、呂蒙正趕齋、吊樓、掃花堂、鬧簧學、永樂觀燈、百忍堂、百子堂、小辭店、桃花洞、傅羅卜取經、梅龍鎮、機房教子、壩王山、漁舟配、鳳姣投水、腌臘菜、小放牛、打補丁、唐老三下江南、張監生調情、打蘆花、打城隍、打砂鍋、張懷庭打長工、打豆渣、王和賣錢、賣梔子花、張三賣豆腐、打瓜園、柏老四反情、賈四成嫖院、假報喜、打面缸、掐菜苔。
目前學界關于皖南花鼓戲研究的論文,主要集中在其源流考述、傳承保護對策方面。陳雨婷《皖南花鼓戲源流考述》一文對皖南花鼓戲形成的源流進行了探討;施俊《皖南花鼓戲的產業開發及運營對策研究》《安徽皖南花鼓戲藝術發展及問題研究——以〈當茶園〉為例》,張靖、伍和友《皖南花鼓戲保護與發展的因素分析及方向探討》等文章對皖南花鼓戲的保護與傳承現狀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保護對策。對于皖南花鼓戲劇目特色進行研究的文章相對較為缺乏,因此,對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價值。
1 傳統小戲的題材來源及其分類
1.1 題材來源
皖南花鼓戲作為地方戲曲,具有十分濃郁的地方鄉土氣息。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在題材來源上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原創劇目。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之中,有大量是當地藝人原創的劇目,這些劇目成為皖南花鼓戲的特色所在。如《打瓜園》《當茶園》《雞籠山》《鬧公堂》《湘子渡妻》《天平山》《雷公報》《陰陽錯》等,這些原創劇目成為皖南花鼓戲的特色所在。
第二,改編移植劇目。皖南花鼓戲作為一種流行于地方的戲曲,其傳統小戲在題材來源上自然而然受到周圍其他地方戲的影響。皖南花鼓戲的許多傳統小戲是從其他地方戲劇目移植改編而成,如《藍衫記》與黃梅戲以及廬劇《大辭店》的情節內容相似;《天仙配》與黃梅戲《天仙配》類似;《柳蔭記》與廬劇《梁祝》以及黃梅戲《山中訪友》情節相同;《雙插柳》則是與泗州戲《太行山》情節如出一轍;《機房教子》與京劇《三娘教子》的情節吻合等。皖南花鼓戲作為植根于民間的一種藝術,在進行移植改編的過程中,往往將當地的鄉土審美風格融入其中,從而形成獨屬于自己風格的劇目。但由于其流傳過程中的民間化,很難準確判斷出到底哪種劇種的故事在前。
第三,從古典戲曲改編創作的劇目。中國古典戲曲有著悠久的歷史,無論是元雜劇還是明清傳奇,都在一定程度上對地方戲曲的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皖南花鼓戲不少劇目都是從古典戲曲改編而來的。如《呂蒙正趕齋》從元雜劇《呂蒙正風雪破窯記》以及南戲《彩樓記》改編而來;《云樓會》則是根據明傳奇《玉簪記》所演變的故事;《思凡》則是根據傳奇《孽海記》改編而來;《傅羅卜取經》受到了鄭之珍《目連救母勸善戲文》的影響。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題材來源豐富,成為其能夠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
1.2 題材分類
關于戲曲題材的分類,中國古代的戲曲理論家早已進行過相關的論述。元代夏庭芝在《青樓集》中對元雜劇題材有著如下分類:“有駕頭、閨怨、鴇兒、花旦、披秉、破衫兒、綠林、公吏、神仙道化、家長里短之類。”[3](P7)明代的朱權在《太和正音譜》中提出“雜劇十二科”的說法,所謂“雜劇十二科”,即“神仙道化、隱居樂道(又曰‘林泉丘壑’)、披袍秉笏(即‘君臣雜劇’)、忠臣烈士、孝義廉潔、叱奸罵讒、逐臣孤子、鈸刀趕棒(即‘脫膊雜劇’)、風花雪月、悲歡離合、煙花粉黛(即‘花旦雜劇’)、神頭鬼面(即‘神佛雜劇’)”[4](P24)。夏氏與朱氏關于元雜劇的題材分類有著十分相似之處。
關于明清傳奇題材的分類,很少在明清曲論之中見到相關的論述。今人對于戲曲題材的分類的研究還是相當充分的。比如臺灣的羅錦堂先生將戲曲題材分為八類,即“歷史劇、社會劇、家庭劇、戀愛劇、風情劇、仕隱劇、道釋劇、神怪劇”[5](P5)。許金榜先生在《中國戲曲文學史》一書中,將戲曲的題材分為“清官斷案劇、忠智豪杰劇、愛情婚姻劇、遭困遇厄劇、倫理道德劇、道佛隱士劇”六大類[6](P20)。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所包括的八十七個劇目,其題材內容涉及面廣泛,結合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的劇目題材特點,可以將其題材分為愛情婚姻類、倫理道德類、清官斷案類三大類別。
1.2.1 愛情婚姻類
愛情題材在中國古典戲曲之中所占篇幅相當之大。元代有所謂的“四大愛情劇”的說法,到了明清傳奇之中,這種愛情婚姻劇的數量更是達到了一個頂點。清代著名的戲劇家李漁曾經指出明清傳奇有“十部傳奇九相思”的特征。到了地方戲之中,這種以愛情婚姻生活作為主要題材的劇目的作品數量更是龐大。“戲曲具有寓教于樂的功能,歌頌真、善、美,抨擊假、丑、惡,為民眾思想找到排解和宣泄的窗口。人們向往美好的愛情,但愛情卻常常受到封建禮教、綱常倫理的歪曲和束縛。”[7]在皖南花鼓戲的傳統小戲中,出現了一大批以表現男女愛情為題材的作品,如:《掃花堂》《打補丁》《繡荷包》《秦雪梅觀畫》《思凡》等。《掃花堂》寫馬忠、馬秀英兄妹和朱娃子在員外家做工,秀英與朱娃子相愛,在打掃花堂時,秀英要哥哥向朱娃子說出她心里的話——把自己給朱娃子做媳婦。充分展現了下層民眾對于婚姻愛情的追求。《打補丁》寫寡婦王翠紅與表哥周溪云的日常相處,特別是通過周請王打補丁這一細節,刻畫出兩人復雜的感情。《繡荷包》通過宋幺姑為意中人周良成繡荷包的一段故事,生動刻畫了宋幺姑的樸實、熱情。《秦雪梅觀畫》則是寫秦雪梅與商林兩人的戀愛故事,著重展現了兩人對于彼此堅貞不渝的感情。根據昆曲《孽海記》改編的皖南花鼓戲《思凡》,通過小尼姑思念凡塵,欲擇偶成家,經思想激烈斗爭后,半夜走出禪堂,逃下山的行動,肯定了人的正當欲望。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之中對于愛情婚姻的描寫,往往具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其背后體現了皖南一帶民眾生活愿望與審美情趣,這一類題材的小戲因此在皖南當地深受民眾的喜愛。
1.2.2 倫理道德類
中國地方戲曲是民眾表達自我的方式,它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傳承著民族倫理精神,成為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載體。皖南花鼓戲中倫理道德題材的小戲往往將倫理道德與情感的關系作為關注中心,其中所表現的倫理關系大多以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間的倫理關系、情感關系、利益關系為主。在皖南花鼓戲的傳統小戲作品之中,出現了大量以宣揚社會倫理道德為題材的作品,如《珍珠塔》《打紅梅》《小姑賢》《湯老二試妻》等。《珍珠塔》通過窮書生方卿,為姑父祝壽,被嫌貧愛富的姑母趕出門外。后方卿高中狀元,乃喬裝賣唱道情,以此來諷刺姑母的無情無義。《打紅梅》寫蔡員外無子,納婢女紅梅為妾,紅梅懷孕,原配江氏善妒,虐待紅梅,并將其趕出。后紅梅子高中狀元,闔家團圓。《小姑賢》寫王氏虐媳寵女,經常無端尋釁責媳。在其子及女兒的勸說下,終有所悟。《湯老二試妻》寫湯老二得知其妻與許小生暗通,回屋試妻。最終將其妻推入河中,其妻答應日后定安守本分,從而被湯老二救起。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對于倫理道德的呈現,往往帶有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讓民眾在不經意間,得到教育,這一類作品在整個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所占的比重也相對較大。
1.2.3 清官斷案劇
現存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劇目之中,有大量是以清官斷案作為主要題材的劇目。這類劇目大多反映民眾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塑造了一大批清官的形象。其中,在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劇目之中,包公這一人物形象反復出現,例如《下揚州》《平頂山》《陰陽錯》《賣花記》等劇目,都塑造了包拯這一清官的形象。《下揚州》中的甘氏魂魄將楊權捉去,經過包大人用還魂扇將楊權扇活,并命楊超度甘氏,以解冤仇。《平頂山》中的王太師為了得到寶貝,心存歹意,殺死書生李自貞,后經包拯審理,將王太師處死,用陰陽扇將李自貞救活。《陰陽錯》之中的土地公將林大姑、二姑身份弄錯,后經包公審理,才最終使兩人魂歸本體。《賣花記》中曹鼎將賣花女張氏逼死,包公與權臣曹鼎正面交鋒,將其鍘死,并用陰陽扇將張氏救活。
皖南花鼓戲之中以包公作為主要題材的傳統小戲數量眾多,這是下層民眾愿望的集體反映。“包龍圖——包公題材的文學創作歷久而獨特,其原因在于‘民意’的推涌。歷史人物包拯的思想性格為其成為文學形象和故事‘箭垛’提供了‘民意’基礎。”[8]皖南花鼓戲作為流行于民間的俗文學,其故事題材大多反映了下層民眾的審美情趣與生活愿望。
2 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藝術特色
皖南花鼓戲作為安徽傳統的五大地方戲之一,在民間有著廣闊的群眾基礎,這也成為其能夠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皖南花鼓戲自身所具有的獨特藝術魅力,是其能夠吸引皖南地區民眾的重要因素。其藝術特色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2.1 情節結構簡單化
縱觀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的情節結構不難發現,皖南花鼓戲情節模式具有類型化的特征。這種情節類型化的特征,不僅存在于皖南花鼓戲之中,其他地方戲也有。這種特征早在中國古典戲曲之中就已經存在,南京師范大學孫書磊教授認為:“中國戲曲在經歷了元代北曲雜劇和明中葉南曲傳奇的兩度輝煌之后,到明清之際即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進入了它的第三次繁榮時期。較之于前兩次,這一時期戲曲敘事的類型化現象十分突出,成為中國戲曲區別于西方話劇的創作特征。”[9]在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之中,無論是婚姻愛情劇,或者是清官斷案劇,這種類型化的特征都十分明顯。但不同于其他地方戲曲情節模式上的類型化特征,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的情節結構相對較為簡單。一般來說,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的情節線索以一條或兩條為主,戲劇沖突也相對較為簡單,能夠滿足下層民眾的欣賞能力。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有大量劇目都是采用這一方式來進行呈現的,例如《掃花堂》,整個故事主要人物就三個,主要情節線索就一條,講述馬秀英與朱娃子之間的愛情。《打補丁》講述了寡婦王翠宏與表哥周溪云之間的愛情故事;《打瓜園》則是通過費大娘與文姐的摘瓜,與看瓜童龔繼之間發生沖突,最后雙方之間互相諒解,矛盾得以解決的故事。除此之外,皖南花鼓戲在對中國古典戲曲故事改編過程中,對故事的情節進行很大的弱化與消解,往往只保留最為核心的情節內容。例如《云樓會》根據明代高濂的《玉簪記》改編,改編之后整個故事僅僅保留了潘必正“偷詩”與陳妙常“趕潘”這兩個最為核心的情節;《思凡》改編自明傳奇《孽海記》,僅僅保留了“小尼姑下山”這一核心情節內容。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的故事情節趨于簡單化,通過短小的故事來傳達主要思想內容。
2.2 人物形象類型化
“人物是敘事文學作品中的核心要素,人物形象的呈現是文學敘事的主要目的之一。同時,人物作為事件的行為主體,其形象特征又與情節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可見人物形象在敘事藝術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0]中國古典戲曲之中大量的人物有類型化的特征,這種特征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古典戲曲表演方式上的“虛擬化”與“程式化”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又與中國古典戲曲故事本體“寓言性”的特征密不可分。華東師范大學譚帆教授認為:“古代劇論家視戲劇故事的本體為‘寓言’,而寓言所體現的那種‘主體性’與‘象征性’正為戲劇人物塑造中的‘類型化’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11]這種類型化的人物形象一直成為中國古典戲曲人物形象塑造最為主要的特征,同時對后來的地方戲人物形象塑造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繼承了中國古典戲曲人物形象塑造類型化的基本特征。皖南花鼓戲之中出現的主要人物按照身份不同,可以分為書生、農民、尼姑、繼母、清官、商人等。這些不同身份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一種類型化的特征。例如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中的書生往往是貧窮卻滿腹才華,《呂蒙正趕齋》中的呂蒙正,《吊樓》中的張大洪,《荒年記》中的尚文秀,《天仙配》中的董永,《雙合鏡》中的張德義,《珍珠塔》中的方卿等,這些書生往往出身貧寒,但憑借自己的才華,最終考取功名,得以發跡。同樣,在皖南花鼓戲之中,清官的形象也富有類型化的特征,他們往往成為正義的化身、驅邪扶正。《大清官》中的余成龍,《賣花記》《雙插柳》《陰陽錯》《平頂山》《下揚州》中的包拯等,他們往往主持正義與公道,幫助底層民眾伸張正義,成為下層民眾心目中的正義化身。值得關注的是皖南花鼓戲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具有類型化的特征,例如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之中的繼母形象。在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之中,繼母形象往往是惡勢力的化身。無論是《送香茶》中的馬氏,還是《倒栽麻》中的藍氏,抑或者是《店家會》中的姚氏,都是惡勢力的化身。這種類型化的女性形象,是皖南花鼓戲創作者長期植根于日常生活所創造出的符合當地民眾審美情趣的形象。
2.3 嫻熟的戲劇技巧運用
清代著名的戲劇理論家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提出戲劇創作要有“機趣”。關于“機趣”這個概念,他解釋道:“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12](P20)對于廣大觀眾,特別是下層民眾來說,觀看戲劇最重要的目的便是為了得到精神上的娛樂與消遣。“人們往往有一種本能的好奇心理,而多變的、新鮮的信息對于人的神經中樞是一種強刺激,容易引起審美的注意。”[13](P192)因此,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之中運用了大量的戲劇技巧,以保證“戲劇性”的存在。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劇目大多情節較為簡單,但在簡單的情節之中,卻要傳達復雜的思想內涵。縱觀皖南花鼓戲八十七個傳統小戲劇目不難發現,皖南花鼓戲創作者對于戲劇技巧的運用十分嫻熟。無論是“突轉”,還是“發現”,抑或者是“誤會”,還是“巧合”,在皖南花鼓戲傳統小戲之中常常都可以看到。
《姚大金報喜》作為皖南花鼓戲的代表作之一,整個劇作將戲劇技巧運用到了極致。故事一開始,姚大金將妻子給他買年貨的錢賭輸了,妻子讓他上山打柴去賣一點錢購置年貨,他卻編織了一個“謊言”,告訴岳母妻子懷孕了,從岳母那里騙取了年貨。劇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運用“欺騙”這一手法巧妙地讓姚大金的岳母產生“誤會”,從而大大增強了故事的戲劇性,激起了場下觀眾的興趣。整個故事情節尾端發生“突轉”,姚大金的岳母跟小姨子突然到訪,打破了這種謊言所營造的平衡,得知真相后,姚大金成為批判的對象。通過這種嫻熟的戲劇技巧,大大增強了戲劇性。
《打瓜園》是一出風趣的生活小戲,整個故事就是由于一個“誤會”所產生的。龔繼來發現瓜園中的瓜被偷,第二日躲在瓜園之中想捉偷瓜人,費大娘與文姐路過口渴,在瓜園之中摘了瓜來解渴,龔繼來將她倆誤認為“偷瓜賊”。接著,由于相互之間的諒解,沖突得以化解,誤會解除。“誤會”這一手法在地方戲之中成為重要的情節構建的技巧。有學者指出,誤會這一手法“不僅能鋪設局部性情節,而且具有構筑支架、撐起大廈、統攝全局的作用。換言之,即整個戲劇之結構、沖突緣起于‘誤會’,并以此為契機,延伸拓展,貫通全劇”[14]。《打瓜園》這部劇便是典型的由于“誤會”所建構起的故事。在皖南花鼓戲之中,這種由于“誤會”所建構出的故事不在少數,也成為皖南花鼓戲的一大特色。
2.4 濃郁的喜劇化色彩
皖南花鼓戲作為流行于民間的地方戲,在很大程度上注重其娛人的功能,娛樂性成為民間地方戲最重要的特征。早期的地方戲,已經開始顯示出這種濃郁的喜劇化的傾向。有學者對清代錢德蒼《綴白裘》之中選取了三十多出地方戲的風格做過總結:“入選的地方戲風格多樣,異彩紛呈。有的像漫畫幽默風趣;有的像泥人樸實粗獷;有的像小丑取鬧,滑稽熱鬧。”[15]可見,早期地方戲已經十分重視其娛樂的功效。
皖南花鼓戲作為成長、流行于皖南地區的民間戲曲,繼承了早期地方戲的娛樂功能。皖南花鼓戲的娛樂功能主要集中在其喜劇性的構建上。“喜劇性作為審美的范疇之一, 是戲劇的靈魂。”[16](P259)皖南花鼓戲的喜劇性的建構主要集中在喜劇情境的建構、喜劇人物的塑造、喜劇語言的運用這幾個方面。在喜劇情境的建構方面,皖南花鼓戲主要運用的是“誤會”“巧合”“突轉”“發現”等手法,前面已經探討過,這里不再贅述。在喜劇人物的塑造方面,皖南花鼓戲刻畫了一系列具有鮮明性格的喜劇人物。如姚大金、龔繼來、朱娃子、周良成等人物已經深入人心,特別是姚大金已經成為一個“好吃懶做”的符號存在于皖南地區民眾的心中。在喜劇語言的運用方面,皖南花鼓戲運用了大量口語,增添了生活化的色彩。
3 結語
皖南花鼓戲作為一種從民間生長起來的地方戲曲,在審美風格上具有濃郁的鄉土色彩,正是這種鄉土色彩,才使得皖南花鼓戲愈來愈具有強壯的生命力。在皖南花鼓戲發展的百余年歷史中,流傳地域和社會現實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遷, 有些傳統劇目逐漸被遺忘并消失了,有些經過改編、調整后重新上演。皖南花鼓戲的傳統小戲所具備的藝術性正是其流傳至今的重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