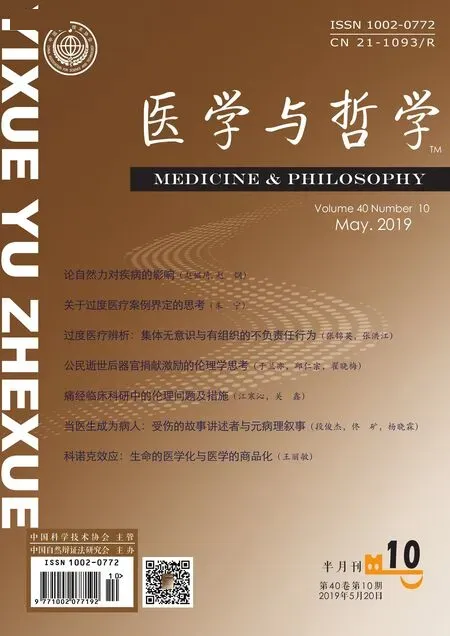關于過度醫療案例界定的思考
朱 寧
1 過度醫療的確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由于認為醫學無所不能觀念的影響、社會公眾對醫學的過度期盼以及醫學作為資本效用引起的“不道德、不規范”的醫療行為越來越突出,過度醫療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當今的過度醫療,遠比蘭德公司調查報告公布的情況嚴重[1]。2016年5月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志》的一篇研究報告稱:美國開出的抗生素處方中有近1/3不對癥。僅濫用抗生素導致耐藥性感染每年約200萬人,致死2.3萬人。研究發現,2011年,美國共開出2.62億張門診抗生素處方,全美3億人,幾乎一人一張,而其中有一半不對癥[2]。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提供一個研究報告說,美國每年約有25萬~44萬人死于包括過度用藥在內的醫療不當[3]。根據美國學者提出的過度醫療是“由于醫學機構對人們的生命采取了過多的控制和社會變得過多地依賴醫療保健而引起”[4]的觀點,過度醫療涉及包括生活醫學化在內的過度醫療供給、過寬過廣的疾病診斷標準、對控制疾病無益甚或有害的治療(包括沒有必要的手術)等多方面的問題。本文僅就臨床實踐中如何界定過度醫療作一討論。
臨床實踐中的過度醫療,是指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違背臨床醫學規范和倫理準則,為患者提供了超過患者病情需要和有效的醫療[5]。具體一點兒說,過度醫療是指為患者提供了脫離患者病情實際的沒有必要的過度檢查、過多和過長時間的用藥、沒有必要的手術、沒有必要的輸液等。或者說,在治療過程中,不恰當、不規范甚至不道德,脫離患者病情實際而進行的檢查、治療等醫療行為。其后果不僅是徒增患者治療費用、耗費醫療資源,更為嚴重的是可能為患者健康帶來傷害,有時甚或危及患者的生命。當今我國過度醫療的問題似乎是普遍現象,筆者曾很反感來醫院看病還要找熟人,但是現今筆者自己的朋友來看病,筆者也要特意找一個信得過的醫生問一問,討個“實話”,感到不是筆者熟識的醫生恐怕“真話”都聽不到,會被“過度醫療”。筆者認為是否過度醫療不是下定義就可以確定的,實際上只有主管醫生心里最明白。換句話說,只要問一下如果患者是您自己的父母兄妹,您是否給這項醫囑?如果您也說做,那就不是過度醫療,除非醫生的業務水平實在太差。
在大家普遍反感過度醫療之際,筆者以為要對各個病例是否是真正的過度做具體分析,很多情況并不是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簡單,甚至還有不少醫療不足或診療不到位的情況。以下以筆者本人遇到的病例就此作一分析。
2 實實在在的過度醫療
例1:一位64歲女性患者,平素體健,每天參加廣場舞、爬山,近期曾體檢心電圖正常。半月前感冒、發燒、咳嗽遷延未治,后逐漸出現心慌、氣短,去醫院檢查診斷肺炎、房顫、低鉀血癥。收治在心血管心律失常病房。患者第一天即被告知需要射頻消融手術治療房顫。次日查HOLTER發現室早900多個,三陣室速(連續12個室性搏動),立即告知需置入價值十幾萬元的植入型心律轉復除顫器(ICD)。患者、家屬均不知所措,醫生不解釋疾病從何而來,只是兩個字“手術”,“不手術就出院”。醫生只看一次心電圖、一次HOLTER結果,不考慮患者平素狀態,不追究心律失常的來源,就提出收費那么高的重大手術治療方法,讓患者、家屬驚恐不已。而實際上患者入院后經消炎、補鉀、控制房顫心率治療后,癥狀很快緩解,房顫自行復律。復查HOLTER室早明顯減少,無室速發生。該患者是呼吸道感染誘發房顫,感染控制后房顫自行復律,根本不需要射頻消融手術治療。又因患肺炎進食差,造成低鉀,誘發室性心律失常,補鉀后室性心律失常明顯減少,完全沒有ICD手術的必要。
此例患者的經歷反映了醫生追求新時尚的診療手段,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益,不認真傾聽患者的病史,而是僅依靠儀器設備與實驗室檢查結果,一味追求多做手術,患者的心理社會因素得不到重視;忽視對患者病情的全面綜合分析,忽視了醫生與患者的交流,必然導致過度醫療的泛濫。如果患者是醫生的母親,他/她絕不會如此迅速決定要手術治療此患者的心律失常。
例2:84歲女性患者,因為頭暈半年,近期略有加重而入住某二甲醫院。既往高血壓病20余年,平素控制較好,無糖尿病,無心腦血管病史,無胸痛病史。生活自理,承擔家務以及上下4樓(無電梯)無困難。食欲、尿便、睡眠均可。入院后查體無明顯異常,心電圖:無缺血改變。腦CT提示腔隙性腦梗死,頸動脈、椎動脈超聲見到有斑塊,局部狹窄<50%。診斷:腦供血不足。醫生解釋說:腦動脈有斑塊了,心臟血管也可能有問題,一起檢查一下吧。因此行冠狀動脈造影,果然三支血管都有病變,前降支最重,狹窄近90%,當下決定給予治療,但是多次嘗試不成功。為此轉入當地最大的三甲醫院行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經過一番努力后成功完成冠狀動脈前降支支架治療。但是回到病房僅2個小時就出現心力衰竭,血壓不穩定,查體發現室間隔穿孔,被告知是斑塊掉到血管遠端,堵塞了血管末梢,造成心肌壞死,室間隔穿孔。隨即給予主動脈內球囊反搏(主動脈大血管內放一個球囊,病床旁一個大機器不停歇地運轉著)治療維持血壓。12天后行小切口完成室間隔穿孔修補術,手術成功,送入ICU。術后恢復順利,幾天后搬出ICU回到普通病房。不幸的是著涼感冒,隨即發熱、咳嗽、黃痰,肺炎,立即給予了抗生素,但是隨后又出現肝功損害,給予保肝治療后又出現腎功異常,最終血濾腎臟替代治療,反復調整抗生素等,共住院近2個月,自費部分花費20幾萬元,最終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患者家屬無奈地說:我媽的“病”治好了、人沒了……
這是典型的過度醫療的嚴重后果,醫生只講科學的滿足,治療狹窄的血管,而不考慮患者的需要,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血管有狹窄但是足夠支持她的日常生活,完全沒有必要把狹窄的血管都開通。此例過度治療應該是源自醫生追求高花費、新技術,本意絕對不希望患者是這樣的結局。思考這個案例,該患者從開始就不需要做冠脈造影這項檢查。
例3:14歲男孩,重點高中的優等生,因略感尿頻去醫院就診,尿液及前列腺液檢查有些小毛病,不足以診斷什么病,但是醫生對孩子和家長說孩子可能有“無菌性慢性前列腺炎”,孩子因此有了心理壓力,不斷查電腦了解這個病,無心學習并出現焦慮狀態,經心理醫生多次治療方好轉。因此家長投訴要求賠償。其實醫生如果好好問診,就知道這是青春期小孩錯誤的手淫導致的刺激癥狀,給予正確指導癥狀即可消失。
這是一例不負責任的過度診斷。真正目的是醫生開具有回扣的藥品。
例4:60歲低保男性,因左大腿外側脂肪瘤逐年增大(10cm×5cm),因此手術,醫生選擇了腰麻加靜脈復合麻醉手術,最終花費萬元,患者、家屬不能接受這個數字,無法承擔這個負擔,要求賠償。此例脂肪瘤實際上完全可以采用局麻手術,4 000元即可完成所有住院及手術。
這是明顯的過度治療,本質還是醫生斂財。
3 誤判過度醫療的若干案例
例5:筆者所在醫院急診室來了一位突發急性下壁心肌梗死的93歲老人,來院時血壓低于80mmHg,心率低于50次/分,而且繼續在下降,身上已是大理石樣花紋,說明已是休克狀態,血液循環臨近崩潰。兩個女兒非常好,說老人平日身體很好,生活自理,自己做飯。并說:大夫您說該怎么辦就怎么辦。筆者立即聯系了心導管室,告訴他們立即會送去一位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的93歲老人,請給予急診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導管室護士回話是:朱老師,您腦子有病啊!這么大歲數,情況那么糟糕,那是要死在手術臺上的!筆者的回話是:如果不立即手術的話,幾個小時之內肯定死亡,手術的話有可能活!結果順利完成手術,老人五天后出院,體健如前。
一般而言,一個九十幾歲的老人急性心肌梗死,即使死亡了,家屬都可接受。相反如果老人手術后死亡,大部分人必定會說:這么大歲數了,還做手術?!純屬過度醫療!“過度醫療”的定義中曾有一條:對某些死亡征兆已經很明確或死亡即將到來的病人仍進行挽救生命的治療,盡管此種醫療處于家屬的要求,也可視為過度醫療干預[6]。但是這是一個平素身體很好的老人,突發急性下壁心肌梗死,造成血壓、心率持續下降,如果開通了血管即可立即解決問題,當然應該嘗試一下。所以這絕對不是過度醫療。
例6:“非典”那年,凡是有咳嗽、發熱的年輕學生都會送到發熱門診就診,擔心“非典”,并且都會“擴大化”詳細完成各種檢查,結果出乎意料的是發現了一個一個的結核病人,而且不僅是這一個學生患了結核,而是他整個宿舍幾個同學都患有結核病。反過來想,如果不是“非典”時期,這樣的年輕人根據非“過度診療”的“原則”,往往按照感冒,不做任何檢查,給點感冒藥就讓學生回學校去了,結果可想而知,那就是結核病的傳染播散。
所以看似簡單的感冒也不能掉以輕心地對待,該檢查的還是要查。這不是過度醫療。
例7:20世紀90年代初筆者曾去美國進修,跟著美國醫生出門診,遇到一個很簡單的筆者認為很明確的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如果是筆者,會給點對癥的藥物緩解癥狀就可以了。可是美國醫生開了一大堆的檢查,包括肺、心、化驗等,完成這些檢查項目都需要近一周的時間,等檢查結果出來時,恐怕感冒已經痊愈了。筆者當時問美國醫生,做這些檢查用得著嗎?他們的回答是:I will not take the risk! 意思是說他不承擔風險,萬一是“非典”呢?萬一是“結核”呢?萬一是“心衰”呢?我們知道上述這些病的早期表現都是與感冒類同!
所以美國醫生做的上述檢查,也不是過度檢查。
例8:一個五十幾歲女性患者主訴胸痛、心慌、心煩、失眠,年輕醫生接診后考慮“冠心病”可能性大,因此立即查心電圖、心肌標志物、超聲心動圖、24小時動態心電圖、運動平板、冠狀動脈CT甚至冠狀動脈造影。結果均為陰性。患者癥狀越來越重。換了一個年資老的醫生,根據多年經驗感到該患者更年期綜合征可能性大,未再做任何檢查,給予更年期的治療,2天癥狀完全消失。
即同一個患者遇到一個年輕醫生,開出一些檢查他認為是必要的;可能一個老醫生就認為沒有必要,原因是經驗不同。也就是哪些檢查是正確診斷所必需的、哪些是多余的,都是由醫生根據自己的經驗和水平而定的,因此,對過度醫療的判斷真的沒有一個具體的量化指標。
4 界定過度醫療的幾點思考
4.1 排除私念和偏好,可以避免許多過度醫療
上述四例過度醫療,例2、3、4都與醫生的私心有關。例3中一個14歲的男孩,因尿頻尿急就診,經查尿液有點小問題,為何要戴上“無菌性前列腺炎”的帽子?無非是想從中得些藥品回扣;醫生長期從事一個固定的專業,極易形成一種專業偏好。病例1平素健康,只因心慌、氣短,去醫院檢查診斷肺炎、房顫、低鉀血癥。對于這樣一個體質較好的患者,理應先考慮控制肺炎,同時用藥控制房顫心率,待肺炎控制后再考慮房顫轉律或射頻治療的問題,但醫生第一天就告知患者需要射頻消融手術治療房顫。這顯然與醫生的偏愛有關。一位外科醫生曾說:我一天不做手術就不舒服,只要沾點邊可手術,我就開單子做手術。長期工作在自己專業領域,往往習慣從本專業看問題,遇到患者,首先是從本專業出發安排醫療方案。這也是應當提倡多學科協作的重要原因。
4.2 重視基本功,勿將運用現代技術就視為過度醫療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腫瘤科熊斌教授,20多年一直堅持肛門指診,如發現問題再做腸鏡,而不是直接做腸鏡[7]。一般低位大腸癌在距肛門緣7cm內,指診可及。就憑這“一指功夫”診斷了無數患者,在醫學界享有盛譽。筆者剛畢業時曾被要求做到問完病史就應該能估計出體格檢查的結果,體格檢查后就能估計出輔助檢查的結果。筆者申請給患者做的輔助檢查如果得到陰性結果,就會感到很沒面子,說明自己的臨床判斷錯了。CT、超聲檢查要求陽性率均在80%以上,而今相反,陰性率達80%[8]。現今患者入院立即開出去一大堆檢查,檢查不回來就完全沒有思路,不知道什么診斷。這是基本功的嚴重缺失,不能提倡。但是另一方面現代技術的優勢我們也要充分利用。筆者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復高考第一批入學的七七級醫學生,1982年畢業,那時還沒有CT,沒有心臟超聲設備,心血管系統疾病的診斷很大程度上依賴最簡單的問病史、聽診器。患者平均住院時間是28天。而今心血管病房平均住院時間只有6天。因為現在患者入院1天~2天各項檢查完成,診斷明確,治療藥物、手段先進,很快解決了患者的問題,好轉出院。而20世紀80年代初患者的治療常常依賴“試驗性治療”,臨床判斷是“心力衰竭”,但是按照心力衰竭治療了幾天不見好轉,醫生就想到心力衰竭可能不是主要問題,而“肺炎”是主要問題吧?從而改換治療策略。又治療幾天仍不見好轉,再想到是不是“心包積液”啊?…… 如此治療下來就是20幾天。如今入院時病情很重的患者,按照以往醫療條件必定無法出院,會病逝。但是如今設備、藥物都非常強有力,這些以往應該死亡的患者都會好轉出院。記得剛畢業時經常有一個手術名稱叫“剖腹探查”,因為實在弄不明白,只有開腹來看。而如今窺鏡、CT、磁共振清晰得如同鉆進肚子里肉眼看到了一樣。再也不會有剖腹探查的術式。醫學的進步就是造福于人類,而其主要進步是在設備上。當今磁共振在神經科、骨科、消化內科,甚至心臟科都是必不可少的檢查項目,可以給醫生提供準確的醫療信息。例如,神經內科沒有磁共振,就無法確診脊髓炎、脊髓多發性硬化。一個頸椎病的患者常常需要頸椎三維片、CT、磁共振三樣都要檢查,是過度檢查嗎?不是,三種檢查手段各負其責,沒有磁共振就無法明確診斷脊髓、神經損傷、神經變性。心臟血管支架救了很多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置入支架開通血管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仍像20世紀80年代初只用聽診器、心電圖、透視機、A型超聲,不可能有那么多患者一直長期生存。應該用好現代技術造福人類,即使價格昂貴。
4.3 指南、共識不是唯一標準,個體化治療是醫學的靈魂、醫生的智慧
很多臨床情況不是按照指南、共識、臨床路徑就可以處理的。
例9:48歲中年女性體檢發現先天性二葉式主動脈瓣伴輕度返流,各心腔大小正常,即尚未出現血流動力學的影響,患者本人沒有心力衰竭的癥狀。超聲大夫、外科大夫均極力動員患者接受換瓣手術,按照指南有手術指征,但也可繼續觀察等待。
心臟手術畢竟是大手術,有一定風險。筆者問道:如果該患者是醫生您的姐妹,您會建議立即手術嗎?回答是:可以再觀察幾年。
例10:78歲老年房顫患者,按照指南100%應該給予抗凝治療。但是該患者已房顫40年,從未用過抗凝藥物,因此很抵觸用抗凝藥。醫生則遵從指南一定要患者接受抗凝治療,不巧又發生出血事件,結果被患者要求索賠。
記得多次世界心血管大會上,主持人要求與會代表(均為心血管醫生)表態:如果是您本人或親人有病您是否接受某某手術(當前熱捧的手術),結果均是出人意料,50%以上的醫生本人選擇不手術。
例11:一位十年前曾行二尖瓣換瓣術的76歲老人,目前因瓣膜老化、瓣膜狹窄、頑固性左心衰嚴重肺淤血,以至于肺內感染久治不愈,雪上加霜,使老人極其痛苦,難以生存。按照常理,這么大歲數,除了心衰還有肝、腎、肺功能都很不正常,預期壽命只有1個月~2個月,又是難度大,風險大的瓣膜二次手術,多不建議患者手術治療,因為生存可能性太小,這個患者如果手術一定會冠以“過度治療”的帽子。但是患者本人特別堅決,視死如歸也要手術。結果手術順利完成,患者生活質量大大提高。大家都非常有感觸,即患者不同,有時家屬不同即可造成治療效果大不相同。
本例成功手術是患者本人的決心加之患者術后的密切配合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如程顯聲老先生所說:個體化治療是醫學的靈魂,是醫生的智慧。過度醫療也是要個體化考量。
4.4 診療方案的確定,要考慮患者生活經歷和精神狀態
現在醫生考慮對患者的治療,一般依據理化檢測提供的資料。這當然是需要的,各種理化檢測,提供了患者機體運行的情況,反映了疾病對機體的影響,醫療干預的目的是糾正某些生命指標的偏離,但是有些生命指標的不正常,不只是生物因素所至,還與患者生活經歷和情緒直接相關。
例12:一個35歲支氣管哮喘的患者,經治療后理應恢復正常,但患者卻愁眉不展,療效不理想,反復就診。細心的醫生問她有何難心事,是不是丈夫和婆婆想要你再生一個孩子。因為醫生記起曾和她說過,目前不宜懷二胎。患者聽后淚如雨下,這位醫生聽后一下子明白了問題所在,說你如果相信我,將你家電話告訴我,我和你婆婆、丈夫談一談。當晚這位醫生就和她的家人通了話,第二天這位患者來到醫院,一掃臉上的愁云,病情明顯好轉。
我們醫生考慮患者的治療,不僅是依據患者的醫學世界,還有患者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只有這三個世界加在一起,才能構成較好的醫療。這位患者如果只是從醫學世界考慮,就只能是加大藥量,延長療程,過度醫療就出來了。1988年世界醫學教育大會的愛丁堡宣言明確指出,醫生應當是:“耐心的傾聽者,仔細的觀察者,敏銳的交談者”,最后才可能是“有效的臨床醫生”[9]。
4.5 重視“過度”與“不足”并存的情況
例13:有一個23歲的學生感冒后發燒,咳嗽來門診看病,肺CT提示肺炎,醫生覺得這么年輕的患者,問題不大,沒有再做其他檢查,給輸注6天抗菌素,病情好轉不明顯。第7天晚上病情突然加重,來急診室檢查發現血壓220/140mmHg,急性心力衰竭,腎功能衰竭,入住ICU不足兩天就去世了。原來這個特別肥胖的孩子原本就有高血壓、腎臟病,而沒有主動告訴醫生,當然醫生也沒有詳細詢問。回頭審視門診醫生如果能稍微“過度”一點,做些檢查就可以及早發現問題,也就能挽救一個孩子的生命。
造成“醫療不足”的原因可能更多地來自醫生缺乏經驗,或者責任心不強、不夠細心所至。這一點對年輕醫生特別需要引起重視。盡管當前過度醫療是較為普遍的現象,但治療不足或不到位的情況導致嚴重后果的事例也應引起重視。
一個好的診療應該是個體化綜合治療,既不過度也不缺位。究竟是過度還是不足,一切要以是否符合患者的實際需要為準繩,以患者受益是否最大化為準繩。我們反對隨意誘導開藥、多開藥、用好藥,反對誘導體檢、過度檢查,反對過度手術,因為這既浪費資源,更嚴重的是可對患者造成傷害,但若碰上疑難雜癥,或患者的某種特殊情況,根據需要建議患者做必要的包括一些高新技術的檢查,向患者推薦某種新藥、建議患者聯合用藥,建議患者手術,這絕不是過度醫療,不應隨意懷疑醫生的建議,給醫生扣上過度醫療的帽子。該檢查的就要檢查,該用先進技術的就用先進技術。我們可以給過度醫療下個一般性的定義,但至于具體某一患者是不是過度醫療,要根據患者具體病情而定,不能認為,凡使用了高新技術的檢查,凡是用了好藥,凡做了大手術就是過度醫療。只要是出于為了患者的一片誠心,有時即使多用了某種藥或服藥的時間長一點,或者檢查多了一點,筆者以為也不要扣上過度醫療的大帽子為好。醫學,特別是臨床醫學,充滿了未知數,很多情況下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很難一下子就能做到恰到好處。醫生的成長有一個不斷總結和積累經驗的過程。既不過度,又不不及,是一種高超的技藝,是醫生竭盡終身才能純熟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