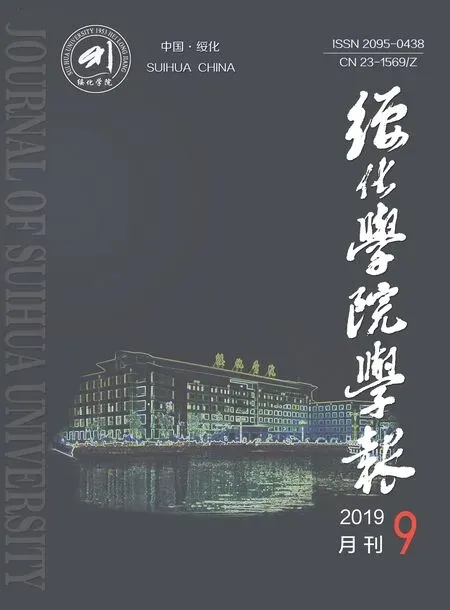狂歡中的顛覆
——《哈克貝利·費(fèi)恩歷險(xiǎn)記》中國(guó)王與公爵的狂歡化特征解讀
張麗雯 黃淑芳
(華東理工大學(xué)外國(guó)語學(xué)院 上海 200237)
《哈克貝利·費(fèi)恩歷險(xiǎn)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7)是美國(guó)文學(xué)史上的里程碑,它在推動(dòng)美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縱觀小說,“國(guó)王”與“公爵”二人作為書中最大的反面人物,他們的形象十分滑稽可笑,但可笑之余,這二人在推動(dòng)情節(jié)發(fā)展和理解小說意義上有著很大的重要性,馬克·吐溫花了大段篇幅來描寫“國(guó)王”與“公爵”這兩個(gè)人物,可惜二者卻不是學(xué)者研究的重心所在。“國(guó)王”與“公爵”二人滑稽的身份偽裝,充滿笑謔的怪誕式節(jié)目表演以及被識(shí)破真面目后的悲慘下場(chǎng)與巴赫金提出的狂歡化理論遙相呼應(yīng)。本文從狂歡化理論中的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和狂歡節(jié)儀式這兩個(gè)視角入手來研究“國(guó)王”與“公爵”在小說中所展現(xiàn)的狂歡精神,從而揭示作者馬克·吐溫對(duì)愚昧落后的美國(guó)南方種植園社會(huì)的顛覆以及自私虛偽的美國(guó)白人的嘲弄。
一、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
(一)“國(guó)王”與“公爵”的生活。小說中,“國(guó)王”與“公爵”的出場(chǎng)方式極具喜劇和荒誕特色。哈克遇上并解救了當(dāng)時(shí)正在被人和狗追捕的二人,兩人中的其中一個(gè)“約莫七十歲,興許還大些”,而另一個(gè)“大約三十歲”,兩人的穿著打扮“一樣的不入眼”。[1](P125)而就是這樣狼狽邋遢的逃亡者上了小劃子之后,搖身一變就成了異國(guó)“貴族”;上一秒還是騙人招數(shù)被識(shí)破而遭人追捕的騙子,下一秒就成了身份尊貴卻歷經(jīng)坎坷的“國(guó)王”與“公爵”。二人為了在小劃子上享受高人一等的服務(wù),編造了自己的身世,也正是從他們“坦白”自己“國(guó)王”與“公爵”身份的那一刻起,他們身上就有了滑稽和戲謔特點(diǎn)。兩人穿的衣著和干的行當(dāng)與他們口中的尊貴身份格格不入,從而營(yíng)造了一種怪誕喜劇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下看這兩個(gè)騙子的生活:一個(gè)借著迷信風(fēng)氣當(dāng)過假醫(yī)生、給別人算過命、冒充過傳教士進(jìn)行傳教;另外一個(gè)賣過假藥、當(dāng)過戲劇演員和算命師傅、還到過學(xué)校教過書。他們完全過著一種流浪漢生活,沒錢的時(shí)候去干些坑蒙拐騙的勾當(dāng)來賺錢,有錢的時(shí)候就去酒館喝個(gè)痛快,全然沒有社會(huì)教條規(guī)矩的束縛。這種生活的狂歡與自由正體現(xiàn)了狂歡廣場(chǎng)式的生活的隨意無拘性。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xué)問題》(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中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中的狂歡化源自于狂歡節(jié)式的慶賀活動(dòng),狂歡化的淵源就是狂歡節(jié)本身;狂歡節(jié)中的狂歡精神不止體現(xiàn)在節(jié)日內(nèi)的演出慶典活動(dòng)中,也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2](P122)因此,人們總是過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種是“常規(guī)的、十分嚴(yán)肅而緊蹙眉頭的生活”,人們?cè)谏钪斜3种伺c人之間絕對(duì)的等級(jí)秩序,生活中充滿了壓抑和克制;另一種是“狂歡廣場(chǎng)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人們?cè)谶@種生活中輕松愉悅,官方生活中的等級(jí)不復(fù)存在,所有人和事物都可以隨意不拘束的接觸,人與人之間可以平等而自由的交往。[9](P129)“國(guó)王”與“公爵”倆人常年的行騙生涯說明了他們眼中早已沒有束縛性的禮儀道德的存在,也擺脫了宗教信仰所帶來的崇敬和虔誠。他們的生活是一種脫離了軌道,遠(yuǎn)離了權(quán)威規(guī)定的無拘無束的狂歡廣場(chǎng)式生活,這種生活恰是正常官方生活的戲仿“翻版”。“國(guó)王”和“公爵”這樣的狂歡式的人物,把嚴(yán)肅古板的生活變成了令人發(fā)笑的鬧劇。他們狂歡廣場(chǎng)式的戲謔生活充滿了滑稽的笑,這種笑將正常生活中“所有生硬、僵化的”階級(jí)與規(guī)定“一掃而光”,使得身處這種生活中的所有人都暫時(shí)忘記了原本官方世界內(nèi)嚴(yán)格的等級(jí)和身份。[2](P133)這一點(diǎn)尤其表現(xiàn)在兩人同黑奴吉姆共處同一個(gè)劃子上:吉姆覺得自稱為“公爵”的騙子十分可憐、從尊敬所謂的“國(guó)王”與“公爵”到受不了他們、甚至在后來覺得他們是“迪迪倒倒(地地道道)的壞蛋”。[1](P157)這表明了在狂歡廣場(chǎng)式的生活中制約著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一切等級(jí)和規(guī)矩被暫時(shí)取消了,黑奴能夠肆意表達(dá)他們對(duì)白人的可憐或者是鄙視。這無疑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社會(huì)等級(jí)的顛覆,同時(shí)也消弭了與等級(jí)相關(guān)的各種恐懼和尊敬。
(二)全民性的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國(guó)王”與“公爵”兩個(gè)騙子在平日里過的是狂歡廣場(chǎng)式的無拘無束的生活,他們本身就具有強(qiáng)烈的狂歡特色,因此當(dāng)他們又動(dòng)起了壞腦筋想要去岸上重操舊業(yè)時(shí),岸上小鎮(zhèn)的活動(dòng)場(chǎng)地就變成了全民性的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小說中這樣全民性的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一共有2處。
第一處是兩個(gè)騙子在遇到哈克和吉姆后的第二次上岸行騙。“國(guó)王”收獲頗豐的演講行騙給了二人莫大的鼓勵(lì),兩人滿心籌劃著第二次騙人的把戲。當(dāng)“公爵”發(fā)現(xiàn)自己精心準(zhǔn)備的莎士比亞戲劇收效甚微時(shí),他想出了一個(gè)更加荒誕的表演——《王室異獸》,海報(bào)上打出了“驚心動(dòng)魄的悲劇”、“婦孺恕不接待”這般的宣傳語,吸引了一大批人前來觀看。[1](P153-154)觀眾們看著“國(guó)王光著身子,手腳并用地蹦上場(chǎng)來”,全身都是一些花紋和圖案,“一個(gè)個(gè)笑得死去活來”。[1](P155)巴赫金在其論著《對(duì)話的想象》(The Dialogic Imagination)中討論過流氓、小丑和傻瓜的作用:“他們受他人嘲笑,同時(shí)也嘲笑他人。他們的笑聲是民眾聚集的公共廣場(chǎng)的標(biāo)志。”[3](P159-160)小說中的“國(guó)王”與“公爵”正是狂歡節(jié)儀式中的小丑,他們滑稽另類的戲劇表演召喚了一大批鎮(zhèn)民的到來,從而形成了一個(gè)全民性的狂歡廣場(chǎng)。在這樣的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中,“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相互關(guān)系”,所有人都是相互平等的,人們之間可以隨意而親昵的接觸,互相打鬧,插科打諢。[2](P123)雖說是“國(guó)王”的怪誕式表演促成了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但實(shí)際上,狂歡節(jié)表演“沒有演員和觀眾之分……人們不是袖手旁觀,而是生活在其中”,所有人都參與到狂歡節(jié)的演出中,“按照狂歡節(jié)自由的規(guī)律生活”。[4](P7)每個(gè)人都是狂歡節(jié)表演的參與者,表面上看似是觀眾對(duì)于“國(guó)王”的恣意嘲笑,實(shí)際上“國(guó)王”和“公爵”這兩個(gè)騙子也在嘲笑觀眾的愚蠢和無知。對(duì)于哈克而言,小劃子上的尊貴的服務(wù)對(duì)象“國(guó)王”淪為了自己的譏笑對(duì)象,哈克與“國(guó)王”之間的原本的等級(jí)消失了;對(duì)于觀眾而言,享譽(yù)全球的“英國(guó)戲劇演員”竟然脫光衣服為他們表演如此滑稽的戲劇,演員和觀眾之間的種種隔閡消失了;對(duì)于“國(guó)王”和“公爵”而言,自己作為被人追捕厭惡的騙子,在此刻看著無知的鎮(zhèn)民主動(dòng)付費(fèi)來看自己胡亂編排的戲劇,他倆和鎮(zhèn)民之間的地位差距也消失了。在全民性的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中,“烏托邦式的自由、平等氣氛得以形成,社會(huì)等級(jí)也不復(fù)存在,薩圖爾努斯的‘黃金時(shí)期’似暫時(shí)復(fù)返。”[5](P153-154)
第二處全民性的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發(fā)生在“國(guó)王”與“公爵”兩人被揭穿了騙子身份的時(shí)候。當(dāng)時(shí)心善的哈克還想著要替“國(guó)王”和“公爵”通風(fēng)報(bào)信,等到了鎮(zhèn)子中心才發(fā)現(xiàn),大群的人“手拿火把,狂呼亂叫,敲著白鐵鍋,吹著號(hào)角……國(guó)王和公爵騎在一根單杠上……他們?nèi)砟税赜停鲋鹈薄1](P232)“國(guó)王”和“公爵”這兩個(gè)騙子作為鎮(zhèn)民的敵人,在經(jīng)過一番波折后終于被鎮(zhèn)民們捉住,小鎮(zhèn)居民們也用狂歡的形式對(duì)他們倆進(jìn)行了懲罰,整個(gè)懲罰的過程充滿了狂歡節(jié)輕松愉快的氛圍。兩個(gè)騙子最后沒有一點(diǎn)人的模樣,“恰如兩根嚇人的軍人戴的粗翎子”,這種私刑雖然殘酷血腥,但是哈克的笑謔描述卻緩解了這種恐怖的氣氛,產(chǎn)生了特殊的幽默效果。[1](P232)誠如巴赫金研究學(xué)者潘牧·莫里斯(Pam Morris)所言:“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使得原本束縛人們交往的等級(jí)制度都不再存在,人民奪得了話語權(quán),從而可以肆無忌憚地嘲弄一切權(quán)威和一切僵化的社會(huì)體制。”[6](P196)兩個(gè)騙子最終的下場(chǎng)正是說明了狂歡廣場(chǎng)的全體性和平等性,“國(guó)王”和“公爵”最初在狂歡廣場(chǎng)中通過行騙所獲得的心理優(yōu)越性和高人一等的地位再次在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中消失殆盡,優(yōu)越感所象征的權(quán)威和等級(jí)也在狂歡廣場(chǎng)中蕩然無存,每個(gè)人都能在狂歡廣場(chǎng)中進(jìn)行放肆的接觸。
二、加冕與脫冕的狂歡節(jié)儀式
(一)“國(guó)王”與“公爵”的加冕和脫冕。在全民性的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中,左右人的一切制度等級(jí)和規(guī)范都被取消了,也就是說所有權(quán)勢(shì)和地位都被解構(gòu),而粗俗和卑微卻得以重視,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不平等都能夠以自由平等的面貌重新出現(xiàn)在狂歡節(jié)廣場(chǎng)中,最高的世俗權(quán)威被脫冕的同時(shí),粗鄙和低俗被加冕,因而狂歡廣場(chǎng)也是一個(gè)加冕脫冕的狂歡廣場(chǎng)。加冕和脫冕是狂歡節(jié)慶典中最主要的儀式,它是“笑謔地給狂歡國(guó)王加冕和隨后脫冕……而且受加冕者,是同真正國(guó)王有天壤之別的人——奴隸或是小丑”,這種儀式在狂歡節(jié)所有節(jié)慶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xiàn)。[2](P124)
“國(guó)王”與“公爵”,這兩個(gè)官方世界中的小丑,可以說是小說中當(dāng)之無愧的狂歡國(guó)王。他們的出場(chǎng)方式極具狂歡特色,人物本身也帶有明顯的狂歡化色彩,騙子們通過冠冕堂皇的言辭來掩飾自己的無恥私欲,兩人在哈克和吉姆面前用荒謬的邏輯為自己加冕:一個(gè)成了英國(guó)的勃烈奇瓦特公爵,另一個(gè)成了被流放的法國(guó)國(guó)王。騙子們?cè)凇胺藗€(gè)的世界”中的地位一步登天,從落魄的求救者到發(fā)號(hào)施令的權(quán)威者。[2](P127)然而“加冕和脫冕是合二為一的雙重儀式,加冕本身便蘊(yùn)含著后來的脫冕”。[2](P124)加冕者在脫冕儀式中,會(huì)受到全民的嘲諷和鄙夷,從而被揭開“另一副真正的面孔”,被撕下他們的“偽裝和假面具”。[4](P197)當(dāng)哈克和吉姆發(fā)現(xiàn)“國(guó)王”和“公爵”依靠欺騙村民賺到了四百六十五塊大洋的時(shí)候,他們的“尊貴身份”就在哈克和吉姆心中被脫冕了。吉姆內(nèi)心敬仰的“國(guó)王”與“公爵”成了卑鄙的壞蛋,哈克也評(píng)價(jià)說,“所有的國(guó)王十有八九是壞蛋……他們是一伙壞種”。[1](P157-158)哈克和吉姆的評(píng)價(jià)是對(duì)包括兩個(gè)騙子在內(nèi)的所有崇高階級(jí)和極端嚴(yán)肅的嘲諷。在非狂歡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真正的國(guó)王和公爵象征了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和周圍人保持著絕對(duì)的距離,令人畏懼和敬仰;但是在狂歡世界中,國(guó)王和公爵的頭銜卻成了滿足享樂欲望的借口,他們實(shí)際上是由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小丑——處于底層的騙子手和下流坯,通過欺騙的手段加冕而來的。高級(jí)的世俗權(quán)威和低級(jí)的滑稽小丑聯(lián)系在了一起,這使得加冕有了“引人發(fā)笑的相對(duì)性”。[2](P124)這種狂歡化的笑既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中權(quán)威和嚴(yán)肅象征物的嘲笑,也是對(duì)它的“狂歡化的‘脫冕’”。[7](P57)所以加冕從一開始就暗示著會(huì)被脫冕。哈克和吉姆撕下了“國(guó)王”和“公爵”給自己戴上的假面具,揭穿了他們厚顏無恥的實(shí)質(zhì),同時(shí)也嘲諷和顛覆了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絕對(duì)權(quán)威。
雖然自我加冕的“國(guó)王”與“公爵”在哈克和吉姆的對(duì)話中被脫冕了,但是在狂歡結(jié)束之前,假“國(guó)王”和假“公爵”仍然享有他們的權(quán)力和地位,仍然要完成最終加冕和脫冕的步驟。[8](P105)“國(guó)王”和“公爵”這兩個(gè)騙子最終被鎮(zhèn)民們抓住,鎮(zhèn)民手舞足蹈,狂呼亂叫得在他倆身上澆熱柏油,撒滿羽毛,處以私刑。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騙子和小丑在“統(tǒng)治期”結(jié)束后迎來了最終的脫冕儀式,通過欺騙手段獲得的地位和權(quán)威最終被消除。他們被扒下了身上的華服,被摘下了頭上的王冠,受到了“全民的辱罵和毆打”。[4](P197)鎮(zhèn)民在狂歡化的笑聲中取消了對(duì)于世俗權(quán)力的畏懼和尊敬,從而和嚴(yán)肅的社會(huì)上層代表的“國(guó)王”與“公爵”隨意而親昵的接觸,甚至譏笑懲罰他們。“國(guó)王”與“公爵”加冕和脫冕的過程體現(xiàn)了新舊交替的過程,也說明了世界中所有事物的相對(duì)性。在狂歡生活中絕對(duì)的權(quán)威和等級(jí)是不存在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階級(jí)和真理在狂歡世界中成了相對(duì)性的。加冕和脫冕的儀式對(duì)于社會(huì)中的權(quán)威等級(jí)有著顛覆作用,在另一方面也嘲弄了南方白人的愚昧。
(二)擁有脫冕特點(diǎn)的崇高戲劇的降格。狂歡節(jié)加冕和脫冕的儀式,包含著狂歡世界感受的所有范疇;儀式中引人發(fā)笑的相對(duì)性特點(diǎn)消除了“任何等級(jí)制的(疏遠(yuǎn)的、規(guī)定的)距離”,拉近了高級(jí)與低級(jí)、智慧與愚蠢、神圣和粗俗之間的距離。[3](P23)崇高和卑下之間原本涇渭分明的界限在加冕和脫冕的活動(dòng)中逐漸變得模糊,隨時(shí)向?qū)α⒌膬蓸O轉(zhuǎn)化。
在小說中,“公爵”想出了胡亂編排戲劇讓鎮(zhèn)民付費(fèi)觀看的方式來騙取錢財(cái)?shù)姆椒ǎ汀皣?guó)王”兩人也因此排練起了莎士比亞的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陽臺(tái)情話、《理查三世》中的斗劍場(chǎng)景以及《哈姆雷特》的不朽獨(dú)白。然而,莎士比亞的偉大作品經(jīng)過“公爵”的改編后變得不倫不類。《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經(jīng)典場(chǎng)景由兩個(gè)男人來演,其中朱麗葉的角色的扮演者甚至是一位70 多歲的禿頭老人,這與傳統(tǒng)意義上朱麗葉所代表的柔美女性形象相差甚遠(yuǎn),但是“公爵”卻說“那些土包子不會(huì)想到這上頭去”。[1](P134)兩人排練時(shí),“公爵”指導(dǎo)“國(guó)王”背誦臺(tái)詞時(shí)透露出的信息清楚表現(xiàn)了朱麗葉和“國(guó)王”形象的大相徑庭。“喚羅密歐的時(shí)候,你不能像公牛似的吼出來——你要喚得嬌滴滴、病懨懨、如怨如訴……你要知道,朱麗葉是個(gè)嬌小動(dòng)人,還是個(gè)孩子的姑娘,她絕不會(huì)像頭公驢似地嗚嗚叫。”[1](P104)此時(shí)《羅密歐與朱麗葉》這部曠世的愛情悲喜劇被改編為低俗喜劇。更不用說哈姆雷特的獨(dú)白了,在“公爵”碎片化的背誦中,丹麥王子的經(jīng)典獨(dú)白前言不搭后語,《麥克白》、《哈姆雷特》和《理查三世》劇本中他處的臺(tái)詞甚至還亂入其中,故而超越時(shí)代的偉大悲劇脫冕為面目全非的滑稽鬧劇。“公爵”對(duì)于莎劇的改編實(shí)際上是對(duì)它的戲仿,巴赫金認(rèn)為這種戲仿是狂歡化的戲仿:它是“一種‘滑稽模仿’或戲謔形式”。[7](P168)這種滑稽模仿使高級(jí)向低級(jí)轉(zhuǎn)化,原本遙遠(yuǎn)的權(quán)威和神圣事物在降格后變的滑稽,它所引發(fā)的笑將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疏遠(yuǎn)的距離全都消弭了。因此,崇高文學(xué)中的悲劇英雄哈姆雷特降格成了“公爵”滑稽模仿的戲劇獨(dú)白中前言不搭后語的小丑;偉大愛情劇中嬌美動(dòng)人的朱麗葉形象則脫冕為發(fā)出牛吼聲的禿頭老漢。
滑稽模仿將高級(jí)轉(zhuǎn)向低級(jí)的同時(shí),也對(duì)它進(jìn)行嘲笑和批評(píng),在這過程中,被戲仿對(duì)象會(huì)“被揭示出所有的局限和不足”。[3](P56)在莎劇表演的當(dāng)天,只有“大約十二個(gè)人看……看客還笑個(gè)不停……戲還沒有完,人就走光啦,除了一個(gè)男孩,他是睡著了”。[1](P152-P153)這種場(chǎng)景說明了處于狂歡世界中的鎮(zhèn)民對(duì)于官方世界里崇高文學(xué)主題的抵觸,也揭露了偉大悲劇可能存在的局限性。鎮(zhèn)民們拒絕的是莎劇在官方世界中無與倫比的神圣權(quán)威地位,嘲笑的是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絕對(duì)的權(quán)威和階級(jí),但莎劇本身“在整個(gè)過程中并沒受到羞辱”。[3](P56)此外,查爾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還認(rèn)為滑稽模仿將被戲仿對(duì)象從至高無上的高雅王座拉下的同時(shí),還會(huì)將“低俗或大眾的東西提升到更高。更復(fù)雜的層次”。[7](P250)與莎劇表演當(dāng)日的景象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是,第二天騙子們上演《王室異獸》時(shí)門庭若市的景象。原本崇高的莎士比亞偉大悲劇徹底降格成了無人問津的低俗喜劇,而荒誕惡俗的猥褻演出青云直上滿足了觀眾的需要。莎士比亞戲劇的權(quán)威性在狂歡廣場(chǎng)中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非狂歡的官方世界中低俗惡趣味的東西。這種崇高和卑下之間的荒誕戲劇性轉(zhuǎn)變?cè)俅握f明了:非狂歡的官方世界中的權(quán)威的,主流的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在狂歡化社會(huì)中被徹底顛覆了。馬克·吐溫在小說中對(duì)處于絕對(duì)權(quán)威地位的莎劇的戲仿表現(xiàn)的是他對(duì)愚昧無知的美國(guó)南方民眾的嘲笑,以及對(duì)官方世界中絕對(duì)等級(jí)和嚴(yán)格制度的徹底顛覆,追求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自由平等。
馬克·吐溫在小說中關(guān)于戲仿的寫作技巧也證明了他的偉大。戲仿文本除了將高級(jí)淪為低級(jí),對(duì)社會(huì)權(quán)威進(jìn)行嘲弄和顛覆以外,它還通過引用被戲仿文本來喚起讀者的期待。小說中“公爵”對(duì)哈姆雷特的獨(dú)白進(jìn)行了滑稽模仿。“公爵”先是向讀者鋪墊“那是莎士比亞頂頂出名的段子……每回總是全場(chǎng)叫好”,他的介紹和稱贊喚起了讀者的期待。[1](P141)但接下來“公爵”呈現(xiàn)的卻是讀者從未想到的荒誕版本,此刻讀者的期望被徹底顛覆,讀者在期望被顛覆后會(huì)對(duì)作品和現(xiàn)實(shí)產(chǎn)生自己的反思,而這種引起讀者反思的作用恰好就是偉大作品及偉大作家的共同特點(diǎn)。另外,戲仿與被戲仿作品之間的巨大差異和不協(xié)調(diào)創(chuàng)造了一種滑稽效果,這種滑稽效果也是戲仿的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于1884年出版,但是直到20世紀(jì)早期關(guān)于戲仿的研究理論才開始逐步成型。馬克·吐溫在作品中展現(xiàn)的超前意識(shí),以及對(duì)于戲仿技巧的熟練運(yùn)用都讓人不禁感慨他不愧是世界文壇上的巨人。
結(jié)語
“國(guó)王”和“公爵”作為小說中的小丑形象,本身就帶有典型的狂歡特色。在全民性的狂歡廣場(chǎng)中,官方世界里將人與人隔絕開的權(quán)力、等級(jí)和制度不復(fù)存在,所有人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對(duì)“國(guó)王”和“公爵”的加冕、脫冕以及對(duì)崇高事物的降格使得原本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失去其優(yōu)越性,表現(xiàn)了馬克·吐溫對(duì)美國(guó)白人和南方權(quán)威階級(jí)的諷刺和顛覆,也寄托了他對(duì)于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希望構(gòu)建一個(gè)烏托邦世界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