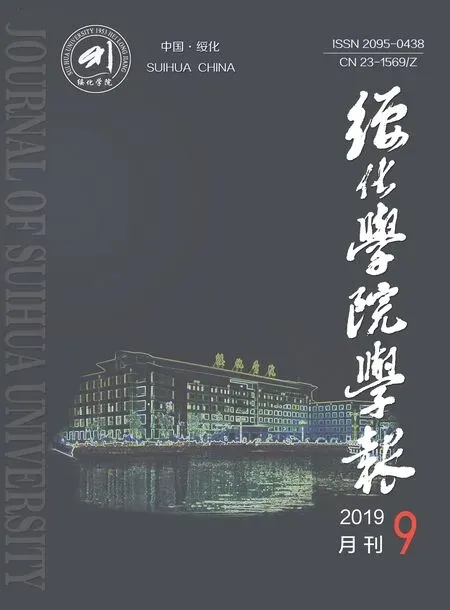從《鰥夫的房產》管窺蕭伯納的早期戲劇觀
郝涂根 汪 宇
(安慶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安徽安慶 246001)
《鰥夫的房產》(下文簡稱為《鰥》,Widowers’Houses)是英國戲劇大師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的首部劇作。該劇的初稿寫于1885年,由他與好友兼戲劇引路人劇評家威廉·阿契爾(William Archer,1856-1924)合作撰稿,后因兩人意見不一而中途流產。七年后(1892年),應劇評家杰克·格蘭(J.T.Grein)的邀請,蕭伯納翻出束之高閣的初稿,修改完成了劇作。該劇隨后在格蘭的“獨立劇院”(The Independent Theatre)上演,雖然僅公演兩次,卻引發了極大轟動,一時間成為公眾的熱門話題。倫敦各大報紙接連兩周在頭版報道該劇,劇迷們和評論家也對其獨特的劇情爭論不休。受此鼓舞,蕭伯納堅定了戲劇創作的信心,相繼撰寫《華倫夫人的職業》(Mrs.Warren’s Profession,1893)、《武器與人》(Arms and Men,1894)和《巴巴拉上校》(Major Barbara,1905)等膾炙人口的劇作。
時至今日,《鰥》已沒有當初問世時那么引人矚目。國內外的蕭學家們將目光集中在蕭伯納后期更成熟的佳作,極少關注這部處女作。以國內學界為例,用“鰥夫的房產”為主題詞搜索中國期刊網,僅有12篇期刊論文和6篇碩士論文。這些寥寥可數的評論大多集中討論人物、語言特色、荒謬元素、哲學和倫理內涵,均忽視了《鰥》與蕭伯納早期戲劇創作觀的聯系。作為蕭伯納的首部作品,《鰥》無疑是蕭伯納實踐其戲劇創作理念的最初平臺。受易卜生(Henrik Ibsen)現實主義新戲劇的熏陶,蕭伯納極為反感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戲劇界為取悅觀眾制造出大量脫離實際、庸俗淺薄的劇作,推崇戲劇的現實意義和道德教誨功能。而他與引路人阿契爾最后的分道揚鑣恰恰證明這位銳意革新的年輕斗士決心與當時戲劇界盛行的媚俗風氣進行徹底切割,大膽嘗試書寫針砭時弊和整飭人心的新戲劇。
一、《鰥夫的房產》的創作始末
在《不愉快的戲劇》的序言(Preface to Unpleasant Plays,1893)里,蕭伯納詳述了《鰥》的創作始末。1885年,阿契爾向蕭伯納提議共同撰寫一個劇本,由他擬定情節大綱,蕭伯納負責撰寫具體的臺詞。受當時風靡英法劇壇的佳構劇的啟發,阿契爾計劃寫一部“略帶傷感的浪漫愛情‘佳構劇’(Wellmade play)”[1](P12)《萊茵的黃金》, 擬定的劇情如下:青年屈蘭奇與多愁善感的白朗琪在萊茵河畔邂逅相愛并締結婚約。白朗琪的父親富商薩托里阿斯對這門婚事樂觀其成,準備贈予大筆金錢作為嫁妝。隨后屈蘭奇發現準岳父的萬貫家財源自不義之財,他憤然拒絕,并“極富于英雄氣概”[2](P202)地將這筆骯臟的錢財扔進了萊茵河。蕭伯納據此寫完前兩幕后,希望好友能提供更多資料,繼續后面的創作;可阿契爾卻對此有異議,認為劇本到此便可結束;而且劇本中的對白太多,情節過少。失望之下,阿契爾取消了合作計劃。七年后,應杰克·格蘭之邀,蕭伯納找出未完成的劇本繼續創作。他有意將屈蘭奇設定為出生顯赫家族的貴族青年,將薩托里阿斯描述成倫敦貧民窟的房東,通過剝削壓榨窮租客來聚斂暴利。除此之外,蕭伯納修改了第二幕的結尾和添加第三幕,即屈蘭奇拒絕饋贈后,未婚妻白朗琪并沒有站在他的一邊。她不愿放棄優渥的生活,認為單憑屈蘭奇的微薄收入,他們將會艱難度日。兩人不歡而散,婚約也就此作廢。隨后薩托里阿斯得知屈蘭奇因自己的不義之財而耿耿于懷,便向他揭示了真相。其實屈蘭奇的家族正是薩托里阿斯的主要債權人,維系他體面生活的收入也同樣源自對窮苦租客的盤剝。在接下來的第三幕中,薩托里阿斯與人密謀翻新貧民窟舊宅以獲得政府高額賠償金,并準備結束與屈蘭奇的借貸關系,尋覓新的合伙人。因為害怕收入銳減,屈蘭奇改變了原來的想法,和白朗琪言歸于好,并與薩托里阿斯合伙打理房產投機生意。
仔細分析《鰥》一波三折的創作歷史,不難發現兩位劇作家的分歧之處主要在于劇本的情節設置和編劇技巧。首先,阿契爾設定的是一出令觀眾愉悅的浪漫喜劇,采用“佳構劇”的形式。傳統的“佳構劇”一般包括三幕,遵循“展示—沖突—解決”的模式,即第一幕展示主要人物和事件,第二幕描述中心沖突,第三幕解決沖突。根據這個固定范式,阿契爾所設想的劇本結構如下:第一幕介紹故事背景和主要人物;第二幕詳述主要沖突, 即男主角屈蘭奇在金錢與道德之間的抉擇;第三幕沖突得到圓滿解決。面對來路不明的大筆財富,屈蘭奇堅守氣節,斷然拒絕,并與白朗琪有情人終成眷屬。而蕭伯納雖然表面上遵循“佳構劇”的三幕結構,卻在兩幕內就寫完了阿契爾提供的情節,并在第二幕末尾改寫了主要沖突,突破佳構劇的固定劇情。在屈蘭奇謝絕不義之財后,他并沒有得到白朗琪的支持,兩人在是否拒絕饋贈問題上意見不一,并由此導致婚約失效。隨后蕭伯納筆鋒一轉,逆轉之前的劇情。屈蘭奇被薩托里阿斯點醒,自己自認為“干凈”的收入也源自骯臟的收租錢;自命清高的他也是社會罪惡的共謀者。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選擇妥協,和薩托里阿斯同流合污,并與白朗琪重訂鴛盟。與阿契爾相比,蕭伯納設置了更復雜多變的情節。通過不斷反轉劇情,他不僅顛覆了傳統“佳構劇”的固定范式,而且更深刻地揭露貧民窟租客的生存困境,房東及地產所有者的罪惡等社會問題。
除情節設置外,兩位作家對該劇的編劇技巧存有異議。阿契爾十分強調情節在劇中的地位,認為劇作家在創作時應以情節為重點,然后再考慮語言、人物塑造等要素。因此他最先著手的工作便是構建全劇的結構和設置各幕的情節大綱。然而蕭伯納在具體操作時,不僅有意偏離好友設置的情節,而且精心設計了長篇幅的人物對白。他特意為主要人物安排大量臺詞表達各自不同的觀點,并圍繞某些話題相互展開爭鋒相對的辯論。例如,在第二幕的末尾,薩托里阿斯和屈蘭奇就“骯臟”的收入進行激烈討論。屈蘭奇抱怨薩托里阿斯為富不仁,不該通過榨取窮人錢財發家致富;而薩托里阿斯隨即進行反擊,指出屈蘭奇根本沒有資格指責自己,他的家族正是貧民窟地產的所有者,每年都會向自己收取高額利息。“我是經手人,你才是東家……由于我的房客全是窮人,我要擔很大的風險,你卻趁機以高得可怕的七份利從我身上榨取利息,逼迫我不得不把我的房客榨取得干干凈凈!”[3](P50)無獨有偶,在第三幕,蕭伯納又設計了另一場討論,屈蘭奇、薩托里阿斯和李克奇斯圍繞“改造貧民窟房屋”的合理性發表各自觀點。屈蘭奇嘲諷兩人不顧廉恥,想方設法聚斂財富,“房子愈骯臟,房租就愈多;房子愈體面,賠償費就愈大。因此,我們現在就舍骯臟而就體面了。”[3](P51)虛偽的薩托里阿斯則辯解自己的所作所為完全出自人道主義,是為了迎合時代進步的需求;而李克奇斯直接揭開內幕,花錢改造貧民窟的目的無他,就是為了規避罰款、判刑等風險,通過“合法”的途徑賺取更多的金錢。
二、維多利亞時代流行的戲劇觀
如前所述,《鰥夫的房產》的創作始末反映了蕭伯納與阿契爾在情節設計和編劇技巧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不同并不能簡單視為兩個劇作家的意見相左。從深層次來看,它實際上折射出他們在探索英國戲劇革新道路的分歧。兩位革新者受易卜生現實主義新戲劇的啟發,都主張將改革之風引入庸俗僵化的英國劇壇。然而在隨后的戲劇革新道路上,蕭伯納超越了他的引路人阿契爾,與當時戲劇界盛行的媚俗風氣進行了更為徹底切割。
與群星閃耀的前幾個世紀相比,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戲劇已不復往昔的輝煌。自1737年《劇院法》(The Licensing Act of 1737)頒布之后,英國戲劇經歷了長達百年的嚴格政治審查。雖然該法案于1843年被《戲劇法》(Theatre Regulation Act)取代,仍余威猶在。劇作家們不敢輕易嘗試揭露現實的嚴肅劇,紛紛效仿歐洲同行撰寫圍繞男女情愛且情節離奇夸張的鬧劇、傳奇劇和風俗喜劇等。為躲避審查風險、取悅觀眾,倫敦各大商業劇院上映了一部又一部拙劣改編的莎士比亞作品和“翻譯的法國鬧劇和巧妙的色情勾引及感傷的英國情節劇的廉價混合。”[4](P384-385)當時最受熱捧的劇作便是“佳構劇”。“佳構劇”由19 世紀法國劇作家歐仁·斯克里布(Eugène Scribe)首創,后被引入英國劇壇。其內容流俗淺薄,多為瑣碎無聊的情感糾紛和家庭矛盾,人物扁平臉譜化,情節離奇曲折,與現實社會嚴重脫節。為追求轟動性的舞臺效果,“佳構劇”大多設計精巧,結構嚴謹;注重情節發展,遵循“展示—沖突—解決”的模式;且有若干固定套路,例如誤解、巧合、偷聽等。由于迎合大眾獵奇尋樂的口味,“佳構劇”在維多利亞時代擁有眾多擁躉,其中不乏迪翁·布希高勒(Dion Boucicault)等知名作家和戲劇評論家。
三、蕭伯納的早期戲劇創作觀
直到19世紀末,英國劇壇沉悶庸俗的風氣才有所改觀。以阿契爾、威廉·珀歐(William Poel)為首的評論家和劇作家相繼發出革新的呼聲。他們以易卜生為榜樣,主張戲劇應與現實緊密聯系,反映社會生活的各種問題(尤其是道德問題)。作為易卜生劇作的主要譯介者,阿契爾承襲易的現實主義傳統,呼吁英國戲劇應在國民精神生活中發揮積極的影響作用。他認為評論劇本好壞的標準在于該劇是否能“再現嚴肅的道德問題”[5](P2)。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戲劇技巧方面,阿契爾卻與易卜生觀點有所不同。他推崇“佳構劇”的結構和編劇技巧,認為一個典型的現代劇本應是“一個結構嚴謹的有機體”[6](P117),而三幕制正是劇本最理想的設計。基于此,好的新戲劇包括問題劇的主題和“佳構劇”的技巧,兼收并蓄,博采眾長。例如,他對當時佳構劇大師阿瑟·平內羅(Arthur Wing Pinero)贊譽有加,認為后者在《譚格瑞的續弦夫人》(The Second Mrs Tanqueray,1893)和《丑名遠揚的埃布斯密斯夫人》(The Notorious Mrs.Ebbsmith,1895)等劇中塑造了有道德瑕疵的女性形象,引導大眾關注現實生活中的婦女問題。
然而,同處革新陣營的蕭伯納卻對阿契爾的觀點持有異議。在蕭伯納看來,新戲劇雖反映了若干社會問題,卻往往隔靴搔癢,未觸及深層原因。此外,這些問題大多涉及家庭矛盾、失足婦女等,過于狹隘淺薄。而作為“人的感情與人類制度發生沖突的產物”[7](P220)的社會問題應是有關“社會轉型時期的英國國民心態和國民道德”或“個人意志與社會環境、傳統習俗沖突”[8](P19)的重大問題。受費邊主義[9]的影響,蕭伯納進一步指出面對現代社會層次不窮的社會問題,文學家應積極效仿雪萊,成為“政治的鼓動者和社會鼓勵者”[7](P227),將這些社會問題訴諸于筆端,引發相關社會組織的關注,促使其采取改進措施解決問題。基于此,蕭伯納認為真正的戲劇決不能如同“佳構劇”一味獻媚觀眾,亦不能像新戲劇那樣對現實問題淺嘗輒止。它肩負著重大使命,是“思想的工廠,良心的提示者,社會行為的說明人,驅逐絕望和沉悶的武器,歌頌人類上進的廟堂”[10](P47)。戲劇的功用不僅僅在于提供消遣,愉悅大眾,更在于道德教化和宣傳思想。為了達到這一功用,蕭伯納提出戲劇應擺脫佳構劇中常見的“庸俗愛好、貪婪或慷慨、委屈和虛榮、誤解和偶然等”[11](P348),忽視新戲劇中狹隘單一的社會問題,著重反映現實生活中那些“重要新奇、有說服力,或者至少讓觀眾感到不安”的問題[12](P221)。而“文以載道”的方式不是以通篇說教讓觀眾被動接受觀點,應是通過富有啟發性地討論這些問題,引導觀眾主動思考,進而反思和改變現實。因此,蕭伯納將“討論”視為戲劇創作的主要技巧,并盛贊其重要作用。譬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正是通過“討論”征服了整個歐洲。
正是基于上述幾點信條,即強調戲劇的道德教化功能,以討論為主要技巧,以社會問題為題材、以解決問題、改良社會為最終目的,蕭伯納故意偏離阿契爾的最初構思,將一則輕松愉悅的佳構劇寫成了一部針砭時弊、發人深省的劇作。在后來的《不愉快的戲劇集》的序言中,他明確指出《鰥》是“宣傳劇、教誨劇、帶有目的戲劇”[1](P13),意圖解決一個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倫敦郡貧民的住房問題,故意引導大眾在郡議會選舉中支持改革派。因此,他無意描寫佳構劇中的男女情愛,有意突破阿契爾對現實問題的輕描淡寫,直指倫敦貧民窟中窮苦租客的困境:他們受房東及地產所有者的層層剝削,生活難以為繼。為了凸顯這一社會問題,蕭伯納在角色身份、劇名的更迭、情節設置和寫作技法上進行了巧妙的安排。首先,他為主要人物設計了雙重身份。屈蘭奇和準岳父薩托里阿斯不僅是貴族青年和富商,也是貧民窟地產的所有者和貧民窟房東,他們共處于一個利益鏈上,共同盤剝窮苦租客。其次,原擬定的《萊茵的黃金》被特意改為《鰥》。“鰥夫的房產”源自《新約全書·馬太福音》(23:14),“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罰。”毫無疑問,偽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映射的是劇中薩托里阿斯和屈蘭奇,以及現實中壓榨租客的貧民窟房東和地主。此外,在情節設置上,蕭伯納有意顛覆佳構劇的固定套路,在后兩幕屢次反轉劇情。譬如,男女主人公一波三折的婚約,屈蘭奇對薩托里阿斯的態度變化,從開始的劃清界限到最后的同流合污。在寫作技巧層面,劇中存在若干長篇幅的討論,話題包括“骯臟”的收入、貧民窟改造的合理性等。通過上述安排,蕭伯納引導觀眾直面存在現實生活中“不愉快”的社會問題——“貧民窟房東的罪惡,城市假公濟私的劣政,它們之間金錢與婚姻的關系,以及一些靠不勞而獲而生活的高貴人物——他們以為這些卑鄙勾當與它們的生活毫無關系。”[13](P156),進而引導他們從以往簡單的愉悅觀影經驗中擺脫出來,主動思索這些社會問題的深層原因,積極尋求解決之道。
從《萊茵的黃金》到《鰥夫的房產》,蕭伯納不只完成了劇名的更迭,也吹響了徹底革新維多利亞戲劇的號角。在以后的創作生涯中,他不斷實踐自己的創作理念,針砭時弊,整飭人心,發揮戲劇的道德教化和思想宣傳的功能。在他的引領下,英國戲劇一掃媚俗拜金的不良風氣,煥發出新的生機。
時過境遷,雖然現在蕭伯納的劇作已極少被劇迷和學術界之外的人提及,但他的戲劇觀仍有不容忽視的現實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電影邁入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統計,2016年我國電影票房已達457.12億元,觀影人次突破13.72億[14](P1)。但是繁榮背后卻存在隱憂。受商業價值的趨勢,充斥市場的國產片大多以商業片為主。為了贏得更多票房,編劇導演如同蕭伯納筆下的“文學機器匠”[15](P46-47)將電影制作視為工業,制造大批粗制濫造的商業片,這些作品或是特效勝于內容、或是情節流俗離奇。觀眾也大多適應這種現狀,抱著娛樂消遣的心態前去觀影。而那些關注現實的電影卻備受冷遇,票房慘淡。蕭伯納的戲劇創作觀或許能給文藝工作者一定的啟示:電影和其他文藝作品不能簡單以經濟價值作為唯一衡量標準,其社會價值更為重要。在愉悅觀眾的同時,文藝作品應給予他們更好的藝術享受和更多的思想啟迪。